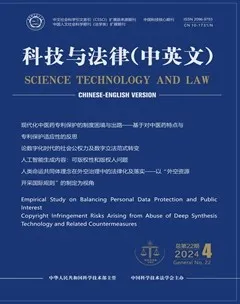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外空治理中的法律化及落实
摘 要:外空资源开采活动是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最新发展趋向,而现有国际空间法尚未涵盖外空资源开采相关制度,如何制定外空资源开采国际规则是外空治理中面临的难点问题。外空资源法律属性的确权是外空资源开采国际规则建构的立论前提,应从法哲学、法社会学和法经济学视角界定外空资源共有物的属性。至于外空资源开采具体规则的制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了当今外空资源开采活动蓬勃发展的趋势,从价值、目的、环境保护和长期可持续发展四个维度对现有的外层空间法进行了巩固和新发展,具有引领外空资源开采国际规则建构的理论根基。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不会自行转换在外空资源开采国际规则中,需要对该转换途径加以研究,可以通过递进式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外溢效果和内化为外空资源开采的具体规则两种途径,实现其在外空治理中的法律化及落实。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外空治理;外层资源开采;落实路径
中图分类号:D 92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9783(2024)04⁃0094⁃10
一、问题的提出
只有当所有的国家受制于同一法律制度,法律的公平才能决定优势或劣势,而不是取决于国家实力、政治力量的强弱[1]。目前外层空间资源开采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尤其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意欲通过外空资源开采活动抢占外空资源以及现有国际空间法无法应对外空资源开采过程中出现的法律问题束手无策的背景下,只有所有国家共同制定相关的外空资源开采国际规则,才能确保外空资源开采合法进行,惠益共享至每个国家。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我国的外交事务指导思想和国际治理理念,已逐渐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理念的落实离不开规则的保障。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构建国际新秩序的中国方案和理念,需要调整国际关系的国际法体现并落实[2]。国际法的其他领域如气候变化领域和国际海洋法均已引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具丰富且成功的国际实践。外层空间法是独立的国际法的分支,引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亟须完成的重要课题。外空资源开采制度的制定是外层空间法的新发展,联合国外空委一直致力于制定外空资源开发的国际规则,但是目前各国在外空资源的法律属性和制度构建问题上存在分歧,有必要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解决这些问题。
外空资源开采国际规则的构建依托于外空资源属性法律问题的解决,通过梳理和分析学界对外空资源属性的不同观点,利用法哲学、法社会学和法经济学方法深入剖析赋予外空资源共有物属性的法理基础和合理性。外空资源法律属性的厘清和明示可以更好地探讨如何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构建和完善外空资源开采的具体规则。随后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适用于外空资源开采国际规则的逻辑基础,最后经由递进式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外溢效果和内化为外空资源开采的具体规则两种途径,明确中国对外空资源开采国际规则制定的立场和观点,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外层空间的法律化和具体落实。
二、立论前提:外空资源法律属性的厘清
确权往往是有效的激励机制,既是激励国家积极探索利用外空及网络的经济学基础,也是划分具体权利义务、定纷止争确定责任的法律基础[3]。目前关于外空资源法律属性的确权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月球协定》确定了外空资源的法律属性是“人类共同财产”,冻结各国擅自规模开发与利用月球自然资源的活动[4]。第二种观点认为基于“贪婪”的人性,对外空资源法律属性作出的判断就是“无主物”[5]。第三种观点认为采回的外空矿产资源的属性是共用物,不是共有物和人类共同继承遗产,私人实体或非政府组织可以在此基础上主张所有权或用益物权[6]。可以看出,学界对外空资源法律属性的界定尚不明确,界定外空资源的法律属性不仅是外空法领域的当务之急,也是人类命运体理念落实在外空资源开采国际规则的立论前提。
而关于外空资源的法律性质到底是什么问题?笔者认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应先回归财产权的法哲学理论中追本溯源探索外空资源的应然属性,随后通过法社会学视角审视外空资源法律属性的现有域外规定,得出外空资源的实然属性,最后结合法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理论界定出最佳的外空资源属性定义,认定外空资源的法律属性是共有物,而且属于消极共有,这一认定不仅具有法理基础而且合理。
(一)应然属性:从法哲学视角解析外空资源属性
从普通法系的财产权出发,普芬道夫的财产权理论可以为外空资源的法律属性提供法理依据,普芬道夫关于财产权的观点是以《圣经》中的教义为基础的,即上帝在创世纪时就已经把世上的万事万物赐予全体人类了,认为人类有一种对自然万物的原始共有权(origin al community of possession)[7],他提出:“所有事物都向所有人敞开,不属于一个人也并不属于另外一个人(belonged no more to one than to another)”[8]。也就是说在人们达成任何协议之前存在着对世间万物的共有关系,这种共有关系应当是一种“消极共有”[8]。普芬道夫在遵循自然法的基础上,与格劳修斯一样认可财产共有权,并对财产共有权进行了具体划分,分为“积极共有”和“消极共有”,也可以称为“现代共有”和“原始共有”。所谓“积极共有”是指一种被仅仅作为整个人类一部分的一群人所分享的权利,余下的那一部分人就被排除在该财产之外[7]。而“消极共有”指的是最初万物都被认为是上帝无区别的给予所有人,所以它们并不属于一个人,如同不属于其他人一样[7]。因此“积极共有”与“消极共有”的本质区别在于该财产权是否具有排他性,“积极共有”的权利人对非权利人具有排他性,非权利人不可以对此种共有物进行使用、收益和处分,而“消极共有”将世界万物属于全人类这一整体,不归属任何人,不可以排除任何人对共有物的共有关系。而外空资源明显属于世间万物中的一类,根据普芬道夫的财产权理论,外空资源在没有明确的国际条约规定之前属于共有物,并且还是消极共有,不是私有财产权之客体。全人类对外空资源享有共有关系,任何外空行为者均无权排除任何其他外空行为者探索利用外层空间的权利,不能将外空资源据为己有,也无法以法律行为将其探索开发的外空资源移转给第三方。换言之,没有任何外空行为者对外空资源享有所有权。
(二)实然属性:从法社会学视角分析外空资源属性
法社会学视角是以一国法律为基础进行研究,揭示法律制定的规律,如韦伯主张,法社会学注重研究法律的实际运转以及对社会的影响[9]。法社会学视角可以揭示和解剖法律规范对外辐射出来的意图[10],通过关注制度规范来解释其背后深层的意图和目的[11]。通过法社会学视角审视外空资源法律属性的现有规定,不仅在现有规定下分析外空资源的法律地位,更有助于剖析各国对外空资源立法背后的目的。如今的《外空条约》和《月球协定》没有明确规定外空资源的法律地位。针对空间资源开采和使用方面的法律空白,美国、卢森堡和日本等国率先颁布了单边国内立法,赋予私营实体享有外空资源的所有权。譬如美国2015 年的《商业航天发射竞争力法案》规定从事小行星资源或太空资源商业回收的美国公民应有权获得任何小行星资源或太空资源1。此外卢森堡2017年通过的《太空资源与利用法案》赋予私营公司享有从小行星或其他天体提取太空资源的权利2。随后,日本和阿联酋也做出了类似的规定,赋予私营实体享有外空资源的所有权。一国法律可以带来经济利益的机会[9] ,德国著名法社会学莱塞尔也认为,“法律尤其是所有权关系,其基础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统治关系,因此它也无非是这种统治关系的一种表达方式,是该国统治秩序的反映,也是为权利提供服务”[12]。通过对美国、日本和卢森堡等国外空资源开采的政策和法规分析可知,美国等国的国内法赋予私营实体享有外空资源所有权,不仅是为了鼓励外空活动,更显示该行为背后的动机和意图是这些国家企图单边开采外空资源,垄断获取和占有外层空间资源,维护美国在外空的霸权地位。
在外空资源开采规则有待拟定的背景下,外空资源开采活动主导权的角逐不再仅限于空间技术能力领域,更属于规则范畴。如何制定有利于本国外空资源开采活动的国际规则是各国之间在具体制定方面的博弈。美国等国不仅是为了发挥国内法的内在效力,赋予私营实体享有外空资源的所有权,为本国在外空资源开采活动披上合法外衣,更是为了影响外空资源开采国际协定的制定走向,以期国内政策和法律辐射至全球外空资源开采规则体系,构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外空资源开采规范体系,获取开采外空资源的所有权和收益。
(三)最佳属性:从法经济学视角阐明外空资源属性
由于外空资源的稀缺性和高价值性,有必要对外空资源法律属性进行深入分析和确权,实现外空资源的效用最大化。然则从法哲学论和法社会学两个层面看外空资源法律属性迥异,此种迥异是客观性与主观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应然性与实然性的矛盾体。而法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理论(cost-benefit analysis)提出,在权利状态不明确时,通过降低谈判成本、协商成本以及诉讼成本等交易成本,会大大增加效益[13]。成本效益分析理论可以保障外空开采活动的正常运转并实现外空资源的最佳配置,界明外空资源产权属性显得至关重要,在利用法经济学成本效益分析理论进行外空确权行为时涉及对法律成本和收益两方面的仔细权衡。
第一,外空资源共有物的法律属性可以降低法律成本。通过分析人类共同财产、无主物以及共用物这三种不同观点认定过程中的谈判、协商和影响等法律成本的大小,确定最佳的空间资源法律属性。若将外空资源依据《月球协定》认定为人类共同财产,遗憾的是目前《月球协定》仅得到十几个国家的批准或加入,这也意味着大多数国家对空间资源不认可属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14]。为此,联合国需要共同推动《月球协定》能够被大多数国家批准加入,这需要巨大的谈判和协商成本,而对于外空资源开采规则急需的国际形势下,显然是不合理且不具备效率的做法。若利用国际法上的先占制度将外空资源认定为无主物,这不仅会导致空间开采能力发达的国家,如美国、日本和卢森堡等国在外空领域实施霸权,而且明确确定外空资源的初始位置非常困难,也就是说,确定外空资源开采的边界面临较高的成本。但是当物品为界定为共有物时,就免去了确认和维护私人产权的成本[15]。国际社会对“天体上的矿产资源是共有物”的观点没有争议[16] 。因此将外空资源的法律属性确定为共有物,不仅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各国在这一法律问题上的谈判和协商成本,而且可以涵盖不同外空资源观点的共性,最重要的是共有物这一法律属性的确定可以为外空资源开采的具体法律制定奠定基础,而不用一直困惑于外空资源的法律属性这一前提问题,最重要的是可以聚焦于外空资源开采中的权利义务等具体规则。
第二,外空资源共有物的法律属性可以提高法律效益。所谓法律效益是指通过立法对法律权利资源进行最优配置,除去各种法律成本耗费后,进而实现法律资源在质上和量上的价值最大化。它意味着以价值最大化的方式利用权利资源和获得满足,并突出体现为法律应然价值和实然价值的重合和差异,实现制度效率性的提高[17]。外空资源共有物的法律属性不仅可以降低国际社会在外空资源开采活动中的立法成本,极大提高外空开采规则的制定效率,而效率往往是隐藏在公平正义背后的价值追求。具言之,外空资源共有物的法律属性是以公平利用为目的,对外空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维护良好的外空开采秩序,通过赋予外空资源共有物的法律属性,为每个国家提供开采外空资源的机会以及公平的获酬分配。最为重要的是,外空资源是共有物的这一界权可以保障空间技术不发达国家的外空利益,而且可以与《外空条约》第二条的规定具有理论上的自洽和逻辑上的一致。
综上,利用法经济学的成本效益理论分析外空资源的法律属性,是一种最优组合规则,不仅可以均衡应然属性和实然属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还是对外空资源法律属性应然状态和实然状态评价的统一,是外空资源法律属性的最佳评价机制,满足空间技术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多种需求,更好适应外空活动发展的客观需要,使得所有国家都能从中受益,也为推进外空资源开采国际规则的制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外空资源共有物法律属性的界定在利用法经济分析后,尤其“成本效益分析”理论的运用可使外空资源共有物这一法律属性更具有涵摄能力,而且更论证了共有物理论适用于外空资源的合理性。
三、理论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外空资源开采国际规则的逻辑证成
人类命运共同理念若转换入外空资源开采的国际规则之中,应先找寻出其与外层空间法规则的契合之处,以及对于外层空间法理念的更新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只有与外层空间法具备共同的法理依据,才能更多地被国际社会接受,更可能转换在外空资源开采国际规则之中。
(一)革新和修正外层空间法的价值目标
《外空条约》的序言特别提到,为了和平目的而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全人类共同利益,呼吁全人类在外层空间探索和利用这一过程中享有共同利益,不应归于单个或者少数空间大国利益,而是归于全人类[1]。序言明确表明了《外空条约》的价值目标,就是全人类共同利益,考量不同角色间的关键利益平衡,即缔约国不论其在外层空间和天体探索利用中的科学或经济差异如何,都应作为一个整体应当从中获益,不应忽视发展中国家的空间利益。随着外空资源开采新型活动的兴起,《外空条约》这一空间宪章对新兴的外空活动不具有实际可操性,导致英美这样发达国家企图摒弃现有的空间条约基础,重新建立有利于本国空间利益的外空资源开采秩序,替代现有的国际空间规则。例如,近年来美国的《阿尔忒弥斯协议》和英国的《阿斯特拉宪章》鼓励各国和私营实体加入其制定的外空资源开发规则。英美国家的这一行为罔顾其他国家的空间利益,抢先占有外空资源,使得《外空条约》规定的人类共同利益原则受到严重挑战。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空条约》全人类共同利益原则进行了发展和修正,经由对《外空条约》制定的历史背景可知,《外空条约》中的全人类共同利益主要以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利益为主,包括空间国家的利益和非空间国家的利益以及发达国家的利益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没有将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出发,顾及全人类的国际利益,也误导国际社会对外空领域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理解。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意识在面对外空活动尤其资源开采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影响单个国家,也会对全部的国家外空活动造成影响,因此外空开采活动的合法有序不应仅要求主权国家在开采过程中“独善其身”,仅考虑自身的空间利益,更应注重将所有的国家作为整体,都可以从开采活动中受益。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空条约全人类共同利益这一原则的具体含义进行了革新和修正,不仅包含了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利益,还纳入人类整体的国际利益,实际上包含着综合利益理念,强调国家利益外的共同利益[18]。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人类共同利益原则与国家利益并不冲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之上,但同时也是任何一个国家之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19]。
(二)巩固和深化外空活动目的
《外空条约》第4条和《月球协定》第 3 条都规定了对外层空间的利用应为了和平目的。然而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进行外空活动,各国航天技术的发展使得太空权力对比发生改变,对美国的太空霸权地位造成威胁。在这场“权力—利益”的博弈中,美国为了维护本国霸权的空间利益,主要通过以下方式,竭力推进太空军事化和武器化。第一方式是2022年1月美国向联合国提出了限制“破坏性直升式反卫星导弹试验”(联合国第77/41号决议),对冲中俄提出的PPTW条约草案。“破坏性直升式反卫星导弹试验”的决议表面上中俄的外空活动列为影响外空安全的最大威胁,其主要意图是遏制中俄在外空领域的空间技术发展,保障美国在外空领域的军事优势。此外美国对其他国家在太空军备控制领域提出的防止太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的议题方案一概拒绝,屡次投反对票。而在实践中,美国却大力推进太空武器化,加快太空建军步伐[20]。第二种方式是美国和英国大力渲染夸大空间碎片的危害,利用不符合国际法的规则将外空活动主观地化分为“负责任/不负责任”行为,所谓推动“负责任外空行为”“空间碎片治理”“空间交通管理”以及“空间态势感知”等议题,但实质上是利用以上议题作为借口,利用外空长期可持续发展为幌子,掩盖美国大力发展太空军事化和武器化的事实。例如,美国空间发射技术、深空探测技术的发展使小行星资源的开采具备了现实可能性,其中涉及对从事开采小行星资源的空间资产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以小行星为基地进行军事活动、通过捕获小行星开展军事利用等威胁外层空间安全的因素。美国宇航局于 2013 年便开展小行星捕获计划,即在捕获小行星至月球远程逆行轨道的基础上,派宇航员登陆该小行星,为日后火星登陆探测做准备。这种捕获行为一旦获得技术成熟便极具武器化风险,并且天体轨道稳定性的特点使得这种潜在的武器始终处于“临战状态”,由此对外空安全造成挑战。目前外层空间面临的安全危机比联合国成立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严重,急需新的理论促进国际和平。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内涵是,在当前世界局势剧烈变动的时期,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各国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程度空前加强,各个国家应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21]。中国同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一道,努力推进防止太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的军控进程,倡导在太空率先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 年 11 月,中国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第 72 届联大负责裁军和国际安全事务第一委员会(简称联大一委)通过的《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进一步切实措施》和《不首先在外空部署武器》两份安全决议[20] ,缓解了外空安全治理赤字,巩固外空活动应为外空和平与发展。
(三)拓展和指引外空环境保护
由于外空蕴含丰富的矿产资源,以英美为首的发达国家竞相制定外空资源开采计划,向外层空间发射大量卫星群进行资源开采和深空探测活动,也随之产生大量的空间碎片。外层空间被数以万计的空间碎片充斥,不仅对外层空间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同时也对现有的国际空间法规则造成挑战,是人类可持续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面临的挑战之一。鉴于外层空间的特殊性,若不对外空环境污染进行治理,不仅会对空间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而且还会损害后代和具有潜在空间能力国家的利益。《外空条约》第9条可被视为外空环境保护的基础,规定了避免或者尽可能减低对外空环境造成的有害污染[1]。空间碎片属于有害污染的一种,但是《外空条约》第9条并未明确“有害污染”这一概念的通常含义,更没有规定在何种情形下必须采取适当措施。虽然1979年《月球协定》第7条明确提及防止月球的平衡遭受破坏和环境污染,并将采取预防措施的义务施加于各国,但是该协定由于仅有十几个国家加入而不具备普遍的法律拘束力。外空条约的滞后性和规则模糊性导致在外空环境治理中无法发挥理想作用,不利于外空环境治理中的整体协同解决。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了经济、文化、政治、安全、生态五个组成部分,而生态环境处于基础地位[21]。环境安全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本来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题中应有之意[22]。因此在构建“外空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应该把更多目光投向如何保护外空环境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外空环境治理具有积极价值:第一明确指出了外空环境治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与其他外空发展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清洁美丽的外空环境是实现外空长期可持续发展、外空和平探索利用和外空安全的必要前提,恰好缓解了外空环境治理困境。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外空环境治理规定了具体的治理方式。目前外空环境治理情形严峻,但其治理行动迟迟没有进行和面临层层障碍,究其根源在于各国在外空环境治理责任分配上存在分歧和不公正,无法在治理责任层面达成共识。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突破了各国之间的责任分歧,着眼于全人类在外层空间的整体利益,认为国际组织、国家和私营主体都共同负有治理外空环境的责任,可以平衡空间行为者之间的责任冲突。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不是对现有外空环境保护制度的颠覆,而是超越国家本位从人类整体角度出发推动外空环境治理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不断进化。
(四)高度契合外空长期可持续发展
外空拥有丰富的资源,其资源如月球上的氦-3开采可能会带来能源革命,从而蕴藏着不可估量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外空资源开采除了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外,也是技术战略和政治战略需要[23]。为了使外空活动长期可持续发展,联合国通过了《外空活动长期可持续性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其内涵以实现公平获取外层空间的惠益这一目标的方式,将空间活动无限期维持到未来,以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同时为子孙后代保护外层空间环境[24]。由于《准则》不具有国际法的法律约束力,而且指导原则中的任何内容不构成对外空条约的修订、限定或重新解释,不被解释为给各国带来任何新的法律义务,导致外空资源这一有限资源,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及其非政府实体所使用,严重影响外层空间活动的长期可持续性。例如,美国、日本、卢森堡和阿联酋全然不顾《准则》的规定,相继颁布了外空资源开采的国内法,发射巨型卫星星座进行外空资源开采活动,大力抢占外空资源,并在外空活动过程中造成严重的外空环境污染,导致《准则》在国际实践中的实施效果欠佳。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蕴含的时空观和义利观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存在高度契合,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理念,也是对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完善和深化[21]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5],将可持续发展放在了重要位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契合外空长期可持续发展,而且作为外层空间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因素和实现外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工具,兼具保护外空环境与外空发展的二元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空资源活动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整体观和全球治理观。其中可持续发展的整体观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是将全人类空间资源开采活动与外空环境保护进行了双向互动 3,认为全人类空间活动与外空环境构成了外空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彼此联系。全人类空间资源开采活动是外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子系统,而外空环境保护经由全人类空间活动得以巩固。其次是将当代人的空间利益需求和后代人的空间利益需要作为整体,即当代人在获取外空资源,共享空间惠益时,应顾及后代人对空间利益的需求。而且人类命运共同理念为外空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全球治理观,提出外空资源开采活动长期可持续发展与全人类息息相关,其目标的实现不能单靠某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任何空间行为主体都不能独善其身,需要各个空间行为主体的协同努力。
四、落实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外空资源开采国际规则的建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契合外层空间的新发展,更对现有的外层空间法进行了更新和迭代。但我们必须意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且也并非仅具有国际法方面的含义。因此,如果要将其转化为国际法,需要将其以法律的语言加以细化,以便于其最终转化为国际法律制度[26],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不会自行转换在外空资源开采国际规则中,需要对该转换途径加以研究,可以通过递进式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溢效果和内化为外空资源开采的具体规则两种途径加以实现。
(一)实施途径:递进式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溢效果
当下外空资源开采国际规则在联合国层面有待制定,中美两国在外空资源开采领域存在规则博弈,中国作为一个航天大国,应抓住这一机遇,积极主动提出外空资源开采的具体制度,一方面可以保障我国在外层空间的空间利益,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目的是主导外空资源开采国际规则的制定,反击美国的太空霸权。而想要推动外空资源开采国际规则的制定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目的,中国可以通过“国内战略层面—国际舆论层面—国际规则层面”这一层层递进的范式,逐步争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欧洲部分国家的支持和认可,推动外空资源开采国际规则的制定。
首先,国内战略层面是外空资源开采国际规则得以制定的出发点。美国发布了一系列外空资源开采的政策和法律,2015年美国颁布《商业航天发射竞争力法案》,赋予美国公民和公司从事太空资源开发并拥有使用的权利,随后2020年4月6日,美国白宫发布《关于鼓励国际支持太空资源回收和利用的行政命令》,该行政命令与《商业航天发射竞争力法案》立场一致,鼓励政府和私人实体根据适用法律占有和利用外层空间资源[27]。2021 年 12 月美国发布的《美国太空优先框架》概述了美国太空政策优先事项,鼓励竞争性和新兴的美国商业活动[28]。美国以上关于外空领域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都重申了其外空战略目标,即确保美国在太空探索和科学的领导地位和优势。美国一系列关于外空资源开采活动的国内法规定将会对外空资源开采国际规则产生影响。我国关于航天活动的规定仅体现在《2021中国的航天》白皮书,规定把发展航天事业作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9],而对于外空资源活动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有待制定。我国应先从战略层面进行积极应对,具体建议如下:第一,在法律层面,加快航天立法仍然是当务之急[30]。近年来我国的航天活动取得了丰硕成果,航天技术远远领先于航天法律制度,我国关于外空活动的《航天法》还没有颁布,《航天法》的实施有助于对我国外空活动进行整体规范,解决我国私营实体对航天法的内在需求。第二,从政策方面,由于《航天法》的出发点是规范我国外空活动和落实国际义务,因此《航天法》不宜明确涉及外空资源[31]。但是我国可以通过发布一系列政策鼓励私营实体进行外空活动,并且对私营实体开展外空活动制定具体的监督办法。综上所述,我国应制定和发布关于外空活动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在国内形成体系化的外空活动规制体系,只有具备了外空活动国内规制体系才可以更好地反击美国对我国在外空领域的遏制,也可以为推动外空资源开发国际规则的制定提供方案和理论依据。
其次,国际舆论层面是外空资源国际规则得以制定的重要保障。外空活动尤其资源开发作为人类今后在外空探索领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当前国际社会越来越频繁地被提及,而在国际外空规则即将迎来变化的时刻,2020年5月美国率先制定《阿尔忒弥斯协定》,2023年 6 月 28 日英国又在“负责任外空行为”的基础上,推出了《阿斯特拉宪章》,发达国家想要主导国际社会制定外空资源开发规则走向的意图不言而喻。目前英美等发达国家以政治舆论开路,激化已有的关于外空规则解释或制定的分歧,通过渲染空间碎片的威胁,营销中俄两国在外空活动中产生的空间碎片,无理由地将中俄的外空活动划定为“不负责任的行为”,然后以识别“共同威胁或不负责任”等行为为借口,企图在道义和政治上绑架中俄[32],将中俄排斥在外空活动之外,制定有利于本国外空活动的国际新秩序,实现美国在外空领域的霸权地位。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部分欧洲国家对于外空活动仍缺乏全面和深入认识,所以尚未加入《阿尔忒弥斯协定》,我国应抓住这一时机,注重舆论层面的重要作用,应积极主导、参与国际场合关于外层空间资源开发立法的讨论,成为解释国际空间法律规则的重要参与者,争取主动权[30],争取获得大量发展中国家和部分欧洲国家的支持。
最后,国际规则层面是外空资源开采国际规则得以制定的最终目标。英美等发达国家目前在积极抢占外空资源领域规则博弈的主导权,我们必须意识到,外空规则博弈,是大国争夺外空秩序主导权的重要途径和最终手段。因此我国除了在战略和舆论层面做好相应的应对措施,更为重要的是,应提出制定外空资源开采国际规则的具体方案。如上所述,一直以来,中国从各国在外空资源开采中的共同利益出发,顾及不发达空间能力国家的外空利益,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多次被写入外空委决议,这表明国际社会已经接受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外空领域的应用。笔者认为中国更有条件代表多数国家的利益诉求[32],在制定外空资源开采国际规则制定方面,具有天然的法理优势。
(二)法律化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化为外空资源开采的具体规则
中国作为航天大国,需要深度参与国际外空规则的构建,推动甚至引领未来的外空法律秩序[33]。那么在外空资源开采国际规则有待制定的关键窗口期,我国应在国际层面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外空资源开采活动中的实施。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化在外空资源开采规则之中不仅有助于保障我国的空间利益,更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外层空间法律制度的话语权。因而外空资源开采国际规则的制定应始终坚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由空间发达国家和空间能力一般的国家以及没有空间能力的国家共同协商,在平衡各方空间利益的基础上共同构建,共同享有外空资源开采所获得的惠益成果,在此基础上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象化,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化为外空资源开采的具体规则,切实指导外空资源开采活动。
第一,外空资源开采主体不得对外空及天体主张所有权。外空资源开采主体不能对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行使所有权,尤其禁止对外空主张主权和领土权益[1]。禁止对外空主张主权可以防止有些国家将外层空间殖民化,也有助于防止在领土或殖民野心的驱动下产生冲突的可能性[1]。而美国《阿尔忒弥斯协定》提出建立外空资源开采的安全区,并避免对安全区域的有害干扰,对于安全区的大小、范围和时间则根据运营的状态而确定4。《阿尔忒弥斯协定》中主张的安全区有悖于外层空间共有物的法律属性,变相地将外层空间的部分区域据为己有[34],通过划分“安全区”以谋求月球等天体的主权[35]。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全人类共同利益原则将所有的国家作为整体,注重从外空资源开采活动中受益。因此任何试图将外空资源据为己有的行为都会影响空间强国与非空间国家之间的利益平衡,更违反了外空法,都是不被允许的。
第二,外空资源开采过程不得假借开采行为实施外空军事化。即使外空资源开采活动本身并不意味着军事化,但日益增长的月球开发活动势必与月球军事化产生某种关联[1]。21世纪之前外空军事化控制虽然举步维艰,在联合国层面的外空军事化议题主要聚焦禁止外空武器化和军事化单一议题,基本处于一种弱纳什均衡状态,但外空安全并没有完全失衡。进入21世纪后,外空活动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使得联合国层面对于外空的法律议题也更加交叉融合,各国参与太空军控谈判的具体利益诉求出现了多样化,例如,2020年英国以《阿尔忒弥斯协议》为基础,提出了“负责任外空行为倡议”,得到盟友美国的大力支持,在联合国层面通过了该倡议。英美两国这一举措表面看是着眼太空环境保护,实则是基于掩盖本国在外空军事化行动。这对其他国家进行外空资源开采活动产生了消极影响,也是在外空实施霸权主义的表现,威胁外空的安全和稳定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议提出普遍安全原则[36],明确反对假借开采行为实施外空军事化的外空活动,不支持因进行外空开采活动而划定安全区的做法。
第三,外空资源开采不得损害外空环境。近年来美国开展了密集的空间资源开发和提取活动,如深空工业公司通过提供勘探、收获、加工、制造和销售太空资源所需的技术资源、能力和系统集成,改变太空产业的经济效益[37]。外空采矿行为虽然可以从小行星上提取自然资源,但也会导致外空环境污染问题,包括空间碎片、地球大气层污染以及核污染等。由于外空开采行为本身极具危险性,可能会对外空和地球环境同时产生影响,并造成重大损害。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绿色和清洁美丽世界,是应对外空环境恶化的可行解决方案。因此在外空资源开采应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消除开采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得干扰他国的空间利益,不得污染外空和地球环境。开采主体在对外空自然资源开采的同时,应发布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用于评估开采项目对外空和地球环境的潜在环境后果,并且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应从其采矿作业开始到结束为止进行持续更新,确保可持续且负责任地进行太空资源开采。不得损害外空环境还包括在开采过程中尽可能不采用对外空环境产生损害的技术,并在完成任务后恢复采矿区[37]。
五、 结语
外空资源开采国际规则的制定是一场“空间技术—空间利益”的博弈,在这场博弈中,英美等发达国家不仅通过颁布国内法,鼓励外空资源的开采活动,更是外空资源开采的国内法推动外空资源开采国际规则的缔结,遏制他国空间活动的发展,维护在外空活动中的领先地位。但无论如何,外空资源开采国际规则的制定归根结底还是须由主权平等的国家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制定。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才可以真正促进外空资源开采国际规则的讨论和发展。虽然有些国家企图通过国内资源法和区域协定输入本国外空资源开采标准,不顾及空间不发达国家的空间利益,但这种做法必然会损害人类探索利用外层空间的利益。我国作为航天大国,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落实外空资源开采国际制度的建构中,提出公平有效的开采制度,积极推动相关规则的制定。
参考文献:
[1] 斯蒂芬·霍贝,伯恩哈德·施密特.科隆空间法评注(第一卷)[M].李寿平,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36⁃140.
[2] 王传良,张晏瑲.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现代海洋法的发展——以“BBNJ国际协定”的制订为视角[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73⁃85.
[3] 王国语.外空、网络法律属性与主权法律关系的比较分析[J].法学评论,2019(5):145⁃158.
[4] 廖敏文.外空资源法律地位的确定问题研究[J].国际法研究,2018(2):40⁃66.
[5] 段欣.外空资源法律属性的界定与中国立场[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139⁃148.
[6] 蔡高强,刘云萍.论采回的外空矿产资源权属法律制度[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126⁃138.
[7] 王铁雄.普芬道夫的自然财产权理论[J].前沿,2010(7):66⁃73.
[8] 张林.洛克劳动财产权理论与知识产权的“共有状态”[J].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123⁃129.
[9] 高其才.法社会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2.
[10] 何珊君.法社会学新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4.
[11] HYDEN H.The sociology of law potential: exploring its scientific landscape[J]. Front Sociol, 2023, 8(1): 1⁃4.
[12] 托马斯·莱塞尔.法社会学导论[M].高旭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2014:53⁃55.
[13] 张永健.物权法之经济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32.
[14] MARYIN S.Outer space, an area recognised as res communis omnium: limits of national space mining law[J].Space Policy, 2022, 60(1): 2.
[15] 肖松.法经济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2017:28.
[16] 颜永亮.论天体矿产资源单边商业化开采的合法性问题[J].地方立法研究,2019(3):111⁃126.
[17] 冯玉军.新编法经济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104.
[18] 李寿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国际法治变革:逻辑证成与现实路径[J].法商研究,2020(1):44⁃56.
[19] 周振春.论全人类共同利益原则及其国际作用[J].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47⁃53.
[20] 徐能武,龙坤.太空军备控制的现实争辩、理论逻辑和参与策略[J].国际展望.2021(6):56⁃79.
[21] 吴昂.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国际环境法治实现研究[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3⁃26.
[22] 姚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意涵:理念创新与制度构建[J].当代法学,2019(5):138⁃147.
[23] 王国语.拉开外空采矿竞赛的序幕?——美国行星采矿立法的法律政策分析[J].国际太空.2016(5):12⁃21.
[24] Guidelines for the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of Outer Space Activitie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Peaceful Uses of Outer Space[EB/OL].(2021-06-20)[2024-01-18]. https://www.unoosa.org/documents/pdf/PromotingSpaceSustainability/Publication_Final_English_June2021.pdf
[25]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EB/OL].(2022-10-25)[2024-01-16].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26] 车丕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法学思考[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6):15⁃24.
[27] Encouraging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the Recovery and Use of Space Resources[EB/OL]. (2020-12-04)[2024-01-18].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0/04/10/2020-07800/encouraging-international-support-for- the-recovery-and-use-of-space-resources.
[28] United States Space Priorities Framework[EB/OL].(2021-12-01)[2024-01-18].,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12/united-states-space-priorities-framework-_-december-1⁃2021.pdf.
[29] 2021中国的航天[EB/OL].(2022-01-08)[2024-01-20]. 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1/28/content_567 0920.htm.
[30] 聂明岩.美国允许私人实体外空采矿立法对国际及国内法发展的影响[J].西部法学评论,2018(1):96⁃103.
[31] 吴晓丹.开发外空资源:国际法合法性、制度走向和对策[J].载人航天,2019(4):552⁃560.
[32] 王国语.美国《外空防务战略》对外空军控国际规则博弈的影响分析[J].太平洋学报,2021(3):94⁃106.
[33] 冯国栋,史忠军,许伟春.对外空资源开发相关政策法律问题的思考[J].中国航天,2021(11):22⁃26.
[34] 谢文远,张光,姚伟.美国《阿尔忒弥斯协定》剖析[J].国际太空,2020(8):61⁃63.
[35] 李晋阳.浅析美国《阿尔忒弥斯协定》中的“安全区”[J]. 国际太空,2020(12):57⁃60.
[36]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EB/OL].(2017-01-19)[2024-01-20]. https://www.rmzxb.com.cn/c/2017-01-19/1294301.shtml.
[37] HOFMANN M,BERGAMASCO F.Space resources activ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ility: legal aspects[J].Global Sustainability,2022,3(1):1⁃7.
Legal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Outer Space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m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Rules
for Outer Space Resource Exploitation"
Yang Kuan, Lu Yu
(Law School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exploitation of outer space resources is the latest development trend in the explor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outer space. However,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space law has not yet covered the relevant systems for the exploitation of outer space resources. How to formulate international rules for the exploitation of outer space resources is a difficult problem in the governance of outer space. The confirmation of the legal attributes of outer space resources is the premis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rules for the exploitation ofcTgREAUFl39AAyL5wUuGiWPEbEtrkI93lWNcZuPvmtA= outer space resources. The attributes of the common property of outer space resources should be def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egal philosophy, legal sociology and legal economics. A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specific rules for the exploitation of outer space resources,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onforms to the trend of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outer space resource exploitation activities today. It consolidates and develops the existing outer space law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value, purpos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long-ter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ha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lea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rules for the exploitation of outer space resources. However,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ill not be automatically transformed into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for the exploitation of outer space resources.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path of this transformation. It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two ways: progressively enhancing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internalizing it into specific rules for the exploitation of outer space resources to achieve its legal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in the governance of outer space.
Keywords: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outer space governance; outer space resource exploitation; implementation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