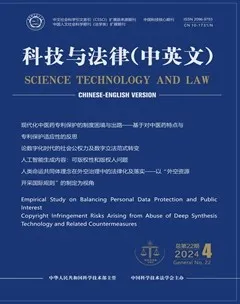论复杂人工智能生成物在著作权法的定性
摘 要:对于AI生成物的可版性认定,我国司法实践采取了“简单—复杂”场景二分的裁判思路。然而,囿于对独创性概念的有限阐释,司法机关并未对该问题形成逻辑融贯的论证,进而引发争议。对此,有必要以复杂生成场景为定位,并沿袭独创性概念的规范阐释脉络,从客观、主观和行为三个维度来回应争议:第一,著作权法并仅不限于保护“大师”作品,生成式AI“排列组合式”的创作也能满足客观面向的“一定美感”;第二,复杂AI生成物具有高度定制化的特征,因此具备主观面向的“个性因素”,“人机二分说”将工具误认为主体,“算法唯一说”缺乏对创作流程的完整考量;第三,《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条第一款的“直接”应解释为“主要贡献”而非“直接决定”,后者既与域内外的一贯实践不符,也有悖于社会化创作的现代艺术发展规律。
关键词:生成式AI;人工智能;著作权法;可版性;独创性;ChatGPT
中图分类号:D 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9783(2024)04⁃0073⁃10
2023年11月27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对“AI文生图著作权侵权第一案”(以下简称“AI文生图案”)作出一审判决1,这是“ChatGPT时代”来临后我国司法机关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以下简称生成式AI)可版权性的首次承认。基于比较的视野,此次判决凸显两个鲜明特点:一是时代性,相较于既往的国内判决,本案的司法论证更为翔实、严谨(如对于AI图片生成过程的分析),突出司法界对于人工智能认识的与时俱进;二是探索性,放眼全球司法实践(如美国至今未承认AI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我国法院作出更具创新性、开放性,以及更符合中国实际的判决,从而为全球人工智能的版权治理做出了有益探索。
然而,与法院的开放姿态截然相反的是,目前业界和学界对该份判决却多持负面看法。例如,有律师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指出本案中的AI绘画模式具有“不可预测”的特点,因此并不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条关于“直接创作”的规定[1];还有学者针对判决文书本身,指出该份判决只是从政策性的角度进行了认定,而对于一些关键性问题仍然缺乏足够的司法推理等[2]。毫无疑问,以上观点都不同程度上揭示了判决存在的不足,笔者认为此类观点存在一定合理性。然而,囿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任何判决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寄希望于一份判决就能彻底解决人工智能著作权争议的想法显然不切实际。
司法实践所不及之处,正是法学研究的肇始。对此,本文秉持建构性的思路,在总体承认“AI文生图案”判决结果——承认AI生成内容可版权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司法实践的不足,针对性地澄清尚待回应的具体争议,以期为人工智能版权治理的完善“添砖加瓦”,为人工智能艺术行业的蓬勃发展“保驾护航”。
一、人工智能生成物可版性的症结聚焦
当前司法实践表明只有复杂的AI生成物才具备可版权性,然现有判决过多侧重于图片生成的技术流程,而忽略了独创性要件的法理阐释,进而导致事实和规范之间形成裂隙。基于此,本文将以复杂生成场景为考察对象,以独创性概念的规范阐释为分析脉络,从而进一步完善有关论证。
(一)司法现状:“简单—复杂”场景二分
目前,国内关于AI生成内容可版性的案例主要有3个,除了“AI文生图案”,还有2019年审结的“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诉上海盈讯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以下简称“Dreamwriter案”)2,以及2018年审结的“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以下简称“菲林律所诉百度案”)3。这三个案例皆是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三条对于作品的定义4,尤其是独创性要件而作出的判决,其判决结果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沿袭了一脉相承的判决倾向,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秉承面向未来的司法理念,在总体上承认AI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在“Dreamwriter案”中,法院承认自动写作软件Dreamwriter所作文章的可版权性tNgHDcrLM05hAXQc7w//3FcGSt8s9zap9XG61IJnOJE=,原因在于Dreamwriter自动运行的背后体现了原告的个性化选择——数据类型的输入、文章框架模板的选择,以及算法模型的训练等均由原告的创作团队进行选择和安排,因此涉案文章的形成与原告的智力活动有着直接的关联,符合《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条的规定,故涉案文章满足独创性的要求。作为司法层面的最新进展,“AI文生图案”不但肯定了AI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还进一步展现了判决背后的政策考量[3]。法院明确指出,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亲身投入越来越少是客观的艺术创作规律,利用AI进行绘画的本质仍然是人利用工具在进行创作,而鼓励先进工具的使用则有助于更多没有绘画基础的人投身创作,因此肯定AI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与《著作权法》鼓励创作的目的相符。
第二,重视个案分析,强调AI创作的作品必须体现“人”的个性化表达。在“AI文生图案”中,法院虽然肯定了涉案图片的可版权性,但同时也提到判断AI生成图片是否具备独创性“需要进行个案判断,不能一概而论”;同样出自于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在“菲林律所诉百度案”中法院就否认了涉案报告的作品属性,因为该报告系由威科先行自动生成,原告对于报告的贡献仅在于“提交了关键词”“应用‘可视化’功能自动生成”,这并没有体现出原告的思想、情感的独创性表达,故报告因缺乏个性化表达而不能成为作品。
总体上承认AI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个案层面强调具体分析,意味着法院采取了“简单—复杂”场景二分的裁判思路。具体而言,通过比较三款软件的使用场景,可以进一步明确法院的裁判逻辑:Stable Diffusion是一款专业的图像生成软件,在“AI文生图案”中原告使用的提示词甚至达到了“工程级别的复杂性”[2];Dreamwriter则是腾讯公司内部研发使用的软件,其面向的是专业的软件开发团队,所以使用场景必然是高度定制化、专业化的。可见,这两款软件的使用场景足够复杂,以至于可以让法院清晰识别“人”的贡献,进而判定有关生成品的可版权性。反之,威科先行库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及时、准确、权威、内容丰富的信息解决方案和服务”5,效率是用户的核心诉求,因此该软件的操作流程简洁,报告的生成反而难以体现用户的精力投入,因此法院否认了涉案报告的可版权性。总的而言,法院的深层考量是,只有那些生成过程足够复杂,体现了“足够”人类精力的AI生成物,才能称之为“作品”。
(二)症结所在:独创性概念的有限阐释
“简单—复杂”场景二分的裁判思路既符合生成式AI运行的内在规律,也与我国作品认定的司法实践惯例相符6,因此总体上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在具体的司法论证中,由于论证方向的偏颇,导致判决并没有形成严密的逻辑链条,进而招致非议。具言之,以“AI文生图案”为例,法院运用长达10页的篇幅去描述原告是如何通过Stable Diffusion生成涉案图片后,对独创性要件进行了如下认定:首先,原告通过提示词和参数的设置形成了画面元素的基本设计,从而获得初始图片,这个过程体现了原告的“选择和安排”;其次,原告通过参数的进一步修正,获得最终的涉案图片,此处再次表现了原告的“审美选择和个性判断”。
目光在事实与法律规范间“来回穿梭”是法律适用的普遍特征[4]。该判决论证的重点显然只停留在“事实”层面,至于如何确定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对应关系,尤其是独创性要件的解释以及适用问题,此处显然没有作出足够的回应。质言之,该判决只能说明涉案图片的生成的确有自然人的参与,但不能必然地推导出有“足够”的人类参与。以“菲林律所诉百度案”作为对比,“关键词”或“提示词”作为引导用户使用软件的交互式设计,二者在功能上并没有实质上区别。然而,为何作品的生成模式同样是“输入提示词(关键词)—生成内容”,“AI文生图案”就体现了原告的“审美选择和个性判断”,而“菲林律所诉百度案”就没有“传递软件用户思想、感情”?进一步分析可知,问题的关键并非有无人类智力投入的“事实认定”问题,而是人类智力投入程度如何才能满足独创性标准的“规范解释”问题。这就好比著名的“Feist案”,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尽管原告公司对电话号码的编排付出了劳动,但由于电话号码簿的制作缺乏“最低程度的创造性”,因此不能构成版权法意义的作品7。可见,人类智力的投入并不能导向可版权性的必然结论,如何在创作的具体语境下理解独创性概念,才是争议的症结所在。
(三)抽象概念的具体把握
独创性要件鲜明凸显着著作权法鼓励文化创新的核心目标,故世界各国普遍将其公认为作品可版性的必备要件[5],理论界目前关于AI生成内容可版权性的探讨也多集中于此[6]。然而,《著作权法》虽明确将独创性列入作品构成的要件范畴,但对于这一基本概念的具体把握,我国立法文件却并未予以明确[7]。根据《审理著作权案件适用法律解释》第十五条,即“作品的表达系独立完成并且有创作性”,国内通说认为,独创性应包括独立完成和创作性两个方面。“独立完成”概念的指向十分单一且明确,即并非抄袭[8];然而,“创作性”概念则复杂得多,学界目前尚未形成共识[9],司法实践中用于表达该概念的术语更是五花八门[10]。这源于主流学术著作对这一重要概念的有限探讨。例如,法工委出版的释义书将“创作”一词解释为作者基于对社会生活素材的构思和选择,并塑造出艺术形象的创造性劳动[11]。这个定义本质上只是在描述创作的过程,其并未提供任何关于判断“创造性劳动”的标准。与之类似,对于何谓创作,有学者认为是“作者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经验,运用一定的创作技巧,投入一定劳动时间的活动和过程”[5],同理,这种“名词解释式”的定义并无益于司法实践的裁断。
脱离实践的理论只是概念游戏,以抽象概念解释抽象概念的做法永远无法建构法律的规范意义[12]。由于《伯尔尼公约》并未明确作品的定义,更没有对“独创性”概念作出具体规定,世界各国因而在实践中形成了标准不一的独创性认定制度。从比较视野来看,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采取以作者为中心的主观标准,认为作品应“反映作者的个性”;美国、英国等英美法系国家则采取以作品为中心的客观标准,认为作品应具有“最低程度的创作性”[13]。我国《著作权法》同时借鉴了以上两个法系的规定[14],因此准确地说,独创性概念应至少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应是“具有一定的美感”,美感是一种相对客观的、针对特定艺术水平的要求,其意在排除一些创作过程随意和表现形式简陋的内容;第二层含义应是“由自然人创作”,即该作品并非是随机发现或抄袭他人的,也并非是自然或纯粹由机器产生的,而是蕴含着作者感情、认知和艺术观念的个性化表达。此外,除了以上基于作品表达层面的定义,为了识别作品背后的权利人,《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条还基于行为层面来对该概念进行了不同维度的界定,进言之,创作的第三层含义应是“直接产生作品的行为”。
考虑上述情形的复杂性,有观点提倡要对独创性概念进行“重构”[15]。本文认为,独创性多元的概念内涵形成于世界各国的长期历史实践,其在本质上与著作权法鼓励人类创作的目标相一致,“避重就轻式”的讨论无助于回应现实争议。有鉴于此,本文将基于独创性概念的完整内涵,以复杂生成场景为定位,对AI生成艺术品的可版性予以进一步论证。
二、客观层面:“一定美感”之讨论
(一)概率统计逻辑下生成式AI的固有局限
讨论AI生成内容的客观创造性,本质上就是在考察生成式AI的“创作能力”。个案的比较缺乏普遍意义,因此有必要以目前最先进的AI艺术创作工具——ChatGTP为代表,从技术原理的底层逻辑来展开深入分析。具体而言,生成式AI的技术包括生成式对抗网络(GAN)、生成式预训练变压器(GPT)、生成扩散模型(GDM)等,其中ChatGPT就是通过生成式预训练变压器(即ChatGPT中的“GPT”)技术实现的具体应用[16]。该技术有效降低了模型的训练成本,进而使得ChatGPT在整个互联网数据“喂养”的基础之上,成为可应用于各个领域的“通用人工智能”,最终降低了人工智能的使用门槛[17]。由此可见,生成式AI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机器学习最底层的技术逻辑,即模型训练的基础仍然是基于相关性和概率性分析的大数据逻辑[18],而非基于因果推理的真实逻辑[19]。换言之,生成式AI只是因其数据训练的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因而具备训练海量数据的通用属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成式AI就突破了机器学习的固有局限——人工智能因缺乏对现实世界的真正认识而并不真正具备“人的智能”,生成式AI尚达不到强人工智能的标准[20]。有学者称,生成式AI最显著特点就是“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21],这十分恰当地揭示了生成式AI在统计技术逻辑下的必然局限。
(二)“最低限度的创造性”有别于艺术创新
基于以上认识,有观点认为生成式AI的输出模式就是“排列组合”的过程,其生成的内容大体上类似于一本“流水账”,而非兼具内容和形式的“文字作品”,故而缺乏客观层面的“最低创造性”[22]。无可否认的是,生成式AI本质只是在进行“知识重组”,而非创造知识[23],因此,纯粹由生成式AI创作的作品必然是中庸的、一般水平的,而绝不可能是划时代的、创新的、伟大的作品。然而,著作权法并非只保护“大师”作品。以专利法的客体作为对比,一项技术发明是否具有先进性通常具有客观的判断标准,因此可以严格要求技术进步的“新颖性”作为技术发明受保护的门槛;但作为著作权法的客体,作品的评判往往更具主观性和历史性。例如,著名画家梵高的作品在其生前无人问津,在其过世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却屡屡刷新艺术品的世界拍卖纪录[24]。
如此看来,专业的艺术家们尚且难以识别“大师”作品,更遑论让“业余”的法官来裁决作品的客观价值。霍姆斯法官对此曾表示,“让只接受过法律训练的法官成为插画作品的价值评判者,是一项危险的事业。8”因为天才的作品法官通常不能理解,而平民化的作品法官却难以欣赏,如此一来将导致大量艺术作品无法受到保护,进而危及整个艺术行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创作往往只需具备“最低限度”的创造性即可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9。以文字作品为例,著作权法只关注该作品文字的排列组合、遣词造句等表达形式是否为独创,而不关注文字的内容是否蕴含着别具一格的观点[25]。因此,即使是普通人缺乏艺术造诣的创作往往也能成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而相较于普通人的创作,AI生成的作品虽然同样缺乏艺术创新,但其在质量上显然要更胜一筹,因此当然能够满足客观层面的创作性标准。
三、主观层面:“个性因素”之讨论
所谓主观层面的个性因素,即法院在判决中反复提及的“思想感情”“审美选择”和“个性判断”等要素。AI生成作品的实质是人工智能与人类的交互[26],因此,若要判断AI生成作品是否蕴含个性因素,首先需要厘清人工智能是否在创作过程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从而完全排除了人类作者个性发挥的空间。如果以是否具备人的意识作为判断标准[27],那么现阶段的生成式AI显然尚未达到具备“独立人格”的强人工智能阶段[28]。如上文所分析,ChatGTP实际上仍然是一种概率统计模型[19],而人的意识活动则是一种因果推理的过程,因此生成式AI并不拥有“自己”的意识,在目前阶段只能作为人类创作的辅助工具[29],AI生成作品当然离不开人类作者。以“AI文生图案”为例,创作本质上是由数字艺术品生成工具Stable Diffusion在原告的逐步引导下完成的:原告通过提示词的输入,如“梦幻般的黑眼睛”“红褐色的辫子”等,利用该软件初步“刻画”了一个符合原告审美、优雅知性的女性形象;在此基础上,原告通过参数的修正和提示词的进一步输入,最终塑造并呈现了一个原告心目中的“完美”女性画像。可见,利用Stable Diffusion软件生成的图片极具个性特色,理应满足创作性的要件构成。然而,限于AI艺术品生成机理的复杂性,有不少学者出于对AI创作规律的“误解”而提出主观层面的否定意见,主要可以分为“人机二分说”和“算法唯一说”两种观点。
(一)“人机二分说”将工具误认为主体
有学者认为,各国所确立的独创性标准皆是以“人”为前提,而人工智能创作软件本质上并非“人”,因此机器人的创作当然不能称之为智力成果,故不满足作品的构成要件[30]。此类观点夸大了人工智能的作用,将“创作工具”误认成“创作主体”,从而陷入了人机对立的单一化思维。固然,纯粹由AI生成的内容普遍为世界各国著作权法律所不容,这是因为著作权法的宗旨仍然是鼓励“人”的创作,在人工智能尚未突破“主体—客体”二分理论的技术临界点[31],并取得民事能力而成为法律主体之前,这一立场在可预见的将来都不会改变。例如,著名的“猕猴自拍案”,法院认为涉案猕猴“鸣人”(Naruto)并不是版权法意义上的作者,不具有诉讼资格,因此驳回了动物保护团体善待动物组织(PETA)的诉讼请求10。与之类似,2023年8月18日,美国哥伦比亚地方法院对“泰勒诉美国版权局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认为“人类作者的身份必不可少”⑪,并基于“作品是(完全)由机器自主创作”这一法律事实⑫,最终作出驳回原告诉求,即认同涉案的AI图片不应予以版权注册的决定。
然而,笔者并不否认人类作者之于著作权法的“神圣”地位,上述将人工智能视为创作主体的观点显然有误。如上所述,无论产业界和学术界将ChatGTP描述得如何先进,无可否认的一点是,生成式AI仍未能取代人脑,其在实质上只能作为人类创作的辅助工具,因此AI生成的艺术品当然具有可版权性,而作者正是AI软件工具的开发者或使用者。所以,与其将生成式工具创作的艺术品称为“AI生成内容”,不如称之为“AI辅助生成内容”更为贴切。由此可见,人类创作和机器创作并非泾渭分明[15],尤其是在弱人工智能阶段的当下,AI创作的过程往往伴随着人类的意志,纯粹的AI创作只存在于乌托邦的想象。正如“Dreamwriter案”的法官所言,Dreamwriter软件自动运行并不等同于其“具有自我意识”,在主创团队投入巨大精力的情形下,将Dreamwriter软件视为创作的主体显然“与客观情况不符”。在上述泰勒案中,法官豪厄尔(Howel)也承认,如何考虑人工智能在艺术创作中的工具地位,是目前著作权法领域具有前沿性和挑战性的问题⑬。是故,从创作主体层面来否认AI生成物可版权性的观点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二)“算法唯一说”缺乏对创作流程的完整考量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AI生成内容是应用算法、规则和模板的结果,AI生成工具就相当于电子表格软件,AI创作就类似于将数据转换为表格,因此最终生成的结果具有唯一性,从而排除了用户个性发挥的余地[32-34]。在“AI文生图案”中,法院也提到了“机械性智力成果”的概念,然而却作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事实上,判断一项作品是否具有足够的创作空间,应根据具体的场景来进行分析,而非仅仅基于创作工具的抽象视角。例如,法院曾认定药品说明书缺乏自由创作的空间,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药品说明书的写作具有严格的法定格式规范⑭。法院也曾认定“错题本”缺乏个性发挥的空间,因为其仅涉及表格、简单文字和图标等简单要素的排列组合⑮。由此可见,在实际案例中机械性智力成果的判断是十分具体的,且权衡的重点在于“表达”,而非创作的“工具”。人工智能是一种先进的生产工具,但并不是作品本身;目前可以通过生成式AI创作的作品就有文本、图片、音频和视频等多种类型,以图片生成为例,生成式AI就有Stable Diffusion、Midjourney、DALL·E和文心一言等专业化和个性化程度不同的多款软件可供选择,由不同软件所生成的不同作品所留有的个性创作空间显然并不相同。
例如,在“黄某与上海包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中,涉案图片系原告利用数字化技术来根据演员陈乔恩的海报进行的二次创作,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涉案图片大体上只是进行了动漫化的风格转换,主体构图包括人物形象、元素布局等方面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⑯。这种AI创作的模式就类似于给一般照片加上滤镜,滤镜的类型都是预先设定且极为有限的,当然缺乏足够的个性创作空间。与其所不同,生成式AI明显具有更高的个性化程度,生成图片不但可以根据提示词定制,还可以不断修改,且这种修改可以细化到人物的眼镜、发型、眼睛和嘴唇等[35]。当然,否定观点仍会辩驳,在提示词和参数确定,且排除了随机数的因素以后,那么生成式AI的输出结果仍然是唯一的,因为确定性是算法的基础性特征,机器人作画本质上就是“高度程式化的过程”[34]。
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参数多达万亿且训练数据高达PB 量级的当下[36],上述观点的片面性将进一步凸显。具体而言,假如将AI生成的过程区分为输入端和输出端[37],那么输出端的结果固然是唯一且确定的(排除随机数因素),但大模型丰富的“语料库”却为输入端提供了无限可能。这就好比拍照摄影,拍摄前的场景、角度和人物的选择必然是多种多样的,这些元素的呈现方式既能体现摄影师的专业水准,当然也展现了摄影师的个性审美;在确定了这些要素以后,那么使用相同型号和参数的相机所拍摄出来的照片则必然是唯一的。然而,基于反对观点的逻辑(即只考虑输出端),摄影只是电子感光元件或胶片将光线转换为图像的过程,这个转换的过程同样是某种“算法、规则和模板的结果”,因此摄影缺乏个性选择的空间。显然,这与现实不符,因为早在1885年的“Burrow-Giles v. Sarony案”起,照片就普遍地被承认是作品的一种类型。在该案中,被告持类似观点,认为照片只是机械地再现某些物体的物理特征或轮廓;但法院却指出,原告根据自己的构思,为拍摄对象设计姿势、选择服装和通过调节光影来布置场景的行为,应被视为“智力创作”,可以成为版权法保护的对象⑰。总的来说,“算法唯一说”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该观点将视角局限在工具本身,而非创作的具体完整流程,导致最终忽略了人类之于人工智能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得出片面的结论。
四、行为层面:“直接产生”之讨论
(一)“直接”应解释为“主要贡献”而非“直接决定”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条第一款将创作行为限定为“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无疑,如何理解“直接”一词至关重要。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此处的“直接产生……作品”应被解释为“基于自由意志直接决定表达性要素的行为”[38],简言之,即作者对作品的表达形式应具有最终决定的能力(下文且称之为直接决定论)。对于AI研发者而言,其只是负责设计和训练了人工智能模型,但该模型具体会生成何种内容,研发者根本无法预测;对于AI使用者而言,用户的指示只是划定了AI生成的方向和范围,同样无法直接决定AI生成内容的表达性要素[38]。因此无论是AI的研发者或是使用者,都无法通过其自由意志来“直接”决定该AI创作的内容,故AI生成物的生成过程不能满足“创作”的定义,进而无法成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对于上述“AI生成表达无法预测”这一观点,笔者并无异议;然而,对于该学者之于“直接”一词的解释,笔者并不认同。一般而言,同一法律条文不同条款之间通常存在有机的关联。《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条第二款从反面的角度,排除了合作创作中仅提供辅助性工作的人员成为作者的可能。由此可见,在完整的语境之下,“直接”一词应指向“主要贡献”之意,换言之,即谁对作品的创作作出了主要贡献,那么谁就应该成为作品的作者,这与著作权法保护创作行为,而非物质保障等其他次要行为的宗旨相符[6]。然而,“直接决定论”似乎在“主要贡献”的释义基础上再引申出一层含义——“直接决定”作品表达要素的行为固然可以视为“主要贡献”,反之却未必。仍然以AI生成绘画为例,受限于人工智能的运行机制,用户固然无法“直接决定”每一个表达要素,如同一个提示词之下的人物构造往往神色各异;但是,这并不妨碍用户通过提示词的调整而使得AI绘画愈发“逼近”内心中对于具体艺术形象的想象。试问,当用户输入的提示词多达数百个且多次调整参数的情况下,用户的行为仍然不能称作“主要贡献”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关于“直接”一词的解释,域外立法以及国内司法实践皆对“主要贡献”之意作出了例证。英国现行版权法,即1988年《版权、外观设计及专利法案》于第9条第3款明确,“对于电脑生成的文字、戏剧、音乐或者艺术作品而言,作者应是对该作品创作进行必要安排的人”[39],“必要安排”意味着作者之于作品应是“不可或缺”或“主要贡献”之人。司法实践中对于“直接”的引用亦多采“主要贡献”之意⑱。例如,在“徐超与张亚卓等侵害著作权纠纷案”中,法院就将《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解释为作者是对作品作出实质性贡献的人⑲,此处强调的是“作出实质贡献”而非“决定表达形式”的人。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徐超案”还涉及了自然科学论文的作者认定问题。根据国家标准《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⑳,除了直接参与实验研究以及论文写作的人员可以列为作者外,选定研究课题和制订研究方案的人亦有资格成为作者。假如按照“直接决定论”的观点,那么论文的具体表达就是由直接参与实验研究(提供实验数据)以及论文撰写的人员所决定的,这部分研究人员当然是作者;至于选定研究课题和制订研究方案的人,由于只提供了论文方向指导、实验场所和经费等间接性帮助,因此不能进入作者之列。这种观点显然与现实所不符。社会分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40],科学研究的发展亦如此。鉴于现代自然科学已进入精尖化阶段,每一项重大突破的背后都必然蕴含着大量科研人员的努力,一篇自然科学的论文署名人数多达几十上百并不罕见,署名的作者并不见得都“直接决定”了论文的表达,但却必然对论文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此外,影视作品作为艺术创作“工业化”的典范,更是为“主要贡献”区别于“直接决定”的解释路径提供了绝佳例证。《著作权法》第十七条规定,著作权由负责统筹和募资的“制片人”取得,而非“编剧、导演、摄影”等“直接决定”作品表达形式的人取得,这条明显有别于一般著作归属原则的规定,只有从“主要贡献”的角度才可以理解——一部影视作品的顺利发行离不开制片人的资金保障、组织协调以及宣传发行,因此制片人作出了无可代替的“主要贡献”;而其中的导演、灯光、摄影等人则更类似于制片人的职工或受委托人,具有可替代性,对影视作品形成不了决定性的贡献,因此影视作品的著作权理应归属于制片人[11]。
(二)“直接决定论”的“主创—辅助”二分有悖于现代创作规律
基于社会化创作的情形越来越普遍,上述持有“直接决定论”观点的学者亦进行了针对性的补充论证。该学者认为,“直接决定”不意味着创作活动只能单独进行,共同创作也能满足该定义。例如,在辅助创作的场景中,最终决定是否采纳助手贡献的仍然是主创者,因此依然可以证明作品的表达性要素是由作者(即主创者)的自由意志所决定的[38]。问题是,在上述自然科学论文署名的情形中,尚能分清谁是“主创”,谁是“助手”吗?一般而言,在众多人员署名的情况下,论文的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往往会被视为最主要的作者,即所谓“主创者”。第一作者通常是青年学者,是论文工作的主要完成人,具体承担包括设计研究、获取分析数据以及论文初稿的撰写工作;通讯作者则是资历较深的学生导师或团队负责人,负责投稿发行等行政性工作[41]。此外,在实践中通讯作者往往还会对实验方案确定、论文撰写等具体工作起到把关和指导作用。假如按照本文主张的“主要贡献”方法来解释,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都对论文的形成以及最终发表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因此他们当然都是论文的作者。然而,如果依循上述“直接决定论”的“辅助—主创”标准,作者的认定似乎存在一定的困难。我们既可以认为第一作者是“主创”,因为通讯作者只是对作品的形成提供了意见,决定论文最终表达的仍然是第一作者;我们也可以认为通讯作者是“主创”,因为作为科研团队负责人,通讯作者的意见通常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第一作者或许只能根据通讯作者的指导(或要求)完成论文。由此可见,“直接决定论”对于创作的定义难以反映科技论文的创作规律。
不仅如此,在上述影视作品的例子中,又能分清谁是决定作品表达的“主创”吗?以制片人、导演、演员三者的关系为例,电影的剧本往往是由制片人决定的,而电影的具体拍摄,即演员怎么演,场景道具怎么布置,以及镜头、机位、灯光如何运用,则是由导演负责的,而演员也并非完全没有自我发挥的空间,如何具体呈现一个角色,演员个性发挥无疑至关重要[42]。演员刘敏涛就曾在专访中表示,演员就是要在角色的基础上即兴发挥,通过自己的“二度创作”,以填补剧本的空白[43]。可见,在三者的关系中,没有非此即彼的“谁”决定了作品的表达,三者在不同层次上,由宏观的剧情设定、中观的拍摄调度,再到微观的角色呈现,共同决定了该作品的表达性要素。当然,“直接决定论”会强调作品的最终决定者才是“主创”,依此来看,制片人似乎符合该标准。然而,此处又滋生了两个问题:第一,制片人掌握电影制作的最终话语权似乎只是一般的、理想的情形,现实中往往会出于各种原因,比如导演或演员的名气比较大,而不得不进行一定妥协。在相互妥协的现实情形中,还能识别谁最终决定了电影的表达吗?假如制片人完全按照导演的想法拍摄,那么导演是不是就成了该电影的唯一作者,从而享受专有著作权?这显然与《著作权法》的规定所不符,也违背了法律可预测性的基本原理。第二,电影的生产创作模式,更类似于AI创作的“宏观—微观”模式,而非上述作者试举的“主创—辅助”的模式[38]。在电影创作中,制片人显然并没有对作品的每一个表达都形成了具体的想法,制片人只有一个宏观的剧本,在剧本的框架内,导演被赋予了极大的个性发挥空间,这实质上就形成了与AI创作的共通之处——用户就像制片人,对AI下达的指令就相当于宏观的剧本,而AI则类似于导演,负责承担起整个剧组的工作,“拍摄”出合格的作品。如果AI用户无法成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者,那么制片人法定作者地位的法理又何在?基于此,“直接决定论”又再次作出了与我国《著作权法》相违背的推论。
总的而言,现代版权史被誉为是一部技术的进步史[44],因此对版权法的理解理应立足于动态发展的目光。假如用社会的发展形态来做类比[45],“直接决定论”对艺术创作的理解就相当于停留在农业时代,其眼中的创作是小规模、个体化的,即便是在合作创作的情形中,也必然是能够分清主次的“手工作坊模式”;事实上,现代艺术创作不但早已进入了社会化、规模化创作的工业信息时代,艺术创作的分工变得多元和复杂,而且随着生成式AI等先进人工智能工具的出现,现代艺术创作甚至开始步入“人机不分”的智能创作时代。有鉴于此,对于《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条第一款的理解,“主要贡献说”显然要比“直接决定论”更能适应智能时代的发展需求。
五、结语
本文立足于独创性概念的规范阐释,对复杂AI生成艺术品的可版性进行了全面论证。行文于此,仍有两个关联问题有待回应:一是著作权的归属问题。在软件开发者和软件使用者均对生成艺术品的创作作出了“主要贡献”的情况下,难以区分“真正”的作者。然而,这仅仅是理论上的难题。软件通常可以分为内部使用和公开使用两种类型,前者并不涉及用户,而后者往往会在协议中明确将生成艺术品的著作权赋予用户,因此现实中并不存在此类争议。法学是一门现实性的学科,应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纯粹假设性的问题缺乏研究意义。二是复杂生成场景的认定。所谓“术业有分工”,相较于法学研究者的“纸上谈兵”,对于人工智能领域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新场景和新应用,产业界和实务界理应具有更前沿、更具体和更准确的把握。因此,如何进一步区分简单和复杂的生成场景,并形成AI生成作品认定的“层进式”路径,应留待实践作深入探索。
参考文献:
[1] 王春晓. AI著作权首案宣判,判赔500元[EB/OL]. (2023-12-08)[2024-01-26]. https://mp.weixin.qq.com/s/PjPfoFw5q4JuIm7lO4oZSQ.
[2] 李汶龙,郭佳仪. GenAI版权分析需超越基础概念框架:评北互/李昀锴案[EB/OL]. (2023-12-04)[2024-01-26]. https://mp.weixin.qq.com/s/cycYiC1Ze9owHi1TXL_7rg.
[3] 李绪青.“AI文生图”著作权案一审生效[EB/OL]. (2023-12-27)[2024-01-26]. https://mp.weixin.qq.com/s/AzhPYHqLCCXiWwL2AuKjnw.
[4] 伯恩·魏德士. 法理学[M]. 丁小春,等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5] 冯晓青. 我国著作权客体制度之重塑:作品内涵、分类及立法创新[J]. 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2,9(1):80⁃96.
[6] 吴汉东. 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著作权法之问[J]. 中外法学,2020,32(3):653⁃673.
[7] 吴汉东. 知识产权法[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
[8] 熊文聪. 作品“独创性”概念的法经济分析[J]. 交大法学,2015(4):130⁃139.
[9] 杨利华. 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问题探究[J].现代法学,2021,43(4):102⁃114.
[10] 何怀文. 中国著作权法判例综述与规范解释[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11] 黄薇,王雷鸣.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导读与释义[M].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
[12] 魏干. 法学概念:离开实践就是空中楼阁[N]. 检察日报,2017-08-17(3).
[13] 丁文杰. 通用人工智能视野下著作权法的逻辑回归——从“工具论”到“贡献论”[J].东方法学,2023(5):94⁃105.
[14] 孙正樑.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问题探析[J]. 清华法学,2019,13(6):190⁃204.
[15] 丁晓东. 著作权的解构与重构:人工智能作品法律保护的法理反思[J]. 法制与社会发展,2023,29(5):109⁃127.
[16] 喻国明,刘彧晗. 理解生成式AI:对一个互联网发展史上标志性节点的审视[J]. 传媒观察,2023(9):36⁃44.
[17] 徐思彦. 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演进及产业机遇[J]. 人工智能,2023(4):43⁃50.
[18] 郭鹏,李展鹏. 预测分析技术背景下的个人信息行政保护新机制建构[J]. 学术研究,2023(7):77⁃84.
[19] 曹建峰. 迈向可信AI: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治理挑战及应对[J].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3,38(4):28⁃42.
[20] 李翔,旷银. ChatGPT类人工智能及其生成物的刑法思考[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78⁃91.
[21] 徐伟. 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法律地位及其责任——以ChatGPT为例[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3,41(4):69⁃80.
[22] 吴昊天. 人工智能创作物的独创性与保护策略——以“ChatGPT”为例[J]. 科技与法律(中英文),2023(3):76⁃86.
[23] 於兴中,郑戈,丁晓东.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法律的六大议题:以ChatGPT为例[J]. 中国法律评论,2023(2):1⁃20.
[24] 文思敏. 梵高三幅画作现身纽约拍场总计近10亿元成交[EB/OL]. (2021-11-23)[2024-01-24]. https://mini.caixin.com/2021-11-23/101808787.html.
[25] 王迁. ChatGPT生成的内容受著作权法保护吗?[J].探索与争鸣,2023(3):17⁃20.
[26] 吴汉东,刘鑫.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知识产权法律因应与制度创新[J]. 科技与法律(中英文),2024(1):1⁃10.
[27] 刘宪权. 人工智能时代的“内忧”“外患”与刑事责任[J]. 东方法学,2018(1):134⁃142.
[28] 丛立先,李泳霖. 生成式AI的作品认定与版权归属——以ChatGPT的作品应用场景为例[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171⁃181.
[29] 李晓宇.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与权利分配刍议[J]. 电子知识产权,2018(6):31⁃43.
[30] 许明月,谭玲. 论人工智能创作物的邻接权保护——理论证成与制度安排[J]. 比较法研究,2018(6):42⁃54.
[31] 刘洪华. 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资格的否定及其法律规制构想[J].北方法学,2019,13(4):56⁃66.
[32] 陈晨. 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问题——以ChatGPT生成内容为例[J].科技与出版,2023(6):98⁃106.
[33] 陈虎. 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以我国著作权法语境中的独创性为中心进行考察[J]. 情报杂志,2020,39(5):128⁃153.
[34] 王迁. 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35(5):148⁃155.
[35] 崔国斌.人工智能生成物中用户的独创性贡献[EB/OL]. (2024-01-05)[2024-01-26]. https://mp.weixin.qq.com/s/nNV2r9msxzujbZ5R-vosuQ.
[36] 车万翔,窦志成,冯岩松,等. 大模型时代的自然语言处理:挑战、机遇与发展[J]. 中国科学:信息科学,2023,53(9):1645⁃1687.
[37] 郑飞,夏晨斌.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著作权困境与制度应对——以ChatGPT和文心一言为例[J]. 科技与法律(中英文),2023(5):86⁃96.
[38] 王迁. 再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J]. 政法论坛,2023,41(4):16⁃33.
[39] 《十二国著作权法》翻译组. 十二国著作权法[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40] 赵磊. 澄清质疑共产主义的三个理论困惑[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4):34⁃43.
[41] What is a Corresponding Author?[EB/OL]. (2020-03-24)[2024-01-26]. https://scientific-publishing.webshop.elsevier.com/publication-recognition/what-corresponding-author/.
[42] 谈谈制片人、出品人、导演、监制都是怎样的存在[EB/OL]. (2021-03-16)[2024-01-26].https://mp.weixin.qq.com/s/_zyDY6dvGU0W7M5kmHzmEw.
[43] 韦娟,刘敏涛. 二度创作是做演员最过瘾的地方[EB/OL]. (2021-03-16)[2024-01-26]. http://m.xinhuanet.com/2017⁃03/06/c_1120573013.htm.
[44] 黄汇,黄杰. 人工智能生成物被视为作品保护的合理性[J].江西社会科学,2019,39(2):33⁃42.
[45] 孙伟平.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域中的“智能社会”[J]. 哲学分析,2020,11(6):4⁃16.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Artworks Generated by Complex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Copyright Law
Guo Penga,b, Li Zhanpenga,b
(a.Law School; b.Intellectual Property School,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The current judicial practice in China indicates that only complexly generated artworks are copyrightable. However, due to the limit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originality, the judicial authorities have not formed a logical argumentation on this issue, which has led to disputes.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the complex generated artwork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follow the norm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originality to respond to the controversy by dividing it into three levels, namely, objective, subjective and behavioral, with a view to contributing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pyright governance of AI.
Keywords: generative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Copyright Law; copyrightability; originality; ChatG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