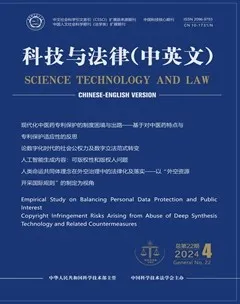比较听证:公共数据运营权分配的制度重塑
摘 要:公共数据运营权分配的地方实践呈现行政指定、申请评估、竞价拍卖及招投标等模式的多元并进格局,但存在数据垄断风险和程序封闭的困境。实践路径分歧缘于公共数据市场化开发应用与安全风险的内在张力、公共数据权属不清等制度因素。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应当超越数据界权,以公共数据资源分配的程序正义构建公共数据的开放利用秩序。比较听证制度是基于交往行为的理性建构过程,能够为利益相关方提供“理想的沟通情境”,实现程序正义,缓解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内在张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特许经营属性也能实现与比较听证制度的耦合。比较听证嵌入公共数据运营权分配的体系化建构,需要确立竞争性授权原则,保障竞争的公平公正;完善比较听证的制度构造,科学设置市场准入资格、听证程序、比较标准及效率补偿机制;以监管沙盒制度和可信数据治理技术消解比较听证引入公共数据运营权分配的制度困境。
关键词: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比较听证;数据安全;分配正义
中图分类号:D 9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9783(2024)04⁃0040⁃11
数据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当前数据要素市场90%的可用数据都被公权机构掌握[1],公共数据的开放利用成为推动数字产业发展的关键。然而,我国公共数据开放利用存在数据可用性低、数据质量差、数据开放难以持续及开放利用成效不高等问题[2],阻滞公共数据要素价值的释放。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提出,“开展政府数据授权运营试点,鼓励第三方深化对公共数据的挖掘利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正式成为一项国家顶层制度设计。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是指,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引入市场主体,将非结构化的公共数据资源加工处理成可用的数据产品或服务,并进行市场交易的行为。授权运营旨在引入市场主体开发数据产品,实现公共数据赋能经济发展和提高公共治理水平的目的。从政府角度看,授权运营是政府将其管理控制的公共数据资源向市场主体进行分配的过程,也即向市场主体分配公共数据运营权。由于公共数据内生于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承载公共价值[3],政府有义务保障公共数据资源的分配正义。从市场主体角度看,被授权单位是实施数据加工处理行为的主体,决定了数据产品或服务的品质,影响公共数据价值释放质效。《开放数据晴雨表》报告也指出,市场中介是利用公共数据创造商业价值、改善公共治理的中坚力量[4],政府应当寻求以适当的方式配置数据资源,与社会组织合作利用公共数据。
在国家政策推动下,地方积极探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新方式,形成了多元化的制度设计。但遗憾的是,当前学界主要围绕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性质、地位、权属等问题展开讨论,尚未能给出完善的公共数据资源分配方案。基于此,本文选取24个不同程度开展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省级行政区为研究对象1,以其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相关规范性文件和授权运营实践为样本,对公共数据运营权分配的实践面貌展开观察,在对实践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公共数据运营权分配的理论方案。
一、公共数据运营权分配的实践面相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数据二十条》)提出要完善数据要素配置机制,释放公共数据内在价值。对24个省级行政区运营实践的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对公共数据运营权的分配呈现多元并进的制度格局,形成了行政指定、申请评估、竞价拍卖及招投标等不同分配模式。
(一)行政指定模式
这是指政府以行政命令直接指定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单位。地方政府在整合本地数据公司的基础上,组建国有大数据集团,并授予其公共数据经营权,不涉及招标、评估等环节,程序较为简单便捷。贵州省、河南省、上海市以及成都市等地莫不采取该模式。比如,2014年贵州省人民政府率先批准成立云上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实施数据汇集、共享和开放等运营活动[5],河南、上海等地也相继组建数据集团,开展公共数据开发交易活动。从制度产生逻辑上看,该模式是国有资产增值保值与数据安全保护双重因素相互叠加的结果。譬如成都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内在机理就蕴藏于这一制度逻辑中[6]。一方面,地方政府将公共数据作为国有资产,通过市场化运营获取收益,并将运营收入按比例上缴地方财政,实现公共数据从“资源”到“财政”的跃升。另一方面,数据处理行为可能会危害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公共数据授权运营需要确保重要数据安全可控[7]。政府直接授予国有大数据集团运营权,能够通过人事管理管控数据安全风险。目前一些地方数据运营机构的负责人并非企业化的职业经理人,普遍采用政府直管模式,由大数据局直接委派或抽调人员兼任 [8]。进一步地,政府可以通过外派人员的方式,参与公共数据产品开发运营管理,控制数据开发交易风险。
(二)申请评估模式
基本构造表现为“公告—申请—评估—授权”:(1)政府发布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公告,明确申请授权运营的基本条件、申请材料、申报期限等事项;(2)市场主体在规定期限内提交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申请;(3)数据主管部门组织专家组对授权运营可行性进行评估;(4)核实申请单位是否符合安全条件、信用条件等要求后作出授权运营决定。浙江省在制度建构和运营实践方面最为典型,已经实现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省市两级全覆盖,且均采取申请评估模式授权运营公共数据。比如,《温州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实施细则(试行)》规定的授权程序为:“发布公告—提交申请—材料预审—专家审查—终审—社会公开—授权备案”。2023年10月20日,温州市已完成公共信用、卫生健康、金融服务领域首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工作2。相较于行政指定模式,以“申请—评估”为核心的制度构造,能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让更多的潜在市场主体参与到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活动中,有助于优化公共数据资源配置。此外,申请评估模式的制度优势还体现在嵌入专家咨询制度,增强政府的决策理性。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涉及诸多技术性事项,比如,区块链、隐私计算等数据安全保护技术,算法、大模型等数据开发程序,面对高度复杂的技术性难题,政府官员由于缺乏专业知识难以作出准确判断,而行业专家对于纯粹技术性知识具有深入研究,具备专业知识优势。因此,在公共数据运营权分配中借助专家理性作出决策,可以有效增加行政决定的合理性、正当性。
(三)竞价拍卖模式
这是指转让方发布竞价公告,明确竞价标的、竞价条件及竞价期限等竞拍事项,竞买人出价竞拍,并由出价最高者获得公共数据经营权。“衡阳市政务数据资源和智慧城市特许经营权出让项目”是国内首例公共数据公开竞拍交易项目。2023年11月10日,衡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交易公告,以网上竞价方式出让衡阳市政务数据资源和智慧城市特许经营权,起始价为1 802 441 200元,竞买人缴纳保证金后可在交易系统出价竞拍3。竞价拍卖采取“价格优先”原则,由出价最高者获得公共数据运营权,是一种遵循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能为政府提供充分的“数据财政”激励。但遗憾的是,由于当前公共数据权属不清、数据使用的合法性界限存在争议,2023年11月15日,衡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再次发布公告,暂停“衡阳市政务数据资源和智慧城市特许经营权出让项目”交易活动4。竞价拍卖模式也遭遇诸多理论批判。比如,有学者指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应警惕单纯逐利冲动,授权运营制度的具体设计要消解公益性与营利性的紧张关系,让公共数据资产惠及广大社会公众[9]。
(四)招投标模式
招投标是政府采购的主要方式之一,其制度构造为“发布招标公告—市场主体投标—招标单位评标—确定授权运营单位”。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中,济南市、北京市及海南省等都曾以招投标方式采购公共数据运营服务。譬如,2023年8月18日,济南市大数据局发布《济南市大数据局公共数据治理服务公开招标公告》,采购数据治理运营、标准地址库建设、法人库及应用、数据直通车建设、社会数据采购及电子证照系统升级等六类公共数据治理服务5。招投标型授权运营模式的逻辑预设在于:一方面,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释放公共数据资源的内在价值,因为竞争能够提高两种效率——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10];另一方面,以标准化的政府采购合同明确数据产品质量、价格、数据安全保护义务、违约责任等事项,建构起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约束机制。招投标制度有效运行的前提是对评价标准科学赋权,在对投标单位评估的基础上择优授权。必要的信息构成参与者认知和理解自身利益的基础[11],政府在招投标公告中通常发布详细的评标标准,保障招投标程序的公开透明。
二、对公共数据运营权分配实践的反思
各地均以公共数据的市场化开发利用为目的开展授权运营实践,但是地方政府对如何授权明显存在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在同一制度目标下,缘何形成不同的制度形态?
(一)公共数据运营权分配方式迥异的成因
1.市场化开发应用与数据安全保护之间的张力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初衷是提高公共数据市场化开发应用水平,释放数据红利,实现公共数据由“资源”到“资产”的跃升。然而,公共数据的汇聚、传输、开放、开发及交易等流通处理行为,会对国家安全、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带来安全风险。《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以下简称《数据安全法》)第四十条规定,国家机关委托他人存储、加工政务数据,应当经过严格的批准程序,并应当监督受托方履行相应的数据安全保护义务。《数据二十条》也要求,强化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把安全贯穿数据供给、流通、使用全过程,鼓励在保护个人隐私和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推进实施公共数据确权授权机制。在中央顶层设计的推动下,我国形成了包括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在内的数据安全保障规范体系,这给予地方政府很强的“安全激励”。公共数据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和价值载体,也具有经济价值,可以扩大政府财政收入和促进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数据安全法》在构建数据安全风险管控体系时,也规定要“促进数据开发利用”。因此,地方政府具有实现数据经济价值的动力,甚至扩大数据财政来源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实施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主要动因。
地方公共数据运营权分配路径的分歧,是公共数据风险防控和经济利益激励双重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如上所述,在行政指定模式下,被授权单位不仅是政府以行政命令直接指定的,而且由政府直接批准成立,政府或国资委代表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12]。也就是说,被授权的国有数据集团是政府在数据要素市场的代理人,地方政府通过对被授权企业的行政管理实现管控数据安全风险的目的。进一步地,政府排除市场机制,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直接授权国有数据集团运营公共数据,强化政府在公共数据资源配置中的管理控制能力,避免纯粹市场化资源配置带来的非法爬取、贩卖、泄露数据等负外部性问题,并且国有企业运营收益也可以为政府带来财政收益。申请评估模式和招投标模式是地方政府平衡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安全风险与经济价值的尝试,尽管二者的程序构造存在差异,但都试图融合资源配置的行政与市场两种手段。一方面,政府给予市场主体参与授权竞争的机会,发挥市场竞争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功能,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政府掌握作出最终授权决定的权力,避免纯粹市场竞争带来的负外部性。与之不同的是,竞价拍卖模式主要受数据财政利益的激励,采取功能主义建构模式,将法律视为政治机器的工具[13],充分发挥供求、价格、竞争等市场机制的作用,由出价最高者获得公共数据运营权,保障政府数据财政收益最大化。然而,该模式在实现公共数据资源经济价值的过程中忽视了数据的安全保护问题,安全利益让位于经济利益,完全的市场化竞争机制容易造成安全风险积聚,市场的负外部性问题也无法由市场自行消解。
2.公共数据权属不清下的制度实践
当前我国中央立法尚未对数据权属作出界定,《数据安全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均回避了数据确权问题,各地对授权运营的探索是在公共数据权属不清背景下展开的。有些地区认为公共数据属于国有财产,归国家所有,如《福建省政务数据管理办法》第三条、《重庆市政务数据资源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贵州省政务信息数据采集应用暂行办法》第七条等。在此进路下,一些地区认为公共数据资源既然属于国有财产,自然由政府代为行使所有权,可以直接授权国有企业开发运营。有些观点更进一步指出,国家所有权的性质是一种私法上的所有权,同私人所有权的权利性质和权能构造具有一致性,国家对国有财产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能[14]。这进一步扩充了政府自由处置公共数据的制度空间,强化了经济利益对政府的激励,从而产生竞价拍卖等单纯逐利式的公共数据资源分配方式。《衡阳市政务数据共享开放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二条规定政务数据权属归国家所有,在数据财政的激励下,衡阳市突破该《办法》的授权规定,采取拍卖方式分配公共数据资源。也有一些观点认为,公共数据属于公共资源、公共财产[15],具有公物属性,应当按照公共物品的特别使用机制来构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制度。因此,部分地区采取招投标或申请评估方式也具有理论支撑。
(二)对地方实践的进一步反思
上述分析表明,竞价拍卖模式不是有效的公共数据资源配置方式。遗憾的是,其余三种公共数据运营权分配模式也存在难以避免的制度困境,无法为公共数据资源的分配提供有效制度支撑。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目的是引入市场主体提高公共数据开发利用效率,这就要求授权运营活动不能是内部式的、封闭式的,应当具有开放性、竞争性[16],否则授权运营容易异化为圈占和垄断数据的手段,最终损害公共价值的实现。然而,行政指定模式是政府以行政权强力介入公共数据资源配置的产物,政府直接授权的政策偏好排除了对潜在市场竞争主体的比较评估,相关竞争者无法进入市场,造成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数据鸿沟”,形成“开放但垄断”的数据利用秩序[17],这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关切。申请评估模式引入专家咨询制度,借助专家理性对企业的运营能力进行评估。但是在授权评估中,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简单,难以为专家评估提供全面的事实知识,限制了专家理性的发挥。譬如,杭州市《关于首批领域征集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主体的通告》规定的七项申请材料中,并不包含企业的技术资质、专利数量和项目团队实力等材料,影响了专家评估的准确性。招投标制度往往将竞标价格作为主要考量因素,忽视了对企业数据风险防控能力和数据价值挖掘潜力的评估,扭曲了竞标制度的评价标准。譬如,在“济南市大数据局公共数据治理服务公开招标”项目的评标标准中,价格因素占有10分的权重,而对技术服务能力所赋权重普遍偏低,甚至运营项目组织管理方案仅占5分的权重6。更重要的是,不同于公共数据普遍开放对社会主体带来的反射利益,能否获得行政授权关涉申请主体的公平竞争权和重大经济利益。然而,公共数据运营权配置方式的封闭性,导致申请授权企业难以参与到政府的授权程序就自身比较优势举证证明和质证反驳,评估结果不是在各方理性沟通的前提下作出的。
三、比较听证与公共数据运营权分配制度的耦合
数字时代的行政法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在合法性的基础上追求最佳性[18],在数字经济语境下,实现公共数据资源的分配正义成为行政法的重大理论命题。分配正义的实现建立在程序正义基础之上,也主要是指公共数据资源分配的程序正义,起源于英美法系的比较听证制度能够实现与公共数据运营权分配的耦合。
(一)逻辑起点:公共数据资源分配的程序正义
理论和实践中对公共数据的开发利用存在权属规制路径和行为规制路径两种模式。授权运营以公共数据的社会化开发利用为旨归,“数据权属明晰”并不构成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必要前提[19]。相反,数据确权带来的数据锁定效应和数据垄断结构对公平获取利用数据极为不利[20]。国家的任务在于以公共数据运营权分配的程序正义为中心,构建并维护一种公共数据资源的配置和利用秩序,促进授权运营的公平性、开放性及效益性[21]。具言之:
公共数据是政府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及依法履行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企事业单位,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或收集的数据。公共数据具有依附性的特征,产生并服务于公共职权的行使或公共职责的履行,公共数据开放利用要关注公共数据所处的法律和社会关系[3]。公共数据依附于公共管理或服务职权,产生过程具有公共性,属于公共资源、公共财产,原则上应当以开放为原则,向社会公众平等普遍开放[22],满足公民生产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但由于高价值公共数据往往内含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信息,数据的普遍开放会增加安全风险。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就是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将不宜直接开放的公共数据授予特定市场主体,由其垄断经营并向社会提供数据产品或服务。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是公共数据从普遍使用到特别使用的转变,而这一过程必然首先遭遇分配正义的问题,即什么样的公共数据运营权分配方式才是符合正义要求的。这与企业数据不同,企业数据是企业在生产经营中产生并由其控制的生产资料,具有私有财产的属性,企业数据授权应用遵循私法领域中的意思自治原则。相反,公共数据属于公共资源,政府对公共数据运营权的分配理应遵循正义原则,而不能当作政府私产自由处置。
公共数据运营权分配正义的关键问题是确立正义的标准,即正义的一种应然状态。当前关于分配正义的诸种理论处于相互诘责的辩护与棘手的理论建构困扰之中,实际上对分配正义的研究可以分为结果正义与程序正义两种理论路径。结果正义承继“给予每人以其应得的东西”之分配正义理念,主张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23],对于什么是所应得东西的判断标准,则存在柏拉图的个人美德、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阿玛蒂亚·森的自由及阿奎那的习惯等理论主张。结果正义的实现往往需要由一个具有超然地位、超越所有利益之上的力量来主持分配,分配的最终状态是否符合正义要求就取决于这个超然力量的道德能力[24]。然而,从结果正义的理论主张来看,在公共数据运营权分配中,政府不仅无法对高度抽象的评价标准作出准确判断,还因为数据财政对政府的经济激励使其无法处于超然地位,甚至存在“政企合谋”的负外部性问题,更遑论实现公共数据资源的分配正义。相反,程序正义排斥美德、自由等价值前提,关注的重点是社会利益分配的过程,即以何种程序、形式、规则进行利益分配。罗尔斯主张,可以把正义原则理解成理性的人们所作的选择,正义观可以以这种方式得到解释和辩护[25]。公平机会原则的作用是要确保合作体系成为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其实践优点,即它不再需要追溯无数种的特殊环境及具体个人会不断变化的相对地位[25]。相较于结果正义的乌托邦式理论模型,程序正义是一种“看得见的”理想形式。也就是说,公共数据运营权分配正义的实现需要建构一种科学的授权程序,通过公共数据运营权市场化配置过程的正义实现分配正义。
(二)比较听证的制度价值
公共数据运营权分配制度构建的重点是探寻一种正当的分配程序。如果将观察的视野放到域外法治实践中,可以发现起源于英美法系的比较听证制度是实现公共数据运营权分配正义的理想模式。比较听证是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用于分配广播运营权的制度,当两个以上市场主体申请使用同一广播设施或会相互产生干扰的设备时,他们的申请被认为是相互排斥的,FCC不能简单地批准某一个申请,而必须对所有此类申请进行比较听证,在相互排斥的申请者中选择最合适的许可人[26]。在“Ashbacker v. FCC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正式确立了比较听证程序,规定FCC应当为竞争性许可举行比较听证,使每个申请者都有机会证明自己能比竞争对手更好地为社会提供服务,在审查证据并考量申请者的每一个实质性差异后将运营权授予最具竞争力的申请者[27]。
1.比较听证的程序正义价值
比较听证制度的核心是允许相互竞争的申请者围绕比较标准举证质证,就支持或反对的意见展开辩论,在理性沟通的基础上为行政决定提供事实材料和法理支撑。比较听证的过程也是政府与利益相关者对话交往的过程,行为者通过行为语境寻求沟通,以便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把他们的行为计划和行为协调起来[28]。正义原则并非建立在道德推理等抽象价值基础之上,而是由利益相关者在公平对话基础上,通过沟通、协商、交流、谈判等交往行为实现的[29]。交往理性使不同的参与者克服掉他们最初的那些纯粹主观观念,论证话语在不受强制的前提下达成共识,并为了共同的合理信念而确立起客观世界的同一性以及生活语境的主体间性[28]。比较听证制度的实施为利益相关者提供了理性交往的平台和理想的沟通情境,在比较听证中利益相关者可以了解拟议的行政行动的理由和支持这些理由的假设策略,有机会检验和反驳这些理由和事实,并有机会在政府采取行动之前陈述和解释自己的立场[30]。简言之,比较听证制度通过为相互竞争的申请者提供理性沟通、彼此辩论的机会[31],塑造公平的竞争程序,保障分配正义的实现。
2.比较听证制度有利于缓解市场化运营与数据风险防控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比较听证程序中,每个申请人都有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可以就自身在公共数据场景化运营方案,区块链、隐私计算及数据沙箱等技术嵌入数据安全保护的策略等优势举证质证,就对方质疑作出自我辩护。具体来说,在比较评估程序中申请授权的市场主体可以在证明自身具备基本数据安全保护条件的基础上,进一步就自身的隐私设计能力等技术资质证明、数据安全保护认证、算法设计中的隐私保护技术方案等技术优势提交证明材料,由行政机关、中立的第三方机构结合公共数据开放利用场景来权衡每个竞争者的比较优势,选择合适的授权对象,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起始端管控市场化运营带来的安全风险。
3.比较听证的制度不足
对比较听证制度价值的理论分析,也应当认识到其存在一定不足:(1)仍旧无法完全消除公共数据开发利用的安全风险。公共数据授权运营面临“决策于未知”的难题,即行政机关尝试通过对被授权单位现有数据安全保护能力的审查,为未来公共数据市场化运营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然而,网络攻防技术迭代、数据逆向工程策略更新都表明数据安全风险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风险的长期存在和不可预知构成了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现实环境。行政机关对“未来安全”的判断是基于当前证据材料的逻辑推理,具有暂时性、主观性,无法对授权运营风险进行全面客观分析,仅仅依靠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起始端的严格管控,难以完全消解授权运营的安全风险。从申请人角度看,为了获得公共数据运营权,在比较听证中申请人可能会采取策略性行动[31],在获得运营权后不履行数据安全保护承诺,进一步造成数据安全风险的累积。(2)实施效率不高。由于政府需要在举证质证、交叉辩论、比较评估的基础上作出行政授权决定,比较听证嵌入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也降低了行政授权的效率。比如,在FCC对比较听证的实施中,有批评者指出,听证和裁决程序的低效率和复杂性会推迟电视台建成并投入为公众服务的时间[26],比较听证制度成为一种成本昂贵的正义。需要指出的是,对比较听证制度的批评主要停留在制度的技术操作层面,难以克减其程序正义价值,通过对比较听证制度构造的调试和保障体系的建立,可以实现与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制度的耦合。
(三)引入比较听证的制度容许性
比较听证是在两个以上相互竞争的申请者中配置权利的制度,适用于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十四五”规划创造性提出了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概念,但尚未明确其法律属性,能否引入比较听证,还有待于对其性质作进一步分析。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属于行政许可中的特许经营,具有明显的数量限制。我国公共数据供给机制包括公共数据开放和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前者是一种非排他性的公共数据供给方式,任何社会主体都能够自由获取;而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开发利用的是受限开放数据,非经行政机关授权任何企业不得开展运营服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第二条对行政许可的定义。但不同于一般行政许可,公共数据授权运营需要政府与运营单位签订特许经营协议,具备“行政授权+运营协议”的双阶特征,这将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与一般行政许可区分开来。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排他性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公共政策导致的排他性。授权运营的数据是不宜直接向社会开放的受限开放数据,该类数据的大规模流动可能会侵害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如若对授权运营主体不设置数量限制,会增加数据汇集流通中的安全风险。实践中各地也都将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作为受限许可,限定授权运营单位数量,比如成都市以及上海市、贵州省等地都授权大数据集团作为唯一运营单位,浙江省也规定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实施总量控制原则。其次,实施排他性授权是出于提高市场化经营效率的考量[32]。公共数据开发利用需要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域进行,引入过多市场主体会造成运营设施的重复建设,存在众多相互竞争的运营单位是没有效率的。再次,原始公共数据以非结构化的形式存在,对数据进行自然语言处理、数据建模、关联分析需要占用大量信息资源,在授权运营域算力有限的前提下,数据的开发利用会产生拥挤效应[33],从而需要限制许可数量。
上述分析表明,当两个以上市场主体就同一项目申请授权运营时,申请人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政府不能随意批准任一申请人的申请,对彼此存在竞争关系的申请者进行比较听证具有现实必要性。实际上,《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七条也规定,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在作出许可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中蕴含的公共利益及申请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属于该条规定的“重大利益关系”。因此,将比较听证引入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具有制度容许性。
四、比较听证嵌入公共数据运营权分配的体系化建构
承前所述,比较听证制度是在相互竞争的市场主体中选择适当申请人的制度,能够有效实现公共数据资源的分配正义,将其引入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具有正当性和制度容许性。在我国数据法治环境中,引入比较听证制度还应当做好以下三方面制度设计:
(一)前提条件:竞争性授权
比较听证适用的前提是存在相互竞争的市场主体,也就是说存在两个以上公共数据运营权申请主体,而政府不能同时满足各申请人的授权需求,也只有存在多个竞争主体政府才有必要对申请者进行比较评估,择优授权。在比较评估程序中,申请者为获得公共数据运营权,应当举证证明自身的比较优势,这可以激励参与竞争的市场主体以符合分配效率和生产效率的条件提供商品或服务,政府预先设定行政许可的目的不是为了限制市场竞争,而是确保所有在市场上竞争的企业或产品能够满足某些最低的标准[34]。从制度运行的底层逻辑来看,竞争性授权是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制度属性的要求。如上所述,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属于行政许可中的特许经营,公共特许经营权分配理论主张,公平竞争是特许经营分配的关键要求,这可以激励在公众之间建立一种以守法获益为目标的竞争,它使公众意识到,若自己主动、及早依法行事,则可获得多于他人的利益[35],而这种竞争可以有效提高公共数据运营品质,最终实现社会福祉的提升和经济总量的增加。
现阶段,竞争性授权秩序的构建首先应当为各种所有制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机会,取消对被授权运营企业性质的限制,保障竞争的公平性、开放性。公共数据运营权分配正义的实现以竞争机会的公平为前提。罗尔斯指出,正义的实现依系于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否则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们觉得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感觉就是对的,即使他们能从那些占据这些职位的人那里获利[36]。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是对公共资源的配置,被授权单位是开发处理行为的直接主体,对被授权单位设置一定的市场准入资格具有正当性,但是这不是政府实施垄断性授权的理论依据。遗憾的是,地方政府普遍存在将运营权授予国有企业的决策偏好,而将私有制企业排除在授权范围外。比如,北京市《关于推进北京市金融公共数据专区建设的意见》第七条规定,经市政府同意,由市经济和信息化部门授权具有公益公信力、技术能力和金融资源优势的市属国有企业对专区及金融公共数据进行运营。行政机关行使公权力、作出行政行为,应当符合目的正当性要求,不得将与权力行使目的不相关的法律或事实因素纳入考量。地方政府的决策偏好在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之间造成不公平竞争状态和数据垄断结构,而相较于市场的垄断结构,公平竞争更能够为企业带来创新激励,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37]。因此,在比较听证程序中,政府应当遵循公平竞争原则,平等对待参与授权竞争的市场主体,不能因市场主体性质不同而采取差异化评估标准,更不能因竞争主体是国有企业而直接授予运营权[16]。
另一方面,应当建立公平竞争审查机制,监督政府以行政权力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基于国有企业在我国的特殊地位,政府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中存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双重角色,仅靠政府道德自觉难以消除行政垄断风险。《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第二条规定,行政机关制定有关市场准入和退出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政策措施时,应当进行公平竞争审查,评估对市场竞争的影响,防止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为此,行政机关应当完善内部审查和外部监督机制,通过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公开听证会、专家咨询等形式广泛征求意见,营造公平竞争的数据要素市场环境。
(二)制度本体:比较听证的构造
在明确比较听证适用的前提条件后,应当结合公共数据运营权分配制度特征,对比较听证展开制度续造。易言之,比较听证的制度设计既要有效发挥优化公共数据资源配置,实现分配正义的制度价值,也要保障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比较听证的时间成本。
1.制定、公布及审查市场准入资格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客体是受限开放数据,相较于无条件开放类公共数据存在更高的安全风险,因此公共数据运营权的分配无法像无条件开放类公共数据那样向市场主体普遍开放。政府应当事先制定市场准入资格并向社会公布,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提供基本的数据安全保护条件。但是,政府在确定市场准入条件时不宜严苛,更不能设定歧视性市场准入条件,保障授权竞争的公平性、开放性、有效性。政府机关在收到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申请后,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是否完备齐全、是否符合规定形式进行审查,对于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的政府机关应当履行指导义务,允许当事人补充修改申请材料。在申请期间届满后,政府应当对申请主体是否具备市场准入资格进行审查,判断申请者是否符合基本的市场准入条件。
2.启动、举行比较听证
比较听证程序的启动包括依职权启动和依申请启动两种方式,不应由政府垄断启动权,否则行政授权活动就可能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运行环境中。政府机关经依法审查,存在两个以上符合市场准入资格申请主体时,应当给予各申请人表达意见的机会,不得未经听证径行作出行政许可决定。政府应当依职权主动启动比较听证程序,如果怠于听证,行政相对人也有权申请举行比较听证。在确定听证后,应当及时发布听证公告,明确听证的时间、地点等事项,告知相关利益主体申请参加听证,并进行听证人员登记。比较听证是相对人的权利,因此在比较听证过程中,申请人可以放弃参加听证的机会。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涉及数源单位、授权单位、市场主体等多方利益主体,公共数据的价值释放也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因此政府在组织比较听证中应当有效地组织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听证程序,关照多方法律关系,公平合理地考虑各方面的利益需求。需要强调的是,在听证员的选择上应当发挥行业协会在比较听证中的专业作用。在既往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中存在忽视行业组织作用的倾向,实际上行业协会不仅具备数据安全风险防控等专业知识,也能够从经济转型升级的视角提出数据场景化应用建议,可以发挥专家咨询建议功能。民主程序使得议题和建议、信息和理由的自由流动成为可能[38],听证过程的本质是行政机关与当事人之间信息的互换与整合,通过说理论证影响最终授权决定的作出。比较听证程序应当为当事人提供一种“理想的沟通情境”:(1)潜在利益相关者均有同等参与对话论证的权利,任何人均可发表支持或反对意见,可以提出疑问或反驳质疑;(2)任何参与对话者均在提出解释、主张、建议和论证时不受任何压制;(3)任何对话参与者都有平等的权利实施表达行为;(4)任何对话参与者都有平等的权利实施自我辩护等调节性话语行为[39]。在听证程序中,当事人可以围绕比较标准举证质证,进行反诘与辩论,聘请律师、专家证人等专业人员就自身比较优势提出专业意见。听证会议中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发表的意见应当由政府工作人员记录成听证笔录,并由当事人签字确认。
3.建立科学的比较标准
竞争性授权的制度逻辑是,申请人不仅应当证明具备基本的市场准入资格,而且还应当被认为是在相互排斥的申请者中“最好的”,这些申请者是参照比较标准进行评估的[26]。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比较标准,应当围绕授权运营的安全风险与经济利益这一矛盾展开,关注数据红利的共享性、普惠性。公共数据开发处理在硬件上依托通信网络、大型服务器、计算机存储器等智能化设施;在软件上依托云计算、大模型等计算程序。在此意义上,根植于硬件和软件中的数字技术预设了数据处理环境,关涉数据安全保护和数据产品或服务的品质。因此,对申请企业有关技术和团队实力的比较是判断比较优势的关键。授权运营场景是否具有可行性、运营收益分配方案、数据产品或服务的交易价格等因素也影响数据价值释放的可及性、持续性。因此,比较标准的设定应当是多元化的,具体可以包括:(1)数据安全保护技术及制度成熟度;(2)技术水平和团队实力;(3)授权运营应用场景可行性;(4)可能产生的社会和经济效益;(5)拟提供的数据产品或服务的价格;(6)授权运营收益分配方案;(7)企业数据产品开发运营与维护经验;(8)其他因素。正式听证会结束后,政府机关应当依据事先确定的比较标准,对申请人之间的每项实质性差异进行比较,并赋予各项标准不同的权重,从而确定授权对象。授权决定应当载明记录在案的所有重大事实依据、法律问题和认定结论,告知当事人法定救济途径及期限。
4.建立效率补偿机制
比较听证程序的显著特征是听证参加人数量多,涉及的比较标准较为宽泛,提供证据的范围广[26]。因此,为简化比较听证的结构复杂性,正式听证前可以召开预备会议,让当事人就自身比较优势充分发表意见、提交证据,筛选当事人所争议的事实,简化听证事项,加快听证的过程[40]。此外,还可以建立非正式听证程序,通过书面审查的方式,听取利益相关方的意见;也可以建立简易听证程序,政府机关在授权决定中就争议较大的比较事项作出听证决定,允许当事人就自身优势举证证明,最终形成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相结合的比较听证制度。
(三)制度保障:可信的数据要素处理环境
公共数据开放的秩序构建需要的是对开放活动信任环境的维护[41],然而比较听证制度的引入并不能完全解决政府判断的主观性、数据安全风险的动态演变问题。为此,可采取监管沙盒制度和可信数据治理技术塑造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安全治理框架。
1.建立监管沙盒制度,形成场景化的数据要素保护方案
监管沙盒是一个“安全的空间”,企业可以在其中测试创新产品、服务、商业模式和交付机制,而不会立即产生从事有关活动的所有正常监管后果[42]。公共数据价值释放具有高度场景化,决定了地方政府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实践具有高度的个案化特性,公共数据的安全开放利用秩序很难通过直接套用通用数据安全保护方案得到实现。监管沙盒的制度优势是监管部门可以根据沙盒实验项目的风险特征和应用场景,通过“一企一议”的方式为企业制定个性化的监管方案,在企业出现数据安全风险后,监管部门还可以为企业提供数据安全合规指导,监督企业有效控制数据安全风险。《宁波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第十二条规定,申请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单位应围绕拟申请使用的公共数据和拟开发的数据产品、服务,在规定期限内向市公共数据主管部门提出测试验证申请,并按照要求提交相关的公共数据清单、开发方式及市场化应用方案。宁波市大数据局组织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域)运营单位提供最长不超过6个月的免费数据实验室服务,并在测试验证结束后,向申请单位出具数据测试验证技术评估报告。这为监管沙盒制度与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融合提供了制度依据,未来应当进一步扩大监管沙盒制度的适用范围,形成从授权前的实验验证到授权后实验监管的全链条式制度设计。
2.可信的数据治理技术
数据本质上是在计算机系统中以二进制形式存储的信息,公共数据授权运营高度依赖智能化信息技术和计算网络系统,讨论公共数据可信治理难以脱离建造、构筑、编制网络空间的代码,“代码即法律”[43]。构建安全可信的数据治理环境需要从风险预防角度,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行为提供一种“通过设计保护数据”的技术策略。在公共数据运营平台搭建中应当将数据安全保护规则落实为计算机系统运行的程序性方案,将法律语言转化为技术语言。“通过设计保护数据”要求计算机控制者应当在数据处理中采取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等技术和组织措施,落实数据保护原则;通过有效性的技术设计保障数据处理过程及结果的可预见性;技术方案的设计还应当考虑市场上最新技术进展,数据处理的性质、场景及目的,数据处理的风险等级等因素[44]。在公共数据运营平台的技术底层维度上,运营主体应当采取数据沙箱、联邦计算、区块链及隐私计算等技术方法,按照“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的要求,为社会提供数据产品或服务,共享数据价值。
参考文献:
[1] 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数据要素市场发展报告(2020—2021)[R/OL]. (2021-04-25)[2024-04-08]. https://www.cics-cert.org.cn/web_root/webpage/articlecontent_101006_1387711511098560514.html.
[2] 宋烁. 构建以授权运营为主渠道的公共数据开放利用机制[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23, 41 (1): 83⁃94.
[3] 胡凌. 公共数据开放的法律秩序:功能与结构的理论视角[J]. 行政法学研究, 2023 (4): 40.
[4] The World Wide Web Foundation. Open data barometer leaders edition[EB/OL]. (2022-09-14)[2024-03-08].https://opendatabarometer.org/leadersedition/report/.
[5] 秦晓东.政府数据运营企业定位与职能[J].中国建设信息化,2017(23):64⁃65.
[6] 张会平,顾勤,徐忠波. 政府数据授权运营的实现机制与内在机理研究——以成都市为例[J]. 电子政务, 2021 (5): 34⁃44.
[7] 刘金瑞.数据安全范式革新及其立法展开[J].环球法律评论,2021,43(1):17.
[8]刘枝,于施洋. 还数于民:公共数据运营机制的构建[J]. 图书情报知识, 2023, 40 (5): 53.
[9] 马颜昕. 18亿“政务数据第一拍”暂停 公共数据运营要警惕单纯逐利冲动[EB/OL].(2023-12-04)[2024-04-10].https://e.cdsb.com/html/2023⁃12/04/content_767246.htm.
[10] 唐纳德·凯特尔. 权力共享:公共治理与私人市场[M]. 孙迎春,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58.
[11] 夏金莱. 论行政决策公开——从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视角[J].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29(4):170.
[12] 刘阳阳.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生成逻辑、实践图景与规范路径[J]. 电子政务, 2022 (10): 37.
[13] 马丁·洛克林. 公法与政治理论[M]. 郑戈,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186.
[14] 朱虎. 国家所有和国家所有权——以乌木所有权归属为中心[J].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6, 19 (1): 20.
[15] 孙清白.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营利性与公益性的冲突及其制度协调[J]. 行政法学研究, 2024(3):150.
[16] 常江,张震. 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特点、性质及法律规制[J]. 法治研究, 2022, (2): 128⁃132.
[17] 何渊. 政府数据开放的整体法律框架[J]. 行政法学研究, 2017 (6): 63.
[18] 查云飞. 大数据检查的行政法构造[J].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22, 25 (1): 63.
[19] 李悦. 激励与规制: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法律机制构建[J]. 行政与法,2023(6):41.
[20] 陈越峰. 超越数据界权:数据处理的双重公法构造[J].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25(1):26.
[21]王锡锌,黄智杰. 公平利用权:公共数据开放制度建构的权利基础[J].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22, 25 (2): 63.
[22] 沈韵,冯晓青. 公共数据商业利用边界研究[J]. 知识产权, 2023 (11): 73.
[23] 柏拉图. 理想国[M]. 郭斌和,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354.
[24] 唐娟,侯伊莎. 分配正义的两种理论:结果正义和程序正义[J]. 特区理论与实践, 2003 (1): 30.
[25] RAWLS J. A theory of justice[M].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4⁃76.
[26] ANTHONY R A. Towards simplicity and rationality in comparative broadcast licensing proceedings[J]. Stanford Law Review, 1971, 24(1): 3⁃51.
[27] BUCK R W. FCC comparative renewal hearings: the role of the commission and the role of the court[J]. Boston College Law Review, 1980, 21(2): 422.
[28] 尤尔根·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 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M]. 曹卫东,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7⁃115.
[29] 姚大志. 何谓正义:罗尔斯与哈贝马斯[J]. 浙江学刊, 2001 (4): 11.
[30] BYSE C. Opportunity to be heard in license issuance[J].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952, 101(1): 75.
[31] 宋华琳,孙沛. 行政许可比较听证的制度架构及其展开[J]. 法治现代化研究, 2023, 7 (2): 69.
[32] 张卿. 为什么要施行政府特许经营?──从法经济学角度分析[J].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0(6):33.
[33] 马颜昕.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类型构建与制度展开[J]. 中外法学, 2023, 35(2): 337.
[34] OGUS A I. Regulation: legal form and economic theory[M]. Orehon: Hart Publishing, 2004: 318.
[35] 董淳锷. 法律实施激励机制的基本原理及立法构造[J]. 法学, 2023 (9): 164.
[36]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66.
[37] ARROW K J. Economic welfare 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or invention[Z/OL]. [2024-03-09]. https://www.nber.org/system/files/chapters/c2144/c2144.pdf.
[38] 霍尔斯特.哈贝马斯传[M]. 章国锋,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0 :80.
[39] HABERMAS J.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M].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6: 104.
[40] 王名扬. 美国行政法(上)[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5: 432.
[41] 徐珉川. 论公共数据开放的可信治理[J]. 比较法研究, 2021 (6): 152.
[42]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Regulatory Sandbox (November 2015)[EB/OL].(2015-11-10)[2024-04-12]. https://www.fca.org.uk/publication/research/regulatory- sandbox. pdf.
[43] 劳伦斯·莱斯格.代码 2.0[M]. 李旭, 等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6.
[44] The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Board. Guidelines 4/2019 on Article 25 Data Protection by Design and by Default Version 2.0[EB/OL]. (2020-10-20)[2024-04-12]. https://www.edpb.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files/file1/edpb_ guidelines_201904_dataprotection_by_design_and_by_ default_v2.0_en.pdf.
Comparative Hearing: Institutional Reshaping of the Allocation of Public Data Operation Right
Chen Zhenqia,b
(a. School of Law; b. Local Legislative Research Base of Jiansu Province,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Abstract: The local practice of allocating public data operation rights presents a diverse pattern of administrative designation, application evaluation, auction and bidding. However, there are challenges related to data monopoly risk and closed procedures. The differences in practice paths are attributed to institutional factors such as the internal tension between market-based development and the application of public data, security risks, and unclear ownership of public data. The authorization process for public data should extend beyond boundary rights and establish an open use order with procedural justice in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comparative hearing system is a rational constobze7eG+e2UgzhX05jSKpw==ruction process based on communication behavior that can provide an "ideal communication situation" for stakeholders, achieve procedural justice, and alleviate inherent tensions in public data authorization operations. Additionally, the franchise attribute of public data authorization operations can be integrated with the comparative hearing system. Establishing competitive authorization principles is essential to ensure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competition within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comparative hearings embedded in the allocation system for public data operation rights. Furthermore, perfecting the system structure of comparative hearings involves scientifically setting up market access qualifications, hearing procedures, comparison standards, and efficiency compensation mechanisms; utilizing regulatory sandbox systems and trusted data governance technology can resolve institutional dilemmas introduced by comparative hearings.
Keywords: public data; authorized operation; comparative hearing; data security; distributive jus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