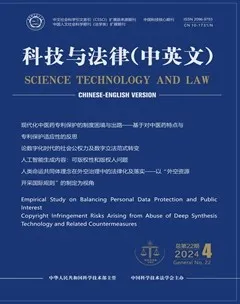论数字化时代的社会公权力及数字立法范式转变
摘 要:自创生系统论指出,社会公权力具有主体的社会性、内容的公共性、来源的事实性,并为数字立法范式转变提供了理论基础。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具有利维坦式权力风险,数据在其形成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本质在于数据成为形构数字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通过风险探究与本质考察发现,除具备工业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一般特质外,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还具有权力产生上的数据化,权力表现形式上的场域化、多元化、去中心化,权力运行方式上的监视性与规训性之特点。对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规制还是要回到自创生系统论的思路,根据其上述特点,推动数字立法范式的转变。
关键词:数字权力;社会公权力;数据;立法范式;自创生系统论
中图分类号:D 9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9783(2024)04⁃0020⁃10
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权力观认为权力仅指代国家权力,这是因为仅国家有可能掌握支配力量并形成对私人自由权利的侵害。20世纪以来,社会主体支配地位的不断提升,使得对社会公权力的关切应运而生,如芦部信喜所言,“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度化,社会中出现了很多像企业、劳工组织、经济团体、职能团体等那样的拥有巨大势力,类似国家的私团体,产生了威胁一般国民人权的事态。另外,晚近时期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展所产生的环境公害、信息社会下大众传媒对隐私权的侵害等也时有发生,并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1]”尽管学术界在讨论社会公权力时也常使用“社会性权力”“私权力”等表达,但不可否认的是,权力体系的构造应当加强对社会公权力的关注,基于此的权力约束、法治塑造与立法范式研究应当成为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随着数字化时代进程的深入,人工智能技术与大数据对私人法律权利的构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企业等社会主体对数据资源的掌控造就了社会公权力孵化的温床。现有理论对社会公权力的理解,是从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进行阐释[3],或是以宪法基本权利的概念作为理解的基点[4],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特点发生了一定变化,对于私人权益的侵害不再仅仅伴随工业化发展与信息传媒进行,而现有研究鲜有相关论述。现有理论对数字权力的理解也多从主权出发,即便考察数字权力的社会性,也并未采取社会主体视角[5],或是对数字权利进行社会性考察,而忽略了数字权力的社会性[6]。虽也有学者从法治的维度探讨数字私权力的塑造[7],而数据对于理解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具有抓手作用,应当将二者并列讨论。本文有两个核心论题:一是如何理解社会公权力,数字化时代的社会公权力有何不同?二是如何实现对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限制?前者是后者的依据,后者是前者所提示问题的解决思路。围绕两个论题,本文从四个方面展开:一是社会公权力概念的理论研究与社会中心立法范式的阐释;二是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风险以及其展现出的区别于工业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特点;三是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本相所在,及其与数据的关系;四是根据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特点的限制思路以及数字立法范式的转变路径。
二、社会公权力:理论、概念与立法范式
(一)自创生系统论与社会中心范式
社会公权力概念之兴起源于理论界对社会主体所具有能量的关注,如宪法学界提出的对基本权利限制的社会中心范式[8],这体现了社会学研究方法对法学理论视域重心的影响。卢曼《社会系统》的出版,标志着卢曼理论从“功能—结构”论向“自创生系统”论转型[9],卢曼将法律放置在社会子系统的做法为社会公权力概念的提出与社会中心范式的厘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卢曼自创生系统论的提出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生物学范畴的自创生系统意指,细胞依靠建立复杂的内部结构,通过自我指涉调节与环境的物质传递、能量交换,神经系统对于环境仅仅是建构性的映射而非完整的客观反映,系统与环境之间只是通过共振互相联结,而并没有直接接触[10]。概言之,有机体意义上的自创生系统意指运作上的封闭与认知上的开放。卢曼在此基础上对社会结构进行搭建,他将一般社会系统作为总体,将法律视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将沟通作为社会系统的基本元素。而法律沟通作为沟通的一种,以合法与非法作为区划标准与外部社会世界进行交互性诠释,从而建构了作为社会系统子系统的法律系统,实现了法律系统规则上的封闭与认知上的开放。在卢曼看来,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外部世界是进行交互的环境,社会系统内部也需要通过社会分化的形式进行化约,法律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其他子系统以及社会系统的整体都是法律系统的外部环境,法律系统通过内部合法与非法的符码运作,将外部环境交互的信息转译为法律沟通,通过规则上的封闭与认知上的开放,实现了法律系统的自创生[11]。自创生系统论对于理解社会公权力概念的一个重要作用在于卢曼将政治与法律作为不同的社会子系统进行分别考察。卢曼认为,政治与法律在各自的符码上运作并进行沟通,政治以有权或无权的符码运作,二者分别以政治的沟通及法律的沟通为基本构成元素,在形成各自操作的封闭性的基础上,进行认识上的开放互动[12]。
在卢曼的观念中,政治与法律的关系是一种结构上的耦合,政治与法律的联系是偶然的。在传统法理学观念中,我们在讨论公权力这个概念时,意指国家公权力,即政治权力,这是因为传统法理学在讨论法律与国家政治权力的关系时是以国家政治为中心的。如果采用卢曼自创生系统论的视角,政治与法律分属平行的社会子系统,政治沟通与法律沟通分别以不同的标准在各自的子系统中进行封闭运作,并在观念上进行开放互动,法律对政治权力的授权与限制,是法律与政治在观念上开放互动的耦合。而作为法律开放观念来源的外部环境,政治只是其中一项来源。从子系统的位阶上讲,政治与法律是自主的平行子系统,其他子系统同样构成法律观念上的来源,而这些子系统都隶属于社会这个统一系统,因此以社会为中心视角观察法律观念来源就具备了理论上的依据。对于公权力的厘定与限制,当然也不应当局限于国家政治权力,而是应当抽象出公权力的共同特征,社会作为法律外部环境的集合,当然也构成权力的来源,故社会公权力概念具备理论依据。换言之,传统法律系统中对公权力的定义是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耦合的结果,其他子系统与法律系统的耦合也构成对公权力概念的厘定,且对公权力概念的考察应当以社会总体系统为中心。在此基础上的立法范式也应当接受向社会中心转变的思路,数字化时代国家权力不再是威胁人权的唯一来源,对社会公权力的规制也应当引起立法重视。范式作为科学研究问题的重要方法,具有厘定问题边界、提供解决问题思路方法论的作用,自创生系统论指出了以社会整体为视野,同时也指出了以社会整体作为思考、解决问题的惯式。概言之,自创生系统论为社会中心研究范式与立法范式的确立以及社会公权力概念的引出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工业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概念
德国法社会学家托伊布纳作为卢曼自创生系统论的集大成者,他在对卢曼三大原理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宪治学说[13]。托伊布纳对自由主义宪法的批判、对碎片化时代社会宪治的理解以及对全球化宪法制度的建构,体现了他对社会公权力概念的思考。托伊布纳认为,宪法不仅不应被视作政治与法律子系统的结构耦合,还应当被定义为法律与其他社会系统的双重反思性耦合。在他看来,在卢曼理论中既无中心又无顶点的功能分化社会系统下,宪法不应当被局限为政治与法律系统的结构耦合,经济、科技、医学、艺术、传媒等子系统与政治系统一样,同样以其独特的符码封闭运作,以沟通的形式通过与外界互动发展系统理性。故其存在着侵害其他系统完整性并涉及个人自由权利的部分,亦即并非只有政治系统才构成宪法领域的问题。托伊布纳认为,多元化时代宪法的性格体现为法律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的双重反思性结构耦合,即法律系统内部通过次级规则对初级规则正当性的反思,以及社会系统自我反思的双重反思性[14]。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并无意讨论宪法的定位抑或是评析社会宪治理论合理性等诸如此类的宏大命题。概因公权力之概念一般涉及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侵害,限制公权力保护个人权利被认为是宪法的基本任务,因此在讨论社会公权力定义时,本文借鉴了宪法学者的相关理解。在托伊布纳的观点中,宪法不应当拘泥于政治与法律的结构耦合,那么公权力的概念也不应当拘泥于以政治为中心的国家机关,具有经济、科技、医学、艺术、传媒等因素的社会主体如果符合公权力的本质定义,同时可能侵害个人权利自由,就应当认为构成社会公权力,且社会公权力的概念与传统国家公权力概念在位阶上至少应当是同阶的。此外,卢曼对政治宪法限制公权力目的的阐释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经济、政治、法律、科学、文艺、传媒、教育、宗教等子系统从社会系统中分化,实现了功能的异化,宪法限制公权力的目的在于保障各系统的自主性,并保障各系统覆盖摆脱阶层身份的个人[15]。
总而言之,综合参考托伊布纳社会宪治学说中对社会公权力的理解、卢曼对宪法限制公权力根本目的的揭露以及我国学者的相关定义[16],可以对工业化时代社会公权力概念作如下解释:首先是权力主体的社会性,构成社会公权力的主体包括其他所有社会子系统,因此包括具有营利性质的企业,非营利的公益团体、基金会、政党、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其次是权力内容的公共性,政治权力之所以被称为公权力,是因为其具有公共性,即影响了多数人的利益,社会公权力也具有内容的公共性,即影响了一定数量人的利益。最后是权力来源的事实性,社会公权力不同于国家公权力来自宪法和法律的授权,社会公权力源自社会主体掌握了事实上的明显资源优势,形成对个人的实际支配力,故具有权力来源的事实性。
数字化时代的社会公权力除具备上述特征外,还演变出诸多全新的特质。为了明确这些特质,应当对其可能造成的风险进行分析,同时,对风险的明确也是完善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规制思路的前提,亦即证成数字立法范式转变的必要进路。利维坦的隐喻体现出不受限制的国家主权的风险,而以自创生系统论的视角对利维坦进行重新解读,可以对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风险进行全方位考察,同时,本文将指出数据作为这一风险成因的作用。
三、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风险:利维坦的另一种解读
数字主权作为数字法学的一个热点问题,大数据时代的复杂算法与海量数据,使得对数字权力脱离制度制约的关切应运而生。“算法利维坦”“技术利维坦”的命题展现出深厚影响力[17],现有研究在使用“算法利维坦”一词时均是从国家权力的角度出发,在社会中心范式下,社会主体成为数据掌控者时,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展现出利维坦式风险。
(一)国家权力语境下的利维坦式风险
霍布斯对利维坦这一意象的使用源于《约伯记》的描述,利维坦被认为在陆地上没有其他生物像其一样无所畏惧,凡高大之物其无不藐视,利维坦骄傲地在水族作王,是一切骄傲之王。霍布斯将缔结契约建立的国家比作利维坦,意指绝对意义上享有无限权力的国家权力[18]。霍布斯认为,为了建立以抵制外来侵害为目的的公共权力,所有人需把自己的力量授予某一个人或是一个可以将多人意志最终溯源为某个人意志的集体组织,并最终使得这一个人或是这个集体组织可以代表每一个人的人格,并形成一个统一的人格。通过签订契约、建立共同权力、形成统一人格[19],伟大的利维坦应运而生。霍布斯提出利维坦的本意在于以契约理论证成国家建立过程,这与同样采用契约理论的洛克存在着区别。洛克强调契约对国家权力的分权作用,而霍布斯认为,国家权力并不参与契约的订立过程,而仅仅作为旁观者见证契约的订立,因此国家权力仅接受公民对自身权利的让渡,而不负有义务,相反公民负有履行契约的义务,否则就是不义的[20]。此后,尽管洛克的思想广泛为人接受,但利维坦也具有警惕公权力风险的意义。
利维坦式国家权力风险在数字化时代仍然具备理论生命力,随着算法算力的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有学者指出大数据时代引发了与霍布斯的主张同构的半契约逻辑[21]。在数字利维坦时代,一方面,普通公民为了自身生活的便利,不可避免地让渡一部分权利;另一方面,算法的复杂性以及数据的海量性,使得普通公民对于让渡权利的性质无法进行客观有效的衡量,而权力机关在公民缔结契约时同样出现阙如的情况,导致数据利维坦权力的绝对化与不可逆化。有学者指出,数据利维坦具有看似相悖实则相辅相成的双重面向,一方面数据利SvgdX5mTUbgljFjsmCHRqw==维坦的权力有绝对化的失控风险,另一方面国家主权存在着依托数据而面临被削弱的风险[22]。在国家权力语境下,数字权力的利维坦式风险源于权力机关过于依赖算法与数据,政治理性面临被技术力取代的可能性。而在社会公权力语境下,数字权力同样面临利维坦式风险。
(二)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语境下的利维坦式风险
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利维坦式风险的形成,源于数字化时代社会力量的不断提升。如托依布纳所言,当今时代宪法的任务已经不再是自由主义宪法时期对国家权力限制以保障私人权利,而是要向社会宪治转向,亦即实现社会中心范式的转变,在多元社会中宪法要解决的问题是释放经济、科技、医疗等领域的社会能量,并避免其造成不必要的破坏[23]。这种研究范式与立法范式的转变不仅存在于宪法领域。在数字化时代,科学技术与商业行为结合后所蕴含的社会能量呈指数倍增长,“算法利维坦”“技术利维坦”与数据结合,引发了社会公权力不断膨胀的风险。社会主体在使用个人数据信息提供服务,或将个人数据作为大模型学习数据来源时,同样可能处于绝对权力地位。正如霍布斯证成利维坦的逻辑那样,公民缔结契约、让渡数据信息权益时,仅是公民间作为契约缔结的主体,企业、大模型使用者等社会主体作为第三人仅是起到见证作用,因而只接受公民让渡的权利而不负有义务。这一点不仅体现在社会主体对公共空间数据资源的使用,还表现在算法黑箱、算法歧视、算法垄断、大数据杀熟等数字问题缺乏相关制度的规范。数据利维坦在这种语境下伴随着个人信息数据而再生,利维坦式风险关切伴随着数字化进程转移到社会公权力的领域。从权力的主体维度上,形构数据利维坦的主体表现为掌握数据资源的企业,因而具有主体上的社会性。从权力内容的公共性维度上,社会主体获取的数据往往来自公共空间,也侵害了一定数量个体的自由权利,具有权力内容的公共性。从权力来源的事实性维度上,社会主体权力的形成源自其对大数据、算法等资源的事实掌握,数字化时代,计算机高新技术与数据资源集中于社会主体已经是现实趋势所在。因此,企业等社会主体的数据使用行为可能构成社会公权力,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也具备社会公权力的一般特质。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引发的利维坦式风险,最终导向的结果是,大企业对公民具有绝对权力地位,形成了对其他私主体的事实上的支配力。企业通过掌握数据信息,进而掌握科技、经济、文化等资源,并最终成为社会公权力主体,形成对数字人权造成威胁的数据利维坦风险。
在数字化时代,数据资源成为社会公权力支配力来源的重要资本,具有生产性要素的作用,故数据的获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公权力的形成。概言之,数据利维坦的风险,既指因为数据资产在当今社会价值的不断提高,造成伴随数据资产而产生的具有绝对权力不受限制的公权力出现,也指因为数据使用场景的社会化与商业化,使得公权力不再仅表现为国家权力的形式。其一,数据资产价值的提高促进了权力重心向社会方向的偏移;其二,数据资产的广泛使用促进了社会公权力的形成;其三,数据资产的分配成为社会公权力支配力强弱的重要标准。综上,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语境下的利维坦式风险解释了上一节所提及的三个问题:第一,数据在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形成过程中的具有决定支配力大小、社会主体间力量关系的作用,进而印证数据对于理解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抓手作用。第二,社会主体在涉及数据交换的法律关系上,具有与利维坦式隐喻同构的半契约、主体阙如的逻辑,这导致绝对化不受限制的社会公权力的风险关切,数据利维坦的风险担忧应运而生。第三,在对数据利维坦的风险进行描述的同时,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在权力产生上具有与工业时代社会公权力的不同特质,即权力产生上的高度数据化。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公权力语境下的数据利维坦式风险同时印证了自创生系统论的洞见。国家权力语境下的利维坦式风险仅仅是拘泥于政治与法律系统的结构耦合。数字化时代,应当以数据为抓手,将权力规制的思路放置在社会整体系统中,亦即关注社会公权力语境下的数据利维坦式风险。至于数据与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关系,本节在诠释数据利维坦式风险时仅提示了数据在权力产生上的作用。数据对社会公权力的意义不仅于此,本文认为其具有揭示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本质的意义,故下一节将从后结构主义的视角考察数据与数字化时代社会结构的关系。同时,数据利维坦导向的社会公权力的绝对化,让人不禁产生这样的疑惑,后结构主义的社会消亡式预言是否会在数字化时代实现,社会结构在数字化时代何以可能,对数据利维坦的社会公权力限制何以为之。总之,从福柯的解构主义观入手,可以通过数据揭示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本质,并进一步阐明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特点,进而为其风险应对与限制提供思路,为数字立法范式的转变进路提供依据。
四、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本质:数据与结构
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从社会基本构成要素的角度,对社会结构进行了全方位的解构。尽管后结构主义的解构尝试可能是失败的,但同时其解构思路是具有启发性的,以社会结构的角度考察数据揭露了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本相,对后结构主义的批判反思可以进一步阐释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特质。
+N13PuK1AMFEHFI5ai5ShQ==(一)权力的社会性解读:结构或解构
社会结构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在法社会学研究中同样受到广泛的关注。社会结构的理论经历了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发展,形成了由比照自然科学的结构对社会结构进行描述、到从社会功能出发形构社会结构、到摆脱宏观微观形成综合结构、到结构消失实现彻底解构的发展路径[24]。勒弗、鲍德里亚作为两位深受后结构主义思潮影响的法社会学者,他们分别从象征着社会结构的文本[25]、符号[26]出发,对权力进行全方位建构的同时实现了社会解构。福柯则在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对权力进行了社会性的解读。吉登斯在《社会学》一书中提出的计算机科学是否会造成认知障碍的疑问[27],在数字化时代更加凸显。数字化时代,数据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是结构性的还是解构的,基于此的权力观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为探明这些要旨需从福柯的观察视角入手。
法国社会法学家福柯作为后结构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尼采“上帝已死”的论断中进一步推导出“人的消亡”。福柯从结构主义的语言分析入手,他关注话语的对话性,着重分析话语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性与社会性。他进而揭露出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决定了对话的形式,并对以话语形式传播的知识产生着影响。认知范式事实上制约了一个时代的知识体系与认知形式,权力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方式筛选、组织、支配着话语的传播,任何时代的对话都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权力的产物[28]。因为对话是多元性的、场域性的,福柯的权力观也是多元性、场域性的。福柯认为权力是一种结构性的关系而不是客观存在的物品,权力的场域性表现为一种交织错杂的关系,即权力关系网。每一个体都处于权力关系网中,都可能成为支配权力或者被支配的对象,进而他认为在权力网中是不存在权力主体的,人仅仅作为权力实施的工具。同时,正是这种场域化权力的存在,福柯认为权力同样表现为去中心化,即国家权力不再是权力中心,权力是分散在对话联结的网络关系中的[29]。总而言之,正是福柯所采取的微观权力观使得他提出了规训性权力,即一种并非由宏大的国家机关产生的以暴力为后盾的权力,而是借由对话形成的网络,并经过精妙的设计、计算、技术力构成的微观权力。规训性权力通过规范化的监视使得人成为权力支配的工具。
福柯的权力逻辑表现为,对话是构成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而对话的产生是由背后的社会权力关系决定的。福柯认为对话被权力关系的支配最终将导致人成为权力的工具,造成“人的消亡”。通过这一进路,福柯实现了对人理性能力的解构,他认为非主体化、去中心化的权力意味着理性的消亡。尽管福柯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新闻等宏观权力载体的作用,从自创生系统论的角度,后结构主义思潮忽略了政治、传媒、经济等其他社会子系统的宏观作用。但是,从微观权力观的视角对于阐明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特点具有提示性意义,福柯对社会结构的归纳也与数据在数字化时代的意义具有内在的联系。
(二)形构社会结构的数据与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
沿着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思想的理论路径,可以观察到数据对数字社会进行了再形构。同时,数据作为社会构成要素,既是数字化社会公权力的本质所在,亦促进了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扩大。为证明这一观点,本文论述如下:
第一,作为社会结构研究对象的基本结构要素,在数字社会表现为数据形式。数据成为社会基本构成要素表现在对于传统社会构成要素的包容性。后结构主义主张的对话、文字、符码等要素在数字社会中均体现为数据的形式。传统社会基本构成要素的对话、文字不仅以数据的形式存在,还衍生出编程语言、计算机代码的形式。数据成为社会基本信息的重要载体,在某些方面或许与鲍德里亚笔下的符号具有类似的性质,但鲍德里亚对符号的使用更多也只是着重分析其作为传播媒介的作用,而数字化时代数据的作用远不止于此。无论个人的信息、偏好、行为模式,乃至企业的经营、技术、商业运转,甚至政府机关的决策、行动标准,均可以由数据作为载体。这些数据也同样成为社会主体获取利益、形成社会公权力的来源。换言之,数据的社会信息载体作用,成为其建构社会结构的原因。传统社会构成要素的对话、文字、符号仅仅是作为人的意志、理性的载体,而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未来,数据甚至可以成为人工智能形成“意志”“理性”的学习基础。理性与意志的边界在数字社会甚至存在被重塑的可能。诚然,现有技术力尚达不到此种程度,但作为人的理性与意志的重要表达成果的知识产权,其权利构造存在着嬗变的现实可能。人工智能确实已经深度参与了人类智力成果的产出活动[30]。概言之,传统社会构成要素趋于数据化,以及数据的生产性要素作用,均表明数据成为数字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
第二,作为基本社会构成要素的数据,现实地集中于少部分社会主体,基于数据产生了数字权力,这与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内涵相同。作为传统社会结构要素的对话、文字、符号,具有映射社会的权力关系的作用,而数据作为基本结构要素时甚至放大了其与社会权力之间的联结。一方面,对数据进行筛选、处理、汇编依赖大模型的算法,算法语言事实上决定了数据的使用与表达,因此算法成为信息时代主宰数据表述信息的权力源泉,算法权力因而产生。另一方面,对数据的掌握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权力的支配关系,如在商业活动中,消费者、竞争对手的数据在企业竞争中的作用逐渐凸显,而数据与大模型结合作为海量学习的来源时,就可能形成大企业对普通公民、其他企业在数据处理上的支配关系。同时,因为数字化时代的数据是散落在互联网中的并与每一个体息息相关,这也与福柯所描述的权力的场域化、多元化、去中心化不谋而合。在这个语境下,数据作为权力的载体,通过场域化的分散将每个主体联结。一方面,数据的分散使得权力的去中心化凸显;另一方面,数据向掌握大模型的企业流入,使得权力中心不再是以国家为中心,以社会为中心的公权力在数字化时代会日趋强大。概言之,数据作为社会构成要素的观察视角揭示了数字化时代的社会公权力在表现形式上场域化、多元化、去中心化的特质。
第三,作为基本社会结构要素的数据同样受到权力关系的支配,代码替代法律成为权力形成的来源,社会公权力凭借对数据的垄断谋求私人利益。福柯之对话受到权力体系支配的观点,在数字社会仍然适用。区别在于,因支配权力性质的变化,权力来源发生了一定变化。社会公权力支配着数据资源,这导致了代码具有替代法律成为社会公权力权力来源的倾向[31]。与国家公权力不同的是,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支配数据要素时,目的在于谋求私人利益。此外,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通过对数据的支配,还表现出替代国家公权力的趋势。福柯通过微观权力分析观察到现代社会存在着规训性的权力,规训性权力作用的结果是对社会的各个角落进行无死角、全天候的监视。对社会监控的论述可追溯至边沁关于“圆形监控设施”的构想。边沁设想的监狱是一种全开敞式的,在圆形监控设施中,每个人被分为单独的隔间,且监视者是可以随时监控到隔间内情况的。被监视的人却不能知道自己处于监控状态,即这种全开敞式是单向的[32]。基于边沁的构想与福柯的监视理论,有学者提出基于大数据的监视文化,在大数据时代为了社会生活的方便、健康、安全,政府、企业对个体进行了全方位的监控,这种监控是监视者与被监视者在一定范围上达成合意的柔性监控[33]。数据的社会结构化不仅构成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本质,还延伸出社会主体谋求私人利益时对数字人权的侵害。这与边沁构想的“圆形监控设施”的隐喻不谋而合,公民对于被使用的数据是不知情的,对于这些数据的法律性质也是无力追溯的,这种监视是单向的。监视者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机关,以企业为中心的社会公权力成为监视的主体之一。国家权力的运行存在着完备的法律制衡机制,而对于社会公权力限制的相关法律制度并不完备,公民的数字权利难以得到保障。概言之,社会公权力通过对数据这一数字社会基本构成要素的支配,在权力运行方式上,表现出监视与规训性权力的特质。
综上所述,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本质在于数据成为了社会基本构成要素,并形构了数字社会。因此对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限制,除需应对社会公权力语境下的利维坦式风险,还应把握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本质特点。亦即正确处理数据问题是限制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题眼所在。本文认为,对于社会公权力的规制还应当回到自创生系统论的社会中心范式的思路,实现数字立法的范式转变,协调法律子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的联动。
五、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限制:数字立法范式转变
自创生系统论提示了社会中心范式的形成,所谓范式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哲学家库恩提出,他认为范式意指选择问题的标准,只有在范式辐射范围内的问题才被认为是有解的,科学共同体才会鼓励成员去研究它。概言之,范式意指形式上的科学共同体与实质上的科学共同体研究问题的标准[34]。对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限制应当回归自创生系统论的思路,针对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风险与特点,实现数字立法的范式转变。故本文所述数字立法范式转变的思路,与前文所述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特点、本质相互印证。根据前文所述,其特点总结如下:第一,权力主体的社会性。数字化时代的社会公权力主体仍然包括其他所有社会子系统,但主要表现为具有营利性质的企业。第二,权力内容的公共性。数字化时代的社会公权力不仅从影响公共利益这个面向上具有公共性,还因构成权力来源的数据来源于公共空间,而具备公共性。第三,权力来源的事实性。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事实性表现为社会主体对数据资源的事实性支配。第四,权力产生上的数据化。第五,权力表现形式上的场域化、多元化、去中心化。第六,权力运行方式上的监视性与规训性。本文根据这些特点,对数字立法的范式转变作如下展开:
第一,数字立法范式转变的首要目标在于明确社会公权力的概念,正确厘定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范畴。数字立法中应当合理区分社会主体的私人权利与社会公权力,避免对社会主体的私人利益进行不当限缩。正确处理限制社会公权力与保护私人主体私权利之间的张力,关键在于明确数字立法中的社会公权力概念。其依据就在于本文归纳的社会公权力的构成要件性特点,即权力主体的社会性、权力内容的公共性、权力来源的事实性。针对主体要件,数字立法应明确社会公权力的可能主体,如平台、数据经营公司、涉及大量数据资源的科技公司等。针对内容要件,数字立法应该同时关注公共数据与个人数据。对公共数据的使用当然构成内容的公共性,而对个人数据或客户数据的处理,只要涉及公共利益,不能仅因其来源不具有公共性,而认为其不符合公共性要件。针对来源性要件,是认定社会公权力的核心,并非所有平台都构成社会公权力,也并非掌握数据资源优势就认定为社会公权力。应当严格判断社会主体的数据资源优势是否已经构成对其他私主体的支配,具体而言,社会主体利用数据优势,侵害了其他私主体的选择自由,达到排除其自主选择的程度,才宜认定为社会公权力。概言之,只有当数字私权膨胀,且私法自治保障不能发挥作用,才应适用数字社会公权力的相关规定。
第二,数字立法范式转变的题眼在于数据立法,“三权分置”与社会中心范式具有价值的融贯性。数据成为数字社会的基本结构要素是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本质所在,故数字立法范式转变的关键在于通过数据专门立法实现对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限制。2022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第三条指出,“三权分置”的思路:“根据数据来源和数据生成特征,分别界定数据生产、流通、使用过程中各参与方享有的合法权利,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享有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的,均为具有数据资源优势的社会主体,即可能形成社会公权力。故数据立法的指导思路体现了数据立法的价值取向与限制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价值融贯。具体而言,在进行数据赋权的同时也应进行限制,即应构建数据权利行使限制与数字社会公权力限制的双层制度框架。数字立法范式转变还要求,对数据驱动型经营者实施集中审查监管。例如,在创新相关市场认定、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市场力量认定的技术手段,以及对扼杀式并购、VIE架构等审查标准上[35],加强对社会公权力的监督与限制。除数据专门立法外,数字立法范式转变还意指企业数据赋权与个人数据保护的联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涉及个人数据权益的保护,其有关数据共享制度分类的规定,提出了企业对于数据保障义务的要求[36],相关制度拓展应当以企业等社会主体的义务机制为圆心,推进数据相关立法的社会中心范式转变。
第三,数字立法范式转变的目的在于实现对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多元化限制。数字化时代的社会公权力,在权力表现形式上具有场域化、多元化、去中心化的特点,因此对其权力监督也应当是多元化、去中心化的。其中,去中心化并不意指无中心,数字立法范式转变也不仅指以社会主体为中心。在社会公权力限制上,应当坚持社会主体自治、国家权力监督、行业监管审查、公民权利限制的多元化限制路径。具体而言,对构成数据权力的企业,应当以公共事业对待,实行类似国家公权力的监管[37]。 同时,应当完善行业声誉机制,提高社会主体自治的适用标准,加强公民对于数字权力私主体的监督,以实现多元化规制路径的协同发展。
第四,数字立法范式转变的落脚点在于保障公民的数字权利。数字立法范式转变的最终目的在于保障公民基本的自由权利,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风险也凸显为对公民数字权利的侵害。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在权力运行方式上的监视性与规训性,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算法权力的滥用、算法歧视行为、不当嫁接导致数据泄露的风险等。算法权力滥用主要体现为社会主体通过算法推荐等方式,形成信息过滤机制,使得公民仅能接受到与自己相同或自己认同的观点,并最终形成信息茧房。信息茧房降低了公民对差异的认知可能性,在侵害公民的数字人权的同时,存在着消解社会共识的可能[38]。算法歧视的原因既包括输入算法的大数据本身具有歧视性,也包括编写算法时输入了歧视观念。基于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监视性,算法歧视的破坏力范围日益扩大,形成对数字人权的侵害。此外,社会公权力主体掌控公民数据信息时,时常面临数据泄露的风险,社会主体在享有数据利益的同时,数据泄露的不利后果却大部分由公民承担。数字立法范式转变的最终落脚点,必须是为了保障上述数字人权的实现。数字立法应当增设算法透明机制,在推动反歧视立法的同时,完善数据泄露风险应对制度,以保障数字人权作为限制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目的。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监视性与规训性,提示了数字立法必须加强对数字人权的范围厘定与实质保护。数字人权不仅受到侵害的风险大幅提升,其认知可能的降维更应受到数字立法的关注。公民往往对自己放弃的自由权利的性质并不知情,甚至并未察觉自身权利受到侵害。数字人权以一种形式上的自愿、自治的方式被放弃掉了。数字立法范式转变应当对数字化的意思自治进行重新厘定。
总而言之,自创生系统论将社会整体作为视角的做法,提出了将社会整体作为研究问题的标准,即社会中心范式。因此,方法论的范式转变指出数字立法也要推进社会中心范式的转变。就国内法而言,在立法思路上应当将视域放置在整体社会系统中,对社会公权力的限制还需要具有公法性质的法律发挥作用,立法不应当满足于法律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的单一结构耦合,而应当实现社会整体系统视野下的多结构耦合。一方面社会整体视角为社会公权力的确定提供了观察视野;另一方面社会整体视角也为多子系统联动限制社会公权力提供整体环境。就国际法而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展现了全球治理观、共同利益观、包容互鉴观、可持续发展观。其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狭隘民族国家短期利益,并追求人类长远共同利益的集合,以国家为主要但非唯一成员的共同体,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39]。其所体现的国际法内涵,与自创生系统论的整体社会视域、社会宪治理论的全球社会治理,具有内在价值的融贯性。故应当将国际社会作为整体社会系统进行观察,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为索引,以社会宪治理论与自创生系统论为基础,为国际交互社会综合治理的国际宪治提供理论依据,以实现全球性国际社会的联动治理。
六、结语
数字化时代下,个体都处在数据堆砌的矩阵中,数据的生产要素属性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大模型的广泛开发将逐步显现。对于权力膨胀的利维坦式风险关切,解构社会结构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数字化时代仍具备醍醐灌顶般的理论价值。数据的公开性以及商业运营特点,促进了社会公权力的实现。多元社会的多元力量正在经历不断的扩张,社会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可能侵害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数据化时代的来临,无疑加剧了这一现象。数字人权不仅受到侵害的可能性大幅提升,甚至在无意间被不当放弃。数字立法应当关注到这点,以避免意思自治在数字化时代被解构。对于社会权力的不断膨胀,数字立法应当做到对社会多元力量的因势利导,如同“治水”一般,将权力的洪流均匀地输送到诸多同等的河道,使得每个河道都不会出现干涸或泛滥。现有理论研究应当加强对社会公权力的关注,数字立法在对社会公权力进行规制的同时,也应当实现向社会中心范式进行转向。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建设离不开法治的作用,社会公权力的正确引导也离不开法治的作用。不过,正如美国学者库恩所言:“新理论的同化需要重建先前的理论,重新评价先前的事实,这是一个内在的革命过程,这个过程很少由单独一个人完成,更不能一夜之间实现。[40]”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理论的推进需要学界广泛的关注与共同的推进,数字立法范式的转变需要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共同努力,而数据作为应对数字化时代社会公权力的题眼所在,数据专门立法正是进行数字立法范式转变尝试的一块试金石。
参考文献:
[1] 芦部信喜. 宪法[M]. 林来梵,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6.
[2] 马忠法,赵鹤翔. 人机合作发明专利授权的正当性解释及其制度因应[J]. 电子知识产权,2023(9):59.
[3] 徐靖. 论法律视域下社会公权力的内涵、构成及价值[J]. 中国法学,2014(1):79⁃101.
[4] 李忠夏. 基本权利的社会功能[J]. 法学家,2014(5):15⁃33.
[5] 周尚君. 数字权力的理论谱系[J]. 求是学刊,2024(1):101⁃111.
[6] 刘清生,黄文杰. 论数据权利的社会权本质[J]. 科技与法律(中英文),2023(1):29⁃38.
[7] 孙笑侠. 数字权力如何塑造法治?——关于数字法治的逻辑与使命[J]. 法制与社会发展,2023(2):61⁃83.
[8] 李海平. 论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的范式转型[J]. 中国法学,2022(2):26⁃44.
[9] 鲁楠,陆宇峰. 卢曼社会系统论视野中的法律自治[J]. 清华法学,2008(2):54.
[10] 陆宇峰. “自创生”系统论法学:一种理解现代法律的新思路[J]. 政法论坛,2014(4):169.
[11] 克内尔,纳塞西. 卢曼社会系统理论导引[M]. 鲁贵显,译. 台北: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8:24⁃30.
[12] LUHMANN N. Law as a social system[M]. ZIEGERT, Translat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359.
[13] 陆宇峰. “自创生”系统论宪法学的新进展——评托依布纳《宪法的碎片:全球社会宪治》[J]. 社会科学研究,2017(3):188.
[14] 托依布纳. 宪法时刻来临?——“触底反弹”的逻辑[J]. 宾凯,译. 交大法学,2013(1):22⁃47.
[15] LUHMANN N.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law[M].ELIZABETH K,Translated. Delaware: Soci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Press, 1985: 114⁃125.
[16] 李海平. 论基本权利对社会公权力主体的直接效力[J]. 政治与法律,2018(10):111⁃112.
[17] 王小芳,王磊. “技术利维坦”: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的潜在风险与政府应对[J]. 电子政务,2019(5):86⁃93.
[18] 霍布斯. 利维坦[M]. 黎思复,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9:138.
[19] 李猛. 通过契约建立国家:霍布斯契约国家论的基本结构[J]. 世界哲学,2013(5):93⁃95.
[20] 苏力. 从契约理论到社会契约理论——一种国家学说的知识考古学[J]. 中国社会科学,1996(3):92⁃96.
[21] 张爱军. “算法利维坦”的风险及其规制[J]. 探索与争鸣,2021(1):95⁃102.
[22] 季卫东. 主权的嬗变——数字化“魔兽世界”与法律秩序创新[J]. 交大法学,202305):5⁃17.
[23] GUNTHER T. Constitutional fragments: societal constitutionalism in globaliza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1.
[24] 周怡. 社会结构:由“形构”到“解构”——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之走向[J]. 社会学研究,2000(3):55⁃66.
[25] CLAUDE L. Machiavelli in the making[M].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2: 307.
[26] JEAN B.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M]. St. Louis, Mo.: Telos Press, 1981: 222⁃223.
[27] 吉登斯. 社会学[M]. 赵旭东,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598.
[28] 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等译.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275⁃276.
[29] 陈炳辉. 福柯的权力观[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84⁃90.
[30] 吴汉东,刘鑫.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知识产权法律因应与制度创新[J]. 科技与法律(中英文),2024(1):1⁃10.
[31] 赵蕾,曹建峰. 从“代码即法律”到“法律即代码”——以区块链作为一种互联网监管技术为切入点[J]. 科技与法律,2018(5):7⁃18.
[32] 德赖弗斯,拉比诺. 福柯: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M]. 张建超,等译.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 199⁃201.
[33] DAVID L. The electronic eye: the rise of surveillance society[M].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 90.
[34] 托马斯·库恩. 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M]. 范岱年,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88.
[35] 苏雪琴. 数据驱动型经营者集中:现实源流、规制理路与制度因应[J]. 科技与法律(中英文),2023(1):39⁃47.
[36] 许娟,罗熠琛. 第三方数据共享中企业的个人数据保护义务构建[J]. 科技与法律(中英文),2023(4):32⁃42.
[37] ORLA L. Grappling with data power: normative nudges from data protection and privacy[J]. Theoretical Inquiries in Law, 2019(1): 189⁃220.
[38] 姚尚建. 数字治理中的权力控制与权利破茧[J]. 理论与改革,2022(3):132.
[39] 马忠法. 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治创新[J]. 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21⁃31.
[40] 托马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M]. 金吾伦,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6.
On Social Public Power in the Digital Era and Conversion of Digital
Legislative Paradigm
Ma Zhongfa, Zhao Hexiang
( Law Schoo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Autopoietic systems theory points out that social public power has the social nature of the subject, the public nature of the content, and the factual nature of the source,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aradigm shift in digital legisl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social public power has the risk of Leviathan power, and data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its formation. The essence of social public power in the digital era is that data has become the basic component of the digital society. Through risk exploration and essence inspection, it is found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public power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 era, social public power in the digital era also has the digitization of power generation, and the fieldization, diversific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of power expressions. The supervisory and 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ay power is exercised. The regulation of social public power in the digital era still needs to return to the idea of autopoietic systems theory, and based on its above characteristics,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igital legislative paradigm.
Keywords: digital power; social public power; data; legislative paradigm; the theory of autopoietic syst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