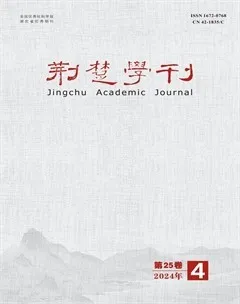东方影像的主体性建构:从中国早期诗电影的审美意象生成谈起
摘要:面对“世界电影”“西方电影”的冲击与影响,虽然已有不少中国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从长远而言,如何在电影本土化发展中彰显东方韵味,建构东方影像主体性仍是摆在电影创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中国诗电影自开始便是“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的过程,早期中国诗电影借鉴吸收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把民族内蕴熔铸到影像艺术的实践中,使影片充满东方美学气质,是建构东方影像主体性的生动实践。在全球化背景下,从中国诗电影出发,建构东方影像主体性是中国电影乃至亚洲电影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诗电影;中国电影史;审美意象;东方影像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24)04-0021-08
“象”的美学内涵最早可以追溯到老子美学,老子认为“气”和“象”是两个同“道”密切相关的范畴,指出如果离开了“道”那么“象”就失去了本体与生命,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物。可见,在老子这里就初露了“象”的外延性,指出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直到《易传》(主要是《系辞传》)进一步对“象”进行规定,提出了“圣人立象以尽意”的命题,将“象”放到一个核心的地位。认为可以通过具体的、显露的“象”来表达朦胧的、幽隐的“意”,进而在单纯中表现丰富、有限中体现无限。“立象以尽意”的提出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后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意象”这个美学范畴,便是发源于此。童庆炳先生在《文学理论教程》中提到:“审美象征意象是指以表达哲理观念为目的,以象征性或荒诞性为其基本特征的,在某些理性观念和抽象思维的制导下创造的具有求解性和多义性的达到人类审美理想境界的“表意之象”。它不仅是观念意象的高级形态,也与典型、意境一样,属于艺术至境的高级形态之一。”[ 1 ] 236可见,通过对“象”“意象”的把握,可能更好理解作品的表意性、朦胧性、寓意性及其内在魅力。
中国诗电影自开始便是“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的过程。“人、景、物、光、色、声”等视听元素通过形象化、象征化塑造后在影像中呈现出一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境界。这种被导演赋予审美化后的“象”,它既能写实,也能表意;既能抒发情感,也能带领观众到更高的境界,完成电影语言的超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电影发展的早期,却因为中国传统美学性格的影响而形成了独特的诗意化审美风格。史东山、孙瑜、吴永刚等导演充分吸收了中国古代诗歌对意象的设置与运用,在当时特殊的年代背景下创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影片中塑造出一系列既能抒发情感、渲染氛围又能营造独特审美意境的“意象”,由此奠定了中国诗电影的基本美学风格。
一、“有型之象”的铺陈:中国早期诗电影的视觉意象塑造
(一)极具现实意义的人物形象
诗电影的主题一般都表现自然美、人情美和人性美,它以情绪贯穿全剧,故事简单,平淡、结构单纯,无叉枝,它并不表现外在的矛盾冲突,戏剧性不强,而表现内在的人物心理冲突,以抒情性见长[ 2 ] 48。虽然诗电影并不以讲述故事作为主要目标,而是着重表达情感和抒发情绪,但是在早期中国诗电影中导演们都很注重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主要人物都极具现实主义意义。电影中的主要人物,不仅可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更具有彰显主题,承载表意的功能,人物的行为举止、情感情绪也能形成电影的核心意象。
早期中国诗电影中的主要人物形象,是那个时代最普通的底层人民。吴永刚导演的《神女》拍摄于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讲述的是上海妓女阮嫂,为了抚养孩子,但因其身份而不断遭到社会的各种压迫,最终她忍无可忍,失手打死流氓,被判监狱服刑十二年。阮嫂由当时颇负盛名的电bb7p7tefl/S2eVJ20C4VsIHLd1t1O2ZSRi/yX09SI48=影女星阮玲玉饰演。影片一开场导演便交代主题,在字幕中写到:“神女——挣扎在生活的漩涡里——在夜之街头,她是一个低贱的神女——当他怀抱起她的孩子,她是一个圣洁的母亲——在两重生活里,她显现了伟大的人格。”当时的上海处于半殖民地的状况,受到外来势力的侵略,社会最主要的问题之一便是妇女的出路。吴永刚导演围绕着“神女”的两重性格和两种生活,通过白描式的影像画面向观众徐徐展开这个悲伤的故事。华灯初上,“神女”站在上海街头点起香烟,吸引“客人”的光顾,在人物处理上,导演并没有可以回避妓女这个职业,而是通过朴素的镜头、淡雅的画面呈现出一个受尽压迫、欺凌的女性,一个温暖、慈爱的母亲,一个不甘堕落、寻找出路的小人物。
1934年孙瑜执导的《大路》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影片不管是叙事还是画面上都呈现出与以往中国电影完全不同的风格形态,极具民族魅力与诗意风格。在人物塑造上,金哥和其他五个兄弟性格鲜明,个性明显、各有特点。借用影片中茉莉的话:“我爱金哥的勇敢!他总是在微笑,他永远向前”“我爱老张的铁臂!他不大说话,他埋头苦干……捏人手一下要痛三天!”“我爱郑君的聪明!世上的事,他知道得那么清”“我爱章大的粗笨!说了就干……干了又悔,粗笨赛过鲁智深”“我爱小罗的志气!又年轻……又美丽……他做梦也在开机器”“还有那小六子的千奇百怪!”勇敢、健壮、聪明、粗笨、导演借助不同的人物性格,通过对修路这个核心事件的象征性表现,书写了正义、浪漫、诗意、热烈的青春赞歌。虽然是在特殊环境下的创作,但并没有影响影片明朗的格调。通过对大自然的礼赞、对热血青年的讴歌,对广大群众的呼唤、在个性化的“群象”下奠定了影片的诗意风格,呈现出浪漫之美、素雅之美、飘逸之美。
可见,早期中国诗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意义,其人物本身并不具有强烈的表意色彩,而是导演通过影像审美化的处理后显现出象征意味,形成独有的“有型之相”,从而直抒胸臆、传情表意。正如当时观众看完《神女》后评价:“故事是非常现实的,为了它现实,所以才能这样感动人。”[ 3 ] 92也正因为人物形象本身的现实主义意味,更贴切了中国诗电影的含蓄隽永之味。
(二)由“一般之物”到“物象之物”
中国古典诗词中,鸿雁与羁旅思乡、菊与高洁脱俗、莲与高尚节操、梅与不屈不挠常常联系在一起,这种物象经过导演典型化、符号化的处理后便成了意象。意象是“意”与“象”的复合物,“象”包含了一般的“物”,物在经过审美经验与情感的熔铸后便成为了表意符号。符号的形式,表现为能指与所指,作为意象符号的物在电影中的所指一般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是物本身有一定的象征性,能够在镜头与镜头、声音与画面之间产生言外之意,打破物本身的束缚;第二是在影片中多次复现。
影片《大路》创作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导演孙瑜将时代命运与个人精神结合在一起,彰显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主义情怀。对于这种精神的把握,离不开对电影中符号化的物象分析。在《大路》中,导演反复在重要情节点、情绪点出现工人“拉铁滚”的场景,使影片主题更为鲜明,诗意更浓郁。铁滚是压路时用到的工具,铁滚所到之处必然是一条平坦的大道,影片中以金哥为代表的筑路工人无论是烈日酷暑还是月明星稀的深夜都在辛勤劳动,在危难之际他们也在同反动势力做斗争,即使献出生命也不屈服。“铁滚”这一物象隐喻着在民族解放过程中遇到的挫折与荆棘;工人们引吭高歌,拉着铁滚一往无前,象征着即使面对再艰难的道路,即使脚下是再泥泞的道路,也不会减弱我们对自由与光明的渴望。虽然个体的力量太过渺小,但星星之火,必然可以燃起希望的光芒。影片最后,铁滚在金哥等工人们的牵拉下,一往无前地向前压去,他们眼神坚定,积极乐观。此时敌军的飞机来袭,疯狂地向工地上的人们扫射,除了丁香之外大家都壮烈牺牲了。此时,导演挣脱了纯粹叙事的限制,让大家又重新“站了起来”,重新拉起铁滚,唱起熟悉的《大路歌》向前走去,使得影片具有浪漫感伤的优美之情的同时,又增添了沉雄古逸的壮美之意。
(三)从个人情感空间到公共话语空间:空间意象的审美嬗变
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反对将空间视为社会关系演变的容器或平台,反之指出空间是社会关系至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空间既是历史发展中生产出来的,又随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结构和转化。[ 4 ] 418电影中的空间,不仅是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景,也象征着当时社会的文化背景与精神。对影片中一系列场景所形成的空间意象进行分析,可以更好把握电影的内在意蕴以及美学风格。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受到殖民势力的入侵,东西文化的碰撞让上海经济文化得以空前繁荣。这样特殊的社会背景自然受到了很多导演的关注,电影《神女》亦是如此。在影片《神女》中,房间、学校、上海街头等场景频繁出现,造就了影片独特的艺术魅力,建构了一组组独特的空间意象。
个人情感空间“房间”对于阮嫂来说既是温暖的“家”也是禁锢的“桎梏”。“房间”给予阮嫂生活的温暖与活下去的勇气,在还没有搬家之前,阮嫂的房间中有鲜花点缀、婴儿摇篮以及样式繁多的旗袍,还这不仅展现了当时上海女性的精致生活更象征着阮嫂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后受到地痞流氓的威胁,阮嫂被迫搬走,搬家后的房间显得些许落寞,没有昔日的鲜花、艳丽的旗袍,只剩下七穿八洞的墙壁、昏暗的灯光,此时的房间布景也寓意着阮嫂压抑的内心和凄惨的人生命运。另一方面,房间意象在影片中也是封闭、禁锢的桎梏。当阮嫂在街头寻觅买春客时遇到了巡警,为了躲避巡警的追捕,无意中闯进了地痞流氓的房间,流氓对阮嫂打量一番后识别出她的妓女身份,要求阮嫂留在这里。此时的房间意象更像在诉说偌大的上海却没有给阮嫂这类女性留下一方生活乃至生存的空间。
相较于房间意象而言,学校意象显现出群体化的特征,是上海社会的缩影。阮嫂即使从事最卑贱的工作也要挣钱送孩子去学校念书,希望通过知识改变自己与孩子未来的命运。在学校,孩子因为母亲的职业遭受同学与老师的歧视与排斥。当阮嫂到学校时,也受到了同学家长的冷眼相待,唯独只有校长十分理解与支持母子二人。正直、善良的校长给阮嫂带来了慰藉,也为影片增添了几分暖色调。可好景不长,校董们考虑到学校的声誉,维护好校风,为将阮嫂孩子赶出学校,不惜把校长也开除了,仅存的温暖也如昙花一现般逝去。在影片中,学校空间多次出现,通过学校来呈现上海的人文风情是一个较为巧妙的视角,在学校空间中不仅有人物与人物的矛盾,更激烈的是这个时代观点与观点的冲突,凸显了时代与神女的压迫。
公共话语空间“上海街头”也是影片中多次出现的地方,在一开始便交代了故事发生的主要背景与环境。夜幕低垂,歌舞升平、灯红酒绿的上海街头充满了欲望,这是阮嫂拉客的地方,一头新潮的发型、一身灿漫的服装,伴随娴熟与老练的手势,阮嫂游弋在上海街头,等待着买春客的到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一个被西方殖民的城市,被观看的空间,女性一度被物化为男性消费的商品,其生存问题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在人来人往的上海街头,阮嫂站在风中显得有些落寞。白天她是一位慈爱、善良的母亲,夜晚她是从事卑贱职业的妓女,神女的形象在这样强烈的反差中塑造得更加饱满。上海街头这一空间意象,为人们的交际提供了场所,显现出公共空间中的消费特征。
从“房间”的私人空间意象到“学校”的群体空间意象,再到“街头”的公共空间意象,《神女》中反复出现的空间意象不仅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背景与环境,也象征着那个时代的上海城市氛围与精神内蕴,更诠释了不同空间之下,神女复杂的内心冲突与悲剧命运。通过对影片中空间意象的把握,能够更好感受影片在空间语言下所营造的艺术意蕴。
二、“象外之象”的暗喻:听觉意象的情境交融
(一)重章复沓:听觉意象的抒情造境
中国古典诗词中诗人常常借用声音来抒情造境,比如张继的“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李白的“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孟郊的“飒飒微雨收,翻翻橡叶鸣”等,也形成了诸如“雨打芭蕉”“月落乌啼”这样的声音意象。声音与影像的配合,也能激荡起多样的艺术境界。在影像中,导演可以借助音乐的节奏以及音乐段落的复沓来营造出一种特殊的意境,用音乐与影像所交织而成的韵律勾画出情景交融、主客合一的“无我之境”。
孙瑜的影片被许多人誉为是“诗人电影”[ 5 ] 100。在孙瑜的主要代表作《大路》中,工人们修路以及拉铁滚的场面常常伴随着激昂的《大路歌》和《开路先锋歌》,渲染了劳动人民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复沓的音乐使影片呈现出一种诗的结构,具有强烈的情绪感染力。在影片的一开场,一群筑路的工人在挥舞大锤,拉动铁滚、劈裂山石,并伴随着宏亮的开路先锋之歌,歌声响彻山间。“轰!轰!轰!哈哈哈哈……轰!我是开路的先锋;轰!轰!轰!哈哈哈哈……轰!我们是开路的先锋!不怕你关山千万重……”高亢的歌声,在一开场便奠定了影片明朗的浪漫主义风格。当金哥决定去乡下修公路,他们扛着工具,高唱着《大路歌》:“哼呀咳嗬,咳嗬咳!哼呀咳嗬吭,嗬咳吭!大家一齐流血汗,嗬嗬咳!为了活命,哪管日晒筋骨酸,嗬咳吭!合力拉绳莫偷懒,嗬嗬咳!团结一心,不怕铁滚重如山,嗬咳吭!大家努力,一齐向前,大家努力,一齐向前!”悲壮的歌声荡漾在山间,此处导演多次采用远景搭配特写的两级镜头,营造出强烈视觉效果,抒发了工人们自强不息、奋进向上的精神气质。值得注意的是,在影片结束时,当金哥等人被敌人的飞机扫射身亡后,只有丁香还幸存着,她驻足望着倒下的工人们说:“不!他们还没有死。”此时,伴随着《大路歌》响起,大家又再次站起来了,他们继续欢声笑语,一同拉着铁滚压平一路的崎岖与碎石,不断勇往直前。显然,此时的《大路歌》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电影语言,而是形成了具有象征意味的声音意象,在多次复沓中超越了原本影像表意的有限性。《大路歌》和《开路先锋》由聂耳作曲,据导演孙瑜回忆,在拍摄演员唱歌镜头时,聂耳同志流着大汗不断在工人之间和悬崖之上跑上跑下,指挥着打节拍,使雄壮的歌声与富有节律的人物动作和画面结合在一起,给观众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力。
(二)疏密相宜:节奏的情境暗喻
伯里曼指出:电影主要是节奏,它在段落的连接中呼吸。“节奏就是个‘调味剂’,可以增强整个故事发展的气势,烘托出矛盾与冲突。因为节奏的变化轻重和缓急,所以才激起观众们在内心产生共鸣。”[ 6 ] 39早期中国诗电影对节奏的处理让人体验到一种独特的美,虽在情节交替中没有较为鲜明的“缓”与“急”,但整体在叙事上的留白与铺陈处理也使得电影脱离了苦闷之感。在绘画速写上,艺术家讲究画面线条要有“疏密疏”的节奏,才能使作品具有一种“透气”的境地,这种创作手法放在早期中国诗电影对影像的处理上也同样适用。在影片长镜头与蒙太奇的处理中,一张一弛、一呼一吸的节奏使观众沉浸在影片之中,感受到生活的态度与情感。
史东山导演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导演行云流水的镜头语言,使影片整体磅礴大气。玲玉不顾姨父姨母的阻难毅然参加救亡演剧队,为抗战一线的战士带来鼓舞与慰藉。在抗战过程中与同伴音乐家高礼彬相爱。等抗战胜利后二人再度返回上海时发现,此时上海完全和自己理想的战后社会有很大出入。虽然生计艰难但他们也坚决不向黑暗屈服,誓死用生命捍卫社会的底线与公平。在传递这种情绪与价值时,导演并没有通过重音、特写等视听手法,而是巧妙地通过张弛有度的节奏来带领观众走进影片与人物,不自觉接受了其中的情感。整个影片借玲玉奔赴的足迹徐徐展开,在抗战时,战争的紧迫穿插演剧队的艺术表演,虽有失去生命的危险,但也有热血青年的毅力。他们苦中作乐、炮火中书写青年志气,不仅使得影片段落衔接流畅,而且对观众情绪的调动也很合适。影片最后,当大家一同寻找玲玉并送到医院生产时,高礼彬已经身患重病,玲玉身体状况也不佳,大家围在病床前,伴随着窗外凛冽的寒风,玲玉说:“你们不要为我难过,你们今后的责任还重得很”。此刻,故事好像又回到了影片的开始,只是如今要扛起重担的是他们的第二代。在回环往复的手法中,观众似乎感受到了另外一个故事,留下无限遐想空间。
吴贻弓导演的《城南旧事》讲述的是民国时期英子童年时代的故事,导演通过运用空镜头、长镜头、叙事留白等的艺术手法,创造出淡然幽远、哀而不伤的散文化风格。影片围绕英子的三个小故事展开:一是英子与惠安馆“疯女人”秀贞和小伙伴妞儿的故事,二是英子在杂草地遇到“小偷”并与之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三是亲如家人的宋妈因为失去儿子小栓子和女儿后不得不回到家乡离开英子的故事。影片虽呈现了三段故事结构,但整体的叙事性却被弱化,呈现出“留白之美”。三段叙事的起承转合中,节奏也形成一定的韵律,渲染了影片的情感与氛围。尤其在影片最后,伴随着漫山红叶的叠化与一曲送别,思念与乡愁仿佛都交给了飞舞的红叶与流逝的时光,“静”中藏“动”,“动”中含“静”,一切情愫皆跃然画面之上。淡淡的离愁、浅浅的乡思,巧妙的节奏处理给予观众情感深处的触动,引发无穷的想象与联想。
三、“象外之境”的触兴:审美意象的叙事突破
(一)空间意象的叙事生成
“死气沉沉的小城,春心荡漾的故事。”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讲述的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江南一个偏安一隅小城发生的故事。丈夫戴礼言与妻子周玉纹结婚八年来都过着寡然无味的生活,丈夫患病终日郁郁寡欢,夫妻二人分居多年,彼此都失去了对于生活的希望与信念。但志忱的到来,打破了这样的氛围,注入了一丝生机。志忱是礼言的昔日好友且还是玉纹的旧时情人。见到玉纹时,不仅唤起了志忱心中昔日的情愫,同时也让玉纹内心泛起阵阵波澜,二人欲迎还拒、欲拒还迎。发乎情、止于礼,在故事最后,志忱还是选择了离开小镇。《小城之春》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费穆先生通过“城墙”“旧园”等小城意象,营造出淡淡的哲思与浓郁的诗意,达到“象外之境”的营造。
花褪残红、断壁残垣、芳草萋萋……影片中这些环境氛围不仅增强了画面的诗韵与张力,更形成了独特的意象符号,在电影语言与诗意渲染下超越了自身“象”的有限性,成为了独特的视听符号,使影片具有了“空间之美”“氛围之意”“时代之思”的美学境界,完成了从言、象、意进而到“境”的艺术创造。
首先“城墙之象”所营造的“空间之美”。破败的城墙、衰败的家园是影片中玉纹、礼言的主要生活场域,但影片借助了戏曲艺术对道具的处理,充分吸收了中国古典美学写意的风格,仅借助一围城墙显现出小城的真实存在。玉纹、礼言、戴秀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小城,从未走出城墙,只有志忱从小城外走来但最后又离开了。影片开场,玉纹旁白道:“住在一个小城里面,每天过着没有变化的日子,早晨买完菜,总喜欢到城墙上走一趟。”城墙是束缚玉纹的一个“围城”,同时也是玉纹心灵的寄托。只有在破败的城墙上走一走,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玉纹内心压抑的情绪才能得以宣泄。与理想的江南人家不同,经过战争的摧残之后,戴家早已是断壁残垣,一大半的房子被摧毁,就连正房也没有了。残破的旧园与消失的正房,象征着戴家家族势力的衰败,也隐喻着封建旧制度的瓦解与凋零。“少爷”礼言的首次出现是伴随着仆人老黄寻找的踪迹,通过废园的墙洞前景之后才发现礼言正坐在一片废墟之上。礼言瘦弱的身子与虚弱的语气,像是在诉说知识分子的无可奈何与当时家族、社会的萧条落寞。破败的城墙、衰败的家园除了是人物的生活环境之外,也隐喻着玉纹沉寂的爱情、礼言抑郁的心情,更象征着二人似有似无、似断非断的关系。影片中有大段故事情节都发生在城墙与旧园之中,在导演的勾勒下,一围城墙、一方家园不再只是单纯意义的物象,而是如虚实相生、气韵生动的中国山水画一般,彰显出元气流动、朦胧感伤的空间之美。
其次“城墙之象”所渲染的“氛围之意”。《小城之春》的编剧李天济在《为了饭碗干上电影》一文中表示《小城之春》的创作受到了苏轼《蝶恋花·春景》的启发[ 7 ] 83。词中写道:“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苏轼上阕写景,下阕抒情,仅一墙之隔,墙外“行人”尽显惆怅,全词带有朦胧的哀怨伤感之情。费穆导演在影片中也巧妙地借助城墙意象将几种不同情愫巧妙地呈现出来。城墙之外是玉纹向往的自由世界,城墙之内却满是压抑的生活之困。情景交融、借景抒情的手法使得影片在浪漫感伤中蕴涵哀怨,在清新隽永中透出含蓄婉约。费穆在《略谈“空气”》一文中表示:“电影要抓住观众,必须是使观众和剧中人的环境同化,为达到这种目的,我以为创造剧中的空气是必要的。个人以为,创造剧中的‘空气’,可以有四种方法:其一,由于摄影本身的性能而获得;其二,由于摄影的目的物本身而获得;三,由于旁敲侧击的方式而获得;四,由于音响而获得”。在《小城之春》中,城墙与家园中的残垣虽是一道“阻隔”,但“空气”沟通起了墙里墙外、房里房外,是一种“不隔”。剧中有一个经典的段落是玉纹、礼言、志忱与戴秀泛舟于小河之上时,波光粼粼的湖面搭配曼妙的歌谣,“空气”中满是喜悦与甜意,费穆导演细腻地捕捉到了此时人物心理的微妙变化,借助“空气”以及巧妙的构图营造出行云流水般的诗韵。
最后“城墙之象”带来的“时代之思”。《小城之春》的故事发生在抗战胜利后的江南小城。经历战争后的生活并不景气,长满荒草的城墙便是很好的见证。“然后由于这部作品反映出的情绪与当时影圈的政治气候格格不入,被不少影评家称之为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没落阶级颓废情绪的渲染;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认为《小城之春》‘反映了费穆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艺术家的两重性及其软弱的性格,反映了他在解放战争的伟大时代中心情的苦闷、矛盾、灰暗和消沉。’”[ 8 ] 3561948年“正是解放战争迅速发展、人民运动处于高潮的时候”[ 9 ] 271,此时“左翼电影业已占据主流,而‘诗人导演’费穆所执导的《小城之春》却显然不合时宜,与奔腾活跃时代脉搏南辕北辙。”[ 10 ] 65《小城之春》真的“生不逢时”?从心理学维度上看,战争之后,人们陷入生活的苦思与压抑,急迫地需要情感的寄托以及精神的抚慰,而放眼望去《小城之春》正是这样一个作品。影片中城墙除了作为重要的物象存在以外,更隐喻着时代的发展之下个人的追求。正如年轻的戴秀所言:“沿着城墙走,有走不完的路!在城头使劲地向外望,就知道天地不是那么小!”编剧李天济回忆说,他写本子时的剧名叫《苦恋》,后又改成《迷失的爱情》,主要想表达内心深处郁结的苦闷失意,怅然无奈的情绪,以及用这种淡淡的哀愁来重重包裹几颗渴求新生活的赤红的心。
(二)人物形象的审美生成
吴永刚导演的处女作《神女》是我国默片时代的一部佳作,影片通过视听语言的巧妙运用,塑造出一个卓然独立的“神女”的形象,使影片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影片在多个段落反复出现一个跪在地上双手反缚在背后的女子在为婴儿喂奶的浮雕形象,配以舒缓、冷静的音。画面中女子即使在临死之前,仍不忘哺育于子,足以可见其伟大品质,也借此隐喻阮嫂无私的母爱与高贵的精神。同时影片在展现阮嫂的妓女身份时,也较为内敛含蓄,凸显出神女的无奈与隐忍。在景别上,多采用远景与局部的特写镜头,比如在阮嫂上海街头接客时,画面中只是阮嫂的高跟鞋和陌生男子脚的特写来表达阮嫂接“生意”的行为。在拍摄角度上,多使用俯拍加远景的方式,比如在阮嫂第三次接客时,导演仅通过展现俯拍阮嫂的头部并和客人一同走进酒店的画面来交代娼妓生活。虽然是含蓄的视听手法,却孕育了一个立体鲜活的“神女之象”,使得影片呈现出一种朦胧感伤之韵。周星在其主编的《中国电影史》中评价《神女》:“整体风格的内敛从容是民族意蕴的表现”,“蕴含的悲剧震撼力深得中国文化魅力精髓”。
在百年中国电影史上,有一座城市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缔造了多个电影史上的传统,滋养了一大批电影工作者,这便是上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处于被殖民与侵略的境地,女性的生存问题是社会关注的焦点,《神女》便是诞生在这样的语境之下。白天的阮嫂是慈爱、伟大的母亲;夜幕低垂,阮嫂穿上艳丽的旗袍,游弋在灯红酒绿的街头,四处寻觅嫖客,是男性观看的客体与消费的商品。虽然阮嫂自身从事最卑贱的职业,但仍要挣钱为孩子念书,希望以此改变孩子和自己未来的命运。可惜社会却并未给出一条出路,善良的校长最后也没有免于辞职的结局。“《神女》的题材是中国电影史中少有的,影片把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卖身女作为表现对象,通过特殊身世展现社会面貌,以生存所要面对的复杂艰难来揭露人生痛苦,由此展开整个人生的悲欢离合,已经显示影片的独特。对社会世相的冷静描摹,对残酷压迫的不动声色的表现,通过个性世界表现生活世界的黑暗,使影 片具有直接的触感,超出了一般作品的震撼力”。[ 11 ]
“《神女》的风格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吴永刚的艺术观、艺术追求的产物。在《论电影布景》一文中,吴永刚写道:‘布景是要忠诚现实,而不是模拟现实。真的方法,在设计之先,要对剧本做详尽的研究,深切地理解了它,然后根据剧中的需要与美的原则,从现实或意象中去构想基干,以暗示的方式传达某一场面’;‘好的布景,常以粗线条构成;粗枝大叶,没有繁琐无谓的装饰,也不是炫耀美丽的,而自然会给予人一个好的印象’”。[ 12 ] 56可见,《神女》的艺术风格并非偶然造就,而是导演吴永刚的艺术创作的产物。注重从现实出发映照社会,从人物本身的社会背景延伸出时代的反思,以大风格替代细枝末节的繁复,以独立的追求超越无谓的束缚,这是神女本身的高尚品质,更是《神女》崇高的艺术魅力。
四、从中国诗电影出发:建构东方影像主体性
(一)诗意:东方文化精神的影像表现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认为,东方这个概念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纵观世界电影史,常常用“他者”来指代东方电影,尤其是东方文化的影像表达。中国、印度、日本等东方国家在电影工业上较早取得突破,形成了民族电影市场,积淀了东方影像美学精神的基础。虽然电影是一种“舶来品”,但电影艺术本身仍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与风格,我们仍需在电影艺术本土化的过程中,立足自身民族文化传统建构东方影像美学。学者钟大丰在其主编的《文化亚洲:亚洲电影与文化合作》一书中对东方精神在电影中的表现作出了详尽的表述,他认为电影中的东方精神难以通过浅层面的娱乐却天生具有思辨和了悟的特征。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诗意文化的含蓄精神表现;第二是诗意文化的跳跃思维暗合电影的优势结构特点;第三是诗意文化的散淡风格符合电影人性探索的视点。钟大丰认为东方精神中的诗意艺术不会在商业潮流中衰亡,甚至在经济迅速发展过程中、观众对于东方精神诗意的渴望会愈加强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东方文化精神在影像中的表现主要为一种含蓄节制、自然淡雅、情景交融的诗意。
(二)中国诗电影建构东方影像主体性的探索与实践
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到:“诗的题材并不是科学抽象的一般,而是体现与个别具体事物的理性,所以诗始终要受民族特性的制约。民族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方式也就是诗的内容和表现方式”。[ 13 ] 26由此可以看出,诗电影的本质并不是影像形式所呈现出的诗意或诗性,而是本身真正在传递民族的内容。徐复观在《儒道两家思想在文学中的人格修养问题》中曾说:“各民族的文学创造,必定受到各民族传统及流行思想的正反深浅各种程度不同的影响。”[ 14 ] 5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电影创作。中国诗电影自诞生之日起便深受中国传统美学文化的影响,电影通过一系列审美意象的并置,以达到诗的韵味、画的意境,彰显出东方美学的自在性。
中国诗电影虽与世界诗电影虽具有内在的一般性,但显现出浓郁的东方美学气质,承袭了东方美学基因,这是中国诗电影独有的个性,也是中国诗电影与生俱来的民族特色。面对“世界电影”“西方电影”的反复冲击与影响,虽然已有不少中国诗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从长远而言,仍然需要从中国诗电影出发进行思考,建构东方影像自身主体性,寻求亚洲电影“作为方法”的突围路径。
对于东方影人而言,如何在电影本土化发展中讲好东方故事、彰显东方风味、呈现东方特色、展现东方气派是摆在面前的重要课题。意象、意境是叶燮提出的“艺术至境”的基本形态,也是最具东方韵味的审美范畴。在中国诗电影发展历程中,诗电影的结构与形式虽不断发生变化,但对意象、意境的追求是艺术家一直以来的不懈追求。中国电影创作者们通过对影片叙事节奏、空气、镜头、色彩、构图等视听语言的把握,建构出具有浓郁东方影像美学气质的佳作。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杨花恨》《大路》《神女》等电影全片充满淡雅之意,既朴素简练也充满悲情。导演通过对叙事节奏的巧妙把握,在写实与写意之间开创出一种全新的影像风格,贴切了东方美学性格中浪漫感伤、秀丽柔婉的特点;到了四十年代费穆导演就“空气”这一源于东方文化的新命题开始了对东方影像美学的探索。电影《小城之春》化景为诗、化诗为情,将诗意在影像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建构出异质于西方电影的东方影像风格,这是中国诗电影发展中的第一个高峰。在影片中,城墙是小城与外界之间的“阻隔”,但画面中连通的“空气”却形成了“不隔”,在隔与不隔之间婉约含蓄的情愫跃然于画面之上,营造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艺术境界。有学者认为:“该片无论是影像叙事还是精神内核层面,都是中国电影史上最具有‘东方’审美特色的标杆。”[ 15 ] 20《小城之春》始终在东方文化的观照下叙事,节奏张弛有度、起承转合恰到好处,有虚有实,耐人寻味;五六十年代的《林家铺子》《早春二月》创造性地丰富了诗电影的艺术语言,具有抒情性与象征性的镜头,展现出悠远的意境,建构出一个情景交融的意象世界;“第四代”与“第五代”导演的创作,善于用“优美的、色彩流丽的影像语言,来表达对往昔年岁,已逝青春美好理想的感叹。”[ 16 ] 104吴贻弓导演的《城南旧事》借助中国传统艺术中的“留白”手法,不仅在视觉上多处使用空镜头作为“留白”,也听觉上使用“静默”的处理,产生“虚实相生,无画处皆生妙境”的艺术境界。在从英子黑暗雨夜中晕倒过渡到英子躺在医院时,导演采用“哎 看报嘞 看报嘞 买报瞧嘞 瞧这母女两人让火车给碾压死”的吆喝,隐晦地表达出秀贞与妞儿被火车撞死的残忍事实, 以“虚”写“实”,恰到好处的留白更增强了影片淡淡的哀愁、沉沉相思的韵味,让人久久不能释然。在张艺谋导演的《我的父亲母亲》中则主要使用色彩来建构东方影像美学气质。在电影中,红色是章子怡饰演的母亲的颜色。红色的袄子、红色的发夹、红色的梁布都代表着母亲热烈的青春以及父亲母亲浪漫的爱情故事。当穿着一身红色大袄子的母亲驻足在漫天飞雪的村口等父亲回来时,鲜艳的红与白雪皑皑的大地形成强烈的对比,冲击观众的视觉,暗喻出当时政治环境的残酷无情。影片在交代“我”现在的故事时则一律使用黑白叙事,这与儿时回忆形成鲜明的比较,渲染出异于寻常的哀伤之情。近年来《路边野餐》《长江图》等中国诗电影在国内国际电影节脱颖而出,凭借的就是独特的东方美学气质。《路边野餐》中多组异质诗词的出现,架构了诗意叙事的篇章,火车、时钟等多组意象的使用,暗喻了时空的交错与疏离。电影《长江图》采用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写意的特点,营造出一种“水墨影像”的质感。水天一色的长江、迷雾朦胧中行驶的轮船、水墨笔触般的村落,多个意象重构了“长江”的内在意蕴,将山水与人情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在万物流动中,一股“气”跃然于画面,增添了影像的诗意,同时也建构了人物复杂的精神世界。
中国诗电影主张的是一种若有若无,欲说还休的美妙意蕴,追求的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艺术境界,即宋代严羽所说的:“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相”,也就是一种“初发芙蓉,自然可爱”之美。中国诗电影借鉴吸收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把民族内蕴熔铸到影像艺术的实践中,使影片充满东方美学气质。另一个角度而言,中国诗电影的美学创作是建构东方影像主体性的生动写照,东方影像具备内在的自觉性、自主性。在全球化背景下,注重民族韵味与本土文化的融入,观照自身美学发展诉求,建构东方影像主体性,是中国电影乃至亚洲电影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童庆炳. 文学理论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2]王国平.论诗电影[J].当代电影,1985(6):40-47.
[3]张华.揭开《神女》的面纱——《神女》在1934[J].当代电影,2008(7):89-93.
[4]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 第三版.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5.
[5]胡菊彬.影坛“诗人”孙瑜——兼评影片《大路》[J].当代电影,1987(5):102-108.
[6]赵鹏.漫谈电影节奏艺术[J].电影评介.2012,(17):39-40.
[7]李天济.为了饭碗干上电影[J].电影艺术.1992,(4):80-85.
[8]黄会林 周星. 影视文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9]程季华. 中国电影发展史[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1.
[10]范志忠.《小城之春》:欲望缺席的年代[J].当代电影.2005,(5):64-66.
[11]周星:《〈神女〉:造就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北京日报》,2005年6月21日,第014版.
[12]木子.《神女》——我国默片的现实主义佳作[J].电影艺术.1985,(1):53-56.
[13]黑格尔: 美学(第三卷下)[M]. 朱光潜译 . 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商务印书馆,1984.
[14]徐复观. 中国文学精神[M].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15]王赟姝.中国电影诗意化的美学追求——论中国电影创作的“优美浪潮”[J].电影新作,2018(4):19-26.
[16]陈旭光.论第四代导演与现代性问题[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102-112.
[责任编辑:马好义]
收稿日期:2023-05-03
作者简介: 谭聪(1998-),男,四川乐山人,四川电影电视学院新媒体学院助教,主要从事影像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