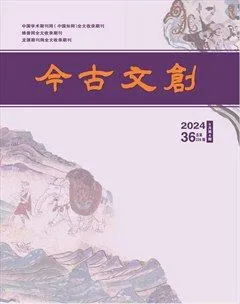斯特鲁伽茨基兄弟《路边野餐》中的隐喻叙事
【摘要】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路边野餐》在苏联科幻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隐喻手法的使用是该小说的一大亮点。本文将该作品中的隐喻分为基础隐喻与特色隐喻,并分别进行含义探析。发现该作品中对“路边野餐”“造访带”及“金球”等事象的描写已不限于故事的情节本身,而是作为一种隐喻的存在,展现了20世纪工业文明发展背景下,作者对科技无序发展、自然环境遭受破坏的谴责以及对人类前途命运的忧思。
【关键词】斯特鲁伽茨基兄弟;《路边野餐》;隐喻;隐喻叙事
【中图分类号】I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6-000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6.002
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哥哥阿尔卡基·斯特鲁伽茨基(Аркадий Натанович Стругацкий, 1925—1991)和弟弟鲍里斯·斯特鲁伽茨基(Борис Натанович Стругацкий,1933—2012)是苏联时期最具影响力的科幻作家。阿尔卡基曾在军队从事翻译工作,鲍里斯为天文学家及计算机工程师。他们自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进行科幻文本写作,联袂创作了《消失的星期天》 (Понедельник начинается в субботу,1965)、《蚁巢中的甲虫》 (Жук в муравейнике,1979)等大量优秀科幻作品。其荒诞幽默的叙事风格深受果戈理、布尔加科夫、卡夫卡等文学巨擘的影响[1],笔触聚焦人与社会,辅以科学幻想,注重人心探索、人类命运及自然生态等现实议题,丰富了苏联科幻文学主题的广度与内容的深度,是名副其实的“现实主义科幻文学(ре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фантастика)”。
《路边野餐》 (Пикник на обочине)出版于1972年,是斯特鲁伽茨基兄弟最负盛名的科幻中篇小说,曾被导演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А·А·Тарковский, 1932—1986)以《潜行者》之名搬上大荧幕,同样也是近年风靡全球的俄罗斯制作的苏联题材科幻动作游戏《原子之心》的重要灵感来源之一。该部小说讲述了未来世界里外星人在地球野餐后引发的故事。外星人野餐离开后留下了“造访带”(Зона Посещения)。“造访带”里遍布外星人遗弃的“野餐垃圾”,充斥着各种放射性物质和强腐蚀性液体,附近的居民竟也患上各种骇人的疫病或发生基因突变,并被迫搬出曾经热闹秀丽的家园。以主人翁雷德里克·舒哈特为代表的“潜行者”们冒着各种骇人的死亡风险进入“造访带”寻宝,靠偷取并倒卖外星人遗弃的垃圾为生,然而活着走出“造访带”的潜行者寥寥无几,幸存者的后代也会发生变异。这部小说于14年后,即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惨案产生了奇迹般的呼应,不仅给这桩惨案发生后的世界提供了描写语言,且对隔离区奇异凋败的景观及复杂沉重的情绪氛围进行了预判。
作为科幻文学文本,《路边野餐》中蕴含的大量生态与科技伦理隐喻在人类面临着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的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因此,本文从基础隐喻与特色隐喻的角度出发,对小说中呈现的生态隐喻、科技伦理隐喻进行解析,力图深入对《路边野餐》中隐喻手法的研究。
一、《路边野餐》中的基础隐喻
隐喻的产生由来已久,可追溯至苏格拉底时期,它是一种“基本而普遍的生存方式”[2],是“根据不同种类的域来理解并构建一种体验域的过程”[3]。文学创作过程中隐喻的使用能够产生别出心裁的文学效果,赋予文字似是而非的朦胧美感。《路边野餐》中便使用了大量的隐喻,可将这些隐喻分为基础隐喻和特色隐喻。基础隐喻是文本中贯穿全文的隐喻,各自构成全面的隐喻体系,是文本中隐喻的基础。
其一,小说的名称“路边野餐”即是最为直观的隐喻之一,是贯穿全文的意象,超出了文本本身的含义。值得一提的是,自从事科幻创作以来,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就以对人类宇宙地位的清醒认知而著称,早在其首部小说《外来者》(Извне,1958)中便描绘了人类与毫不关心人类及其成就的外星人的会面,这种人类的宇宙边缘地位同样在《路边野餐》中得到了体现。
小说中“路边野餐”表面上指外星人路过地球并在此进行的一次随意的野餐,“一次在宇宙的某条小路边上举行的野餐”[4]155。小说第三章中雷德里克·舒哈特的朋友努南进行了一个假设,一群年轻小伙与姑娘驾车沿乡间小路驶至一片草地,从车上搬下酒瓶、野餐篮子、晶体管收音机、照相机……点起篝火、支起帐篷、放起音乐,第二日留下一地的野餐垃圾后离开。整夜惊恐注视他们的那些动物、小鸟、昆虫爬出巢穴,将他们遗弃的满地的油、旧火花塞、散落的滤油器、烧坏的灯泡等物品视为高等科技产品。这些人类习以为常的生活中的小物件,早已远远超出森林中小动物的认知,是给它们带来恐慌的“超越时代的残忍神迹”[4]156。其中,草地象征着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小动物们象征人类,野餐垃圾则象征着科学技术。[5]80在来自高等文明的太空来客眼中,人类之孱弱无力无异于驮鼠,且毫无兴趣与人类进行交流,而人类将他们留下的垃圾奉若神迹,以期通过研究“野餐垃圾”获得财富、改善生活,但却付出了破坏生态环境、被迫远走他乡的惨痛代价。
其二,是贯穿全文的主要线索“造访带”,小说讲述了主角雷德里克·舒哈特三次出生入死潜入“造访带”寻宝的故事,文中“造访带”即指外星人野餐后留下“野餐垃圾”的区域,其隐喻义不难辨明,它象征现代科学技术及其给人类生态环境带来的巨变,体现了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强烈的生态意识。“造访带”中目不暇接的高科技野餐垃圾是“潜行者”们趋之若鹜追求的对象。小说中,雷德里克在与一位移民中介争论时,曾引述已故同事基里尔的一段话:“现在,这里是一条通往未来的通道,我们从这鬼地方捞出的东西,将会彻底改变你们那个糟糕透顶的世界……先进的知识将会从这个地方喷涌而出,一旦弄明白那些知识是怎么回事,我们会让所有人变得富有,人类将飞向群星,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这就是这个鬼地方的价值……”[4]57可见,在雷德里克及基里尔心中,科学理性已被蒙上极度神圣化的面纱,这种对科学的极端崇拜将导致人类自身的异化。正如身为“潜行者”的雷德里克虽对作为鬼地方的“造访带”进行了高度赞扬,但在事实上却背负了“潜行者”后代变异的沉重代价,他的女儿小猴浑身长满金色长毛,并逐渐失去语言与理解功能,与猴无异。
小说中的诺贝尔奖得主,科学家瓦伦丁·皮尔曼也曾如此描述人类寻宝“造访带”的行为:“我们在火中取栗(таскать каштаны из огня)的时候,有可能稀里糊涂地掏出某种地球上的生命难以忍受的东西。”[4]150可见,一如工业革命以来大量欧美科幻文学作品对科学理性的反思,斯特鲁伽茨基兄弟也在《路边野餐》中融入了自己对科学理性的见解,即知识可提升人类生活水平与认知空间,但同时也是一种野餐垃圾,用知识改造自然必将在不同程度上破坏自然环境并危及人类自身。
其三,小说中“潜行者”(сталкер)指“造访带”所在地哈蒙特的“居民对那些不顾生命安危潜入造访区,把能找到的所有东西偷运出来的年轻人的称呼”[4]13。这一单词由斯特鲁伽茨基兄弟改编自英语单词“stalker”,灵感来源于英国小说家罗德亚德·吉卜林的小说《一群鲁莽之人》,其主角是一名绰号为“Stalky”(意为聪明的、狡猾的)的不受管束的英国学生,由此不难看出“潜行者”(сталкер)一词具有鲜明的贬义色彩。这种贬义色彩不仅表现在“潜行者”这一职业称谓上,更在各位“潜行者”的绰号上得到了直观体现。《路边野餐》中塑造的“潜行者”形象大多都拥有自己的绰号,并多以此互相称呼,如“秃鹫”伯布里奇、“大猩猩”鲍勃及“四眼”诺曼等等,他们大多不学无术,没有正当职业,具有人格缺陷,如“‘秃鹫’伯布里奇”,打架斗殴嗜酒成瘾,甚至以家暴妻子为乐。
此外,小说核心人物雷德里克·舒哈特(Рэдрик Шухарт)的姓名由来也极富深意,该姓Шухарт易使读者联想到其同根词,犯罪俚语шухарь (打架、闹事)、 шухарить(出卖、耍无赖)、шухарила(为同伙把风的人)等[5]81,如此命名符合其身份与性格特征,小说中,雷德里克在进行第三次“造访带”寻宝时,为成功安全渡过“造访带”中的“绞肉机”一关,便出卖同伴,设计并牺牲了同行者亚瑟的性命。在当时的未来世界,谋生方式绝非仅限于成为“潜行者”。然而,物质水平的匮乏与精神世界的困顿迷茫,导致他们不确定自己的社会地位,缺乏正确的自我认知,从而做出超脱法律和道德界限的行为。于是为了追求高额收益,他们选择冒着后代变异和威胁生命的风险谋生,甚至不惜选择借机牺牲同伴性命来为自己留下活着将宝物取出的机会。
这样的人物形象塑造意味着小说中的“潜行者”群体表面上是“甘愿将自己置于人类、知识以及圣灵的祭坛上,一群把生命献祭给科学的英雄”[4]29,实乃在生命线边缘沉浮、在危机中自渡且不择手段的逐利者和生态罪犯。
二、《路边野餐》中的特色隐喻
在深入探讨《路边野餐》中隐喻体系的构建与展开时,不难发现,除却为故事骨架提供了坚实支撑的基础隐喻之外,为完整文章隐喻体系、优化文章的表达效果,斯特鲁伽茨基兄弟还在基础隐喻的基础上,设置了大量特色隐喻。这些特色隐喻虽未贯穿全文,但却往往作为关键意象出现于小说情节的关键节点,为情节转折提供了预兆或暗示。
其一,《路边野餐》对“造访带”里各式各样的高科技垃圾进行了详细描绘,如“黑色火花”“死亡之灯”及“蓝色万应药”,其中不乏富有深层隐喻的意象。如“造访带”中令所有“潜行者”梦寐以求的“金球”(Золотой шар),它据传能够实现一切愿望,隐喻了由科学理性打造的乌托邦。亚瑟和迪娜正是潜行者“秃鹫”伯布里奇成功打破“潜行者”后代变异的魔咒、向“金球”诚心祈求得来的完美孩子。小说第三章中,在伯布里奇的鼓动下,主角雷德里克为治疗发生变异并浑身生长毛发的女儿小猴,摒弃了曾经不再担任“潜行者”的决心,再次踏足“造访带”并寻找“金球”。他曾对同行的亚瑟说:“金球只会满足你内心深处的愿望,就是那种如果实现不了,你随时都会从桥上跳下去的愿望!”[4]190希望奇迹出现,女儿恢复正常便是唯一一个支撑他不至于彻底消沉下去的愿望。金色常在20世纪的俄罗斯诗歌中“象征着生与死……一方面指生命的红金色,具有寒冷、刺骨的含义;另一方面形容死亡或者疾病的褪色和脏乱的色彩感觉”[6],在《路边野餐》中,金色成为连接现实与理想、生与死的桥梁。正如雷德里克在首次进入“造访带”前对助手所说:“潜行者都是些插队进入天堂大门的人。”[4]29对于“潜行者”而言,“金球”使“造访带”成为能够实现一切愿望的天堂,它能使变异的风险彻底远离自己的后代,是生命力的源泉。此处“金球”这一隐喻向读者表明,“潜行者”们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一个以科学技术为手段打造的乌托邦[5]82,它能够使疾病褪色、使生死扭转,能够实现一切愿望并创造奇迹,这体现了人类对科学理性的孜孜探寻和对超验世界的美好愿景,既是对人类最原始欲望的投射,也是对理想社会构建的深层思考。然而,真正的乌托邦建构必然离不开人类内在道德与理性的成长,以牺牲自然环境与家园为代价换来的科技进步只能使人类与乌托邦式的奇迹背道而驰。
其二,小说第一章里,雷德里克带领两位国际外星文化研究所的同事对“造访带”进行首次寻宝时,依靠观察所抛出螺母的飞行轨迹和掉落地点来探路,若螺母轨迹无异常,则可按该方向前进,反之则需重抛螺母探路。此处,螺母象征科学理性,三人前进的路则隐喻人类文明的发展道路,通过抛掷螺母探路则反映了科学理性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通过科学实验和观察来获取知识、指导行动,正是人类从原始状态走向文明社会的基本途径。但该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正如螺母的飞行轨迹可能会因未知因素出现异常,人类在利用科学技术改造自然及社会的过程中也会遇到各种意料之外的困难与挑战。这些挑战既包括技术本身的局限性和副作用,也包括人类对如何使用科技成果的伦理和道德考量。
其三,首次探访“造访带”时,雷德里克及同事通过螺母探路成功安全到达寻宝坐标点——一座带有维修站的车库。然而车库蕴含的危险尤甚,这里遍布似燃烧的酒精般不停喷吐蓝色火舌的“地狱黏液”。但这些蓝色火舌与传统意义上的火焰不同,并不产生光亮,反而吞噬周围的光线,使车库愈加黑暗,蔓延着一种浓厚的诡异恐怖氛围。雷德里克的朋友努南推测“地狱黏液”为“胶态气体”,其所经之处将会使一切物体化为同样的黏液。可见,“地狱黏液”呈现出强烈的危险性及破坏性特质。除“地狱黏液”外,小说还描绘了外星人遗留的诸如“燃烧之绒”“捕虫阱”“撒旦之花”等能够使生者瞬间尸骨无存的危险事物。小说借以上隐喻发出震耳欲聋的警醒:对科技的盲目追逐与任意应用将导致自然环境产生难以逆转的损伤和现实世界的扭曲异化。正如尼采所言,理性的出现是因为人类需要为自己整理出一个世界,使其生存在其中成为可能。[7]理性指导着人类社会发展,科技需要理性的制约,否则“由人类理性所创造的科学技术最终将异化为人类理性的主宰”[8]。
三、结语
科幻小说《路边野餐》是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代表作,充分发挥想象,联系社会现实,极富生态哲学深度。具有体验性的隐喻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基本认知方法[9],《路边野餐》中一系列独具匠心的隐喻——不论是作为基础隐喻的“路边野餐”“造访带”及“潜行者”,还是作为特色隐喻的“金球”“螺母”与“地狱黏液”等,都从侧面反映了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对20世纪工业文明时代苏联社会精神风貌的独到认知,渗透了以斯特鲁伽茨基兄弟为代表的优秀知识分子对工业发展道路的深层探察、对人类命运及发展前途的真切忧思,不可不谓科幻文学历史长廊中的佳作。
参考文献:
[1]Саморукова.И.В.Фантастика как генератор событийности:творчество братьев Стругацких и повествовательные модел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прозы 1960-2000 годов[J]//Вестник Самар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2012,№8.
[2]赵一凡.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3]孙毅,王媛.隐喻认知的具身性及文化过滤性[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03):136-143.
[4](俄)斯特鲁伽茨基兄弟.路边野餐[M].刘文元译.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21.
[5]李然,温玉霞.“潘多拉魔盒”:论《路边野餐》的生态隐喻和科技伦理[J].俄罗斯文艺,2020,(03):78-85.
[6]崔晓凤.19、20世纪俄罗斯诗歌中颜色词的象征意义——以普希金、茨维塔耶娃诗歌为例[J].流行色,2021,(10):82-83.
[7]周国平.尼采与形而上学[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8]蔡曙山.论技术行为、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批判[J].中国社会科学,2002,(02):77-86+206-207.
[9]魏在江.隐喻的主观性与主观化[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02):6-11.
作者简介:
刘杨孟仔,女,汉族,湖北人,海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俄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