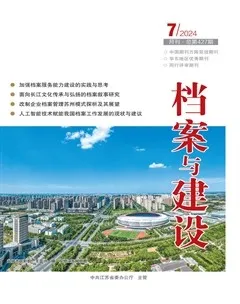记忆、共鸣与理解:红色档案建构政治认同的逻辑进路
摘 要:红色档案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为建构主体的政治认同提供了重要依据。政治认同由初级至高级分为本能认同、情感认同和理智认同三个层次,红色档案通过记忆、共鸣和理解实现政治认同建构,即通过记忆奠基本能认同的底色、通过共鸣唤起情感认同的生发、通过理解达成理智认同的完成。
关键词:红色档案;政治认同;记忆;共鸣;理解
分类号:G270.7
Memory, Resonance, and Understanding: The Logical Pathway of Developing Political Identity Through Red Archives
Chen Fanfeng
( School of Mathematic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1121 )
Abstract: Serving as an essential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identity, red archives possess a distinct political nature. Political identity is categorized into three levels: instinctive identity, emotional identity and intellectual identity. Red archives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identity through the processes of memory, resonance, and understanding. Specifically, memory lays the groundwork for instinctive identity, resonance triggers the emergence of emotional identity, and understanding culminates in the formation of intellectual identity.
Keywords: Red Archives; Political Identity; Memory; Resonance; Understanding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将政治认同定义为“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1],并将其分为由低至高的三个层次,即本能认同、情感认同和理智认同。红色档案作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的忠实记录,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为形塑认知主体的政治认同提供丰富扎实的原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2]。 红色档案是红色资源的重要类型,相关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周林兴[3]、何玲[4]等学者从叙事理论视角探讨了资源开发中的表达及优化策略;赵义良[5]、赵彦昌[6]、桑果果[7]等学者的研究重点是红色档案在思想政治教育和党校教学中的独特价值;朱彤[8]、孙大东[9]等学者从传承红色基因的机理、向度与路径出发,探讨红色档案的重要作用;陈艳红[10]、彭庆红[11]、翟乐[12]从数字人文视域出发阐释红色档案资源的遴选、利用和深度开发;李健[13]、颜涵[14]、黄夏基[15]等学者从媒体传播角度对红色档案的资源内容、体验和效果进行了研究。但将红色档案纳入建构政治认同的相关研究较少,本文将结合现有研究,以本能认同、情感认同和理智认同为基本框架,探讨红色档案建构政治认同的内在机理和运行机制,以期为有效开发利用红色档案资源提供增益性参考。
1 记忆:红色档案奠基本能认同的深层底色
政治认同范畴下的本能认同有别于生物学意义上的本能,本质是主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多重力量彼此交织、碰撞、融合的结果,是“人们对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具有天然的和下意识的归属感”[16]。 本能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认知主体的身份认同。记忆为主体奠基本能认同印染了最底层的色调。记忆的形成是一个集体性和社会性持续建构的过程。自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最早将记忆引入社会学研究,群体及人的群体化存在成为社会学研究的起点和方向,从而实现了记忆与社会框架研究的勾连。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个体是记忆承载的容器,但记忆的产生却非个体心理现象,而是集体持续互动的结果,“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17]。 保罗·康纳顿则指出,传承社会记忆的重要方式主要有两种,分别是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纪念仪式被记忆的部分答案是“一个社群被提请注意其支配性话语(master narrative)表现并在其中讲述的认同特征”[18]。在这里,个人记忆具备了某些认知因素的集体性自传。身体实践又被划分为体化实践和刻写实践,刻写实践即“我们用来储存和检索信息的现代手段,印刷、百科全书、索引、照片、录音带、计算机,都要求我们在人类生物体早已停止发送信息之后,做些什么来捕捉和保存信 息”[19]。阿斯曼夫妇提出了文化记忆理论,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将记忆区分为“热记忆”和“冷记忆”,其中冷记忆的功能是“镇静作用”,即将回忆起的意义附着于有规律性的事物之上。与之相反的是,热记忆具有“刺激作用”,“意义、重要性、值得回忆性等存在于那引起一次性事件,特别是例如骤变、变迁、发展和成长或者衰落、下降、恶化等之中”[20]。综上所述,记忆不是个体性的、心理感观意义上的历史复写,而是一个与社会高度相关、具有集体共创性质的建构过程。
学界认为,在大部分情况下,档案并不能直接化约为身份认同,而是需要通过建构和强化记忆实现转化。记忆通过连接红色档案和认知主体的身份认同,在塑造认知主体的本能认同中起到关键性作用。
1.1 记忆与认知主体身份认同建立天然相关
身份认同是本能认同的重要体现。从修辞学出发,“身份认同”包含“身份”和“认同”。从前者来看,其最初指向“是谁”以及“什么样的人”,是用于区隔其他群体成员的标识和象征,强调的是差异性;从后者来看,其意可延伸出认可、赞同之意,强调的是一致性。在认知主体与他者不断遭遇、交织、合作与博弈的过程中,差异性与一致性不断融合,认知主体的“身份认同”最终形成。记忆具有很强的集体和社会属性,和身份认同的建立是同向共行的关系。
一方面,记忆的共生、共创和共享是身份认同构建的基本前提。法国社会学家格罗塞认为,“无论是主动追求还是被动塑造,有限制的身份认同几乎总是建立在一种对‘集体记忆’的呼唤之上”[21]。这说明身份认同的形成不只是主体运用理性思维纯粹思辨的结果,更多的是认知主体对所处宏观、中观和微观环境所提供的信息进行吸收、批判、加工、整理和内化的实践过程,即构建集体性记忆的过程。主体可以基于利益或其他要素形成一定的共同体,但若论及形成相对稳定牢固的身份认同,构建集体记忆是其无法悬置和架空的环节。记忆共生、共创和共享的过程是认知主体在生产、生活和交往过程中经验累积的内隐,包含了特殊的情感、体验和信仰,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较为稳cu/TnLVtenueVAfyvBKZuw==定并带有鲜明特点的文化标识,而这些文化标识会成为区隔“我群”与“他群”的边界。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文化标识就是“身份”。换言之,记忆为身份认同的建立提供了事实和想象的材料,进而成为群体后继者强化身份认同的心理基础和文化来源。
另一方面,身份认同又是推动记忆再生产的重要动力。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与主体利益锚定、情感确定、价值标定和信仰笃定的过程密不可分,记忆单独或复合上述元素共同构成影响身份认同的重要因子。身份认同一旦建立,群体成员便会基于族群境遇进一步促进记忆的再生产,尤其是在时局多变的动荡年代。例如,近代无数仁人志士挽救中华民族于水火的大义之举成为那个时期一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这些记忆使得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身份认同得以被唤醒并不断强化,而抗日战争爆发后,这种被记忆塑造的身份认同鼓舞着更多的国人去发掘、加工、传播关于中华民族英勇抗争的共同记忆。[22]
1.2 红色档案是形塑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记忆的重要载体
档案学家特里·库克认为“记忆就像历史一样根植档案之中,没有档案,记忆就会摇摇欲坠、对成就的认知就会消退、对过去的骄傲就会消散”[23]。哲学家米歇尔·福柯也认为“历史是上千年的和集体的记忆的明证,这种记忆依赖于物质的文献以重新获得对自己的过去事情的新鲜感”[24]。记忆的形成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档案塑造并分享记忆,群体借此完成身份认同。
红色档案作为在特定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组织、机构和个人进行革命实践活动的原始记录,集中呈现着共产党人一路披荆斩棘的艰辛历程、渗透着共产党人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凝结着共产党人一如既往的革命追求。正是透过这些原始记录,认知主体才能构建起清晰完整、权威可信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探索和民族命运变迁的集体记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无数的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有力佐证。红色档案为认知主体整体建构关于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提供了最为丰富翔实、直接可靠的记忆资源。认知主体通过它们重现峥嵘岁月、实证光辉历史、诠释伟大历程。当然,这些记忆资源并不可简单还原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还需要经过发掘、筛选、鉴定、保存、阐释、开发和利用等环节,才能进入建构记忆的机制。因此,也有学者认为运用档案建构记忆的过程“还包含整个档案形成及其管理活动对社会记忆或档案记忆的构筑”[25]。这些被红色档案所形塑的记忆资源最终成为黏合社会群体的文化资本,促进中华民族记忆共同体的形成。
1.3 红色档案通过记忆参与塑造认知主体的本能认同
记忆是红色档案和本能认同的纽带,认知主体通过对红色档案的体验构建起个体和集体记忆,并在记忆的唤起和共享过程中,其本能认同不断得到确立和强化。值得注意的是,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种单次、单向度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互相作用且循环往复、彼此赋能的闭环系统。阿莱达·阿斯曼认为,“记忆是在三个构成要素的互动中得到形构的,它们分别是‘载体’(carrier)、‘环境’(environment)和‘支撑物”(support)’[26]。就社会性记忆而言,载体是社会群体,环境是群体成员的社会互动,支撑物是“由他们支配的符号媒介建构的”[27]。作为认知主体文化互动场域的重要符号、文本和媒介,红色档案通过制度性安排(如学校教育、党史学习、各类考试等)和生活性浸润(如影视作品、短视频、广播、纪念仪式等)深刻地形塑了国人的记忆结构,成为其“共享的背景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由此影响了群体成员进行社会互动和交往的环境。以抗日战争为例,记载华夏儿女坚强不屈、顽强抗争的原始档案,如战斗通电、电稿、作战命令、战斗经过要图、照片、报纸等,有的成为重要历史教材的插图,有的成为重要纪录片的实证,有的成为某些影视作品或短视频创作的重要参考。2014年,国家档案局发布了专题档案《浴血奋战——档案里的中国抗战》,其呈现以视频形式为主,辅以大量红色档案,详细记录了抗日战争中的一些代表性战役,如卢沟桥事变、平型关战斗、明阳堡战斗、南京保卫战等。这些红色档案在记忆结构中成为一种“支撑物”,一方面构成认知主体满足自我、集体叙事和群体认知的养料,从正向角度主动建构了自我与群体的积极关系,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影响了群体成员讨论这段历史时的舆论环境,形成了约束和规范群体身份认同的道德压力,推拉合力之下最终产生并强化了自身的身份认同。
政治认同是一个多层次概念,在由本能至情感再到理智的连续性推进过程中,情感认同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作用,在培育认知主体的情感认同中,共鸣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2 共鸣:红色档案唤起情感认同的关键动力
情感认同,即“人们对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所产生的热爱、依赖、追随、亲近、归属,以及对政治制度、政治权力的接受、赞同等”[28]。情感是人类的特有属性,是联结他人和外部世界的纽带,对我们感知自我和世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微观视角来看,情感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决定一个人存在范畴的关键要素,直接或间接决定了人自我审视和思辨的向度。从中观视角来看,情感是弥合分歧、有效平衡社群内部张力、推动社群良性互动和发展的支点。从宏观视角来看,情感是促进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承载了人类文明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政治认同范畴下的情感认同与一时兴起的私人情绪不同,它更加稳定和持久,是凝聚和培育社会共识的基础。这种情感认同既不是天赋的也不是单一主体的,相反,它是认知主体在社会持续性的互动中将某种理念和认同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社会集体性心理构建的过程。
2.1 共鸣是唤起认知主体情感认同的内在驱动
共鸣是情感认同的基础。情感之所以能够跨越时空的囿限,沁润社会成员,并经由历史的传承,借助家庭、文化、教育的力量延绵不绝,成为“想象共同体”的纽带、凝聚社会共识的基础,是因为共鸣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西方知觉现象学代表人物梅洛·庞蒂认为,我们的任何一种感知活动都只能在一个现象场中发生。当主体在注视某个客观事物时,就会产生一个视觉场,他认为“看既不是我对外界的被动反应,也不是我对事物的一种单向赋义,而是我与事物之间的一种相互敞开和相互交流。”[29]正是这种主体与客观世界之间双向互构的运动激活了共鸣的机理,并使主体远离异化状态。在此基础上,德国社会1c5f03c474d0cfdb82cee52a05e02a63301c3a17a009c83d209be3475935d5a6学家哈特穆特·罗萨提出了共鸣理论,他将“这种触-动(af←fection,一些事物从外部与我们产生联系)与感-动(e→motion,我们通过反应予以回应并与之建立关联的连接)的双向运动称之为‘共鸣’”[30]。 他认为共鸣能力不仅对于主体和人类社会具有根本性意义,同时,仅就个体身体而言,共鸣也具有决定性意义,“即决定着他以怎样的方式和途径,同世界进行交互活动,在其中行动、调节、感受与思考”[31]。人类作为一种能动性存在物,其存在于世并与物相处的模式不应是占有,而应是在与物共鸣中发生连接。共鸣不是主观臆想的“扩音器”,也不是囚禁主体信息茧房的“回音壁”,而是对客观世界感性体验与主观感受的超越,最终实现与“他者”的相遇,并在这一过程中真正地激发出吸引、感动、震撼等情感要素。
红色档案不仅在宏观层面勾勒起历史演进的纵向脉络,以全景式俯瞰视角粗线条把握国家和社会的整体概要,同时,它还细致入微地记录了一些革命先辈们的生命体验和所思所想,“通过细腻、鲜活、彰显人文关怀的微观叙事挖掘平凡中的伟大,引发深层次的情感共鸣”[32],从而实现认知主体与红色档案之间的双向敞视,并直接促进情感认同的0344df2b5e2d37c228b22dec778c2711651d06748418aa9db47d86015ce9ef2b生产。
2.2 红色档案是触发共鸣的生动之“物”
共鸣关系域是现代社会中主体共鸣孕育的界域。哈特穆特·罗萨提出的“水平共鸣轴”“对角线共鸣轴”和“垂直共鸣轴”分别指代人与人的共鸣关系域、人与物的共鸣关系域和人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共鸣关系域。对角线共鸣轴表征着人与物的关系域,在这里,“‘物’(things)主要指的是那些非人类的或非动物的、即被认为是‘无生命’或‘无声’的‘客体’”[33]。他认为,自启蒙运动以降,人的主体性被过分推崇,但却从未赋予“物”以超出工具性的地位,科学主义主导的“人”与“物”的二元对立关系笼罩下的世界,“物”成为毫无灵魂和能动性的附庸。如何使人与物发生共鸣,他提出了“成物”的概念。“成物是指在共鸣关系中使物成就自身,同时主体也得以自我成就。”[34]成物的过程是主体经由日常生活关系模式与物形成的真正的彼此敞视的回应性关系。红色档案作为一种独立于认知主体之外的历史流传之“物”,显然也具备与认知主体构建共鸣关系的要素。
学史方能知史,知史方能明智。红色档案是一种历史凭证,主体透过红色档案不仅直面作者的原始记录,同时也面对着记录者凝结在档案中的思想、心理和体验以及在这背后的精神追求、情感表达和价值意蕴。此外,主体也可以通过红色档案置身于其作为历史流传物的伽达默尔所谓的“效果历史”之中,深刻领悟中国革命叙事以及蕴含在宏大叙事背后的革命者意志、品格与信仰。以珍藏于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中国共产党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为例,出自1931年的共产党人——江西永新县农民贺页朵之手,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大革命时代,41岁的他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运动之中,由于表现出色,1931年1月25日晚,在他的小榨油坊里正式被吸收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在枯油灯的照亮下,贺页朵拿出自己早已准备好的一块红布,在上面端端正正地写下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C.C.P.’和由毛泽东起草的入党誓词”[35],并将自己的姓名、入党时间和地点抄写在红布之上。细细品读这份饱含赤诚之心的入党誓词,结合当时严酷的斗争背景,认知主体就能直观地感受到共产党人在革命年代“对党忠诚”“永不叛党”的精神,从而引发共鸣。
2.3 红色档案通过共鸣激活认知主体的情感认同
档案可以被视为情感符号化的有效载体。西方文化学者安·克维特科维奇认为,“包括档案材料在内的‘文化文本’是‘情感的仓库’,也是与其形成与接收相关的情感活动的仓库”[36]。档案不仅起到了存储情感的功能,还兼具进一步建构情感的属性,并由此与认知主体的理想、信念、社会规范等建立连接。红色档案通过为认知主体提供经验事实的原始记录,复现峥嵘历史,“如果利用者与这段历史中的人和事产生了某种心理上的联系,必然会有一定的情感上的反映”[37]。加拿大学者伊冯·勒梅也认为,档案与其表征元素——对象、设备、语境与观众,在情感上存在相互联系,能够唤醒情绪并产生共鸣。[38]情感并不只是一种纯粹的个体心理体验,它的起源也不应是生物性或神经性的,而是“文化社会化以及参与社会结构所导致的条件化的结果”[39],具有明显的社会建构特征。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情感不仅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承载了文化规范、信念和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它还能够积极赋予主体认知的主观色彩和方向。
红色档案作为承载和存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感情的仓库”,是主体感情实践活动的重要媒介和资源,认知主体通过它们冲破时空拘囿与历史中的人物和事件发生对话、共情和理解,并促使其使用恰当的情感回应这些意向世界的深层次交往。共鸣就是这种深层次交往的结果和产物,是认知主体“情感上的反映”或“情感上存在相互联系”,同时也是引发情感认同的准备和前奏。认知主体通过红色档案所记录经验事实的真实性、确定性和可溯源性,获得了感情构建的坚实基础。认知主体被红色档案忠实记录的人与事所打动引发共鸣,进而产生两种感情,一种是临时性和偶发性的“场域性感情”,另一种是稳定性的“库存性感情”。在与其他成员进行社会交往和互动时,这两种情感“会形成具有共同体验的情感——集体情感。从集体情感扩张到整个社会,便会形成社会情感”[40]。而红色档案鲜明的政治性必然会将这种情感引向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追随与认同。
理智认同是政治认同的最高阶段,理解是主体正确认知红色档案并由此建立理智认同的基本前提和关键环节。
3 理解:红色档案构建理智认同的终极解码
理智认同,即“人们对全部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把握中,在理性指导下所产生的认同”[41]。理智认同是政治认同中的高级表现形态,具有较强的反思性和建构性,是认知主体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内在统一的过程性体现。理性指的是认知主体经由理解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其自身的关系进行的循环交替不断探索式的思考。因此,可以说理智认同生成的过程就是认知主体以前结构为基点不断更新和重新筹划的过程。
诠释学派代表人物伽达默尔认为,“个人的前见比起个人的判断来说,更是个人存在的历史实在”[42]。此在是历史性的此在,人类受智识水平、社会结构、文化背景和时代局限的种种束缚,绝对理性对于历史性的人类来说是不可能存在的。即便就单个认知主体而言,理解也是在不断对话和理解中完成的,“理解的前结构就是指人总是在自己预先设定的想法中认识、发现自己,通过原有的观点对将要理解的事物有意义的期待”[43]。理解虽然受到前结构的制约,但却是主体不断求真的过程,也是通往真理的唯一途径,“自古以来,诠释学意指通过理解性的解释而发现真理”[44]。但值得注意的是,理解不单纯是一个主观作用于客观的意向性活动,理解的发生是主客体的遭遇,深层次的理解发生在主体与历史传承物的融合和统一之中。认知主体与红色档案也并非一种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被理解的红色档案不是一个被动的存在和对象,而是主体与它的统一体。在理解的过程中,认知主体不断通过红色档案将过去与现在统一、将历史传承物与人之处境统一。如此一来,认知主体的当下视域与历史流传文本视域就会产生融合,这种融合不仅使历史流传文本进一步生成,也使主体加深了对自身的理解。
3.1 红色档案是促进认知主体理解的重要文本
“红色档案归集了党丰富的思想成果、精神成果和工作成果,是承载过去、记录现在和联系未来的桥梁。”[45]翔实的史料、直观的记录、鲜活的影像,为一段段历史标注出了真实的注脚,勾勒出了完整的轮廓。历史不会凭空流逝,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叙事也不会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行的奋斗征程中了无痕迹。红色档案为填充中国革命叙事提供了最为丰富的原材料,透过对这一传承物的诠释,主体跨越历史的鸿沟,不断在主体理解层面对中国革命出场、存在、发展和成功的意义进行扩充。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的关键是“视域融合”。红色档案不只是单纯地承载了历史的踪迹,它还作为当下在场感染和影响着主体对中国革命和其自身的理解。例如,《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刊物,主体通过《新青年》不仅能够直接感受到大师巨匠们的深邃思想和多元主张,也能直观体会到中国文化自辛亥革命后由封建到近现代、由封闭到开放、由僵化到进化的历史进程,还能体味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轨迹,更能体验到这一系列红色档案中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鼓与呼,对革命先贤发出“当急起直追”的迫切情感。不仅如此,主体还会结合当下对自我存在的意义进行反思,在反思中,自我与国家、社会的内在关联性也更加显豁。红色档案划定了主体自我意义筹划的视域,在这个视域内,主体不断建构自我与中国革命的内在关系,自我意义不断被筹划,与此同时,红色档案也获得了当下存在的意义,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流传。主体通过红色档案对中国革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了更深的理解,对自我存在的意义以及自我与国家、社会关系审视的视域也有了进一步的延展和扩充,由此实现真正的理解。
3.2 理解是实现红色档案解码归己的最终归宿
红色档案是一种重要的文本。保罗·利科认为,文本在读者与作者之间具有双重遮蔽的作用——在创作文本时读者是缺席的,在阅读文本时作者亦然。由此便产生了文本的间距化(distanciation),与其他哲学家将其视为某种认识论的异化或方法论的衍生物不同,他认为“文本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特殊情况,它是交流的间隔范式”,“揭示了人类经验的历史性本身的根本性特征”[46],是有其建设性和创造性的,具有本体论意义。利科通过间距化、归属的关系、文本世界和理论等提出了重要的概念“归己化”,即将文本意义化为已有的过程。他进一步认为,理解是在世的结构,是我们对自己各种可能处境的多元筹划。在文本诠释中主体性不是理解的起点而是终点,“理解,就是在文本面前的自我理解”[47],也就是说理解文本不再是认识活动的目的,而是主体理解自身的中介。
文本的呈现方式是多样的,口述史作为一种独立的重现历史的形式,将生活世界与文本世界有机融合起来,是传承红色记忆的重要档案,也是认知主体阅读、解码并最终实现归己的重要媒介。譬如为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由中共丹东市委相关部门组织专业人员和社会力量,以“口述+影像”的方式广泛收集那一历史时期的老战士以及支前模范的口述史。“王秀文老英雄讲述的雪地里吃冻土豆,开房门粘掉手皮,孙文清老英雄分享的‘帽子戏法’‘罐头阵’巧打硬仗夺胜利”[48]等鲜活的记忆、丰富的素材,弥合了由时空断裂造成的间距,认知主体不仅透过口述史了解了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复现那段光荣的历史,重要的是还将这些文本(档案)纳入自我生成与建构之中。
3.3 红色档案通过理解建构起认知主体的理智认同
政治认同范畴下的理智认同是主体在一定的社会实践活动基础之上,对特定政治组织及其理念和信仰的认识和解读。红色档案建构认知主体理智认同的过程是一个由被动过渡到主动的过程。从被动维度来看,传递并强化政治认同心理、观念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主要通过宣传部门和教育系统进行制度化教化,红色档案通过上述渠道被灌输进主体的观念中。从主动维度来看,认知主体为了保持与他人社会心理和行为实践的一致性,主动认同并习得心理、认知、文化乃至行为,在政治认同领域,“主要是指客观的政治环境与个体的主观意识产生互动,个体在经由心理暗示、心理从众、行为模仿、效应放大的过程而形成的相符心理与行为”[49]。
在融媒体时代,红色档案对理智认同的形塑也通过娱乐性媒介以较为隐蔽的形式渗透进来。红色档案在脱离了创作者及当时的文化历史语境之后,继续在全新的时代不断地被阐释,“文本在阅读中超越了自身被创作时的心理-社会语境,并向无限地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产生的阅读视域开放”[50],并有可能产生一系列的新的语境和意义。例如,影视剧《觉醒年代》跌宕起伏的剧情和悲情的人物命运在青年群体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新青年》《湘江评论》《每周评论》等多件有重要影响力的红色档案借助摄像镜头进入观众视野,并作为重要符号推动了剧情发展。而在电视剧之外,档案馆也完整保存了多份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时的往来信件、“五四运动”当天的原始文字和材料记录。革命岁月已经远去,这些红色档案在信息过载、主体注意力流变不息语境下获得了重生。它们与历史事件的相关性已日趋疏阔,逐步演变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并以其独特价值参与了中国革命的意义构造和表征。红色档案不断地被后来者阅读和理解,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主体自我理解的过程,即主体自我建构的过程,是主体对自我的身份、历史及其与社会关系进行的全部批判和思辨,也内在蕴含了对其所在政治组织及其理念的寻绎。
4 结 语
红色档案是百年征程的记录者、讲述者和传播者,是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亦是凝聚人心、增进共识、在当下社会构建政治认同的重要赋能力量。维护好、开发好、利用好红色档案对于认知主体的记忆、情感和理解以及政治认同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阐释红色档案在本能认同、情感认同和理智认同形成中的作用机理,有助于厘清红色档案与身份归属、情感共鸣、自我理解的内在关联,也有助于彰显红色档案在政治认同中的具体效用和价值。
*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2023年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项目编号:Y202353549)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1][16][28][41]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298.
[2]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J].求是,2021(19):4-9.
[3]周林兴,姜璐.红色档案资源开发中的叙事表达研究[J].档案学研究,2022(4):4-9.
[4]何玲,马晓玥,档案研究僧.跨媒体叙事理论观照下的档案叙事优化策略——以红色档案为例的分析[J].档案学通讯,2021(5):14-21.
[5]赵义良,熊文景.红色档案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及其深化路径[J].档案学通讯,2022(4):4-9.
[6]赵彦昌,冯嘉然.高校课程思政视域下红色档案文化传播路径研究[J].北京档案,2023(2):31-34.
[7]桑果果.红色档案资源应用于党校教学的价值、现状、路径[J].档案学研究,2023(4):118-123.
[8]朱彤,曾祥明.论红色档案传承红色基因的生成机理、价值意蕴及实践路径[J].档案学通讯,2022(1):23-28.
[9]孙大东,白路浩.心流理论视域下红色档案传承红色基因的向度与路径[J].档案学通讯,2022(1):15-22.
[10]陈艳红,陈晶晶.数字人文视域下档案馆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的时代价值与路径选择[J].档案学研究,2022(3):68-75.
[11]彭庆红,孙晓丹.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开发利用的路径与梯度[J].档案学通讯,2022(4):10-16.
[12]翟乐,李金格.数字人文视阈下红色档案资源的遴选、组织与开发策略研究[J].情报科学,2021(12):174-178,186.
[13]李健,陈艳红.基于用户评价的短视频平台红色档案资源传播效果研究——对“探影局档案”抖音号的实证分析[J].档案与建设,2023(11):25-29.
[14]颜涵.基于互动仪式链的红色档案文化传播解析——以纪录片《红色档案》为例[J].档案与建设,2023(6):23-26.
[15]黄夏基,卢泽蓉.我国红色档案数字叙事研究——基于省级综合档案馆门户网站的调查分析[J].档案与建设,2023(6):31-34.
[17]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9.
[18][19]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81,91.
[20]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66.
[21]冯惠玲.当代身份认同中的档案价值[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1):96-103.
[22]庞永真,丛楠.基于档案记忆观的红色档案资源建设研究[J].兰台世界,2022,(3):36-39,45.
[23]丁华东,余黎菁.论特里·库克的档案记忆思想[J].档案管理,2014(6):6-9.
[24]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7.
[25]丁华东.昔日重现:论档案建构社会记忆的机制[J].档案学研究,2014(5):29-34.
[26][27]阿斯曼,陶东风.个体记忆、社会记忆、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J].文化研究,2020(3):48-65.
[29]张尧均.隐喻的身体: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研究(修订版)[M].武汉:崇文书局,2023:77.
[30]罗萨,濮玥.迈向美好生活:从动态稳定到追求共鸣[J].国外理论动态,2022(2):148-156.
[31]罗萨.不受掌控[M].郑作彧,马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54.
[32]陈佳雨.传递记忆的微光:论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微观叙事[J].档案与建设,2024(1):51-56.
[33][34]冯学勤.“新异化”的高级感性诊疗方案——论哈特穆特·罗萨共鸣理论的美育性质[J].社会科学战线,2023(3):173-182.
[35]廖俊杰.我党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J].党建,2021(2):63-64.
[36]曲春梅.国外档案学研究的“情感转向”[J].档案学研究,2020(4):128-134.
[37]丁海斌.档案价值论[J].档案学研究,2015(5):4-12.
[38]刘志森,耿志杰.情感仪式视域下档案与身份认同:理论阐释、作用机理及提升路径[J].档案学研究,2022(3):13-20.
[39]特纳,斯戴兹.情感社会学[M].孙俊才,文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
[40]李晶伟.档案情感价值的内涵与特征[J].北京档案,2018(11):9-12.
[42]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392.
[43]格郎丹.哲学解释学导论[M].何卫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55.
[44]洪汉鼎.理解的真理:解读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187.
[45]袁媛.红色档案蕴藏初心使命[N].人民日报,2021-05-24(05).
[46][47]利科.从文本到行动[M].夏小燕,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06,30.
[48]王鑫.用口述历史档案讲好党史故事——以抗美援朝口述历史纪录片《铭记》为例[J].档案与建设,2022(8):68-69.
[49]金家新.后物质时代政治认同的理解向度与心理生成机制[J].思想理论教育,2016(5):45-51.
[50]张进,蒲睿.论保罗·利科的行动阐释学[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6):111-122,193.
(责任编辑:冯婧恺 张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