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刻,我不忧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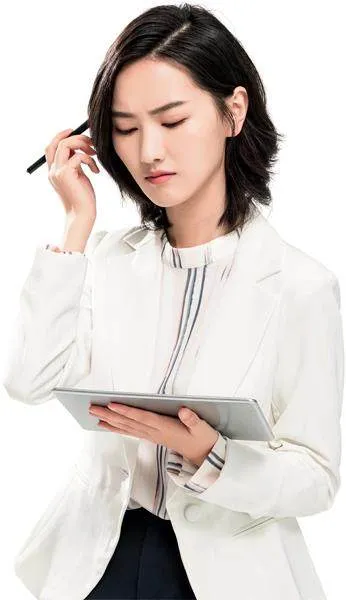
上篇请见《心理与健康》2024年02期,上篇内容提要:焦虑是许多精神疾病的基础。通过文静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广泛性焦虑障碍的表现、影响和成因。广泛性焦虑障碍难以治愈的原因在于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平衡,打破这种平衡意味着要面对内心深处的恐惧和不安。因此,治疗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需要患者勇气和安全感的过程。
对于心理学流派,人们往往会有这样一个误区:当一个心理治疗师隶属某一流派,他就只能通过这种方法来对患者进行治疗。似乎流派与流派之间是难以融合的,它们就如平行线一般,永远无法相交。但事实上,如果一个治疗师不是特别执着于某一流派,不过分封闭自己,那在真正的诊疗中,相关的理论与技术都会被采用,只要这一切有利于患者。
一个光鲜亮丽的壳
人本主义的代表人物罗杰斯,对广泛性焦虑障碍有这样的解释:当一个孩子缺乏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养育者)的无条件肯定时,就会对自己过分挑剔,进而形成严格的自我标准,认为只有达到标准,才能获得肯定。这会让他们不惜这一生都拒绝接受真实的自我。同时因为标准被预设得很高,也会让他们长期处在焦虑和抑郁当中。
罗杰斯的解释是切中要害的。尤其在上篇我们谈到的患者—— 文静身上,刚好印证了这个解释中的核心。一是高标准严要求,二是她始终无法让真实的自我—— 那个既恐惧、愤怒又怨恨的部分呈现出来。而这两点就会导致她的焦虑始终都在,无法退散。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是比较严苛的?”在治疗中,我试探性地问她。
“有。但这不算坏事吧。一个人让自己变得更好,不是应该的吗?”她几乎没有一丝犹豫地回答了我。“嗯。”我点点头,但还是追问了一句:”这会不会有点累呢?”
她没说话,但却不易察觉地叹了口气,这个举动算是给了我回应。于是我尝试做出一些诠释:“我一直觉得你做了很多事,始终保持在很高的水准上。比如好的成绩、工作能力、家庭环境、孩子的健康和优秀,等等。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是你能允许自己差一点的。这种感觉怎么说呢,就好像你在给自己营造一个光鲜亮丽的壳,但要维持它的坚固,却需要花很多力气。至少,你得始终保持紧绷……”
在我说话当中,就已经注意到她一直在点头,而等不及我说完,她就直接回复了我:“是的,就是这样。我很难形容的东西被你说出来了。我活得太累了,从来没有一刻是真正放松的,这个壳耗费了我太多力气,我不想这样但又始终被牵制着,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我能想象到如果放手的话,一定会掉进深渊。”

对威胁作出反应
文静谈到的“深渊”,指的是什么呢?
认知理论这样理解:他们认为这类患者无论在意识还是潜意识层面,关注的都是威胁。换句话说,他们无论何时何地,都会第一时间捕捉到可能迫害自己的信息,然后将其放大,让自己的内在感受处在一个惶恐的境地,仿佛下一秒就会面临危机。而这样时间久了,人的自主思维便开始启动,根本无需真实的证据,身心就会对环境作出过激反应。
简言之,越怕就越会怕,怕的也觉得会成真。
如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何文静根本不能放松,一是因为她的焦虑就如同身体的条件反射,已然被固化。二是她开始相信自己的焦虑,认定这就是真的。而自己只有时时关注,才能避免糟糕的事情发生。
“你觉得,那些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吗?”在第二次治疗中,我开始尝试接触她的忧虑。
“还在上学时,我记得有次考试,我担心会考砸了,结果那次非常紧张,导致我真的考砸了。”文静说起这件事,手还在微微颤抖。
“这就好像你对自己的预言,实现了?”我小心地问。
“我觉得是。所以之后我更加担心。每一次我都让自己打起十二分精神,避免再出现那次的事。”文静也意识到手的颤抖,她死死地握住那只手,努力让它稳定下来。
“所以你觉得,之后的‘好结果’都是打起十二分精神才得到的。”我试着推演她的理解。
文静皱起眉头,仿佛在回忆。之后她犹豫着说,“好像也不都是。有一些成绩还是比较轻松就获得了。”伴随着她的话,我看到她的手在慢慢放松。
“那可以这样说吗?其实不见得都是如此。有时候放松也会有好结果。”
我继续推演。
“好像是的。但我紧张惯了,遇到事情第一个反应就是紧张,然后预想坏结果,仿佛这样做我就能避免似的……”文静的语速慢了下来,似乎在思考。
我没再说话,因为根据经验,这是文静能够向内探索的一个宝贵时机。果然,她过了一会对我说,“我发现,当问题摆在眼前时,我并没有真的思考,而是立刻就害怕了,脑子里开始出现不好的预想。我从来没有思考过我该怎么应对,而是想办法逃避它,好像只要我的感觉不糟糕,就行了。所以我除了担心,其实什么都没做,但只是担心就让我耗尽全部心力了。”
文静的感悟,正是问题所在。
因为患有广泛性焦虑障碍的人,他们的绝大多数精力都放在了焦虑上。可以说那种弥散的、无处不在的焦灼几乎吞没了他们的正常生活,为此他们做了许多没必要的事来阻挡或者消减焦虑,比如在文静丈夫眼中,那个无论多累都还要去拖几遍的地,本身就只是一种象征意义,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作用。
换句话说,真正的威胁并不存在,但想象中的威胁,却已然成为深渊。

我到底在害怕什么
面对这种疾病类型,最直接有效的是认知行为治疗。
但实际上,治疗不该是机械的。如果只从外力入手,矫正一个人的认知角度和生活习惯,忽略其内心深处的焦虑,症状就难以从根本上去除。因为从本质来说,一个人若想均衡和调节焦虑程度,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自我。因此,在以认知为主体的几次谈话后,我们的速度开始放缓,谈话内容也从当前来到过去,从思考回到情感,我也致力于帮助她从“我要快点解决这个问题”的焦灼平稳下来,进入到对内在感受的体验和理解上。
而这个过程不同于其他疗法,并没有刻意地运用技巧,甚至是放下过多的技巧。因为精神分析更强调关系,更在意患者和治疗师之间建立的信任程度。它认定,一旦患者是愿意相信治疗师的,接受对方陪着自己去进行探索内在的工作,其整个人就会慢下来。所以lYcv1TpDK1nWol/MFkXK0Q9q0aBh2mogbisfpzrMCIE=此刻的我也将自己尽量“腾空”,如同一堵白墙。只是接收对方的信息、将其反馈(共情与诠释)、少做提问与干预、将节奏归还给她。
于是渐渐地,某些文静从前没有意识到的,一直深藏于潜意识之中的,她自觉是黑暗的部分开始一点点流露:“……我恨我爸妈,他们根本不在乎我。我也恨我的姐弟,他们抢走了本该属于我的宠爱,如果没有他们该有多好。但我也恨自己,我为什么会这么想……”在某次治疗中,文静艰难地说出这些话,之后掩面哭泣。
我递给她一张纸巾,静静地陪着她。我知道这些话说出来有多不容易,能够让一些听起来非常糟糕但坦诚的情感出来,这是关键一步。而直到她慢慢平静,我才尝试做出回应:“这种恨的感觉非常强烈,当它出现时,都恨不得要吞噬一切,甚至包括你自己。是这样吗?”
“是的。”文静点头。之后她停顿了一下,仿佛想到了什么,眼神突然明亮起来:”原来如此。我明白自己在害怕什么了。我一直认为自己不能恨家人,应该学会感恩。所以我在压抑我的情感。但你说到吞噬时,我意识到我害怕的是自己,害怕我会亲手毁掉自己好不容易建立的一切,无论是和家人的关系,还是如今我的生活。所以当一切变得越好,我就越忧虑,原来令人担心的根本不是外界的灾难,而是我自己。”
直到这一步,一切都解开了。
这就好像一个黑洞被探到了底。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到底在害怕什么,并非是外界那些虚幻的威胁,也不是对家人强烈的怨恨,却是潜藏在内心深处的高度的毁灭欲。
结语
文静的治疗进行了一年左右。虽然直到她离开那天,我无法保证她未来是否还会陷入焦虑,但我深知,她已经从这个过程中逐渐获得对自我更深刻的认知与理解,那个从前看似黑暗的世界,其实只有埋藏起来才是可怕的,拿到光明之下,不过是当年一个小女孩的无力与悲伤。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相信她会开启真正的成长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