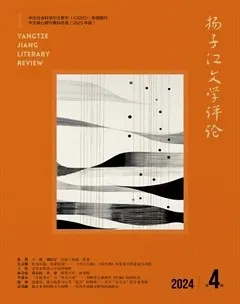汉诗的绝对文本:欧阳江河诗歌中的“量子男孩”与“天使抗体”
诗歌何为?汉诗又何为?在一切都会被纳入程序控制的算法时代、AI也能写诗的时代,诗人何为?如此的提问,无疑也是直接回应海德格尔思考里尔克的文章的标题——《诗人何为?》,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写作,已经在里尔克一首诗歌片断中得到了先知般的指示:
如同自然允让万物本性
在昏沉快乐中的冒险而并没有
于土地和树枝之中特别保护它们,
同样,我们存在的原始根基也
不再喜好我们;它使我们冒险,只是我们
比植物和动物更甚于
随此冒险而行,也意愿如此,有时
冒险更甚(不是出于私己)
更甚于生命本身,为了一次呼吸的
更大冒险……如此把我们带往,于保护之外,
那安全的存在,那位置,重力发挥出
纯粹的力量;最终庇护我们的,
是我们的无保护性,而且我们也
转入到敞开之中,在其中我们也看到威胁
围绕着它,在最宽广圜道的任一处,
我们为法则所触动而把它肯定。a
因为人类比动物更为冒险,或者说人类把动物的冒险带到自身生命之中,导致了生命的极度危险状态。这危险还体现为呼吸(也是灵魂)的危险,致使生命本身进入更大的冒险。而且,人性只能进入如此状态:最终保护我们的是我们的“无保护性”b。我们不得不进入此“无保护性”的敞开之冒险之中,而这也是荷尔德林早就指出的人性境况:人性比神明更早抵达深渊。
而一旦进入深渊这“无所保护”之位置,至为关键的问题就出现了:诗歌是否可以保护当下的人性?诗歌的责任也就由此而生!正是因为考虑到现代的人性已经处于“无保护的保护”之绝境状态,里尔克才进入了哀歌的绵绵歌咏,并在《杜伊诺哀歌》中召唤出他的“新天使”c。
海德格尔在1946年对刚刚结束的战争创伤之回味中,试图通过《诗人何为?》的文本,以里尔克的诗歌来沉思另一种的人性,走出人道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而我们的中文,以“诗歌”何为开始,而不是“诗人”,似乎显得不合常情,因为只有诗人才是行为者,文本如何可能自为?当然在诗人与诗歌之间有着解释学的循环,而我们强调“诗歌”(尤其是汉语诗)何为,乃是面对汉语本身的诗性。因为古老的汉语之独特性,及其所形成的文本书写性,比所有诗人与诗意都要古老,更为博大。我们强调“诗文本”,乃是肯定文本自身的可复制性,这正好是中华文化在生产技术上,以其整体性与繁衍复制性的万物“模造”原理,来对应宇宙生物的繁衍性与基因复制模式。文本自身的自我复制与自身传递,如同青铜器的制作与书法的临摹,都是文本自身的独立性与可传导性,乃至于可再生性的要求。正是由于这个自身复制性,才出现了从鸠摩罗什到玄奘的佛经翻译,复制与再生,乃是生命书写与自然繁衍的对应,如此的文本书写才是绝对文本,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西游记》所虚构的“孙悟空”式的万变形象。
如此,就出现了欧阳江河的“量子男孩”,在人为时空与自然时空之间,在宏观与微观之间,在本文与文本之间,相互穿越,彼此纠缠,相互依赖,彼此共生,自我与他者,原创与翻译,相互生发。
而一旦汉语的诗性在现代性中遇到了再次翻译西方整个诗歌的巨大挑战,“汉诗”何为?现代汉诗要把之前的万物模造的复制书写模式,及其翻译的再生模式,再次综合起来,而形成新的绝对文本吗?如此的广博吸纳,乃是要把当代汉语诗人带往一个更为广博与复杂的“文本性”。一旦从量子纠缠的相互共生与彼此纠缠来重新思考与写作,荷马可能是鸠摩罗什,王维可能是庞德,而欧阳江河可能是爱因斯坦。解构主义的“互文本”(con-text),就转化为“量子文本”(quantum-text)。
此广义的量子文本之为“文-本-性”的体现在于:是“文”之本源或本性的一次次转化:从纹理到文字,从文化到文本,从文典到文脉,从诗文到杂文,从古文到经文(以及佛经),从文字到拼音,从书文(书法文本)到变异的译文,从文明到文码,从中文到外文,从英文到数码等等。这也就意味着,汉字的现代性转化,乃是以“文”为“本”的转化,而且这个转化过程还并没有完成,既然“文之本”包括如此复杂的要素,那么对于诗文而言,如何在如此复杂的文本网络中,借助于量子跃迁与量子穿越,而得到一次伟大的综合?不可思议的合成?以此抵达绝对?
无疑,这正是“长诗”的责任,尽管在1980年代末期的诗人海子与骆一禾,已经充分认识到此种义务,但可惜还处于“草创”阶段,这也是因为中国的现代性转化才刚刚开始,那个万能的复制技术,那个可能的“量子男孩”,还尚未出场,我们等待新的历史时刻,在更为全球化的事件与危机中,重新开始写作,而且呈现的是“晚熟”之境d。
这并非仅仅是年岁的事实——这些诗人基本上都接近六十甲子之年,甚至我们要讨论的诗人欧阳江河,近七十岁,尽管诗人还看起来如此“年轻”,因此更为自觉地承担了这个伟大的责任。此种独特年代的独特经验,被深度异物所整体触感的经验,迫使诗人们不得不面对混杂现代性的更为复杂的文本,即“基因”也是生命的文本。
那么,诗文又能何为?诗性的文本书写可以克服此病毒的算法吗?个体化与文字性的诗文文本,如何可能面对大数据的巨大算法与无形病毒的快速繁衍——这技术与生物的双重算法?要求一个汉语诗人以其短小的诗文,来“解读”(解毒)或解咒这两种“反诗”(或用欧阳江河的“反词”来类比),是否超过了诗歌写作的限度?除非这诗文写作经过传递的转化与变异,进入文本的加速与不同世界的穿越,让已经进入危险的呼吸,经历施行策兰式的“呼吸转换”(Atemwende),而且是生命整体的感知转换。
欧阳江河最近几年所写作的几首长诗,就是如此多重文本的神妙编织,是一次世界性的跨文本的诗意综合,或量子跃迁式的互文本的穿越,诗人仿佛是要以自己诗文的算法,接续甲骨文在商周时代的占卜算法,以及鸠摩罗什翻译佛典的佛法,来面对现时代的数字算法与病毒的复制算法,并且克服人性深度的恐惧,来想象另一种的人性,即发明现代汉诗的诗文书写法则,形成新的“量子文本”,并且召唤出欧阳江河自己的“新天使”——天使疫苗,或具有生命绝对保护性的——“天使抗体”。
一、宿墨文码与佛道算法
现代汉语诗歌在经历了“青春期”的朦胧诗写作,穿越了知识分子之“中年”的戏剧化智性写作,并同时经过“风格化”修辞写作的锤炼之后,很多诗人已经进入了六十岁的“晚岁”写作,诗人欧阳江河是对此年岁进行过最为自觉思考的诗人(在各个年岁的节点上都写出了卓越的评论文章)。什么样的“晚岁”写作,可以以诗性的凝练与智慧,把现代汉语带向时代精华之精神形态的成熟?这个晚熟的秘境,如果不面对时代的灾难与历史的困境,又如何可能具有时代精神升华的高度,而不沦陷到镜中的虚拟幻象之中,并最终抵达文本的绝对性?
如同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所要求的人性“三变”,诗人的文体也必须经过蝴蝶式形态学的“三变”,在算法时代,想象另一种的人性,从而书写出另一种的汉语!此诗性的汉语必须克服算法的计算性,而进入不可计算与绝对偶然的爆发状态,这就不仅仅是庄周梦为蝴蝶,而是更为反转的蝴蝶之梦为庄周,这正是欧阳江河带给我们的“蝴蝶梦”或“史诗般”的转向:
在算法的界面上,考古与仿古
不停地切换真身和插孔之身。
拔掉插头:这或许是个史诗般的决定。
肯定有某种难以释梦的东西,
使蝴蝶飞起时是一只孔雀。
——《圣僧八思巴》
欧阳江河最近的诗文本,在我们这个时代,乃至于在世界诗坛,也许是第一个彻底面对“算法”的文本,并且寻求以“另一种”算法——“不是”算法的算法——比算法“还是”算法的算法——“超过”了所有算法的算法——以“空无”作为算法的算法,即曾经有过的“佛法”,来克服此计算时代的魔法控制,蝴蝶可以转化为孔雀,孔雀可以转化为凤凰,而且是工业时代垃圾拼接的巨大的“凤凰”(如同诗人写给艺术家徐冰的同名观念作品),这就是诗人所写的《佛法与算法》。
但这是“文字”与“文本”的较量,是“原文”与“译本”的颠倒,也是魔法与天使的搏斗,或者这就是歌德的浮士德的神话幻象与梅菲斯特早期资本主义算法的较量,这个壮阔的舞台已经被安排出来了。也许中国当代诗人中,最为具有剧场感与表演舞台感的诗人是欧阳江河,因为他一直处于“事件写作”的漩涡中心,当然这还来自于诗人对于音乐的倾听,对瓦格纳歌剧整体综合的文字感应,继而编制为多重的文本复写。
首先,汉字之为文本,中国人之为“文之人”(不是文人,而是以文为命的文命书写者),既非如同希腊人活在这个充满危险与战争的“城邦式”封闭世界上,也非如同犹太人仅仅活在漂泊不定与语意不详的《圣经》中;也不是如同死去的埃及人之为木乃伊化的象形文字,中国人或中国文人乃是活在不断变异着的文字中。而且,汉字既是文字,同时也是“广义的文本”,也是命脉之所寄,因为中国的文字书写可以在书本中,也可以在大地的石壁上,更可以在内在的呼吸中,甚至可以在幻化的天空中;而且,就是以最为自然的材质——宣纸、毛笔与水墨,带有时间记忆痕迹的“宿墨”——乃是汉语浓于血的苦涩汁液;但进入现代性的汉语与文字,受到西方拉丁字母与语音中心主义的严酷挤压,几乎枯干,这就尤为需要在汉语的新书写中,使其重新变得“甘甜”(如同张枣等人的渴望)。
为什么欧阳江河可以进入此“宿墨”的文命书写痕迹之中?这是因为诗人也是一个以书法为业余爱好的高超修养者,几十年如一日的书法书写,吟唱出“宿墨”的文迹史诗,回溯到了古老器物上的花纹与纹饰之“纹理”,整合了王羲之与《黄庭经》的书法墨迹,进入了黄宾虹焦墨宿墨的涂写痕迹,对应了德里达文字解构的踪迹,抓换了佛典在方言式念经的单调重复,并且转换为阿尔托式呼吸象形文字的残痕,等等,这是整个中国文脉在“残余化”之后的“盈余”继承,也是数字化“转存”之后的诗意转化。在当代汉语诗歌写作中,欧阳江河就是汉语墨迹的隐秘传人,是王羲之与杜甫等待许久的一个“来生合体”——不再是小说式的孙悟空,而是一个即将出生的——“量子男孩”。很少有中国诗人有欧阳江河这样在不同文本与文体,不同思维框架之间的穿越能力,或者说量子式的跃迁之轻逸姿态。
诗人很早就在《黄山谷的豹》中去捕获“斑斑豹纹”——那跑向幻影而灵魂出窍的生命力躯体,已经转化为语词的幻象:“你醒来时发现身上的锁链/像豹子的优美条纹长进肉里。”当然这更是汉语与空无的游戏变形:“这个空无,它就要获得实存。/词的豹子,吃了我,就有了肉身。/它身上的条纹是古训的提炼,/足迹因鸟迹而成篆籀,/嘴里的莲花,吐出云泥和天象。”汉语修辞的幻象,来自于语词动物化纹理的硕大呼吸与变形。
只有汉语,能够让文辞与纹饰、文字与纹理,在空白空间上的书写墨迹中,获得自证的确认,那是在天空与大地之间的舞蹈回旋。因此,宿墨当然与草书相关:“草书般的豹纹,像幽灵掠过条形码,/布下语文课的秋水平沙。”(《黄山谷的豹》)
但对于诗人欧阳江河而言,“宿墨”不仅仅是诗意的踪迹,还必须与“算法”相关:
几个小学生用鼠标语言,/坐在云计算深处,/与山谷先生对谈。/先生逢人就问:有写剩的宿墨吗? /仿佛古汉语的手感和磨损/可以从一纸鱼书寄过来,/从少年人的迫切脚步,/快递给高处的一个趔趄。/先生的手,叠起一份晚报。
——《黄山谷的豹》
时空的错叠与穿越,带有当代电视剧与蒙太奇手法的想象叠加,让宿墨书写不再仅仅局限于纸本上,而是进入了虚拟空间。古代的纸本,无论是法帖还是鱼书,都变幻为现代的新闻报纸的灵媒,传统的媒介与信息因为丧失了文字的手感与深度,材质及其语义都被磨损,而丧失了意义。
因此,哪里还剩下宿墨的纹迹?这是追问哪里还有诗文书写的法则:
法,剩有古人写剩的一点宿墨。
史笔所写,未必字字飞鸟,
它们飞起来,
仿佛被天外手所触摸。
三月三,龙抬头。
男孩走出一生的量子迷雾,
出埃及,出头文字,出3D打印,
入反骨而顺从了纠正。
六祖慧能平静地说: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
——《宿墨与量子男孩》e
——“剩余宿墨”与“量子男孩”的关系(其中第15节)就出现了!并且联系到“法”——法度与法界指向佛教的算法,佛法如何被汉字接纳,佛法如何又重新生成,佛法如何进入文艺的个体化创作,被不断地再个体化,如同《心经》被鸠摩罗什与玄奘以个体化的方式摘录与编撰,“反向”翻译为梵语,形成个体生命的“心咒”守护,此反向翻译是典型的量子纠缠的相互转生之体现!目前这点还很少被人注意与研究。随着量子生命或者量子生物学的出现,全球化与全球史的研究也将改变自己的脑回路或思维结构。而在《西游记》中与无数妖魔的幻象遭际时,不仅仅只有孙悟空的“保护”而已,其实,更为重要的乃是《心经》心咒的“守护”,这才是玄奘肉身的“金刚体”!因此,只有结合玄奘与孙悟空,并且面对虚拟空间与量子世界,才可能出现一个新的合体——“量子男孩”!
有谁会想到,中国诗人竟然虚构出来一个不可思议的“诗意量子男孩”!为什么欧阳江河可以?这是因为他思考了世界多重法则的较量!他面对了中华汉字文本的可复制与可再生的隐秘诉求!现代的汉诗诗文要成为绝对的文本,就必须接纳不同的算法,并且以算法来转化算法,让算法之间彼此纠缠,直到穿越现实的厚墙。
在具体的书写活动中,诗人则是以“量子男孩”穿越一切的幻化想象力,在历史与虚构的空间中自由跃迁,并且对不同语种的文本,反复地进行相互涂写、相互转生,借助于佛教的转生观念,使之与量子跃迁融合,这样就可以如同天使鸟一样掠过历史的美丽肌肤,从自然的文字飞鸟,到埃及的象形文字,再到头文字与3D式,再到六祖坛经,甚至成为冥币,再回到当前的红头文件,又返回到《左传》古音,直到回转到甲骨文与竹简的刻写,再次回到了开始,又以括号的形式,把西方诗人与哲学家的格言警句,转化为诗意的诡异金句,既是翻译又是改写,既是重写又是再生,形成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反复循环,既是转生也是再生,这也许是尼采所梦想的文本之永恒轮回?似乎是去代替《史记》,而写出新时代的灵知主义《伪经》?但最终也会化为灰烬,对于文本之为文档转存会湮灭的惊恐,就出现了第45节所言的:
宿墨废纸,引刀试命,引火焚身,
无非天下文章,一读成灰。
——《庚子记》
一旦进入以科学数字或计算技术为主导的全球化现代性,中国儒道佛三家都寄托与依托的宿墨墨迹,几乎都已经化为了灰烬:“你首先是灰烬,其次依然是灰烬!”因此,如何可能把此“余灰”也重新编码到新的算法程序中?以此穿越量子的计算性与可控性?“量子男孩”应该何为?
一切仅仅是剩余的,一切都必须逆行,“反者道之动”,回归婴儿与赤子状态,这是诗人与笔者都深深相信的——汉字书写的“余化”法则与“持幼态”工夫:
十秒钟,仅仅十秒钟,
有着中暑一样的短暂的激情,使人
像一根冰棍冻结在那里 。这是
对时间法则的逆行和陈述, 少到不能再少,
对任何人的一生都必不可少。这是
一个定义: 必须屈从于少数中的少数 。
——《咖啡馆》
少数中的少数,也是“余数”,是佛教高僧僧肇在翻译佛教时所发明的“有余涅槃”与“无余涅槃”的——“余化辩证法”。
在进入现代的“算法统治”之主权的主宰之前,中国文化曾经进入过另一个文本,那是已经被佛化的佛典翻译。汉语与希腊语、拉丁语以及希伯来语和埃及语都不同,它既一直以象形文字的形态而余存下来,又一直在接纳其他的语种。魏晋南北朝开始的汉语之佛教化的变文,已经改译了汉语的气血,那从上古神纹时代传递下来的汉语,经过战国时代的混杂,以及几次丝绸之路的杂交,再次变异为唐代佛教化的汉语以及诗歌,这也是为什么诗人如此崇拜韩愈——这个彻底反佛的儒生,但依然处于佛法的“中毒”成瘾状态,越是反佛,也越是形成对峙的依赖,直到内在的成瘾——如同对于丹药的需要。因为汉语已经从骨子里,从语气到幻念上,都被佛经的佛理经过语式与语调的翻译而改变了。这在诗佛王维那里,其实最为明显,不是李白与杜甫,反倒是王维,他才是盛唐诗歌佛教化的完美化身,其语言已经不再是《诗经》与《楚辞》时代的汉语文本了,而可能已经是盛唐隐秘的“量子男孩”?当然,这需要把李白与杜甫的诗歌都重叠在王维身上。
现代白话文难道不是来自佛教变文故事?佛教经典与故事的汉语翻译,既收紧了思想也松开了幻念,这才有《西游记》的出现。作为一个出生于佛教与道教都繁盛的四川的诗人,欧阳江河在疫情时代之前就回到了佛教,无论是更早的《圣僧八思巴》 (之前去往印度泰姬陵的写作),还是最新的《鸠摩罗什》,都自觉地开始了以佛法的转译,以神思的文本,来克服现代电子技术的算法文本的努力,借助于语词量子化之后的微妙共振,在词与词、幻象与幻象之间,重建天使翅膀一样颤动的共振节奏。
诗歌写作,不得不面对自己的敌人——算法,对于欧阳江河,则是借助于佛法、念经式的重复,以及翻译时的繁衍,乃至于《心经》式的反向重写,编织新的诗意天网,来共同面对新的敌人——那无处不在的算法,就如同海德格尔借助于歌德的东方自然性与黑贝尔的地方性方言,来转换技术的“集置”,这即是“量子男孩”出现的时刻。
首先,佛法改变了汉字,汉字也改变了佛法:
在午后,鸠摩罗什有些离迷:
贝叶被汉字手写之后,已无
可越俎、可入替的树。
理解力从浅绿变作深绿,
视差渗入叶脉,加深了苍茫。
原文,能否少一点忧郁?
——《鸠摩罗什》
望着比积雪还要沉默的祁连山,
我有点把新月的暗伤,
与白塔寺的秋风经卷弄混了。
若是你生前没读过量子论,
容我替你手抄一遍。
——《圣僧八思巴》
《圣僧八思巴》的写作,面对了语言的混杂。对于诗人来说,一切都是翻译,一切都是解释,一切都是互文,就如同德里达所言——“在文本之外一无所有”。但这是召唤佛来倾听的语言,音乐的演奏不是为了取悦观众,也不是为了愉悦自己,而是割掉自己的耳朵,把倾听留给音乐本身,如同念经的倾听者——其实只有佛本人,如同古琴的演奏也并非为了知音之间的默默交流,而是让自然来倾听。只有佛法与自然,才可能保存我们曾经演奏的余音,让余音萦绕在新月秋风之中,如同被秋风弄混的经卷之中,由此产生出量子的未来纠缠!
“量子男孩”就出场了,他唤醒了中华文本古老的魔法,这是在“宿墨”与“佛法”内在“转生”过程中,让陈旧的诗意大法进一步变异,进入更为黑暗与混沌的中心,进入死亡硕大的惊恐,进入元素的巨大混溶,由此,才会进入新天使“振荡的频道”,这是里尔克新天使在宇宙中歌咏的秘密。f对于欧阳江河而言,这是让语言——彼此陌异的语言,都汇入到沉默的自然,把人心的意念投入佛经文字的秘义之中,因为这文字已经与宇宙的密码合一,我们需要的仅仅是虔诚与祈祷,把自己的呼吸与自然的节奏合一,韵律主宰着世界,“新天使”才可能被召唤出来。
在第十九节,写到了敦煌残纸中,不识字的惠能与忠实翻译的鸠摩罗什,似乎形成了一个汉字绝对无法化解的悖论。从前文字到后文字,从无字之书的天书到绝对可解码的算法之书,任何翻译不都是有着一种疯狂的野心:一切文本都可以翻译,哪怕是佛语也可以,这不就进入了某种翻译的神学与荷尔德林式翻译希腊悲剧时的疯狂?汉语一直被两种疯狂所撕裂:无知的盲者大师或哑语的沉默大师,从倾听的聋子到绝对可知却通天眼的千手观音,或各种怪物,比如孙悟空的72变算法,再一次说,孙悟空不就是最早的“量子男孩”,是唯一可以穿越“欲望的凡俗世界——动物的妖精世界——超越的涅槃世界”的存在,当然也是永远保持“持幼态”(Neoteny)的赤子,道家、佛教、诗人的天真,在他身上三者合一了?
在《庚子记》中,诗人巧妙插入那么多打断气脉的格言警句,就如同外来的“楔子”,在音乐赋格式的分联中,形成了文本自身的“莫比乌斯带”翻转,把汉语带往了另一重的神秘空间。
这也是为什么欧阳江河后来会着迷于徐冰,无论是徐冰的天书《盲文书》——全然不可读的无知之作,还是徐冰利用破烂垃圾堆积而成的《凤凰》——无意义之龙的反讽重组,都是文字与纹码重新编写的欢歌,试图穿越帝国都市环状公路的围困之自由的哀歌,但最终都不得不汇入“大数据”之中。有着穿越的可能性吗?除非有着“量子男孩”的穿墙术。
庄子从太古那边打的过来,
中间穿越了佛的肺叶。
手机里的孔夫子
听见讲中文的尼采先生在咳嗽。
不朽,只剩一小时的锂电。
——《四环笔记》
算法与佛法缠绕在一起
以微小之物提举万物
在提举的最高处
算法,不得不像钉子一样
把人伦挂了起来
而佛,也不得不像聋子和哑子一样
重新定义什么是聋哑
——《算法,佛法》
因为佛法来自于印欧语系,佛法当然也有算法,如同孙悟空逃不出佛陀的掐指一算:
一千种算法算出一个佛身
此一佛身,又增加了另一具佛身
当然,算法也是佛法(第十节):
在算法的内心深处
一切不是人的东西
都让机器变得焚香近佛
那么,佛法与算法的根本差别是什么?(第十二节)
算法先得学习怎么死
方可登佛门,环绕死者而眠
大数据不知死为何物
又怎么给它生命,怎么区分
这是关涉生死的算法,当然是不可能被计算的神秘之物。在诗人的诗歌中有着一种独特的生命之思吗?生命是去活自己从未活过的生命?是把剩余的生命从头开始?这是有余还是无余?或者是从无余处开始新的盈余。这是第二次重获的生命,这是从余生开始的新生命。其实,生命的悖论沉思,在1984年完成的《悬棺》中,早就已经出现了:数据无法“算计”死亡,但死亡却一次次被数据“计算”着!这是汉语的诡计与诡异,也许只有欧阳江河才能在现代汉诗中,如此自如地以诗意的文句,操纵着逻辑的U39qb9XFpp9uioVkexViiw==悖论与圣典的思辨。
二、亡灵的纠缠:“量子男孩”与病毒文本
但进入现代性,汉字的宿墨文本与佛法的翻译文本,最终都必须面对第三个文本——电子或量子的算法文本,这就出现了“量子男孩”这个生命新形象。尽管在写作的时间上,《算法,佛法》写于2021年7月21日,而《宿墨与量子男孩》写于2018年5月,但佛法与算法的互文关系以及在汉语中的命运,文本的可被改写性,文本的可反复涂改性,及其复制性与可再生性,一直都是欧阳江河最近几年长诗的核心议题,是蝴蝶的一对翅膀。
“量子男孩”的出现与量子物理学的胜利凯旋,尤其是算法程序的世界主宰,密切相关,这是一个可以自动组合、自我复制的化身,一只猴子以加速随意敲打的方式,似乎也可能写出一本《荷马史诗》或莎士比亚悲剧了,更不用说中国的古典短诗了。随着ChatGPT的出现与AI翻译的准确率提高,诗歌文本及其翻译再生方式,都遭遇到从未有过的挑战,这个挑战不仅仅导致诗歌丧失了绝对价值,也意味着文字文本随时可能被“数字文本”所取代,文字与图像、事件与人性,都可以被数字所复制而取代,难道这是文字书写与生命书写的完败时刻的来临?
欧阳江河虚构出“量子男孩”,这是最为了不起的诗意想象:这是一个孙悟空与哈利波特的魔灵组合?这是佛法的诗意化身?这是老子的赤子形态?或者只是带上了某种亡灵的鬼魂阴影?抑或是生物科技的未来幻象?当然,这也是生物科技梦想的“持幼态”,生命可以永葆青春活力,这并非神话,这是另一种生命的出生形态,这是技术带来的返老还童的梦幻,如同迪士尼的“米老鼠”一直保持着“持幼态”的动物孩童形象(如同生物学家古尔德的研究所指出的)。欧阳江河可能是世界诗人中,第一个把“生命技术”带入到诗歌玄想中的中国诗人。“量子男孩”,就如同传说中的老子,一直是一个“老小孩”,在母腹中生长了81岁才出生,仿佛永远年轻的“太上老君”。就如同中国文化在佛教化之后,也面临各种奇异幻象的刺激,为了排解无数妖魔鬼怪吞噬生命的惊恐感,《西游记》虚构出“孙悟空”的生命形象,以道教式的修炼来转化佛教,来克服佛教所带有的虚无主义特色的梦幻泡影。在欧阳江河的写作中,让来自庄子“蝴蝶”的变形形象,与这个新的孙悟空——“量子男孩”,进行了彼此穿越与代替的幻化游戏。
欧阳江河的诗文本进入了三重文本的交织游戏:佛法的圣典文本或文句——宿墨的汉字书写与道法的蝴蝶梦——算法的“量子男孩”程序演变。
这是“三重句法”的相互交织与穿越幻化。我们几乎可以在《宿墨与量子男孩》的每一节中,都看到如此“三重文本”的叠加:
不期而至的神秘客人,随身带着
三样东西:蝴蝶、宿墨、电解盐。
核裂变的猫
抓起水中鱼,并没有搁在
主人盘子里,也不和客人打招呼。
这是长诗的第二节,同时带来了三种不同的事物:蝴蝶、宿墨、电解盐,而这就指明了诗歌自身的基本语素或元素。
欧阳江河诗歌中的“鱼”,以能指的游戏带出了汉语特有的谐音:鱼、余、与、育、宇……成为万能的能指与全能的记号本身。欧阳江河延续了汉语不断“可再生”与“可转写”的秘密,从语音的“谐音”书写出发,以汉语特有的“声音”接纳佛教的“异音”——鸠摩罗什翻译带来的空空智慧,再度接纳现代汉语的拼音拉丁化,但又保留了汉字之为方块字形的感知。如同徐冰1990年代在美国做出了《英文方块字》的观念作品,把汉字的笔画转写为英文的字母,欧阳江河其实早就是第一个写出了汉字与英文关系的诗人,让方块字的字形在自身的转换与变异中,生成为他者——英文,就如同《汉英之间》,但现在,欧阳江河甚至要再次接纳“算法”!
《悬棺》的第一章就命名为——“无字天书”:
现在读到的天书以眼睛为文字:每一只眼睛是一种语言的消逝或一堆风景的破碎,繁殖禁忌和遁辞。
以及后来的:
孩子们在广东话里讲英文。/老师用下载的语音纠正他们。/黑板上,英文被写成汉字的样子。
使五笔字型输入法与拼音输入法同时进入算法,汉字的造型所启发的想象,一直引导着诗人的感知与诗歌的意象,更为重要的还是意象,这就是蝴蝶及其翅膀,还有孙悟空这个顽童的变幻体,并催生出了神奇的“量子男孩”。
如果《宿墨与量子男孩》第二节的前三行是总体导引,第四行出现的“鱼”,就是汉字文本墨迹的显影,因此涉及到夜晚的阅读,以及焚书的命运;但幻化为”闪存”——以数字来保存似乎就可以避免文件的被摧毁,文本需要量子式的保存方式;之后,则来到了佛眼的空无,这是佛法的独特算法:空无、盈满、翳蔽,但又与鱼眼重叠;但又被表述为几何的算法。
再次,以《宿墨与量子男孩》第三节为例:
在海量信息流中,
蝴蝶,闪现了一下。
爱因斯坦从量子男孩身上,
看见真雅各扮成一个假雅各,
以此断定:上帝从不掷骰子,
也不揭开撒旦的秘密。
在海量的信息中闪现出了蝴蝶,因为神圣的显现方式都是闪烁与闪现式的,不可能被人性所抓住和控制,但“量子男孩”或许有着某种凝聚神光闪现的组合能力,如同诗句在多维度穿越中的想象力综合。当然,“量子男孩”穿行的偶然性快感,也带有某种撒旦的意外危险,因此,需要神法来平衡。这就出现了一枚毫针(如同阿尔托从中国针灸学习到的残酷戏剧之身体瘟疫化的感知),只有痛感可以把我们从算法世界中带出来,进入所谓的现实世界;当然这个现实世界除非是以诗意来书写的,这就是农具的大地书写与李白的故纸堆上的书写,但最终一切都成了电子书,进入电子式的转存与复制状态。
但没有佛法守护的“量子男孩”,真的可以自由地穿越真实与幻象的世界吗?这是诗人在《鸠摩罗什》中的反思与反讽:
回避了舍利子的量子纠缠。
而一个拉大提琴的量子男孩,
竟天真地以为
弦理论,可以演奏宇宙坍塌。
三、《庚子记》:汉语的解毒剂
中国的现代性,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文”的问题,一个广义的“文之化”的问题,这是章太炎所确立的中国混杂现代性的起点g,既要保留古文的古奥,又要以西方拉丁字母为据,形成新的拼法习惯,既要接受西方的虚无主义与末世论,又要以佛法的平等来接纳西方的自由,但这都是在庄子《齐物论》的统摄下进行的。
鸟群从字典缓缓飞起,从甲骨文
飞入印刷体,飞出了生物学的领域。
——《凤凰》
这是欧阳江河在《汉英之间》 (1987年)中的追问:
一百多年了。汉英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如此多的中国人移居英语,/努力成为黄种白人,而把汉语 /看作离婚的前妻,看作破镜里的家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独自一人在汉语中幽居,/与众多纸人对话,空想着英语,/ 并看着更多的中国人跻身其间,/从一个象形的人变为一个拼音的人。
对于诗人欧阳江河而言,中国文化之为“文”,汉语诗歌之为“文”,都是“文本”,是已经书写过的文本,是被反复书写过的文本,是无数文本的叠加与涂抹,以及相互的转译与篡改,乃至于复写与复生,至于何谓“本-文”,都需要经过后来书写的“文-本”,加以再次的复写。就如同德里达所思考的弗洛伊德的书写装置,中间的蜡纸已经被各种文字的色调侵染,而那个神秘的底版或蜡板其实已经模糊不清,或者它也许已经被数字化了,是储存数字的硅质芯片了。即一切都成了算法的芯片,从生命的心灵书写,到汉字的石头刻写与纸本书写,都成为了数字的算法书写,依赖于算法的存储或转存,我们甚至都不再用纸张与墨笔了,哪里还有书写?哪里还有诗意的个体化书写?
因此,文本,广义的“文-本-性”,才是现代性内在的命运,中国文化或者汉字诗歌,如果还有余存的可能性,其原初的幻念与美妙的墨迹,如果还有所保留,这就是诗歌的责任与任务,否则就是埃及象形文字的木乃伊化,或者仅仅是封闭在自身文化历史的希伯来语化,而象形文字的汉字,到底具有一种什么样的魔法呢?
汉字文本具备双重性:一方面是作为众多语言的一种,作为表音与表意的汉语,这与其他民族语言一样,尽管一直以象形文字的方块字存活下来;但另一方面,汉字不同于其它语言之处,则在于汉字是书法书写,尽管阿拉伯语也有着装饰性的书写性,但汉字书法演变漫长,尤其是个体化特质突出,如同西蒙东所言的集体式个体化,以及个体的再个体化上,是其它文本绝对没有的潜能。
此汉字的墨迹个体化书写,在佛法中得到了延展,这从唐太宗两次让人书写《心经》或佛经,且以王羲之的集字法来复制《心经》就可以看出,这也是与玄奘的翻译同时浮现的双重文本,墨迹延伸到了佛法,佛法进入了墨迹,直到后来的很多草书大师,比如怀素就是僧人。直到禅宗出现,在日本出现简化的禅宗书法,并且延伸到日本的现代书法,比如井上有一,同时又影响了美国抽象表现主义,汉字的书写墨迹一直在蔓延与生长,此文本或书文的痕迹并没有消亡。
那么,进入算法时代呢?“宿墨”与“量子男孩”的深度关系,才是文命之延续。
但是,进入2020年,汉字的诗意文本,还要面对更为严峻的挑战,这就是第四个文本的出现——病毒自身的基因代码,这不断变异的字母符号——已经与我们基因中RNA的转译密码,混合共存了。这就刺激了欧阳江河在庚子之年写出了长诗力作《庚子记》 ,这是可以与布朗肖《灾异书写》媲美的文本,欧阳江河的文本写作由此增加了第四个系列或算法:病毒文本与算法,这是一种漂浮不定,却又深度重塑我们生命的文本。
诗歌写作可以生成出一种文字的解毒剂——“诗性抗体”吗?让诗歌具有保护生命的抗体免疫性,这不就回到了海德格尔对于里尔克诗歌的要求——无保护的冒险中如何获得保护?汉语诗歌可以给人性生命一种灵魂的保护性吗?我们再次回到了“诗歌何为”的根本问题上。
此生命的无保护的保护性,其实在王羲之的书法文本的行为中已经出现,在魏晋南北朝的战争年代,在一个普遍的“服毒”时代——文人们服食“五石散”以化解死亡焦虑与对抗社会秩序,书法的个体化出场,就不仅仅是某种艺术风格,反倒成为一种治疗疾病的代替药物,这就是以书法书写日常书信,直接表达个体生命的痛苦,欧阳江河的诗歌也写出来这“丧乱帖”式的命运。而且,对于王羲之家族而言,书法文字的文本不足以拯救生命,还需要另一种更为强大的法力——这就是借助于道教的符箓书写(王羲之父子及其很多亲朋好友都服食“符箓”治病),草书才由此生成出来,这在王献之的“大草”革命中更为明确,由此确认了书法墨迹的救赎模式。
只有沉浸书法几十年的诗人欧阳江河,才如此着迷于“宿墨”之苍凉与苍劲的历史命运,同时又寻求隐秘的超越救赎,以毒解毒,以丹药解除毒药,这是以更为强大的神秘算法,代替个体化的诗歌算法。
这就是为什么欧阳江河的写作具有一种佛教经典的念经语调,这是经过鸠摩罗什或龙树中观论的诗意转化的新语调,也是经过了现代量子算法,再次进行解构式的书写与变异后的书写算法,这是具有《神曲》建构模式的写作——如同“宿墨”与“量子男孩”具有一种“三三三”的对应结构,三种“文码”以不同的语象展开与交织,到了《庚子记》则是四重文本的编织。
《宿墨与量子男孩》的每一节,基本上都是三重文本的话语组合:汉字墨迹的蝴蝶余化——佛法无边的念经咒语——算法幻象的泡沫神力,基本上每一节都是此三元素的展开,如同但丁《神曲》。而《庚子记》,则增加了第四重文本话语——病毒的形态学与幻化的肢体,形成四方体:
蝴蝶与蝙蝠的形态学重叠——佛典与诗句交叉为引文——算法的大数据控制与转生威力——病毒与口罩叠印的面孔滋生。
这四重话语形成了每一节的叠加与交织,而《鸠摩罗什》在综合后,形成混声与念经的神秘“方言”。当然,每一节都有着诗性的加密,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
这是《庚子记》第二十二节对于疫情的见证书写与图像转换——如同道教与佛教中大量的图像之幻化叠加:
灰皮书,读到花白时,恍若一字未写。
非欧几何,或许是神的庇佑几何学,
但将函数导入肺纤维:神,不这么做。
大资本与小手艺,干的不是一回事。
有纳米的精确,也有大数据的精确。
神准许跳蚤,偶尔发一发形而上牢骚,
准许猫头鹰戴上口罩,去赴光的盛宴。
(以撒亚书:太阳七倍灿烂,仿佛七日合一。)
直到最后,在寺庙空间与肉身译经的时空折叠中,“量子男孩”转化了“飞天”形态的新天使,在“没”与“好”的念咒式对举中,在“非我”与“皆可”的回应振颤中,如同佛经的念咒,不断重复与回旋,让灵魂与语言得以双重获救:
没露滴不是老僧春梦。
没突变不可不变,或渐变。
……
立地成佛也好,长时段待召也好,
一千六百年后上抖音上热搜也好,
……
弃我落日之身或囚我圆月之身,
睡入我梦或肉入我心,
是我之不是,非我之所非,
总之万般皆可, 万般皆可……
总之,我,鸠摩罗什,
要开始译经了。
——《鸠摩罗什》
四、发明“天使抗体”:走向绝对文本
我们可以简要地说,诗人欧阳江河最近几年长诗写作的密码,乃是“四重文本”或“文本密写术”的交织:
1.汉字的墨迹文本。《黄山谷的豹》是代表。新作《移山》也是如此,只是更为复杂。而《埃及行星》则是与汉语象形文字的对照,反思古老帝国的集权与出埃及的诗意民主,形成了“余化”的辩证法。
2.佛法的无边幻象或佛典的改译文本。以《圣僧八思巴》为代表,而《算法,佛法》中面对算法的佛法,也是重新回到佛典对于汉语的改造上。
3.“量子男孩”的程序算法文本,或电子幻象的爆炸。以《宿墨与量子男孩》为代表。
4.病毒文本或基因共在的生命改写文本。以《庚子记》为代表。
5.最后则生成出“新圣典”,或召唤汉语的天使守护,形成诗性经典化的“天使抗体”:新作《鸠摩罗什》是完美的化解与综合。
当代汉语诗歌的写作中,就出现了一种新的“金刚体”或新的“天使疫苗”,这种带有生命绝对保护性的文本,才是“绝对文本”,是克服诗人所言的“反词”的“抗体写作”,对应于佛典《心经》金刚不坏的心咒体。
现代汉语诗歌必须同时呈现这四重文本,或广义的“文”(文字、文本、文化、文迹、文典、文明、文码)的现代性,文本与生命书写的现代性,由此,现代汉语诗歌才抵达它的文字救赎之道,生成为新经典,即《鸠摩罗什》这样的典范杰作!现代汉语诗歌才能成为世界性的“绝对文本”。
这是《庚子记》中的第四十五节:
宿墨废纸,引刀试命,引火焚身,
无非天下文章,一读成灰。
管理利维坦的将是5G,而非国会。
(霍布斯:利维坦……只是一个人造的人。)
发帖,发浩叹, 终归是遍体江湖。
如果武士不以病毒暗藏火焰 ,
会以为见笔如刀的那人是个书生。
真正的执念并非一人独有,而是
万事皆空:勇气,塑造着全人类的示弱。
……
酒以不饮为醉,琴以无弦为音,
心远:自无车尘人迹,何须痼疾丘山。
心远: 哀其一生过往皆成虚妄 ,
于旧日无增,较来日徒减。
就仿佛你是个经过过滤的人。
这一节诗也是四重句法的完美交织。诗句的前两行是“宿墨”的句法,接着后面是“病毒”的句法,然后是技术检测的“数字”算法,经过“量子男孩”的穿越连接,随后是佛法与道法的“抗体”句法。但语词都会再次回返,回到“宿墨”的书写,回到文心的交织,回到虚妄及其克服,回到回纹的交织,借助于“量子男孩”的轻逸,文章、文人、文书、文主、经文、文音等等,得以相互纠缠与彼此交织,最后都归于文心,形成回心的文本,此回心乃是回环的守护,因为任何的算法与读法,都敌不过人心,人心形成的文码,才是可以无尽回返的呼吸轨道。
这是《鸠摩罗什》的第二十六节“十诵律”:
真与讹,按十诵律的教条,
写出一部鸟迹鱼书,
仅仅为了察看土星。
佛之缓慢,一时还不觉扰乱。
要等鸠摩罗什把讲经坛
以光速迁移到土星上去。
要等鸠摩罗什把汉语所无的原质,
赋予统治者的汉语,
等他换一只鹤,
把有言在先骑入死后的舌头。
所有的先行一步者,
终将落在落日之后:
精神邈远,
路远,心远,唯草鞋是新的。
——万法归心,但心却遥远,要让汉语回心,在无尽的诗意颂咏中,把“把汉语所无的原质”植入到汉语之中,这是量子纠缠的反向重构,是多重文本折叠的诗意技术所困难施行的工作,由此才可能让这异质植入或嫁接的元素在未来获得统治的资格!汉语才可能余存,才可能让精神获得渺远的尺度!
这生命守护的形象,就由“量子男孩”转生为天使,这是面对病毒的“天使疫苗”——就如同克利的“新天使”从天而降(《庚子记》的第二十九节):
在罗马,没有一锤定音的天使疫苗。
情侣护士,旧容新冠,磁化了爱的语言。
春梦像是侦探小说里的一枚苦杏仁,
左脑抽屉里,堆着好些符号学零件。
此天使疫苗,如同本雅明思考的新天使双翼,带有威胁与救赎的剪刀般翅膀,其实也是一种生命的修复技术,是生命技术(Bio-technics)的诗学投射。
这不禁让我们想到当代基因修复技术中的CRISPR模式。CRISPR-Cas9是继ZFN、TALENs等基因编辑技术推出后的第三代基因编辑技术,短短几年内,CRISPR-Cas9技术已经风靡全球, CRISPR-Cas系统是原核生物的一种天然免疫系统。其原理是:在最为古老的细菌体内,当其遭到病毒入侵后,立刻把病毒基因的一小段存储到自身DNA里一个称为CRISPR的存储空间中;而当再次遇到病毒入侵时,细菌能够根据存写的片段,来识别出病毒(如同病毒疫苗的类似效果),将病毒DNA切断而使之失效。何谓CRISPR?这个缩写形式,意味着原核生物基因组内的一段重复序列,其全称为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ers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成簇的规律性间隔的短回文重复序列),分布在40%的已测序细菌和90%的已测序古细菌当中,尤其是一些远古而独特结构的古细菌中,从生命技术的哲学角度看,这似乎是自然的天道,为人类保持弥赛亚的种子。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就是通过人工设计的sgRNA(guide RNA)来识别目的基因组序列,并引导Cas9蛋白酶,进行DNA双链有效切割,形成双链断裂损伤,然后再生修复,造成基因敲除或敲入的剪辑效果,最终达到对基因组DNA进行修饰的目的。h
在欧阳江河的诗歌中,这由“宿墨”、佛法和“量子男孩”整合起来的“天使抗体”,就为汉语发明了一种文化基因的诗性剪刀,一种生命保护的诗歌武器,那些有着间隔的回文短句,在欧阳江河的诗歌中随处可见,这是如同咒语一般古老的天籁之回响。
那么,诗歌何为?在我们这个时代,诗歌乃是为生命提供一种来自于深度感知的心灵书写方式,汉语的诗性写作不仅仅是一种审美与修辞,而是世界深处心咒的古老回声。
鸠摩罗什死后梦回武威,
将舌舍利留给西域大地,
去驰骋,去领悟,去见证。
此“舌舍利”化为汉语,汉语就被赋予了佛法的回纹间隔,获得了飞天天使或千手观音式的保护剪刀,但进入现代性,在翻译各种西方圣经或经典之后,我们是否也获得了某种回纹间隔的修饰剪刀?我们必须发明新的“天使疫苗”。
欧阳江河的长诗写作标志着现代汉语与现代汉诗的双重成熟,现代性的文心终于抵达了书文的绝对性,从此汉语写作不再依赖于西方大师的文本及其想象模式,而是从汉语的文字性与书写性,从纸墨的呼吸到异质语文的吸纳,在重新描摹内亚的地脉与文脉的深度交织后,对于机器算法与病毒文码的双重克服,这也是对于技术虚无主义算计的诗意转化。诗文从来不是狭窄的文学修辞技术,而是生命在文本轮回中的自我克服与绝对凝神,它借助于语词的幻象推动事物的幻象,因为生命离不开幻象,但这并非梦幻泡影的翻滚,而是让叠加的重重幻象回到其生命重复的轮回照应中,链接那些有着节奏间隔的回文或回纹,诗歌文本书写的隐秘之手,就是生命诗性密码的解谜者与修剪者,而这正是诗歌天使的工作,如此的“天使抗体”才能给予生命以保护性,如此具有免疫抗体的文本,不会诱发自身免疫的自杀冲动,才是呼吸转化的绝对文本。
【注释】
a此处为笔者自己的直译。
b[德]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c参见[奥]赖纳·马利亚·里尔克:《杜伊诺哀歌》,《里尔克全集》 (第3卷),陈宁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45-896页;[德]彼德·斯洛特戴克:《资本的内部:全球化的哲学理论》,常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d关于“晚岁”的诗歌讨论,随着中国当代诗人(特别是1950-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很多都过了甲子之岁,在王家新与策兰的对话中,尤其是欧阳江河自己最近的文本中,都开始讨论晚岁风格。参看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还有最近发表的《六十之后》等相关文章。尤其在疫情之后,生命的“余生”状态给诗歌写作带来了独特感知。这个维度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展开,是思考中国当代诗歌未来走向的一个重要指标。
e欧阳江河:《宿墨与量子男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相关诗句也请参看诗人的相关诗集,不再一一注明。
f参见[奥]里尔克:《穆佐书简——里尔克晚期书信集》,林克、袁洪敏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215页。里尔克在一些书信中,深入思考了“不可见之物的蜜蜂”,以及诗歌如何进入宇宙的振荡频率,所谓的新天使并不神秘,只不过是要求歌者以自己全部身心的歌咏,汇入宇宙的无尽回旋的空间,发生永恒的共振。也许欧阳江河在欧洲古堡中的沉思,已经触及这个密码,这也是“量子男孩”之为新天使的中国式形象。
g林少阳:《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h参见[美]詹妮佛·A.杜德娜、[美]塞缪尔·H·斯坦伯格:《破天机:基因编辑的惊人力量》,傅贺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版。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