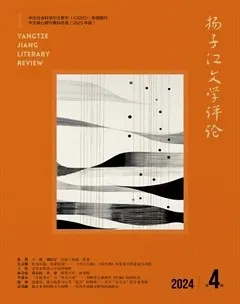“小说考古”与“考古小说”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些作家以“劳模”著称,他们把文学视为庄严的劳动,而他们自身也成了庄严的劳动者。他们不仅创作时间长、历史跨度大,而且在各体文学创作中都有堪称经典的杰作。刘醒龙就是这样一位文坛劳模,他在四十多年来的文坛生涯里勤爬苦作、笔耕不辍,一步一步地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文学王国。如果说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刘醒龙主要以中短篇小说创作见长,那么进入新世纪以后他就主要以长篇小说创作作为自己的志业了。刘醒龙早年写过一部名为《生命是劳动与仁慈》的长篇小说,“劳动”与“仁慈”这两个词其实传达了刘醒龙的生命价值立场与姿态。其中,“劳动”意味着生命要不停地创造,而“仁慈”则意味着生命在创造中不能没有悲悯情怀。这种创造精神和悲悯情怀不仅在他的中短篇小说佳作中有着深刻而动人的表现,而且在他苦心经营的长篇小说系列中表现得更为强烈而深沉。刘醒龙曾经说过:“人有人品,文有文格。‘长’与‘重’,是长篇小说安身立命的根本,长度代表外在标准,厚重则是内在品质。长篇小说是有生命的,有一套在文学史与文学现场中自给自足的体系,就像世外桃源和沙漠绿洲,不依附时世而生存。”a显然,厚重大气的内在精神品质,是刘醒龙长篇小说创作的一贯追求。他希望自己的长篇小说能够像世外桃源和精神绿洲一样,既给读者送去深厚绵长的精神慰藉,又能在文学史和文学现场中保持独立不倚的精神姿态和文体美学。
在刘醒龙的长篇小说系列中,以他的故乡黄冈或鄂东地区为背景的乡土或农村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居多,如《威风凛凛》 《痛失》 《圣天门口》 《天行者》 《黄冈秘卷》等长篇杰作皆是如此,就此他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乡土文学代表作家之一。虽然故乡的山地和平原是他的精神家园,但刘醒龙中年以后实际上长期寄身于城市,即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汉,它已然成为了刘醒龙的第二故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众多的乡土文学大师都是城籍农裔,他们置身在繁华的现代城市中,精神上却漂泊无依,始终无法从内心认同现代城市文明,如众所周知的沈从文就寄望于以传统乡土人文理想疗救现代城市文明病,所以他批判城市知识分子的中篇小说《八骏图》就与抒写湘西美好人性人情的中篇小说《边城》形成了截然相反的艺术对照,让读者从中深味传统与现代、乡土与城市、农民与知识分子之间的文化或精神的分野。与沈从文的小说不同,我们在刘醒龙的长篇小说系列中看不到那种城乡之间的尖锐对立,刘醒龙无意将乡村当作批判城市的文化背景板,而是试图站在超越城乡二元对立的历史视域中客观地审视中国城乡社会中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生状态与精神状况。当然,相较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黄冈和鄂东大地,武汉这座城市对于作为文学家的刘醒龙而言,要想深度书写并不容易。就像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一样,武汉的城市文学形象早就被其他作家提前打上了标签,这意味着刘醒龙必须突破关于武汉的刻板的城市文学印象,重新为武汉这座城市画像。长期以来,武汉给广大读者留下的文学印象是世俗的烟火气和市井的日常性,但这仅仅是武汉这座城市的一个侧面,甚至可以说是城市表象,而被掩盖的另一侧面,或者说作为城市精神的则是春秋楚文化的精神血脉。在我看来,抒写武汉这座城市的深层楚文化精神血脉,借此重塑出不一样的武汉城市文学形象,正是寄居武汉三十载的作家刘醒龙创作“青铜重器三部曲”的文学初心。
所谓“青铜重器三部曲”,其实刘醒龙目前只完成了两部,只不过两部的时间间隔有整整十年之久。由此,不难窥见刘醒龙对长篇小说创作的审慎态度。第一部《蟠虺》问世于2014年,当时就好评如潮。第二部就是2024年新鲜出炉的《听漏》,它与《蟠虺》具有明显的连续性。主要人物曾本之、马跃之、郑雄等人一脉相承,只不过一号主人公由曾本之变成了马跃之,他们都是楚学院的知识精英,一起折射了武汉这座城市的人文知识分子众生相。故事题材依旧是关于楚文化的历史考古,而叙事依旧以武汉的楚学院和湖北省博物馆为中心来展开,只不过武汉之外的故事发生地由《蟠虺》中的鄂东黄冈、黄州,置换成了《听漏》中地处于历史上有名的“随枣走廊”一带的京山。至于小说的主题,则依旧是追问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文化精神,尤其是拷问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人格建构问题。如何赓续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如何重塑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人格,这是刘醒龙在“青铜重器三部曲”中重点思考的中国之问与时代之问。而刘醒龙提供的答案则来自他多年来对楚文化传统的深刻思考、来自他多年来对湖北省博物馆馆藏楚国青铜重器的生命流连,以及对武汉这座城市长期被遮蔽的文化血脉的精神眷恋。刘醒龙在新世纪初曾写过一篇文化思想随笔《楚汉思想散》,其中就隐藏着他对武汉这座城市被遮蔽的楚文化血脉的执着探寻。在那篇随笔中,刘醒龙对清末大员张之洞来到武汉主政后提出“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的说法深表遗憾。他写道:“那位叫张之洞的大员不经意间说的一句话,被一代代的人当了真,弄得天下人都以为这地域上的芸芸众生个个都是人精。”而实际上,在这片土地上“偏偏他们只是率性而为,做事论事,大多凭一时好恶,性情所致,慎思不及。张之洞所言及的以及后人对其理解的,恰恰与此相悖,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在刘醒龙看来,“汉楚”之人是具有浪漫精神的“性情中人”,从古代的屈原到现当代的闻一多和胡风,都是极具代表性的汉楚先贤。“性情中人,好则好矣,不好起来一个比一个下场悲惨。”这就是汉楚之人文化性格之悲剧性所在,虽有“敢为天下先”的辛亥革命之举,但“最终的历史烟云只让它扮演了一名优秀的配角”。由此上溯至先秦时期的八百年楚国史,刘醒龙不禁要发出许多现代人心中难解的一个天大的疑问:“假如当年不是由秦国,而是由楚国来统一中国,中华民族的历史会不会更加光彩?”b然而历史不能假设,作为小说家的刘醒龙只能到残存的“大楚青铜馆”中去寻觅汉楚文化的精魂。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湖北虽然是楚文化的发源地,但作为省会的武汉却与楚文化关系不大。诸如孙权在武昌屯兵,岳飞在武昌抗金,李白和崔颢关于黄鹤楼的诗争,都很难让人将其与先秦的楚文化关联起来。只有俞伯牙与钟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汉阳传说让人还能遥想起三千年前的楚人风神。所以武汉这座现代中国大都市多年来给人的印象还是个“大码头”,以汉口的商业文化和市井生活驰名饮誉于民间。但自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汉口北盘龙城遗址逐步浮出历史地表,武汉逐渐被考古界公认为是商代中国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盘龙城大量出土的商代青铜器表明,武汉不再是一个在上古文化上无根的城市,而是一个历经数千年沧桑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按照李学勤先生的说法:“古代在同样位置出现盘龙城,不是偶然的,它和后来的武汉三镇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c也许因为作为古代交通要塞的武汉是兵家必争之地,其楚文化血脉反而长期被湮没于历史尘埃中。这就给了刘醒龙驰骋历史文化想象的巨大空间。如何在现实题材的“青铜重器三部曲”中重现上古时期汉楚文化的历史辉煌与人格光芒,成了刘醒龙在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创作中深感困扰的谜题。从《蟠虺》到《听漏》,刘醒龙二十余年来一直在倾听和叩问来自武汉这座汉楚历史文化名城精神深处的青铜声响,他想借此重塑武汉的文化风骨和历史风神。当然,最令刘醒龙着迷的还是汉楚文化中的青铜重器。一般而言,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出现过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出现在商代后期,第二个高峰出现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关于这两个时期的青铜器铸造工艺,在考古学界存在范铸法与失蜡法之争。d刘醒龙十年前创作的《蟠虺》就是围绕着湖北省博物馆馆藏的曾侯乙尊盘究竟是由范铸法还是由失蜡法铸造而成展开核心情节冲突的,主人公曾本之晚年力挺范铸法,在科学面前改变了早年观点。而在新作《听漏》中,刘醒龙不再围绕着青铜工艺来构思主要情节,转而将故事聚焦在汉楚青铜重器“九鼎七簋”是否残缺的历史文化之谜的破译上。对于刘醒龙而言,他明白自己不是考古学家,作为一个小说家,他更眷顾那些充满历史残缺的楚国青铜重器,因为只有以残缺的青铜重器作为艺术载体,他才能传达自己作为小说家的想象和才情。相反,完美得天衣无缝的曾侯乙编钟,除了让小说家叹为观止,很难激起他们虚构和重构的冲动。这也是面对历史文物时,小说家与历史考古学家眼光的歧异之处。
在中国,“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正所谓:“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顾名思义,古人所谓的“小说”大多是丛残小语、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与经国大业、不朽盛事之类迥然异趣。所以小说在中国古代长期难登大雅之堂,但随着古典诗文正统地位的逐渐衰落,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样式日渐繁荣,及至近现代则摇身变为文坛正宗。但即便如此,现代人眼中以虚构见长的小说,依旧与求真务实的历史学、考古学大相径庭。虽然有所谓新历史主义或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兴起,认为历史也是叙事的产物,本质上可以划归为虚构范畴,但总体而言,文学或小说重虚构,而历史学、考古学尚真实,前者属于艺术,后者属于科学,这种学科界限还是很难被拆解的。所以当刘醒龙要以小说的艺术形式介入先秦时期,主要是“两周时期”,即西周和东周时期的汉楚青铜重器考古领域时,这不能不让读者感到惊讶,因为长期以来的新乡土作家身份制约了人们对于作家刘醒龙的文学认知。一边是现实的乡村文化,一边是城市的历史文明;一边是街头巷尾流行的“小说”,一边是学术象牙塔里的“考古”,这种文学选择的反差与歧异远远超出了读者对于作家刘醒龙的审美期待。但刘醒龙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他勇敢地走出了自己的创作舒适区,而一头扎进令读者倍感陌生的先秦历史考古领域,以“小说考古”的形式创造了具有独特艺术个性的“考古小说”,不仅颠覆了读者对作家的期待视野,同时也重构了自己的作家形象,开辟了新的艺术领地。所谓“小说的考古”,指以虚构、想象、叙事、修辞等“小说”的方法来讲述历史考古的故事,重在“小说”;而“考古小说”则重在“考古”,强调以小说的形式所讲述的考古内容或考古题材。与“小说考古”所强调的文学性与虚构性不同,“考古小说”要凸显的是文本的真实性与历史性。所以“考古小说”不是市面上流行的某些拙劣的“盗墓小说”,它反对随意穿越或肆意虚构,而建基于科学的历史考古学之上,视历史的真实、文物的真实为生命,绝不戏说历史或戏弄文物。这样说当然不意味着“考古小说”反对虚构和想象,但它的虚构和想象必须站在历史和文物的真实性的基础上,不能逾越历史真实的底线。这就像“历史小说(剧)”虽然不同于历史,但它不能完全丧失了历史品格,必须要处理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如何统一的问题”e。毫无疑问,从《蟠虺》到《听漏》,小说中讲述的历史文物(汉楚青铜重器)的发掘与考证故事必须有历史真实性和科学性作支撑,但小说中讲述的故事情节和塑造的人物形象则完全是虚构的和想象的,当然这种虚构和想象必须来源于社会生活,由此才能达成“考古小说”中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
无论是“小说考古”还是“考古小说”,首先都必须做到将考古的专业性知识纳入小说叙事的虚构与想象中。事实上,这种知识性叙事在中国小说传统中由来已久,以晋人张华的《博物志》为标志的“博物”叙事传统对中国古代小说和近现代以来的小说创作有着深远影响。新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作家尤其是小说家越来越重视叙事中的知识性含量或知识性表达,比如科幻小说在新世纪的勃兴,正是高科技对小说创作直接介入的产物。而新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学,尤其是考古学的繁荣,同样与现代科技进步密不可分。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不断推进和步步深入,许多中华上古文明之谜被破解,这无疑给当代中国小说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创作机缘。据刘醒龙自己说,藏着稀世楚国青铜重器的湖北省博物馆就在他家附近,他曾长期对馆藏的曾侯乙尊盘流连忘返,三番五次、七弯八绕地围着这神奇的尊盘逡巡,直到终于有一天“自己被这种名叫灵感的东西所俘获”,“这有点像爱情,千辛万苦地追求某个心仪的女子,等到抱得美人归时,自己却成了人家终生的俘虏”。f从此,刘醒龙开始不断追踪考古学界有关曾侯乙尊盘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想尽各种办法搜寻与青铜重器铸造工艺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然后将考古学的专业知识消化后溶入自己的小说想象和叙事虚构中,这才有了“青铜重器三部曲”的第一部《蟠虺》的诞生。《蟠虺》中对曾侯乙尊盘的透空蟠虺纹饰的精美神奇描绘令读者拍案叫绝,而有关曾侯乙尊盘蟠虺纹饰铸造的工艺之争,究竟是范铸法还是失蜡法的问题,构成了《蟠虺》的叙事核心,这种充满了专业知识性的情节设置让读者不得不佩服作家刘醒龙的博学多闻。在《听漏》中,刘醒龙再一次调动了自己多年来涉足汉楚青铜考古的知识积累和专业储备,将叙事重点聚焦到破译“九鼎七簋”是否残缺的历史之谜上。而围绕“九鼎七簋”历史之谜的破译,作品以马跃之为中心人物展开了一系列的人事误会和矛盾冲突,如主要人物曾本之与马跃之、郑雄与马跃之、梅玉帛和陆少林与马跃之之间都存在着各种明里暗里的误会与冲突。这些误会与冲突的消解,最后都与“九鼎七簋”历史之谜的破解有关,考古知识性叙事就此成为了整部作品叙事结构的枢纽。
在《听漏》中,刘醒龙设置了许多关于历史考古的知识性叙事,它们大多与青铜重器或汉楚文化风俗有关,给整部作品营造了一种古雅厚重的叙事氛围。按照小说第2章中的说法:“在历史面前,青铜列鼎配列簋,最能体现王者之气。”“在辉煌的朝代,青铜鼎簋会让这种辉煌更加灿烂。”“在衰竭的王朝,青铜鼎簋会将这种衰竭衬托得更加残败。”故而有句行话说,“有鼎无簋,山高缺水”,反之,“有鼎有簋,山河雄伟”。g所以,“九鼎七簋”成了主人公马跃之、曾本之、郑雄等人关注的焦点。《听漏》中花了大量笔墨介绍大楚青铜馆中藏的这件国宝重器,并讲述了诸多与之相关的历史和现实的故事。楚学院就是因1966年在京山县秋家垄发现了“九鼎七簋”而成立的研究机构,由于此后又在随州擂鼓墩发现了更加完备的“九鼎八簋”,所以一段时间其风头被后者掩盖,但对于考古学家而言,完美的“九鼎八簋”缺乏继续探索的空间,而残缺的“九鼎七簋”却成了萦绕心中挥之不去的历史谜团。按照楚学院中最有发言权的周老先生的说法:“完整的九鼎八簋虽然成了两周时期的文化符号,不完整的九鼎七簋才是两周时期政治文化的集大成者。”h如何破解“九鼎七簋”中隐含的先秦政治文化奥秘,就成了楚学院同人必须完成的一桩历史使命。而对“九鼎七簋”的考古探秘以及与之相关的人事纠纷和爱情故事,就构成了《听漏》的主要叙事框架。除了有关“鼎簋”的考古知识性叙事,《听漏》中还讲到有关“矰矢”“青铜方壶”“竹筒葬”“喝早酒”等多种楚地青铜器具或民情风俗的故事。比如小说第13章中重点讲到马跃之破解郭家庙墓葬出土的上古弋射器具“矰矢”的故事。这是为了凸显马跃之尽管早已转行研究丝绸漆器,但依旧葆有精湛深厚的青铜器鉴定功力。面对墓中出土的一堆杂乱器物,包括长条状、纺锤状、鎏金型器物,当楚学院同行一筹莫展时,久疏青铜考古的马跃之还是灵感四溢,及时作出了正确推断。他认为郭家庙一带是随枣走廊入口,是洛邑到郢都、中原到荆楚的通关要道,上古时期接待达官贵人最好的见面礼就是献上一只活蹦乱跳的大雁,所以形成了上巳节司蚕射雁的风俗,其中就包含了一种技术含量很高的职业——“弋射”!这在《周礼》中早有记载,马跃之就此推定墓葬出土器物乃是用于弋射大雁的矰矢!小说中这种考古知识性叙事不仅扣人心弦,而且趣味横生,给读者带来了知识性和趣味性合一的双重阅读快感。
再如“喝早酒”的楚地民风,小说第14章做了精彩的释读。京山湫坝镇喝早酒的习惯一直延传至今,传说当年楚王带兵打了败仗,守城官认为有损大楚国威,不许打开城门迎接,由此迫使楚王带着箭伤再度出征,等到终于得胜还朝,楚王却箭伤复发,一命归西。弥留之际,楚王给每家每户赏赐一坛美酒,湫坝人于是为楚王含冤抱屈,所以每晚夜不闭户,将备好的酒菜置于桌上,待成仙的楚王来享用。但夜里楚王不来,客人不来,美酒无人享用,所以早晨就由主人自己喝掉,然后带着微醺的醉意、怀着感恩的心情上田野劳作。这种楚地民风的破译性解读竟然还可以在《左传》的相关文献中发现部分佐证。据记载,楚文王曾讨伐黄国,在《庄公十九年》中有“还,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这样的简短记述。按照小说中秋风的说法,守城官鬻拳明知楚文王之死与自己没有太大关系,但他还是深感愧疚,于是自行来到湫坝,在楚文王的英魂面前自杀谢罪。临终之际,他还让人将自己的肉身用一种名叫“竹筒墓”的特殊葬俗下葬,这样他在地下苦修三千年后才能转世投胎,以此惩罚自己的罪愆。所以,湫坝这里又有“十恶之人三千年才能还阳”的说法。历史上,崇信巫术的楚人,特别是随枣走廊一带的楚人,发明了一种专门用于对付恶人的严厉方法。他们在地上挖一个竖式竹筒墓,将需要惩治的恶人遗体剥光衣物,头下脚上、倒放其中,再掩上黄土。按一尺等于两百年计算,五米就是一丈五尺,算起来需要等到三千年以后,埋入地下的恶人才能转世投胎。而秋风之所以选择用竹筒墓埋葬自己,既是为了自我惩罚,也是为了惩罚未婚妻小玉老师对自己的背叛,小玉老师果然大受刺激,她怀着无尽的忏悔,在生下一对龙凤双胞胎私生子后,碰死在秋风的墓碑前。此后这对私生子流落民间。而作为私生子的父亲,马跃之长期以来怀抱着难以平复的心灵隐痛,寻找失踪的孩子成了他一辈子的心理牵挂。马跃之与秋风、小玉的情感纠葛,实际上构成了《听漏》的核心叙事密码。
如果说《听漏》中的考古知识性叙事是一种小说的“知识考古学”,那么刘醒龙在《听漏》的创作中还将这种“知识考古学”进一步深入到“文化考古学”的层面,让读者在获取陌生化的考古知识的同时,还能对中国上古的汉楚文化精髓有透辟的理解。事实上,这也是刘醒龙的“青铜重器三部曲”的整体创作原则,从《蟠虺》到《听漏》都遵循了这种从“知识考古学”转入“文化考古学”、从“知识性叙事”转入“文化性叙事”的艺术路径。在《听漏》中,刘醒龙继续像《蟠虺》中一样全力推崇先秦青铜重器文化,尤其是对汉楚青铜重器文化推崇备至。在《听漏》第9章中叙述人转述了这么一段话:“在楚学院的人看来,楚鼎才是两周时期整个东方世界,乃至青铜文化为标志的同一阶段人类社会最有艺术气质的器物。那种用最不起眼的弧度,在鼎身中部做成一段束腰,再配上一对稍稍有些弧形宛若向外飘飞的鼎耳,构建出楚鼎独特气韵的那些弧线,具备了人性中不能缺少的漫不经心的自由和自然天成的约束。同为钟鸣鼎食时重要礼器的秦鼎,楚国人就瞧不上眼。问鼎中原的楚庄王,只关心周朝国之重器的鼎的大小。北方的周朝与大秦制造的青铜鼎,如果没有那对鼎耳,在艺术气质上也还说得过去,丑就丑在那对鼎耳,直愣愣地竖在膀大腰圆的鼎身之上,若放置在世上所有长着耳朵的东西行列里,唯有猪八戒比其更丑。对楚学院的人来说,在昔日楚地的核心区域出现一只秦鼎鼎耳,在文化上了无意义,在学术上也一无是处。”i虽然这里不免有抑“秦鼎”、扬“楚鼎”的情感意气之嫌,但从中不难窥见刘醒龙对汉楚青铜重器情有独钟。在楚学院人眼中,实际上也是在叙述者眼中,楚鼎中蕴藏着人性的浪漫与自由的天性,其艺术的飘逸与灵动是秦鼎所不能比拟的。当然,本文无意于辨析楚鼎与秦鼎、楚艺术与秦艺术、楚文化与秦文化的是非优劣曲直,我们关心的是,刘醒龙所推崇的楚鼎或楚国青铜重器中究竟蕴藏着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文化、人格,让他如此着迷?毫无疑问,在中华古典文明起源时期的上古楚文化中,一定埋藏着我们今天重建中华文明的历史奥秘。有意思的是,《听漏》中反复讲到主人公马跃之无意中发现了一本明版古籍《楚湫》,对《楚湫》的修复与辨认成了贯穿《听漏》全部叙事的一条潜在线索。当《楚湫》的文字被破译之际,也就是《听漏》的揭秘叙事即将真相大白之时。
在民间一直有一个疑惑,为何史书记载都写“随”国,而出土文物却都写“曾”国?《听漏》中的讲解员王蔗对此也大惑不解:“我在大楚青铜馆讲解时,平均十分钟就有人问,为什么史书上只有随国没有曾国,而青铜器上只有曾国没有随国?”这对于楚学院的考古学家而言,同样是一道需要破解的历史难题。楚学院第一代权威专家周老先生生前曾提出过假设:“曾就是随,随就是曾,曾随是一家。”但他的判断始终缺乏历史佐证,无法形成权威结论。楚学院第二代专家中的佼佼者、英年早逝的考古学家郝嘉也曾说,太史公司马迁的人格与人品绝对不在董狐之下,但他只写“随”而不写“曾”,原因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随枣走廊一带原本是“随”的方国,后来的“曾”用极为卑鄙的手段上位,所以拼命地在一切青铜礼器上镂刻“曾”、铸造“曾”,可谓欲盖弥彰。偏偏先秦时期的士人如屈原等人,都极有风骨,坚决不许“曾”在典籍中出现。不仅如此,关于“九鼎七簋”的出土地,郝嘉生前也曾指出,秋家垄是十恶之地,按常理不应该作为王侯将相的寢陵,但“九鼎七簋”偏偏与曾侯有关,难不成就是要使曾侯王族精气消散、脉断根除?郝嘉就此进一步假设,或许当初预定的随葬礼制就是九鼎七簋,而非九鼎八簋。其中,九鼎俱备是表示承认墓主确实位列九鼎,而原本应该出现的八簋,之所以少了一簋,则是为了表明,墓主的九鼎之尊其实存疑,比如来路不正、德不配位之类,所以在簋的数量上做点折损,用来警戒后世。这也可以从随枣走廊一带发现的先秦青铜礼器铭文那里得到部分证明。曾本之和马跃之都注意到,只要是以“曾”开头的铭文,几乎都用“子孙永宝”作为结束语,而其他青铜礼器上的铭文就不是这样,如秦公墓出土的列鼎铭文就很简单,基本上都是“公乍宝用”,一看就自信满满,不像“曾”字头的青铜礼器铭文,动不动就祈求“子孙永宝”,马跃之由此断定铭刻在青铜重器上的“曾侯”底气不足,好比生活中的怨妇,越是遇上不如意的事,嘴里越是喋喋不休、没完没了。曾本之虽然认为这个观点很新鲜,但考古不能靠哗众取宠,必须有实打实的证物才可以形成定论。在《听漏》中,全书最核心的叙事线索就是破解“九鼎七簋”为何缺了一簋的历史之谜,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开“曾”“随”两国关系之谜。这一学术使命在曾本之主动隐退后最终落在了马跃之的肩上。
秋家垄既是楚学院事业的光辉起点,也是楚学院同仁活生生的“滑铁卢”。自从1966年因为修建水渠偶然挖出“九鼎七簋”以来,这个残缺的楚国青铜重器之谜始终无法破解。直至2016年,因为盗墓贼的盗掘,在秋家垄又发现了先秦贵族墓地,于是多年不碰青铜重器的马跃之重回故地,受命主持秋家垄墓葬挖掘工作。马跃之注意到,出土于秋家垄的“九鼎七簋”上没有铭文,但同时出土的其他青铜器物上都刻有“曾仲”或“曾仲游父”,结尾都是“子孙永宝”。但“九鼎七簋”为何残缺一簋,马跃之和他的团队始终无法找到答案。直到有一天马跃之终于将残缺的《楚湫》一页页地修补好,才发现了这样一句神秘的警语:“天子不灭天灭,礼器似享非享。”据这部刻印于万历年间的《楚湫》残本记载,京山湫坝地下多有青铜重器,且出土时每每呈颠倒姿势,此乃周天子敕令之故。曾氏篡随,虽然李代桃僵,但方国治理相当得法。周天子敕令其实有褒有贬,既肯定了曾侯的治理功绩,也隐含了对曾侯犯上作乱的警告。虽然天子不灭曾,但天会灭曾;虽然天子允许曾侯将鼎簋礼器按规制摆设,但没有尊贵德行的曾侯其实不许真正使用,所以随葬鼎簋都被倒扣过来摆放。《楚湫》中之所以反复出现“荣华二十载,倒扣三千年”之句,正是为了说明作为方国王侯的曾侯虽然荣华一世,但却要用三千年苦役来赎身。这是对僭越者的无声警告。事实上,秋家垄贵族墓地的青铜重器及一般青铜器物,无一例外都是口朝下、底朝上,颠倒放置在墓室边厢。这就为《楚湫》的警醒文字,提供了出土文物的铁证。更重要的是,马跃之还带队从秋风的竹筒墓的挖掘中,发现了一只用于制作青铜簋的陶范。陶范上的文字写明:“天子不灭天灭。”这正好与《楚湫》上的文字相互印证。原来周天子敕令七簋之外的八号簋上必须刻有铭文“天子不灭天灭”,这是曾侯不愿意做,又不得不做的事。最后拖到自己一命呜呼,只好将做好的陶范一起下葬。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跃之要仰天长啸了,他深刻地意识到:“不完整的九鼎七簋才是两周时期的政治文化的集大成者。”“九鼎七簋课题,要探究的不是第八只簋,是天下文人的魂灵。”j在曾本之看来,马跃之的发现不可谓不重大,不仅揭开了“九鼎七簋”残缺一簋的历史隐秘,而且解释了“曾”“随”两国关系的学术纷争,更重要的是揭橥了先秦时期政治文化崇正尚义的精髓。
长篇小说必须要有立得起来的典型人物形象,对于《蟠虺》和《听漏》这样的系列长篇小说而言更是如此。刘醒龙十分推崇的作家陈忠实说过:“读小说是为了寻求动人的故事,这是任何阅读者的最基本的阅读心理渴求。然而故事总是由人物演绎的,人物的情感世界和人物的追求以及命运的最终归宿,才是撑起故事框架的柱梁,才是决定故事的质量的主宰,也是决定读者阅读兴趣的最基本的因素。”k无论是考古知识性叙事也好,还是青铜文化性叙事也罢,再精彩的故事和讲故事的方式,也必须服务于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形象的艺术塑造。十年前的《蟠虺》,让读者深深地记住了一个叫作曾本之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形象。他身上的青铜人格堪称“贤良方正”l的典型,尤其是他以楚学泰斗身份敢于自我否定、自我纠错,把真理、把人格放在一切世俗利益之上,这种宝贵的文化人格为我们的时代树立了精神标杆。十年后的《听漏》,当年那个站在曾本之身边的配角马跃之的形象终于变得立体丰满起来。作为汉楚青铜重器考古学家,马跃之不仅以自己的专业能力赢得了国内同行的赞誉,因他在田野考古中修补各类器物速度之快无人能及而被誉为“江南第一捕(补)快”,而且他还凭借自己刚直耿介的学术人格力量征服了同行,成为了继曾本之之后的又一位当代楚学权威。无论是曾本之还是马跃之,他们都不愿成为那种“识时务”的“俊杰”,而选择做一个“不识时务”的“圣贤”。“自古圣贤皆寂寞”,哪怕是为此而失去了诸多世俗功名利禄,这两个心照不宣的当代楚学知识精英也无怨无悔。在《蟠虺》中,探求曾侯乙尊盘制造工艺的真相、为了找回国宝重器曾侯乙尊盘的真身,曾本之隐忍而刚毅,最终让真相大白、让真身归位,展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风骨。到了《听漏》中,马跃之接过了曾本之的青铜考古接力棒,也接过了曾本之的青铜人格接力棒。他多年来被丝绸漆器笼罩的柔性人格,也在青铜重器考古中变得刚毅起来。面对楚学院的实际权柄掌握者郑雄的各种阴谋诡计,马跃之始终镇定自如、不为所动,他在青铜考古事业上孜孜以求,将各种世俗名利视为浮云。他对郑雄的种种“僭越”行径洞若观火,但他明白“天子不灭天灭”的古道仁心,所谓“人在做,天在看”,“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郑雄这样的伪君子的必然命运。
刘醒龙曾说:“一个民族几千年来,连绵不绝,生生不息,一定有其优秀的品质。要警惕我们有可能出现身在此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错觉。”他又说:“对国民的劣根性批判太多,却对国民的优良品质忽略太久,才是莫大的失算。”所以他多次表明自己想“探究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本”。m在刘醒龙的“青铜重器三部曲”中,从目前的《蟠虺》和《听漏》来看,他确实在致力于挖掘我们民族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精神文化奥秘,所以他选择了聚焦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聚焦于上古汉楚青铜文化及其塑造的理想文化人格,探究其作为当代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本的精神文化资源的可能性。在《听漏》中,马跃之有一句名言:“一个人的全部质量加在一起就是灵魂。”他还说:“考古的事既不能靠天,也不能靠地,更不能靠人,唯一能依靠的是灵魂。”对灵魂的重视就是对精神底线的重视,就是对理想文化人格的重视。如果丧失了灵魂和精神的底线,丧失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理想文化人格,就是“头上戴着十顶资深专家的帽子又有什么用”,这是马跃之在被人恶意举报之后,他的夫人柳琴情不自禁地发出的一番感慨。有人说:“西方学人所刻划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竟和中国的‘士’极为相似。”“如果根据西方的标准,‘士’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n其实即使不借用西方的知识分子概念,我们民族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先秦青铜文化中就蕴含着十分丰饶的士人精神文化资源。比如在刘醒龙的“青铜重器三部曲”中所着力挖掘的上古汉楚青铜文化及其塑造的青铜文化人格,就是当代中国亟须的一种有待激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当然,刘醒龙所推许的古典青铜人格并非只重理性与礼制,而排斥感性与浪漫的僵化人格范型。正如他在《楚汉思想散》中反复强调的那样,“汉楚地域上多是性情中人”o,他们行事做人大多率性而为、不拘小节,性情所致,思虑难全。于是我们在《听漏》中看到了马跃之的一段被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浪漫而痛楚的情史。青年马跃之在秋家垄考古时与当地小学教师小玉坠入爱河,为此他伤害了小玉老师以及他的未婚夫秋风,同时也伤害了自己的一双儿女——梅玉帛和陆少林,他们在失踪三十多年后才与亲生父亲相认团聚。自从得知小玉和秋风的悲剧之后,马跃之多年来一直生活在痛苦与懊悔中。而知道真相的曾本之仁义为先、慈悲为怀,为了成人之美,他暗中导演了一出好戏,让马跃之与失散多年的子女相聚。在曾本之看来,“一个好男人能做到至情至性才是真好”。他还对着马跃之背诵了一段古文:“古来烈丈夫、奇男子,往往流连歌楼妓馆中,而矩步规行者,反以庸庸败检。其故何哉?盖有至情,而后有至性;情既不至,则其性已亡。”p马跃之是否是至情至性的好男人姑且不论,但曾本之所推崇的至情至性的“性情中人”必然是中华优秀古典人格中的极品。
推崇“性情中人”的刘醒龙在小说创作中也痴迷于抒情。这与中国文学伟大的抒情传统有关,更与刘醒龙血脉中流淌的汉楚浪漫文学精神有关。从《蟠虺》到《听漏》,虽然写的是楚国青铜重器,是历史、是考古,但这一切都经过了作家的主体情绪映射,在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中投下了精神潜影。关于《蟠虺》的创作,刘醒龙说他是“用写作来化解疼痛,再用那些尽是痛感的文字,表现最撼动我心的抒情”q。由此不难发现,相对于叙事而言,抒情也许才是刘醒龙创作“青铜重器三部曲”的精神旨趣。《蟠虺》如此,《听漏》也是这样。这并不奇怪,同为楚人后裔的沈从文早就在《抽象的抒情》中指出:“事实上如把知识分子见于文字、形于语言的一部分表现,当作一种‘抒情’看待,问题就简单多了。因为其实本质不过是一种抒情。”r不仅仅是诗歌用于抒情,其他各体文学创作都可用于抒情,甚至凡是诉诸于语言文字者都可以纳入抒情范畴,因为其中都投射了主体的情绪,不管是“抽象的抒情”还是具象的抒情。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曾戏称沈从文搞的文物研究是“抒情考古学”,甚至在沈从文八旬大寿的赠诗中有一联云:“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s我们完全可以借用汪曾祺的说法,把刘醒龙创作的“青铜重器三部曲”视为一种“抒情考古学”。事实上,如果脱离了“抒情考古学”,刘醒龙在《蟠虺》和《听漏》中所致力的“知识考古学”和“文化考古学”就失去了爱的附丽,失去了艺术的光晕和神韵。从《蟠虺》中的《春秋三百字》和《青铜三百字》到《听漏》中的《冰心三百字》,刘醒龙创造性地转化了中华古典辞赋文体资源,在文白夹杂、骈散兼行的新辞赋体文字中倾注了强烈的主体情绪,为整部作品营造了浓郁的诗性氛围。《听漏》中关于白露节气的多次描摹同样灌注了主人公马跃之的无限深情和无言隐痛。每年的白露节气,马跃之总是独自来到大楚青铜馆,暗中品尝痛苦的人生滋味。三十多年前的白露节气后,马跃之暗自作出了三分悲哀、七分悲痛的决定——从此远离青铜!小玉和秋风的悲剧让他从此对青铜悲而远之、痛而远之!想到小玉和秋风,念及失去的两个孩子,马跃之对青铜总是望而生畏,或者说是望而生痛!当年小玉老师自尽之前,用绣花针在一对双胞胎的手臂上分别刺下了繁体“马”字的各一半,这其实也是为了纪念她和青年马跃之的浪漫情缘,命运让他们在考古场地各自捡到了一个青铜残片,而残片上的文字居然凑起来刚好是一个繁体的“马”字!尽管这个“马”字长期以来被误认和误传成了“曾”字,但由此给马跃之带来的心灵压迫感和忏悔情结却是始终难以消除和化解的。这也成了推进《听漏》中核心故事情节的强大情感内驱力。
总之,《听漏》中的考古叙事既是抒情性的,也是文化性的,还是知识性的,只有“抒情考古学”“文化考古学”“知识考古学”三位一体,才能共同筑就《听漏》的青铜重器考古叙事新形态。《听漏》中有许多金句,如“文物文物,考古的意义在文,盗墓的目的在物”,又比如“考古考的不是古,是在考验人心”,无不指向了专业知识背后的文化与人心。对于刘醒龙来说,无论是“小说考古”还是“考古小说”,最终的目的都是要用考古所发现的东西完善当代人的精神生活,这才是一个具有人文精神的作家不同于一般的职业考古学家的地方。行文至此,我们还得仿照《听漏》的叙事策略解答读者心中埋藏已久的一个疑问,那就是《听漏》为什么要以“听漏”二字命名的问题。作者借楚学院万乙博士之口说了这样一句话:“考古这行也就是历史的听漏工。”t这就道出了“考古”与“听漏”这两种职业的关联性与隐喻性,可谓意味深长。听漏工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稀见的社会职业,他们主要在暗夜中倾听城市地下管道漏水的声音,为城建部门和老百姓提供难得的技术服务。小说中的“曾听长”就是这样的一位“听漏工”,正是他听出了武汉地铁站工地下的漏水声而避免了一场灾难,也是他听见了楚学界权势者郑雄在深夜里的种种密谋、看到了其种种可疑行踪,暗中保护了马跃之。而由于他是一个和梅玉帛、陆少林一样正在寻父的私生子,所以他借“听漏”的名义对楚学界权威曾本之和马跃之,以及湫坝镇秋老太太、“六大人”、秋风、小玉、“秋大队”等人展开了一系列私下追踪,这就使得他实际上成为了串联起整部作品叙事进程的牵线人。倘若失去了这位“听漏工”,《听漏》构筑的全部青铜考古故事大厦将轰然坍塌。有意思的是,小说中对“听漏”这个特殊的技术工种做了十分专业的知识性描写,这与小说中的各种“考古”知识性叙事相映成趣。所以,“听漏”就是“考古”的别名,“考古”就是“听漏”的书面表达。二者的共通之处在于,它们都致力于倾听来自历史或现实以及文化和人性深处的声音,可谓殊途同归、异曲同工。
【注释】
afmq刘醒龙:《刘醒龙文学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76页、303页、175-176页、304页。
b参见刘醒龙:《楚汉思想散》,《寂寞如重金属》,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77-86页。
c李学勤:《盘龙城和武汉市的历史》,《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90页。
d参见李学勤:《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的两个高峰》,《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6页。
e茅盾:《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从〈卧薪尝胆〉的许多不同剧本谈起》,《茅盾评论文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90页。
ghijpt刘醒龙:《听漏》,长江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第25页、46页、130页、503页、53页、161页。
k陈忠实:《人物才是撑起故事框架的柱梁》,《陈忠实文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年版,第326页。
l刘醒龙:《后记 为故乡立风范 为岁月留品格》,《黄冈秘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477-478页。
n余英时:《自序》,《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o刘醒龙:《楚汉思想散》,《寂寞如重金属》,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82页。
r沈从文:《抽象的抒情》,《沈从文别集·抽象的抒情》,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12-13页。
s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全集》(第3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8页。
作者简介※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