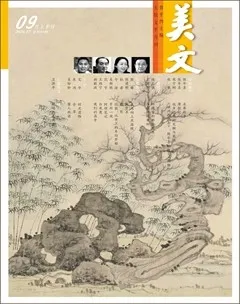《峡河西流去》:陈年喜的散文“韵脚”
我国地势,西高东低,大江大河往往向东流,峡河却偏偏向西流去。只此流向,这条河流就有其不可言说的魅力。
《峡河西流去》的名字是陈年喜起的,峡河是他的家乡名,也是他家乡的河名。他打字告知我的那一刻,我眼前一亮,并对这条河流起了好奇心:倘若说百川东到海意味着融合与生,踽踽向西流则意味着什么?
2021年8月,我与陈年喜相识,经我另一位作者“为你读诗”引荐。那时,他的首部散文集《活着就是冲天一喊》刚刚发行一个月,大众读者反馈迅速且热烈。
读他的文字,仿佛在听一首首每分五十节拍的广板乐曲,这个速率比我们常人的心跳还慢。我以一目十行的阅稿习惯去读,尝试多次,难以行就,因为他的文字密度是惊人的。没有故意煽情却深情,没有刻意抛撒哲思却寓意深远,真情实感和精深思虑都缱绻于他朴实平缓的叙事中。若把叙事进程比作一座山,他笔下的人、事、物,则都在以看似不急不躁的步调爬着坡,爬着爬着戛然停步,驻足在一句甚至半句话就把高潮、意外、终曲合而为一的一刻。这一叙事手法仿佛他诗歌中一个不起眼的韵脚,于他散文中却爆发震颤人心的力量。
我恍然意识到,孕育这一叙事的母体是他背负的矿山。然而,矿山绝非我们常人可轻易认知的世界,那里没有“悲欢离合”,只有“悲悲离离”。听到矿难事故导致矿工伤亡的新闻时,我们会难过,陈年喜则会悲痛。他曾眼睁睁地看着身边一个个鲜活的肉体粉身碎骨,化作冰冷的死亡数字。
生与死极限拉锯的场域,有文学家诞生。陈年喜是体验者,又是记录者。他看惯生死,所以可冷静地对待生死,书写生死。这也是广板乐曲适合给他的文字作背景音乐的原因,这一速率的乐曲所传达的情绪正是悲怆和炽烈。乐曲一响,一颗陨落的小星于他的笔端复活,继而再次赴死。
我爱陈年喜别具一格的文字,无论他写什么,我都愿意为他付梓出版。我们起初讨论的创作主题是“人间旅馆”,依然着眼于务工漂泊中有过交集的故事,但主题归主题,书名不可能是“人间旅馆”,因为人间太挤,市面上已有《人间词话》《人间失格》《人间告白》《人间草木》《人间食粮》《人间值得》等。
做好选题论证后,我申报上会的选题名称是“比天边还远的梦想”,这个标题出自陈年喜的诗歌《在南长河公园》,只因它给了我若隐若现的希望。选题会上,这位文学界的新星引发激烈讨论,即使推崇的人,也担忧他还有多个出版计划在排队,留给我们的是不可预知的盲目期待。
2021年9月,出版合同双签。说服大家的不是我,而是那时就已初露端倪的共识:当代散文,男看陈年喜,女看李娟。
翻看他们二人的人生经历,不难发现,他们都是深度生活体验者,都是以痛感书写自身与周遭的笔者,读一读就知道他们深入浅出、点到为止、巨量留白的文字张力。
约定交稿的时间是2022年3月,与其说那是一纸契约精神,不如说是一串做作的字符。我清楚,这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等待,等待他新建一个空白文档,将至少十万个字符断断续续地敲打进去,因为他的创作环境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漂泊二十余载的陈年喜,回到自己的故乡峡河,这与传统意义上的“荣归故里”不相关,哪怕他顶着“矿工诗人”的头衔,并已在传媒界和出版界小有名气。原因在于,故里死气沉沉,没有欢迎他的力气。
可是峡河,它细嗅到出走时健健康康的陈年喜此遭裹挟而归的满身伤痕:单耳失聪,颈椎错位,尘肺,身上各式各样的创口。它以沉默的方式重新接纳了这个游子,并以他不知情的方式慢慢为他疗伤。
平日里,陈年喜生活在离峡河不远的县城丹凤,说到不远,皆为摩托车成全。他也特意为曾经拥有过的摩托们创作了《摩托记》。对于创作,他眼前最大的变化在于:他要做个“书斋先生”,专职写作。
若说此前的诗歌和散文是他漂泊罅隙中为记录而凝结的产物,此后的文字则多出不少动机:为了生存,为了生活,甚至为了讨好。
陈年喜愿意与我探讨摸索其中的写法。求新求变未尝不是好事,说明他在学习,在思考,在进行以自我为中心的革命。不过,他的发问是露怯的,关心新写法是好还是坏。他陷入茫然,许是怕读者审美疲劳,许是受了职业书评人即使无比青睐也要有褒有贬的套路的影响。
重塑陈年喜对写作的自信心,是对这颗文学新星的一场拯救式行动。我鼓励他听从内心、无问西东,他不着痕迹的最原始的表达欲望才是他与众不同的个人识别码。
陈年喜重拾了他自己,说服他的不是我,而是他的故乡峡河。他在向故乡的这场奔赴中,找到了一种莫名其状的频率,仿佛双方在试探性地重新建立互信。调转主题方向,可能是一念之间达成的。他与故乡天天对视,起了探寻之心,也渴望揭示1998年他内心深处所荡起的那一圈涟漪的奥秘。
那年,陈年喜的家乡撤乡并镇,“峡河乡”在行政版图上消失。对于他的父老乡亲而言,那不过是一条普通的政令,什么都没变,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人还是那人,可在二九未立的陈年喜心中起了微澜。那时,他还无法以文学语言描述那一抹荡漾。待到2021年,他已大不同,无论是反观还是回望,他对个体和故乡的关系都有了深邃的洞察。
读过《1998年的乡村逸事》后,我颠覆了自己的认知:陈年喜的叙事母体不该是矿山,而是他的故乡。他关注一个个渺小个体的命运,实则是他内心羁绊于家乡命运的相似性。
情感上,他的家乡“死”于1998年,树倒猢狲散,务工潮将年轻人和年轻人的孩子带走,岁月将银发一族带走,意外又将剩下的人带走。已故的家乡,就成了故乡。
这就是《峡河西流去》,人、事、物在以不同的形式滑进同一个“韵部”:关于死的一切。
所以说,死,是陈年喜散文的“韵脚”。那么峡河向西流去,是否就意味着归西?
我收稿,对应着陈年喜写稿,他在上游,我在下游。我怀念他每次以一份文档作为我们聊天框开场白的时光。2022年3月10日,这一幕第一次发生。
《磨面记》《土芹》《1998年的乡村逸事》以集合的形式出现,文档名称“峡河西流去”。乍一看,还以为是全稿。不过,收到这三篇稿子使我满足,它们的到来正式宣告漫长等待的长夜结束。
《土芹》中就出现了“韵脚”,初稿的结尾这样写道:“那个晚上,负责点燃十公斤炸药的队长变成了一股血雾。队长姓奔,叫奔有才。此后到今天,我再没见过这个姓。”如此富有诗意的骤然收束是陈年喜的拿手绝活。死,原本也不是拖泥带水的,不过一片花瓣凋落的时间。
我们最后一次交流《土芹》,是在2022年9月22日。那天,陈年喜说给我改好后的稿子,他忘了给,我也忘了要,直到图书出版也没意识到弄丢了它。它成了遗珠,这件事本身就像一个“韵脚”。
《峡河七十里》中的“韵脚”落在陈年喜亲妹妹的身上。那年,他十五岁,妹妹十岁。她的病原本不是要命的病,只是1985年的那场大水断了她就医的路。物理阻隔酿成他全家的这场悲剧,更悲伤的是,“十岁的孩子不配有一副棺材”。
《表弟故事》曾七次易稿,2023年4月18日定稿。临近尾声时,叙述对象从表弟过渡到病友刘大发。刘大发“白肺”,陈年喜“尘肺”,两人聊各自的人生片段聊到很晚,“天亮时,刘大发走了”。这一过渡,是一处从生到死的转场。
《月潭》中炸岩点炮的中年人跌入月潭消失,月潭被填埋消失;《蘑菇故事》也是瓦匠的故事,他是全村人住上瓦房的希望,却被五彩缤纷的蘑菇扼杀;陈年喜栽的李子枝杈死了,亮子栽的活了,陈年喜做爆破工九死一生,亮子做爆破工九生一死,这就是《李子熟了》;《桐子故事》与桐油有关,与异乡人林师傅有关,他以精湛的刷漆手艺征服峡河,却在自己的桐油棺材上留下遗憾;《商州记》依然“押韵”,到商洛看病的新疆男子终于吃到一口家乡风味的拌面,安然睡去;《地板记》原本是陈年喜送给爱人的惊喜,却穿插了一个重庆工友的命运,他去了印尼,“葬身于异国的碧水波涛”;矿口多年无人认领的摩托车,诉说着它们被丢弃的故事。
2023年12月21日,最后一篇《烟尘》到稿,烟尘虽说细小,但有力量将刘师东埋入绝境,也有力量将陈年喜带入当下的处境。其实过去三年,我曾多次闪过同一个可怕的念头,万一,我说的是万一,更为细小的病毒侵害他本就脆弱的肺部该怎么办。
“万一”发生,实则,那时每个人都很有可能患上新冠肺炎。当病毒与微尘在陈年喜的肺部相遇时,陈年喜大病一场,前所未有的疼痛遭遇。因而,我也在良心上留下了可耻的记忆。
2022年12月,我三次例行催稿,都杳无音信。月底,陈年喜回复说,阳过了。我的心紧缩成麻团那么大,揪心,担心,继而是可耻心。我自责,那一次次催稿,吃相过于难看,明明身边同事陆续高烧躺下,我对作者连最基本的关心问候都没有,眼里只有稿子,简直活成自己最厌恶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样子。后来方知,《月潭》《老花》《清明》都是他“阳了”的那段时间运思的结晶。愧疚,如瀑坠渊。
这件事迫使我反思,认知上也有了颠覆的变化:一是我重新定义了自己与作者之间的关系,以文会友,私下也将称呼从“老师”改成“哥”;二是病毒与微尘没能得逞,峡河留住了陈年喜,也让我在重温他的作品时,特别是读到那些“韵脚”时,读到了些许微光。
刘师东以蒙太奇的方式从维吾尔族小镇回到峡河水滋润的故土里;陈年喜为重庆工友铺就的地板还在,他给爱人迟到的礼物也铺就了;到商洛看病的新疆男子,告诉儿子不必把他的尸骨折腾回家,“有拌面的地方就算家”;一封书信让异乡人林师傅的身世真相大白,他,选择了峡河;亮子的尸骨不见,峡河为他建了一座衣冠冢,他的李子树硕果累累;消失的人和消失的月潭,成为路基永远的一部分,成了路;陈年喜的妹妹,在她十岁那年去南阳吃麦了。
“去南阳吃麦”是峡河人对人死的独特表达,也是对逝者的寄语。他们的祖辈从河南逃荒而来,可在他们近三代人的集体记忆中,河南尤其南阳是越发富庶的粮仓。丰收和吃饱是亿万农民最朴素的诉求,峡河人亦然,因而“去南阳吃麦”比“去西方极乐世界”要具象得多,也实在得多。
这么一看,陈年喜散文中的“韵脚”有两层含义:愿逝者安息,也愿生者坚强。他以文笔为峡河人描像,我们所看到的并非清晰的眉眼,而是深藏在文字中的一种情愫:叶对根的思念。
一个个体,无论出不出走或出走多远,他的根源都在故土。
这正是陈年喜两年多时间与峡河对视所思考到的精髓,人的乡愁、故乡情怀、人文艺术根脉,等等,都生发于它。再品《峡河西流去》,他克制的笔触背面有洪流汹涌。
峡河看似人口稀少、屋舍凋敝,但它的四季依然繁荣。春风吹开枝头的杜鹃花,漫山遍野都是,美不胜收。上天不会如此眷顾一块死地,所以,峡河依然活着。只是可惜,美景无人看、无人欣赏。
陈年喜希望在家乡举办“杜鹃诗会”,邀请四海的诗友到峡河赏花吟诗。他也不会如此眷顾一块死地,所以,他为峡河人立传,也为峡河张榜。
2024年3月23日,陈年喜根源散文集《峡河西流去》在西安首发曝光。从完稿到成书,仅仅3个月,中间还跨了春节长假,整个制作流程如流水般顺畅。读者翘首以待多时,我不敢怠慢,也急于见证一座新里程碑的诞生:峡河,注定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另一个地标。
每个读者都会读到《峡河七十里》,这是全书的第一篇作品,文中有这段叙述:“峡河到了武关就归了丹江,再往下就归了长江,水还是峡河的水,但与峡河就没什么关系了。”
一切真相大白,峡河向西流,遇见丹江后便随其向东南流去,终而汇入滚滚向东流的长江。
峡河,无时无刻不在死去,又无时无刻不在重生。
(责任编辑:孙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