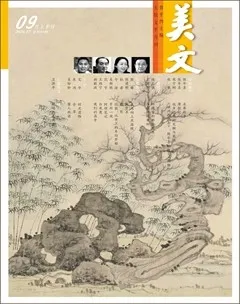故乡之书的笔触与笔法
一、故乡之书
峡河,是陕西70后诗人、作家陈年喜丹凤老家的一条河。“峡河西流去”,是陈年喜在《南方周末》所开的散文专栏的名字,也是他最新散文集的书名(陈年喜:《峡河西流去》,湖南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中国的河流,绝大多数都是向东流,峡河也不例外,只是由于在陈年喜的老家,峡河经历七十里的西流之途,才折向东与丹江汇合,所以,“峡河西流去”并非虚言。
《峡河西流去》是陈年喜的第四部散文集,也是他以故乡峡河作为书名的第一本书。书名中有故乡,也有作者对逝者如斯的感叹,其中含藏着些许无可奈何,却也不乏事后的豁达——毕竟,作者是历经生死病苦,并因此而炼就了心胸的。
一如书名所示,《峡河西流去》是部故乡之书。虽然在此前出版的《活着就是冲天一喊》《微尘》《一地霜白》等几部散文集中,陈年喜或在零星文字中,或在个别篇章中,也曾多次写到故乡,但在《峡河西流去》中,他才以更为细密的笔触,集中书写了故乡。
在该书“自序”中,作者回顾自己的经历,说“我这半生,和两个场域扯不断理还乱,一个是关山万里的矿山,一个是至今无力抽身的老家峡河”。他的诗歌和散文写作,也大致从这两个方面展开。其中,有些文字主要写矿山生活,有些文字主要写家乡山村的生活,许多文字则两者兼有,只是篇幅多少而已,如作者所说,两个场域“扯不断理还乱”。而其所写,有自己,更多的则是他人。因此才称得上是一部故乡之书,而不只是自我之书。
陈年喜从小到大生活在峡河边的山村,那里有他的父母、他的妻子、他的家、他的根。待他长大成人,需要担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而在贫瘠闭塞的农村又找不到生活的出路,实在没办法,才外出打工——尤其是去离家不远的矿上干活。做工的地点,从离家不远的伏牛山、灵宝,到愈来愈远的长白山、鄂尔多斯、山东玲珑、新疆喀什地区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接近边境的地方。可谓天南海北,备尝苦辛。如此经历,也并非他独有,而是与他一样的一代乃至几代山村青壮劳力所共有的。仿佛共同的脚本,不同的只是细节。陈年喜的经历固然丰富、传奇,甚至不乏悲苦,与他一样外出打工的乡邻们,进而在中国大地上上亿的外出务工者们所经历的,又何尝不是如此?甚至有人为此搭上了生命,或者牺牲了身体的一部分,导致不同程度的工伤或残疾,鲜有人能全身而退——陈年喜牺牲的则是颈椎和肺。
天南地北的打工生涯并非单纯的离家、离乡,在另一个空间场域中展开生活。毋宁说,那里没有生活,只有工作和休息间隙。对于千千万万的打工者来说,打工生活算不得真正的生活,真正的生活在另一头的家乡,在一家人的团聚,在日复一日的家长里短和烟火中,虽然外出打工的生活,从时间上来说远远多于在家。
也因此,他们走得再远,也不可能不回头反顾。陈年喜也一样,他心系着家,家里大大小小的事一次次拉扯他回到家乡:孩子出生、父母生病、乡邻去世……更不用说逢年过节,能回家的时候总是要回家。即使平时回不了家,也要通过书信、电话与家中联系。于是,在家乡与打工地之间,就拉扯起更为繁复的情感牵系。
不过,虽然打工的时候常年离乡,切肤的生活经历,却并没有让作者对家乡产生牧歌或乡愿式的美好想象与回忆——这是很多早年生活在农村,后来通过读书而在城市中落脚的人们常会在文字中展露的倾向,实际上也是虚假的倾向,并因其虚假而使得他们地写作变得无效。
身为农民而又不得不成为“(农)民工”的陈年喜,没有奢侈和浪漫的机会,没有对家乡产生那种乡愿式的顾念。他清楚地记得小时候的事,记得在农村时做义工、“大会战”,记得乡村生活中的质朴与狡黠、互助与计较、温情与紧张……记得几代人为什么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但他宽容、豁达,并不苛责个体,而是对过往的人与事,都抱以回望和理解的释然。(《1998年的乡村逸事》)
当然,在这释然里,也有无奈、叹息和徒然的观望。尤其是随着人口的流失,乡村无可挽回地衰败。一如农村里曾经热闹的年戏,已多年不再上演(《年戏》)。就此来说,陈年喜的散文和诗歌写作,其中相当分量,是他生于斯长于斯、他的父辈们生于斯葬于斯的乡村几十年的发展与衰落史。包括作者写到的从乡居到城镇的过渡(《村居现状忧思录》),它的复杂,以及作者对它难以割舍的眷恋:“打工生涯里,我见过数不清的野棉花,在北疆,在青海,在风沙漫天的毛乌素边缘,夏天它们是花,秋天它们是棉,但西沟岭上的野棉花,是最壮观的、最温暖的。”(《摩托记》)这些文字,可说是“月是故乡明”的当代版注释。
不过,陈年喜并没有因此而美化乡村,同样重要的是,他没有在文字中“卖惨”,而是通过清简疏朗的文字,写下略带伤感的真实记录。就此来说,陈年喜的乡村书写与此前梁鸿、黄灯等人的乡村书写一起,构成了新世纪以来,尤其最近十余年以来关于乡村的新图貌,也为我们理解当下的中国农村,提供了真实可信、切实可依、清朗可读的非虚构文学文本。
二、人事风物
书写乡村,必然会写到乡村中生活的人。这些人在乡村中生,于乡村中死,乡村养活他们,也在贫瘠无告中将他们推向外面的世界。
的确,陈年喜在散文中写了很多人,他所认识、接触抑或听说的人与事,从亲人、乡邻,到工友、老板,不仅写他们生命历程中的一瞬,更写他们长达几十年的生活经历,乃至命运,哪怕只是寥寥数笔。
包括他的父亲、叔伯在内的上一辈,由于社会环境的限制,他们大都在山村中度过贫苦、不起眼的一生,至多出过几趟远门,一辈子都在家门口周围方圆几十里地中打转;他的同辈人,则由于时过境转,社会环境的宽松,多外出打工,如他所写:“这些年,村里一半的年轻人都上了矿山,他们星星一样撒落在秦岭、长白山、祁连山、贺兰山脉,或者大河之侧。”(《峡河七十里》)除了打工、下矿井,山村里的年轻人实在没有多少别的出路。如此选择,其实也是生活所迫,陈年喜自己也是其中之一,走过很多地方,经历不少人事。其中,最令人触目、想起来叫人发怵的,就是矿工生涯的艰辛与凶险,以及看似平常的生活中的无常。
某种程度上说,在矿上讨生活,就是与死神对弈。对于在矿上干活的普通民工,命运的残酷与叵测,时时萦绕左右。有的因为意外当时就命丧矿井,有的则在多年超负荷、无保护的条件下劳动之后患病(尤其尘肺病),长期与病痛相伴,并最终因病而逝。如此情形,不仅对于在井下工作的人,即便对那些从事井上工作的人来说,也极为常见,正如他在散文中所写的机师傅(《人们叫我机师傅》)和刘师傅(《烟尘》)们;哪怕从事矿石粗加工并大赚了一笔的小老板们,往往也难以幸免,即使曾经日进斗金一时暴富,到头来也难逃病苦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之艰难(《我的朋友周大明》)。
就此来说,陈年喜所写的无论关于矿井还是关于故乡的文字,都是在写底层百姓的艰辛与小庆幸,悲苦与小确幸。散布于这些人事命运中的,更多是流离与漂泊。正如他在第一部诗集《炸裂志》的“后记”中所写,“这是一部漂泊的诗(集)”。他通过诗文所记录的,既是一个人的漂泊,也是一群人、一代人乃至几代人流离、漂泊讨生活的经历。
陈年喜的笔触并不全是写人事,他也写家乡独具特色的风物,如芦花、桐子、蘑菇、葫芦、漆树、苕(山药)、疙瘩叶儿……只是,这些对山乡土特品物的书写,要么也伴随着对人事或多或少的书写(如《苕》《年戏》等),要么就是以写这些品物为引子,引出与之相关的人事(如《葫芦记》《割漆的人》等)。
如《年戏》,由写山村里春节前后唱年戏而写到参与年戏顺利演出的若干人,以及他们在时光中的老去,同时,也写到故乡河边常见的芦花——“峡河边上,两岸无边的芦花,熬过了冬天,正往春天里白”。文章结尾,作者再次提到芦花,并将芦花比作另一场年戏:
我已经三个月没有回过老家了。
车进峡河,天已黑透了。车灯打起来,明亮的光柱在山边、河边划动。枯水季节,河里几乎没有什么水,只有在有落差的地方还能听到水声。河床宽宽窄窄,九曲十弯,白茫茫的东西充满其间,因势就形,它们丰盈浩荡,摇旗呐喊,前不见所始,后不见所终,那是芦花。
只有芦花还在。它无意见证什么,却见证了所有,它无意说出什么,却说出了一切。它见证了一位少年到中年的历程,见证了年戏从兴到衰的光影。
芦花年年到天涯,那是另一场乡戏和年戏,它高歌苍壮,细柔温婉,沿长江一直唱到大海,唱给风听,唱给水听,唱给天地听。
这里,白茫茫的芦花既是无尽的见证与诉说,又仿佛是离乡之人的化身,替他们守着乡村,此外也更像是对人们离乡之后日益衰败的乡村的祭挽。在《割漆的人》等篇中,作者在书写风物的同时,用不多的文字将笔触延伸到人事,甚至达到令人揪心的程度。
读陈年喜所写的这些有关人事及其命运的非虚构散文,不免会感到沉重。然而,陈年喜并非要刻意这样写、刻意追求这样效果的。正如他所言:“不是我要写得沉重,是我经历的生活、经见的人生本来如此。”(《表弟故事》)对于一个身处社会底层、年过半百的农民作者来说,这就是他——以及他们——在几十年的生活中所经历的,只是由于真实,而令缺少这些经历的人们读来感到唏嘘,甚至不可思议。
三、春秋笔法
陈年喜的散文,在写法上也很有特点。他的文字清明流畅,在写法上,常大开大合,有限的文字里,蕴含着巨大的信息量,比如写离家出门干活,一路上“车过石门、吊蓬、灵口、犁泥河、小河,最后到达杨寨峪金矿坑口”(《摩托记》),仅用十几个字,就勾勒出所走过的路线,既为文章打开辽阔的空间,也为读者撑起广阔的想象空间。比如写时间,“霜露荏苒,日月如捐,一晃二十一年过去了”(《1998年的乡村逸事》),也是在短短一句话里,打开二十一年的时间跨度,打开从现在通往过去的通道,展开关于过去的叙事。不仅如此,作者有意识地避开“光阴荏苒”“岁月如捐”这样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熟语,对其加以精心改造,使文字显出陌生化、个性化的效果。
陈年喜的文字也常含幽默。《表弟故事》写自己年轻时与表弟一起玩猎枪,“那时候,我们都还没有讨到老婆,不过,也并不为讨不到老婆发愁,一则是村里遍地都是大姑娘,那会儿还没有打工潮和大学潮,人生都没有选择余地,像野桃花儿一样,再好的颜色都开在山上,凋在山上;二则是我们有猎枪,对于我们两个光棍,那是比爱情更美好的快乐。我们俩常常背着枪游荡在山林间,如两个响马”。这段文字既是很好的历史叙事,真实过往与现实的写照,又充满幽默与戏谑,使原本有些严肃和沉重的叙事,表现出活泼与弹性。这种叙事方式是汉语叙事中非常稀缺的质素。
陈年喜的文字注重叙事,很少抒情,更不煽情,很懂得以少为多、点到为止的艺术。有论者指出陈年喜的散文“动用了小说写作手法”,有“小说体散文”的特征(武歆:《微尘·序》)。的确,陈年喜散文中的好些篇章,读来都有悬念,个别篇目,如《葫芦记》《割漆的人》等,不仅可以当小说看,更可以看作是他无意中延伸、拓展了散文和小说写作边界。
在一些小说性不那么强的篇目中,他也借用小说的写法,比如《年戏》中,由写汽灯而写到点灯的老李:
点汽灯也是个技术活,不是人人会点,一晚上,两只汽灯,要烧不少煤油,点得好,省油又明亮,点不好,费油又昏沉。村里,只有老李点得好,所以汽灯用的时候,由老李来点灯,不用的时候,就由老李来保管。老李个子矮,平时人们喊他老李,也有人喊他矮子的,只有到了用汽灯时,人们才喊他灯师傅。老李一年的高光时刻不多,有些年景三四回,有些年景一两回,老李每年定数的一回,就是唱年戏时。老李平时难得被人当人,只有点汽灯时,才被人当人,老李这时也把自己当人一回,必须和演员们吃住在一起,戏开演,他也不坐台下,一定得坐两边厢台上,不知道的,以为这人是剧务,或者导演。
这段关于老李的文字,就很有小说的特点,或说小说的笔致。
仅看题目《苕》,以为是写故乡植物的散文,也由苕而写到挖苕,写到挖苕的人——“我”和兔:
那时候,经常和我结伴上山挖苕的,有一个叫兔的女孩。兔娇小,两只眼睛圆、怯,见人躲闪。兔没有哥哥,有一个弟弟,弟弟小、弱,三岁了还不会走路。兔除了上学、做家务,就是带弟弟。我手脚并用地攀到崖顶上,裤带上别一杆小锄,她在下面浑身颤抖,捧个篓,一会儿喊,哥,小心点;一会儿又喊,哥,慢点。声音细细的,茸茸的,像兔毛,白而柔,往人心上蹭。如果岩坎光滑,锄就失去了用场,两手抓住草窠用力一揭,黑乎乎的土层下,苕一下就亮了出来,根根盘绕,竟有胳膊粗壮的。抖净了土,苕毫发无伤,收获了。并不是每次攀上崖都能见到苕,也并非每次都那么幸运,挖到完好的苕。下山,多是在夕阳压巅时,我荷锄,兔背篓,欢天喜地。见人,兔子都会送上一根,好像我们是天下最富有的人。
这里关于名叫兔的女孩的书写,同样以小说的笔调,写出她女孩儿的心性、令人生怜的个性,以及她内在的良善,读来令人动容。
此外,陈年喜还在其散文中写了不少堪称传奇的事。《绝活》中写父亲有一手绝活:看棺断生死。所谓看棺断生死,“是根据打棺工作第一斧头下去木屑废除的方向和远近”来判断受用者的寿数。比如在给一个生病的人做棺材时,第一斧下去,“一片木屑子弹一样呜一声飞起来,它飞向墙壁,在墙壁上撞击了一下折返到另一个方向,它飞过众人头顶,气势凶猛,最后轻轻落在地上”。父亲由此判断,这个生病的人没有福分用这个棺材。果不其然,后来这个棺材被这个人最小的女儿给用了。再比如,有一年村里有人在山西矿上干活,据说出了事,作者被安排和村里几个人一起“过黄河领取尸骨和谈判”,负责在家里打棺材的父亲则说,“人回不回得来还不一定”。最后,果然死不见尸。这些故事读来,都令人咋舌,感叹其传奇色彩。而传奇,既是小说的前身,也至今还是小说的基本方式之一。
《摩托记》中写作者在藏区矿上工作,晾着的裤子被牦牛吃了。“我一怒之下,拿起一根钎杆,冲向它们,它们不敢对抗我手里的铁棍,四散而逃。……这时候,一辆摩托车风一样停在我面前,一个彪悍的人,骑一辆彪悍的摩托车。……事情的结果是他答应赔我一条裤子,并请我到镇上喝酒。……他说我是一条汉子……”这样不打不相识、继而成为朋友的经历,同样带有小说式的传奇色彩。后来,在这位名叫玛旺的藏族青年决定离开家去外面的世界闯荡时,将这辆黑色雅马哈劲虎150摩托车送给了“我”。其豪迈与义气,也一样具有小说式的传奇色彩。
更不用说像《表弟故事》中那样草蛇灰线,布满谜网的叙事——刘大发给表弟看的有关金矿石的化验单是否为真?如果不是,他为什么要那么做?表弟后来怎样了?刘大发在病床上说,这件事他“到死也不会说”,结果第二天天亮时,他就病逝了……读来不仅悬疑,甚至有点幽森诡异之感。
这些写法,都大大增加了陈年喜散文的可读性,也极大地吸引了读者。
四、结语
关于故乡的风物人事,陈年喜怀着克制的情感写了很多。他说:“写作,也是思乡者与故乡彼此走近相看的过程。”(《峡河西流去·自序》)在这“相看的过程”中,有些事物看得更清楚,有些则由于久视而更加含混不定。即便如此也是值得的,甚或说更值得,因为世上的很多事都难以简单地分作黑白,在模糊中看到更多的灰色与难解,何尝不是一种认识的深入、认知的提升,甚至更大的收获?
陈年喜还说,自己“不过是个写信的人,我以文字歌哭、悲喜,以晨起暮歇的有用无用功为世界、为人们、为看见和看不见的事物写信,又以同样或不同的方式接收来信”(《峡河西流去·自序》)。其实,作为读者,我们同样也是收信人,所收到的不仅是来自包括陈年喜在内的作家们的“来信”,更是他们的文字从我们心底唤起的种种情感、记忆与想象。换言之,我们通过作家们的文字最终收到的,是我们的感受、理解与思想,是我们内心的激荡、回应与呼声。而这,也是文学阅读最重要的意义之所在。
(责任编辑:孙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