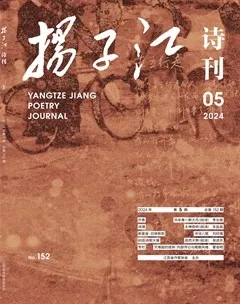今人诗词意象的现代意味
今人在诗歌创作时面对古诗词这一宏大传统势必感到焦虑——古汉语是最适合诗歌的语言之一,其诗词艺术达到的巅峰让后世叹为观止。如何将当代日常语言和生命主题融入诗词形式,这是传统文学留给我们的巨大命题。“20世纪诗坛的真实状况是格律诗、自由诗齐头并进,各有斩获,这在中华古老诗国还是空前未有的格局。”①诗词创作步入21世纪后,文学形式的古雅与生活的现代化势必爆发更激烈的冲突,冲突的火花已点燃周遭的枯草。一些描写当代生活的诗词作品善于推陈出新,而另一部分则极具争议,被指具有显著的“非现代性”。这是我们普遍具有的奇异特质与人性悖论——人既寻求新鲜的形式,又有极为守旧的倾向。一方面,“现代人的旧体诗词中,使用的和古典诗歌相同的词语仍然占有非常高的比例”②。另一方面,不仅现代人患有“现代病”,现代文学与现代艺术均患有“现代病”。繁复、晦涩的意象呈现与对抽象表述的过度迷恋正侵扰人们的诗歌观念。我们是否正像丢弃中国绘画传统那样遗失我们的诗歌传统?古有的光辉正在消逝,有人抬眼一望吗?“确切地说,构成诗意的内部机制,与构成自我的内部机制,不过是人性的一体两面。诗、文明的悖论、野心等,都来自悖论人性的挑动。”③在摇摆与探索之中,仍有一批充满勇气与耐心的文字艺术家,在现代性创作中传承着我们文化血脉中的这一经典体裁。
李攀龙言:“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不少人也直言,当代诗词或新诗,永远无法超越唐诗宋词。每一个独断的观点,都有其生发的具体情境,也有其值得原谅的地方。如果此言为真,创作的历史将走向虚无。创新本身就是冒犯,冒犯固有的习惯和法则,冒犯受众预设好的审美区间和期待视野。而从意象的角度切入当代诗词则是最具传统诗歌批评风格的方法之一。这些当代诗词作者的意象准确、凝练,时而出奇,是诗歌创作中快要失传的品格。更何况在集体无意识中,正是一个个意象、符号、原型编织出了我们的语言,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我们文明的根基。当代诗词不必有所谓“入史焦虑”,“文学史即效果史”,在探索之中,好的作品必然会经过受众不断检验得以不朽。笔者在有限的视野里,摘选数位代表性诗人的作品加以点评,因篇幅有限,时而略去原作者的题注。
独孤食肉兽无疑是创新的先行者,他于2001年出版的个人诗词集《格律摇滚Y2K》,书名就颇具现代意味。在此选取他创作生涯中现代意象突出的作品:
火柴盒里,看对面B座,玻璃深窈。冬雨江城流水粉,树色人形颠倒。达利、庄周,恍然皆我,午梦三微秒。石榴血溅,花间蝴蝶尖叫。 频赴屏后良缘,移形换镜,像素知多少。林表片云凝酽酪,月戴面模微笑。空巷笼音,古垣泌影,仿佛前生到。邮筒静谧,冬眠谁遣青鸟。
——《念奴娇·千禧前最后的意象》
作者在注中提及此处意象借用了卫慧城市欲望小说《蝴蝶的尖叫》,此意象也有策兰的风格。使客观物象人格化,继而发出压抑、刺耳的叫声,让人联想到爱德华·蒙克于1893年创作的画作《尖叫》,是现代人苦闷与焦躁的缩影。现代人在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中扮演众多角色,经历诸多欲望与焦虑的折磨,势必在某一时刻分裂而崩溃。“移形换镜”“石榴血溅”也有些科幻电影《银翼杀手》《攻壳机动队》中“赛博朋克”的意味:人们对现代生活的过度依赖和对科技未来的恐惧相纠缠。在赛博朋克的科幻作品中常出现类似“高科技,低生存”的设定,即都市与科技的现代化程度与人类生存的真实舒适度并不匹配。“月戴面模微笑”好似“达利”“庄周”一同作画,凸显现代梦幻。在《念奴娇·二进制的你我——立冬夜自汉口归江南有作》中,“二进制”与“你我”形成一种奇妙的错搭关系,现代诗意顿生。城市像镜面组成的迷宫,又似一个被巨人旋转的万花筒。在这个“摩天万镜”里,“长车椎刺”。而老相机却能超越时空地将都市人碎片化的记忆融入胶卷。人工智能如火如荼,人类文明正处于重要转型的“拐点”和“奇点”上,人类是否会因工具理性而丢失自身尊严?演化的历史中,人类智能的“涌现”本就难以解释,而从智能中涌现出的新型智能形态,将会重新定义多少这个时代的观念和物象?人是鲜活的,人性充满悖论,充满意外,人难以被简单定义;而人的理性又不断强迫自身提高协作效率,攫取更多资源,容忍甚至渴求自身被定义,被标签化。我们正从文字时代过渡到数字时代,人逐渐被复杂数据淹没和勾勒。在大时代的数据万花筒中,人类将怎样重返一个初冬的江南雨夜?算法将人转为“二进制”时,被上传成数据的我们会感觉到疼吗?
李子梨子栗子也是当代诗词的代表性作者,他在多个维度上为诗词创作增添了新的可能性。在《临江仙·一只小动物》中,在作者多重感官维度的还原下,这只野生动物的死亡触目惊心。诗人凝视下的残酷现实,是从生物界到人类社会反复上演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剧目。“夺吾皮与骨,饰尔帽和襟”表述简短有力,如尖刀直插心脏,面前的小生命任人宰割,“身拳足颤更声噤”。其荒诞性和反讽之处还在于自然界对所谓“弱种”的戕害竟是人们称之为“规律”的一部分。而“缘何天下土,无处不刀砧”的慨叹悲悯发人深省,“从来如此,便对么”?这不禁让人联想到诗人杨键的《冬日》一诗:“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就是两只绵羊,/正走在去屠宰的路上,/我会哭泣,你也会哭泣,/在这浮世上。”
黑洞猫瞳,恒星豆火。周天寒彻人寰坐。我来何处去何方,茫茫幻象云中舸。 沧海沉盐,荒垓化卵。时空旋转天光堕。小堆原子碳和氢,匆匆一个今生我。
——《踏莎行》
作者在诗词中把肉身解构为原子和碳氢链,取消了生与死的简单二元对立,虽迈过了古典时代人对自身的粗糙认知,但转头又陷入了人在“祛魅”后的“价值真空”。通过“茫茫幻象云中舸”的超现实意象表达现代人在“诸神黄昏”后的典型迷思。“黑洞猫瞳,恒星豆火”的意象书写极具跳跃性和生动性,也许多维时空未必充满谜题,人类自身才是宇宙中的一抹异色。
孟依依的创作,在古今交融之中敏锐地捕捉到现代人的痛点。现代日常生活中,噩梦和失眠是典型情境。从文学、绘画到电影,两者都为无数现代主义作家和艺术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在《清平乐·噩梦》中,孟依依写道:“到底红尘刀缓,一刀一次修行。”运用意象精准、狠辣,读者能从骨头上看见刀痕。不但噩梦带来如刀割般的“修行”,“红尘刀缓”的表述更添残酷。“哭哑”的嗓音也凸显噩梦对于苦厄的精疲力竭的“了断”。孟依依的《浪淘沙·微信听秦月明唱陶潜〈拟古〉》:“隔空击案唱兴亡。世路多端皆我异,徙倚彷徨。”作者特地注出此处用典为陶潜《读史》的“世路多端,皆为我异”。寥寥数语透露出深刻的孤独、悲凉与彷徨感。人追求与他人的相似性,却又需求差异性,这是常要面对的悖论。“皆为我异”是人的困境,也是人自我选择的结果。《减字木兰花》:“长生乏味,无限寂寥无益事。”“三魂七魄,幻化万千皆过客。何以为欢,结束今生尚有年。”对于现代生活而言,医疗条件提升,人均寿命愈来愈长,而现代性中虚无主义的幽灵则出没得肆无忌惮,与虚无感并行的还有对这个世界的陌生感和疏离感,遂有“三魂七魄,幻化万千皆过客”这般表述。对一个现代人威胁最大的竟不是死亡,而是“长生乏味”以及“结束今生尚有年”。“重复”何尝不是一个反人性的、使人异化成机械的、让人歇斯底里的魔灵。
夏婉墨多有惊人之笔,网络称之为“豹体”。《山居》:“为棂风透明,著雨春凹凸。放大草精魂,缩微山肉骨。”《昨夜》:“大月弥天巨如谎,照人新梦到清圆。”“美不会受到禁止,也不会服从规定。因为像浮士德那样召唤一切体验的意象,本身是一件非常解放,非常崇高的事。”①“放大草精魂,缩微山肉骨”“大月弥天巨如谎”便是具有现代诗意的意象变奏。月亮不再象征团圆,而是巨大如谎言一般,是自由而不失崇高的现代表述。夏婉墨的《生查子·见玉兰树上的鸟窝作》:“巢于白胖花,孵出清圆月。冉冉向中天,照得千株雪。”一句,视觉形象鲜明,“孵”字甚妙,这大概就是洛夫追寻的,既古典又现代的意象表达。洛夫举的例子是:“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既美又现代,他认为从美学上而言,创造性意味着现代性。而在《柳梢青》里,都市中情爱的突然发生和逝去一样,充满了神秘性与暧昧性,比其他情感关系更为复杂,更为冲动,蕴含着人性的意外。作者在这里点到为止,仿佛智者俯瞰人间,淡看剧中人。都市情爱之意外与惊心动魄,转瞬化作淡淡几点花影。《皂罗特髻·出行》:“我来爱你,像子弹惊春,贯冬而过。我来爱你,要猝无堪躲。茫茫也、我来爱你,擦霜原、万杪神经破。我来爱你,竞太阳升亸。”把“爱你”化为惊春的“子弹”,“贯冬而过”,极具穿透力。读者像经历爱情的主人公一般被命运的弹丸击中。“万杪”与“神经”想呼应;爱不止是上升的,还有宿命般下坠的过程,因此作者又云:“我来爱你,竞太阳升亸”。夏婉墨《长宵》一诗意象奇异,从宇宙洪荒到人类大脑的跳跃极具蒙太奇感:“未别人猿相面对,久疏宇宙自平行。于颅左右成深轨,广播银河有站名。”此句有种《2001太空漫游》中从骨头到宇宙飞船的剪辑感,这类意象跳跃既是视觉的跳跃,也是诗性的跳跃。
石任之的作品时而庄重如古典音乐,时而爆裂似重金属摇滚,精神能量巨大。《鹧鸪天·牡丹为雨所败》:“宿雨腰肢斗沈郎。琉璃碎片减天香。者番春事平生已,第一名花抵死狂。”此处用了沈郎的典故,安静中有爆裂,于寻常处有破碎感,笔力劲道,举重若轻。《焚舟纪》则更具力量感,如同嘶哑着喉咙喊叫的摇滚乐,现代生活中积攒的爆裂与焚烧在此刻宣泄而出:“焚乎,将焚!忧心烈心,掩砧杵之相捣,裂帛余丝越裂,终风扬激声,虺虺然将雷,尔其无闻!四时之改,五内之崩,吾所以有大患者不过此身。请为我炼鲛人之膏,割蚖蛇之脂,伐庄叟之樗,碎孔丘之简,聚此世界生成以来之焰,作无明火洞烧,吞日轮月轮。使芝与艾都尽,一炬无我无人。”通过燃烧中的意象,轰鸣出一连串奇异的高音,甚至是噪音,内在激烈情绪充分外化,毁灭性的能量充分具象化。“了尔火宅已炙之躯,了尔生死流浪,了尔滴蜜调檗万苦一甘终不可入唇。”现代性是什么?据说现代性就是我们身上黑暗的、爆裂的,宣泄出来让我们自己都感到惊讶的东西。在《踏莎行·瓶花初萎,色犹嫣然》中,作者笔锋凌厉,似有招魂之能。读者能听到花朵尖厉的喊叫。“红如白刃秋如砥”,颜色鲜明,意象鲜活,是芹溪笔下“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焦虑和精神困境的深化。如此短短七个字就展现了如此丰富而奇异的景象,直达读者的感官边界。把花瓣比成刀,本就足够锋利,再将秋天比成砥,让花之刀磨于其上,将张力与痛觉推向极致。
华明作为学者、翻译家不光具有极深的文学艺术修养和学理积淀,在创作上也别出心裁,不拘一格,视野宏阔,用典灵活。《七律·哈姆雷特》:“冷刀怀恨匣中吼,沸血蒙羞釜底翻。”“孽业有源弥宇宙,王孙无计整河山。疑思太甚羁决手,延宕岂能雪枉冤。”文学史上一场伟大的延宕,给后人提供了无穷的现代性迷思与影响之焦虑。哈姆雷特身心的复杂性远超我们想象。意象自带温度和情绪:“冷刃”“沸血”相对,“匣中吼”“釜底翻”凸显空间性和戏剧冲突。作者感慨这一难解的“百代谜题”——只要我们还是人类,哈姆雷特就仍是个谜。这一文学形象本就是最经典的人类样本。作者把戏剧冲突的瞬间凝固、提炼于诗中,戏剧主角的每一次犹疑和延宕都有其深邃、迷人之处。也正如欧阳江河的新诗作品《哈姆雷特》写道:“在一个角色里待久了会显得孤立。/但这只是鬼魂,面具后面的呼吸。”作为现代化发源地之一的英国,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也正是现代谜题积累、爆发的时代,面具后面的鬼魂,是“孽业有源弥宇宙”的鬼魂,也是现代性的鬼魂。
朱隐山的创作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具有极强的开拓性,他对当代诗词的发展有着很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正如他在新诗作品中写道:“收复汉语的伟大权柄,那阴凉的拱门。”除了不同现代题材的尝试外,他还擅长集句的写作。集句起源较早,到北宋日趋成熟,它要求作者兼具文学功底与创新思维,因为其本身既有学理的门槛,又有游戏性。此处选取朱隐山组诗中的一首:
桂花吹断月中香,卧后清宵细细长。
忆得鲛丝裁小卓,众仙同日咏霓裳。
——《辛丑秋日漫山岛雅集集李义山句》(其三)
此四句分别取自李义山《昨夜》《无题·重帏深下莫愁堂》《河阳诗》《留赠畏之》四首。创作难度不仅极高,也有“剪辑、拼贴”式的后现代趣味。拼成新作品后,桂花的意象在“卧后清宵”的意境中又多了层神秘感和陌生感,意象群内部既有微妙的时空跳跃,又有某种相互呼应和衬托的氛围,实为巧妙。
渠大白的诗词既多豪壮之句,气象开阔,又有江南气。其诗词陌生化程度高,意境新奇。《登方山十八盘》:“莫辞谢屐觅霓幢,转石迷花晚愈凉。脱尽人寰丸一粒,坐云深处看斜阳。”诗歌的跳跃性惊人,仿佛在古典气息弥漫的登山途中突然获得了宇宙视野。“脱尽人寰丸一粒”兼具意象上的跳跃与思维上的跳跃。《春过扬子江隧道》:“一隧深中飞此身,兆年不见往来春。朅来回望灵光处,隙外幽花即劫尘。”此作呈现了穿越隧道形成的迷思,扬子江隧道似乎也变成了时空隧道。进入隧道的和穿出隧道的是否为同一具肉身?“灵光”处显出“幽花”“劫尘”。日常生活的片刻因思维之玄妙获得神性。《金缕曲·登紫峰大厦》则气势雄浑:“直破苍旻角。翼垂天,风云在下,擘开清浊。万隙灵光连埃刺,一朵如来仙萼。根蒂向、浮沤淳濯。”将今日南京地标建筑紫峰大厦比喻成“直破苍旻角”的“如来仙萼”,震撼而新颖。
李让眉艺术感觉敏锐,意象巧妙,取材丰富,对个体生命和大千世界的感悟深刻而细微。比如,《减字木兰花·丁香》一首,读者在此遇见的分明不是丁香,而是作者本人。在“低妄语”里隐约听见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作者的迷茫与孤独。“如漉微盐。空海淘愁细浪尖。”“不必人间受此香”意味隽永。才华是上苍给青年作者的最“危险”的礼物。有才情的创作者更加敏锐,更易共情,情绪也更易遭遇挑衅,与日常生活的精神兼容需要付出更多努力。这是才华的代价,也是创作的代价。李让眉的《八声甘州·梦返弗莱堡》:“渺衢灯十里向山灯,浩露换秋城。正林花堕雾,平波生岸,一塔孤钉。”作者留学于德国弗莱堡,其中世纪教堂塔楼世所罕有,“孤钉”是作者主观情感与客观物象的结合。
谢冰夷的《奥菲利亚》:“流香渠畔蒲青青,胭脂水色照冥灯。”“宁芙抓破素纱裙,嘲笑王孙枉伤春。‘愿伊来世能御马,踏彼凡躯铜蹄下。’”作者从鲜明的现代女性视角出发,对这位文学史上著名的复仇者进行“复仇”。奥菲利亚死于哈姆雷特自以为绝对正义的复仇之路,可悲可叹,这莫名的献祭让作者反感。作品力量感十足,意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人格的外化:作者内心对女性角色命运的不忿,对崇高的追寻和充满压制性的力量具有摧毁性的美。
殊眉在她的作品《来自抑郁的幻觉》中题注:“感到沮丧、抑郁之时,人如溺深海。这些年,对我影响最深的诗,居然是废名的《妆台》:‘因为此地是妆台,不可有悲哀’”。殊眉的一些诗词意象有李长吉之风,鬼魅、压抑而幽微。“翻书遮腥气,抓笔闻巨响。”在抑郁症的状态之下,人听到最微小的声音也如爆炸巨响一般,且有沉入海底的无助感;在如此幽微的创作之中,此刻“主观的真实是更高的真实”,海啸淹没整个城市。“白骨生铜绿,海石生青苔。阳光溶解我,冰冷一尸骸”,这似乎印证了心理学上较为典型的“人格解体”之感:患者感到人格从“自我”中分裂而出,或熔化分解,痛苦似乎暂时静止了,而“自我”却散落各处,拼接不到一起。此处的奇异意象,传递出人格解体后患者对世界与自我巨大的陌生感和不真实感。
总而言之,当代诗词的创作者首先应当是一个创新者。“即诗歌作为最高语言艺术的特质不会变,但语言艺术的具体审美特征、表现手法及表现形式则会变。”①对于诗词的转型与实验,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耐心,这也许是以世纪为单位的更长时间尺度上的事。“针对21世纪出现的当代旧体诗词,传统诗论词论无法解读、甚至只能低效解读,说明诗词审美已落后于创作实践。”②而强行把新诗与当代诗词对比,也可能是陷阱,毕竟它们从形式和材质角度而言都大不相同。底层逻辑的冲突是注定的,迷惘也是注定的。来自古时的韵律如何焕发新生?回到诗歌文本上看,为意象增添现代意味可能是目前较为可行的探索方式。我们对观念谈得太多,对创作本身知之甚少。创作领域的话题沦为了抽象的观念之争,创作者需警惕这种无谓的消耗,只有往前走,不断试错。今天我们见到的未必是成熟的创作,但这些创作中不缺勇气与韧性,这是当代诗词创作中最可贵的品质。由此出发,创新者们的能量将会得到进一步释放。
“旧体诗”的说法似乎总给人功利主义的消极暗示,仿佛旧的是快被淘汰的,新的就是好的。如此简陋的思维模型是人脑简化世界的结果,偷懒将付出代价。诗词这一文字艺术样式,像一种信仰,信仰具有不可证伪性。“从本质上讲,它不是因其形式而存在,而是因其‘美’而存在,迄今为止,没有一种艺术形式可以在如此精短的篇幅里让审美达到这种极致,并在传达民族神韵的同时凸显民族审美个性。可以说,这古老的形式已是中华民族精神史的一部分。”③
今天的创作者面对的是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诗词生存语境已改变,传统诗词语境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已被现代人与自然的紧张、焦虑打破。人们的目光早已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转向更深刻的人与自我的灵魂深处。”④一个现代人不得不指认自身的幽暗之处;但晦暗不是人性的全部,人性的悖论效应也会在幽暗之处发挥反向作用,让人瞥见个体生命繁荣的曙光。如今世界在前所未有地综合化,万物互联和交融,不同领域的跨界创新随时在发生。人们的阅读、观看习惯,审美习性,与世界的交互方式,正发生着深刻变革。我们需要从一个更高的维度出发,以新的视野来更加自由地讨论当代诗词。提升认知,创新性地增强作品的现代意味是当代诗词旺盛生命力的源泉。要警惕诗词艺术陷入“演化的死胡同”,我们在这条文字的信仰之路上跋涉并不容易,也都深知信仰未曾断绝。在此要引新诗作品《燕子矶》中的一句作注:“诗词不朽,但微妙的需要/仍然傍着江水的流逝。”
作者单位:南京传媒学院
①马大勇:《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的回望与前瞻》,《文学评论》2011年第6期。
②李仲凡:《现代旧体诗词的非现代性》,《求索》2008年第13期。
③黄梵:《意象的帝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39页。
①[西班牙]乔治·桑塔亚那:《诗与哲学》,华明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193页。
①李咏梅、郑家治:《汉语的特性是现代传统诗词延续发展的根本》,《当代文坛》2010年第6期。
②宋湘绮:《当代诗词审美学研究方法和体系的构想》,《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③陈启文:《对当代旧体诗词的再认识和重新发现》,《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
④宋湘绮:《当代诗词创作方法论》,《湖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