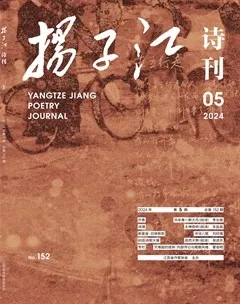独坐辞(组诗)
何晓坤,云南罗平人。著有诗集《与己书》《灯花盛开》《蚂蚁的行踪》等,曾获扬子江诗学奖·诗歌奖、云南文学艺术奖、云南省年度优秀作家奖等多种奖项。
养花记
要掌握空间切割术,以虚拟的视角
安置阳光和云朵。泥土和陶器
不能来自暗处,为风留出最后的退路
读懂植物的生命周期,允许落单的麻雀
在沉默中表达忧伤。黄昏来临
花朵的生物钟,会在霞光里轻轻敲响
此刻就静静地坐下来,忘记修剪
忘记施肥和浇水,看枝头上的瓣儿
在时间的缝隙中,绽开或凋落
不需要禅定,也不需要
夕光滑向虚空的感叹。安静下来
紧紧抱住,一个花匠的幸福与庸常
在泸沽湖
坐猪槽船行至泸沽湖中央
多余的痰,突然从胸腔里咳出
环顾四周蓝得瘆人的湖水
以及湖水之下梦幻般的天空
我立即把这口中的秽物
悄悄强行送回原处
块择河上的断桥
断桥悬在流水头顶的中央
事实上断桥悬而未断,但已经没有
渡的功能。
人们在断桥的上方,重建了新桥
新桥宽阔雄壮,可通巨型车辆
《桥梁志》里的断桥,并没有这样的神力
它只渡人,当然也渡骡马和耕牛
新桥建成之后,断桥隐身新桥的下面
断桥桥头的碑刻,文字日趋模糊
块择河史多了新的条目
曾经在桥畔凿崖为路的人
并没有将影子凿进岩壁,他凿下的碎石
散落在富源的草丛间,凿石的声音
一直回荡在罗平的峰谷里
走碗窑村
黏土里的魂魄已经聚合,龙窑的温度
足以让一次仓促的再生,成功定型
柴火生起之前,借陶还魂的事物
仍有足够的时间,和漏洞百出的往昔
作釜底抽薪的告别
而焚烧和淬炼在所难免
唯有粉身碎骨的疼痛,才能托起夙愿
命运和梦交给神吧,遗憾也交给神
浴火的肉身,对得住任何完美
或一无是处的重生
不问这人世到底有多少隐疾
黏土的本味还剩多少,能唤醒
泉水之外的嗅觉。成精了的植物
都在等待柴火的加冕。尚在修炼的叶子
应拥有面向天空吼声佛号的机缘
所以,当我们伪装成时间的信使
走过碗窑村时,要接纳焚烧之后的坯胎
还要接纳,一把火钳一件马褂的灰尘
最后还应该伫立窑前,闭目冥想
天空深处,托钵走过的背影
太阳宫的上午茶
天地间最大的那扇门,一定在
太阳宫。天地间最大的那扇门
一定是空门。空门并非凡人的通道
比肩接踵的游客,得从狭窄的侧门进来
最后还得从狭窄的侧门出去
舞蹈的魔力,就是把坚硬无比的岩石
舞得波光粼粼,还要把坚硬无比的岩石
舞成蒲团和茶水。舞蹈家的空间
因此容易让人生出太多联想
你看坐下来的游客,一杯茶水在手
似乎就已认定,精神与物质无关
灵魂与肉身无关,艺术与神灵
也无关
如果再继续坐下去,闭上眼睛
他们就能拥有整个洱海
继续闭上眼睛,似乎就成了
太阳宫的主人
在白腊山麓
罗平坝子想给自己开一扇天窗
白腊山腰凹陷下去的地方
因此多出了一座寺庙——腊山寺
而从寺院回来的人,还是看不见
自己真实的样子。白腊山麓
因此多出了一面镜子——太液湖
此后,从湖边走过的人
都能在湖水的最低处,看见罗平最高的山峰
也能看见,自己一晃而过的影子
几百年后,鳞次栉比的高楼
耸立于湖的四周,湖水中的那座高峰
终隐身于钢筋、水泥和玻璃的背后
沧源之夜兼致谢霄雷
怀抱琵琶的人,胸中还抱着
大片旧时的山河。身陷重围的弹奏者
指尖藏着调动万千铁骑的秘笈
杀伐声和霓裳飘舞的声音,并非有
遥不可及的距离,在子弦与缠弦的中央
死士的决绝注定成为这个夜晚的绝唱
佳人们纷纷立于流水的对面
看滚滚波涛覆过,眸子深处的落英
善饮者善醉,中箭的执戟士
现在只能安静地回想,搏命的最后一击
而五音不全的人,并未在惊心动魄的对决中
找到欢乐的密码,但他苦心守护的睡眠
却真的遗失在沧源的茫茫雨夜中
为罗平新建街道命名
总会有看不见的泉水
沿着时间的根部,来到枝头
事实上,那些熟透的果实
在我们到来之前,已经变为泥土
不管你有没有这种知觉,我们都是
其中的受益者。或许文字的天秤
本身就是个陷阱,但辨别轻重
真的不是想象中那么重要
允许色差的存在,才能呈现完整
历史已经很疲惫了
在历史的拐角打盹的当事者
作不了旁证。要允许时光和智慧
出现碎片与空白。在空旷的膨胀中
总会有看不见的泉水,流向
未来或未知的枝头
为罗平新建的街道命名
就是在填满了的沙盘上,找出空白
还给曾经的,或者假寐的
柔软与错觉
九龙河记
九龙河流入老君山的身体后
石头接纳了她,水泥和钢铁也接纳了她
来自富源墨红的流水,在罗平境内
洗去了一身灰尘,成为母亲
一条河流的传奇就此开启
之前的青涩、汹涌、奔腾与咆哮
在山下归于宁静。母性的慈悲开始漫延
同时漫延的还有春光、花朵和稻浪
62公里的河槽,因此被冠以鱼米之乡
河床中的液体,在春天会成为金子
在流淌中等待燃烧。腊庄和大寨
就这样以自身的光芒,为黑暗画出边际
然而这远远不够,作为河流
她还要让自己粉身碎骨,成为绝世风景
所以她纵身跳下。她跳下的时候
每朵浪花里,都建有一座宏大的庙宇
独坐辞
与躺椅有关的事物,隐身于竹林
竹笋逃离了春天,闲置的躺椅
比一杯隔夜的茶水,更加空寂和安静
当我躺下去,这个世界已经消失
当我躺下去,我已经消失,躺椅亦消失
头顶的桂花树冠,亦是消失的伞
前方,天竺葵一边盛开一边凋零
旁边的狗一动不动,不知是熟睡,还是假寐
一座山,或者一个托钵僧
一个托钵僧,在黑暗中提一盏
从未点燃的灯,独自矗立在人间。
这个意境很美,但显然
我不是只想眺望灯塔的人。托钵僧的灯
不需要点燃。我也从未去思考
“一座山就是一个托钵僧”
与“一个托钵僧就是一座山”,哪句话的语境
更能抵达我的溃败?我是不是忽略了
山中之物,忽略了灯火之黑,从而
夸大了有限的钵体内,那些无限的延伸
是的,面对这样一座山峦,我更应接纳
岩峰上的枝条,不断靠近天空
枝条下的青苔和虫子,挤进泥土的后院
接纳昼伏夜出的山猫和虎口余生的羚羊
也接纳光秃秃的山顶,藏进浓雾之中
大雪里的高贵与矜持,被阳光逐一消融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这座像托钵僧的山,或像山的托钵僧
已经为这个春天积攒了足够多的爱
所以我更应接纳所有蹩脚的比喻,尽管
我并不能预测,一场山火的来临
读一朵油菜花
还是从灰烬开始吧
从灰烬回到燃烧,回到灯芯的空寂
人间的灯火,仍在暗夜中
传递光亮与温度。长明的光焰里
巨大的碾子,仍在石槽中缓缓滚动
一朵花的籽粒,从饱满抵达柔软
然后在流淌中将自己点亮
回到颠簸于花海的牛车里的歌声
看外乡人头上的花环,早已高过
春天的额头。回到喧嚣,回到绽放
回到养蜂人的面罩里
最后回到地霭与冰凌的躯体
回到泥土,看无边无际的雨雾深处
一朵花的种子,如何在最初的灰烬中
生生不息
像一座座沉默的山头
夜色褪尽,大地露出干净的面容
万物的眸子里,夜的影子消失殆尽
阳光从天际喷射而来
阳光照亮了这一面,另一面就暗了下去
在阳光下留下清晰的背影是万物的信条
像早春的油菜苗,遮住大地的伤口
像眼前这一座座沉默的山头,饱经风霜
却看不到一丝受伤的痕迹
消失
最先消失的是声音。灯火熄灭之后
合唱戛然而止,木鱼对大地的敲击声
戛然而止。喊魂的人
并没有给自己预留多余的通道
他记下来时的住址之后,选择了隐身。
接下来消失的是影子。风回到原处
云朵的背后,是云朵留给天空的伤口
伤口的背后,曾经驻足头顶的那颗星
已潜回天空的深处。剩下石块
在尘土之间。砖瓦,在荒草之间
塑像和文字,在人心之间
声音和影子,在天地之间
曾经的事物,就这样一退再退
隐姓埋名之后,把更多的空白
留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