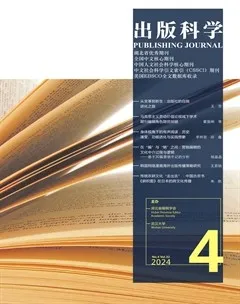身体视角下的有声阅读:历史演变、功能进化与实践想象
[摘 要] 我国有声阅读活动可追溯到上古时期。从身体与阅读的关系视角来看,有声阅读呈现出仪式化阅读、流动式阅读、独立式阅读和交互式阅读四个演进阶段,身体呈现出文本、接入、陪伴和感知的功能,随之推动身体与阅读的关系从陌生走向交互。基于当下有声阅读实践,文章提出,有声阅读应回归身体、打造沉浸式阅读空间、全面覆盖身体的接入场景,塑造陪伴弱势群体的虚拟化身,进一步推动身体与有声阅读交互升维。
[关键词] 有声阅读 身体视角 阅读史 有声书
[中图分类号] G2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24) 04-0028-09
Audible Reading from a Physical Perspective: Historical Evolution, Functional Evolution and Practical Imagination
Li Linrong Qiu Xi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Abstract]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vocal reading activities in China can be traced back to ancient tim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and reading, audio reading presents four evolutionary stages: ritualized reading, mobile reading, independent reading and interactive reading. The body presents functions of text, access, companionship, and perception, which subsequently driv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and reading from unfamiliar to interactive. Based on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audio reading, the article proposes that audio reading should return to the body, create an immersive reading space, fully cover the access scene of the body, shape a virtual avatar to accompany vulnerable groups,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interac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body and audio reading.
[Key words] Audible reading Body perspective Reading history Audiobooks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3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智能传播时代的人机关系研究”(2023NDZD08)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李林容,文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邱鑫,通讯作者,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23级博士生。
自2014年以来,全民阅读连续11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第21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发现,成年国民有声阅读规模持续扩大[1],有声阅读成为全民阅读新的支柱。从古至今,声音作为阅读的重要书写材料,发挥着承载文本和感知意义的效用。在数字时代下,新一代技术革新将有声阅读推向新高地,有声阅读正在回归。
作为听觉参与的学习活动,有声阅读中的身体意涵开始受到人们关注。目前,以身体为视角的有声阅读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学界对于有声阅读中的身体观照基本沿具身认知的“认知-身体-环境”视角出发,对有声阅读的意义、生态建设等方面进行阐释。随着身体成为观测阅读活动的新视角,有学者较早关注到有声阅读的具身认知及价值意涵[2]。吴瑶将具身性作为有声阅读可供性实践一个面向进行考察,提出有声阅读倾向于包容、解放和调动身体的通感体验[3]。袁辉等人认为,有声阅读是身体的具体传播实践[4]。可以发现,有声阅读的身体研究多集中在当下的阅读实践中,缺乏对有声阅读的历时性考察。基于此,本文从身体视角考察有声阅读的历史演变,思考身体在这一过程中有哪些阶段性表征及功能意涵,并提出合理的实践想象。
1 历史演变:走向交互的有声阅读
近年来,有声阅读概念随实践发展从狭义走向广义,内涵得到充分延展。有声阅读的狭义概念是指对有声读物(Audio Book)的阅读[5]。可以发现,如按狭义概念理解有声阅读则易导致阅读与历史割裂,极易将“有声阅读”认作是数字时代的创新性活动。本文认为有声阅读是一种广义的听觉阅读行为,即阅听人通过听觉接受来自出版物、人等中介的文化信息的阅读行为。由此,有声阅读历史性价值得以凸显。
1.1 浮现:我国早期的仪式化阅读
以祀神和讲经为表征的仪式化阅听是政治、宗教活动的延伸,关乎部落与国家的行动决策。参与祭祀的听者身体处于高度紧张的静止状态,并与巫师等表演者置于心理上的上下级关系,这直接影响了听众的意义获得。从两者关系看,有声阅读与身体之间存在较疏远的心理距离。
有声阅读活动最早可追溯至上古时期。这一时期,人们的有声阅读活动围绕以身体为中介的祀神歌舞展开,并以此作为政治活动和日常活动的行动指南。生产生活依赖自然的部落社会孕育出“巫师”角色,加之原始社会缺少成文的经典和专门的庙宇,巫师只能通过肢体表演鼓乐歌舞完成祀神、祭祀等活动。这种情况下,祀神的重要性催生了身体进入有声场的仪式性。基诺族巫师“周巴”在主持祈雨仪式时要跪在地上,表演披雨具和戴斗笠的动作,并唱诵道:“你如不下雨,粮食生不出,钱也找不到……求你快快下雨来。”[6]巫师通过夸张的肢体表演完成大傩、祈雨、祀神、祓禊、雩祭等仪式活动。南北朝时期的讲经活动延续了这种仪式化状态。作为阅听人的僧人、官员和外国使臣的身体被禁锢在“宫苑、寺庙”等讲经场中。沿袭了道安以来的讲经传统,“定座”成为这一时期有声阅读的阅读姿态。在《高僧传·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中提到“行香定座上讲经上讲之法”,即讲经有行香、定座、上讲经和上讲四道流程[7]。可见,在“定座”后诵读经书是讲经的重要流程之一。
1.2 渐成:抄印时期的流动式阅读
宋代“夜市”代替唐代“宵禁”催生市民生活从白天持续到深夜的繁荣景象。雕版印刷、造纸术的发明革新带来了以讲史为蓝本的说书艺术,说书人开始活跃在勾栏瓦舍之中。全新的阅读形态—“说书”促使市民走向勾栏瓦舍。丰富的话本和娱乐场所为市民生活提供更多选择性,身体在茶馆、酒楼与戏院等场所中进行空间置换,并形成“易聚易散”的流动式阅读形态。
崇、观以来,说书人的类型多样、语料丰富。据统计,宋代仅汴梁和临安的“说话人”就高达 124 人[8],包括瓦舍艺伎、小唱、嘌唱、杂剧、讲史、小说等类型。通晓古今的说话艺人生产了一大批话本,为市民的有声阅读提供多样化选择。作为说话艺人重要的话语来源,宋代的书籍名目与这一时期的经济同向发展。《醉翁谈录》中提到,单单小说话本便有8类。此外,还包括讲史、讲经等类话本。随着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市民阶层逐渐形成。对于出没在瓦子中的市民,《都城纪胜》中用“士庶”来表示他们的身份。实际上,他们是一群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有少量世家贵族子弟。《梦梁录》采用“易聚易散”来刻画市民阶层的娱乐属性和聚集形式。有史料记载,宋代说话演出场所包括瓦子勾栏、茶肆酒楼、露天空地与街道、寺庙、私人府第、宫廷、乡村等[9]。以茶馆、酒楼、戏院为代表的娱乐场所是市民听书人的聚集地,也是他们身体置换和交友娱乐的空间场域。
1.3 发展:电子时代的独立式阅读
从巫师祀神到说书人说书,有声阅读均未突破身体在场的收听局限。直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打破了说书时代的“身景”一体化,电子技术的进化推动近代有声读物发展的同时,也催生了身体器官“多任务并行”的形态。
机械录制与模拟录制技术的进化更迭了身体阅读的“在场性”,即便在不同地域,人们也可通过留声机、录音机等设备进入同一个有声阅读空间,身体逐渐脱离元场域。此外,以戏曲、小说、语言、小调、山歌和杂唱为主的有声读物通过留声机、唱片与大众见面,加速了分割身体的步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根据不同的生活需要可选择不同类型、不同时长的有声读物。《上海总商会月报》曾刊登了一则关于新式唱片的消息:“留声机中唱片,十二寸者,约唱四分钟……英国有人创造一种新式唱片,速率有常、始终如一,十二寸者可唱二十分钟云。”[10]这种新式唱片适应了当时城市小资市民的慢生活节奏,他们只借耳朵进入有声世界,身体其他器官则进入另一世界,形成身体被分割的“独立式阅读”形态。《中国艺坛日报》报道了女星英茵的一天,在家庭环境中的女明星英茵放松身体,悠闲地喝着咖啡,听着唱片[11]。《艺文画报》记录了散课女工们聚集收听留声机的场景,她们或站立看报,或坐凳下棋[12]。这种状态下,肢体等身体器官被利用起来,并融入到了其他活动中,耳朵则进入有声阅读之中。
1.4 繁荣:数字时代的交互式阅读
数字时代下,上千年的文化积淀以全新的面貌浸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将身体各个器官发挥到极致,人们由此认识到身体的主体性意义。为更加贴合身体,有声阅读在接收终端、场景适配和内容生产等业态中深耕作业,类型丰富、品种多样的有声书借数字出版大潮迅速崛起,有声阅读成为全民阅读的重要组成部分。智能交互时代下,有声阅读的交互属性被开掘,身体重回有声场域,呈现身体与技术、读物和场景的多重交互表征。
作为声音的接口,耳朵是有声阅读的获得器官。当下,技术拓展了声音进入的渠道,以骨骼为代表的身体组织成为另一个接收端口。从留声机、录音机到移动智能接口的迭代,有声阅读终端正在向适配身体的方向进化得更加轻量;从有线入耳式耳机、无线入耳式耳机到骨传导耳机,有声阅读收听设备更加关照身体功能,为听障群体进入有声世界提供技术支持。在移动智能手机、智能音响和车载收音机等移动终端设备的支持下,多场景移动收听构成了当下有声书用户的收听空间,借助智能穿戴设备,身体可自由进入任何场景,并与有声阅读场景之间形成严丝合缝的互嵌关系。精力盈余时代下,身体需求被极大挖掘。为对接身体场景多样性,有声出版商开发了适应包括通勤-休闲在内的16大收听场景和19大内容图景[13],一个“声”意盎然的听读时代来临。
2 功能进化:有声阅读史中的身体参与
在有声阅读的演变中,身体以多种形态参与阅读,在不同的阶段发挥出不同的效能。仪式化展演阶段,身体是被解读的文本;流动式阅听中,身体是听书场的接口;电子时代下,耳朵独立执行任务,身体呈现陪伴的功能;数字时代下,有声阅读回归身体,身体成为重要的感知器官参与有声阅读。
2.1 作为文本的身体:仪式化有声阅读的身体体验
政教合一的政治形态将身体推向有声仪式的舞台中央,身体成为阅读文本并参与有声展演。此时,有声阅读的意义关乎人、部落甚至国家的行动。口语吟诵与肢体舞蹈的结合是巫师具身讲述的过程,作为听者的氏族或宗教子弟则以听觉进入现场。周冰等人在《试析楚巫舞手势》中提到,“巫舞的手势,就是在举行祈祷祭祀礼仪时,作为人与神、神与鬼、鬼与人相互沟通的媒介,传达信息的外在符号,表达思想感情和意图的图象标记”[14]。此时,巫师的肢体舞蹈成为文本,通过巫歌吟唱进行讲述,辅之以皮鼓、木鼓等器具作取悦、驱赶之用。敲击、拍打是重要的肢体动作,传递出不同韵律与节奏的声音,氏族弟子跟随节奏进入祀神、祈雨现场之中;战争巫术中的进攻与发怒等肢体动作同样伴随着叫喊声与挥剑声,被氏族弟子以虔诚的身体姿态学习、吸收。
在身体定座的讲经活动中,阅听人的身体以沉浸式的状态进入场景,吸纳文化的同时形塑了身体文化容器的功能效果。如《续高僧传·梁扬都庄严寺沙门释僧旻》言:“‘昔弥天释道安每讲,于定坐后,常使都讲等为含灵转经三契。此事久废,既是前修胜业,欲屈大众各诵《观世音经》一遍。’于是合坐欣然,远近相习。尔后道俗舍物,乞讲前诵经,由此始也。”[15]可以看到,讲经人定座后开始讲经,并以一定的声调诵读经书。
2.2 作为接入的身体:流动式有声阅读的身体体验
受惠于唐代的变文熟讲的影响,“说话”伎艺在宋代迎来了黄金时代[16]。这一时期,上至君王,下至市民均作为听书人参与到声音艺术中。民间大大小小的酒楼、瓦肆,多种多样的听书话本为市民的听书休闲提供了可选择的空间,身体获得了可移动的自主权。可以说,流动的身体是进入听书场的接口,它促进了有声阅读的社交意涵显现。
在“易散易聚”的聚会中,更多的说书人开始关注身体表演,学习言说技能,以此吸引、留住听书人。为给听众带来欢乐,宋代的说话人一般都善于“使砌”和“诙谐调笑”,同时还兼有动作[17]。这恰恰说明阅听人的自主性更强,由身体接入带来的有声体验是衡量“说书人”说书质量的标准。有史料记载,有些场所因说书人惟妙惟肖的演绎而人声鼎沸。其中,数瓦舍勾栏、茶肆酒楼等说话场最为热闹,《东京梦华录》有言:“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18]在热闹非凡的瓦子勾栏中,听书人身份各异,有庶民、士人甚至贵族子弟,但他们均因“听书”在此会聚,他们之间打破了身份与阶级的限制,甚至成为听书之友。
2.3 作为陪伴的身体:独立式有声阅读的身体体验
长久以来,声音依靠身体移动散播信息,身体与声音的合一性统摄了古代有声阅读演进的整体概况。直至近代,技术发展打破了这种一体阅读状态,声音录制、复刻技术将耳朵器官从身体中剥离,单独参与到阅听活动中,身体则逐渐成为听读的“陪伴物”,促使有声阅读意义从学习转向娱乐。
当身体脱离政治和权力的束缚,有声阅读不再是强制性的学习活动,并逐渐从仪式化向流动式的阅听转向。当声音被记录和拷贝,阅听模式便从流动式向陪伴式阅听转向,身体获得自由。这种情况下,有声阅读突破在场收听的限制,“易得”成为有声阅读的标签,身体的陪伴性意涵突显。20世纪30年代,随着收音机进入市民日常生活,以家庭为主的收音机拥有量和听众人数大增。据统计,1927年至1937年这10年间上海的收音机便有10万余具[19]。不仅是家用收音机数量增加,在公共场所的有声阅读行为也异常丰富,人们可以进入咖啡厅、舞厅等公共空间中,与朋友交谈聊天的同时收听各类娱乐节目。军人战士、明星名人和普通市民的身体均以“多任务”参与到有声阅读中,一边听唱片一边喝咖啡成为身体常态。这一时期,虽然亦有市民将有声阅读付之学习之用,但从主要功能来看,有声阅读的学习意义较过去已然弱化。
2.4 作为感知的身体:交互式有声阅读的身体体验
随着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服务于身体,人们开始重新慎思“身-心”之间的关系。智能手机成为身体延伸的器官,身体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进入虚拟世界,人工智能正在解构和重构身体,这一系列的技术实践表明身体的意义正在重译。此时,阅读的具身意涵在身体回归的背景下进入大众视野,有声阅读进一步通过身体器官感知并获得意义。
具身阅读视域下,身体是感知意义的中介。在移动传播时代,统合的身体成为感知意义的器官。智能手机、穿戴设备均通过身体呈现效果,身体行为与外界环境联系更加密切。基于此,有声阅读逐渐从触媒环境切入身体感受,丰富的有声阅读场景被发掘,并应用于有声阅读实践。有声书出版商巧妙对接用户多元化场景需求,匹配适应多元场景的有声读物。例如,有声书生产方打造了舒适的睡前听书场景,有效对接有声书用户的“哄睡”需求。亦有研究表明,在开放空间中,当身体感知到不适状态时,人会能动地选择听书阅读等行为进入“安全气泡”以缓解尴尬。这种“安全气泡”是身体与阅读对话所产生的新空间,即在公共空间中相对封闭的自我空间[20]。
3 实践想象:我国有声阅读的身体景观
以“身体”为纽带打造适配不同阅读形态的有声阅读模式有助于强化阅读获得感,推进全民阅读的价值升维。需指出,新兴有声阅读形态并非是对原有阅读形态的彻底颠覆,“复现”是有声阅读重要的存在形态。当下,有声阅读实践呈现出回归身体的表意,在仪式化阅听中强化身体仪式感,打造沉浸式阅读;通过全场景覆盖对接流动的身体进入有声空间;陪伴式阅听下的虚拟化身将陪伴听者左右。
3.1 身体仪式:有声阅读的沉浸体验
作为身心统合下的阅听方式,仪式化阅读是身体全面浸入有声阅读场,学习知识和塑造意义的过程。仪式化阅读状态广泛地存在于移动阅读、社会化阅读之中,但却被人忽视。有必要指出,社会加速时代重访仪式化阅读,旨在审思碎片化阅读与浏览式阅读的浮躁与“去意义化”问题,仪式化阅读给予阅读实践的启示在于,积极开拓有声阅读仪式空间,为身体进入沉浸式阅读提供新入口,从而提高阅读质量,维系有声阅读信仰。
部落行动很大程度上源于身体仪式塑造的意义,身体的虔诚将带来意识的集中,进而强化意义获得。在仪式过程中,身体本身成为仪式空间。安德鲁·斯特拉桑(Andrew Strathern)在《身体思想》(Body Thoughts)中提到,身体“本质上是一个表达空间”,通过身体其他的表达空间得以形成,因此,“身体的空间性……是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形成的条件”[21]。从身体仪式到仪式空间,人们将以身心一体的感知状态进入学习空间。沉浸在仪式化阅读场中的身体,接受来自历史性与现代性交合的有声文本,在虔诚参与中催生意识的觉醒与认知的提高。作为一种社会化阅读,读书会是仪式化阅听的典型形态。强化读书会中的仪式感能促进听者的身体参与感和提高听读质量。譬如,在上海等地举办的新型读书会上,声音及其关联的空间与情感形构了朗读的仪式,朗诵者和听众以不断变动的声音为媒介,构筑了读书会的空间,极大地调动了听者的情感参与并促进了地方情感的升温[22]。在朗读节目中,朗读者的身体被视为仪式的组成部分,与背景音乐、舞台、灯光等元素构筑朗读仪式的物质基础,在身份象征和历史感召的催化下,“表演”的朗读者与“静坐”的听者之间形成了一个“阅读共同体”,进而实现沉浸体验与情感共鸣。例如,《朗读者》中隐喻着身体与身份的对话,与舞台环境同筑朗读仪式。朗读者选择符合自身职业的诵读书目,与舞台形成契合的朗读空间,促成朗读与历史空间、现实生活的接合和嵌入[23],强化了听众对朗读者经历的肯定以及对于不同职业的价值认同。
3.2 身体流动:有声阅读的场景覆盖
约翰·厄里(John Urry)指出,身体流动包括身体的移动。他认为,在时空压缩背景下,从身体本体移动到借助载体移动,身体表现出更高效率的移动状态[24]。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从身体本体到借助载体的身体移动状态催生在地化阅读和在线化阅读两种模式。有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主要移动阅读平台的月活跃用户规模已达3.2亿人,移动阅读成为一种主流阅读方式[25]。梅罗维茨(Meyrowitz)将物理场景与媒介场景统摄于信息系统场景的概念之下,强调人的不同行为需要对接不同的场景[26]。这为流动的身体接入有声场景提供理论借鉴的同时,也为有声阅读的场景覆盖启迪思路。它提示了有声读物出版商应为听众提供遍在的有声阅读场所,打造适应身体移动的收听场景。
当下,崭露头角的有声图书馆、朗读亭和有声体验馆为身体流动提供了在地化场景。通过扫码身体获得进入朗读亭的许可,并在其中获得阅听自由。配以可调适的背景音乐,链接线上图书资源的朗读亭为朗读者提供充足的文本选择,在可录制、可上传和可分享的机制下,朗读亭成为兼具学习和社交双重属性的“听读场景”。朗读亭为身体提供了有声阅读的在地化接口,虽成功覆盖了地面场景,但也难以避免身体离场带来的阅读断裂。由此,基于线上场景的移动阅读或可成为身体流动的解决方案。以移动图书馆和移动阅读应用为代表的阅读服务拓展了实践想象,为身体流动提供在线场景。掌阅、咪咕阅读、QQ阅读、起点读书等移动阅读App通过提供移动入口(智能设备)建构进入场景,整合用户数据进行书籍与话题的分析和推送构建用户使用场景,分享阅读笔记、阅读痕迹和阅读心得建构用户的互动场景[27]。进入、使用与互动场景共置了听众在线收听的流动场景,实时对接听众通勤出行、运动健身和居家休闲等多维场景需求。
3.3 身体再造:有声阅读的虚拟化身
民国时期,军人负伤依靠听留声机、录音机等有声阅读活动达到纾解情绪之用。人工智能时代下,声音的陪伴不再以分割身体为前提,而是通过声音塑造虚拟化身的形式与身体对话。唐·伊德(Don Ihde)将身体分为具身的身体和虚拟的身体[28]。他认为,技术在两种身体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以锤子、手杖为代表的具身技术能够增强和扩展人的知觉,虚拟的身体则较为“单薄”,永远达不到肉体的“厚度”。但虚拟现实等技术却将虚拟的身体不断强化,虚拟身体可能成为真实身体的一部分[29]。这充分拓展了有声阅读的想象空间:深化虚拟现实融入有声内容开发,通过虚拟化身强化阅读与听众间的情感联系,提升有声阅读的陪伴价值。有研究表明,智能语音助手形成的化身形象对用户听觉感官心理意象具有补偿性作用[30]。可以预见,有声读物的虚拟化身将以建设性态势参与社会心理纾解、文化浸润和阅读治疗等实践应用中。
“凯叔讲故事”打造了《凯叔·诗词来了》的“麦小麦”“麦小米”,《凯叔·小知识》的“宝拉”和“肚大嘟”,《凯叔·口袋神探》的“艾小坡”和“鸡飞飞”等一系列虚拟IP。在背景音乐和现场音响等多重声音塑造的声景环绕下,虚拟IP强化了儿童在娱乐探案、学习常识和知识摄取时的场景感、代入感和信念感,发挥了引入与示范作用,成为儿童在有声空间中的“虚拟化身”与“虚拟偶像”。例如,在《凯叔·口袋神探》中,儿童可以借助虚拟IP艾小坡的身体视角进入如图书馆、音乐教室等现实生活场景,这些场景是对现实生活的复刻,能较大地激发儿童的探索欲望。加之艾小坡超强的解密能力,许多儿童将之视为自己在探案过程中的虚拟化身。在评论区中,甚至出现了模仿艾小坡的儿童(听者)声音。随着模仿声音的扩大,虚拟化身不再仅限于再造身体的价值,而更多地成为儿童的学习对象,即成为儿童在有声读物世界中的“虚拟偶像”。
3.4 身体回归:有声阅读的主体交往
近年来,人本范式随技术革命重回大众视野。在有声交互阅读时代下,身体是阅读活动和意义接受的主体。正如梅洛·庞蒂(Merleau-Ponty)所言,dKpcoX3ZV/Rg5b+Luae/1g==“当我的目光投向事物时,我看到的是事物本身。这是因为身体自身及其器官始终是我的意向的支撑点和载体”[31]。交互式有声阅读关注身体主体性,注重身体体验以及关注听众感受,这体现了人本主义理念在身体阅读中的实践意义。早在2017年,有学者提出,新媒体阅读生态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32]。也有学者为深阅读打造“感官战略”,认为数字时代的深阅读,必然是“以人为本”的参与式阅读[33]。目前,有声书已走过FM1.0的收音机时代。在FM2.0时代下,以有声书为代表的有声阅读与身体实现深层次交互。人本主义范式下的交互式阅读呼唤身体主体性回归,为当下的阅读实践提供价值指引与实践参考。人本理念范式注重身体主体性,倡导从交互内容开发着手,帮助身体在深度参与阅读的基础上获得自主性和控制感,以此推动个人阅读质量优化到全民阅读价值升维。由此,有声阅读的实践想象应以身体为基点强化有声阅读的内容开发。
目前,国际有声阅读市场已迈出交互式有声读物的探索步伐,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2020年,波兰电影制片人沃伊泰克·杰佐夫斯基(Wojtek Jeżowski)创作了一款交互有声读物《流行病》(Pandemioza),以帮助疫情下的听众实现身体纾解与苦闷宣泄。在这个有声世界中,故事推进的权利由听众掌握,他们可以自主选择不同的故事线进行收听,对故事的控制感促使身体成为一种自由的存在。2022年,漫游词(Wanderword)与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合作推出了一款儿童有声读物—《哥白尼的遗产》(The Copernicus Legacy)。在这款读物中,儿童可以选择人物身份进入不同的故事线,并能决定故事的进程。与传统的有声阅读相比,身体在交互式有声阅读中获得了自主性,包括对故事的自主选择和对进程的控制,这极大地增强了身体的张力和快感的获得,身体主体性意涵得以显现。
4 结 语
在全民阅读推广时代下,有声阅读成为推动人们学习知识、休闲娱乐、获得意义和形成共识的重要活动。深度媒介化使身体成为接入场景的重要媒介,声音成为移动化身体的接收工具。当下的交互式有声阅读实践正在回归身体,形塑了丰富的身体景观,向仪式化的有声阅读借鉴沉浸效能,以此提升阅读信仰;打造覆盖多个场景的身体入口,帮助身体全面进入有声阅读空间;塑造虚拟化身呵护弱势群体,形成身体关照。在未来,身体将全方位调动并参与有声阅读,它不仅是感知的器官,更是交互阅读的器官,一个“声”意盎然的有声阅读时代正在来临。
注 释
[1] 新华网.第21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发布[EB/OL].[2024-04-23].http://www.news.cn/book/20240423/4891e9f2b2054338abc580d521e2a90e/c.html
[2] 李林容,修伊湄.推动全民阅读:有声阅读的具身认知与意义建构[J].出版发行研究,2021(8):21-27
[3] 吴瑶.具身性、物质性与互动性:有声阅读可供性实践的三重面向[J].编辑之友,2022(3):13-20
[4] 袁辉,郑舒颖.具身认知理论视域下的有声阅读生态研究[J].传媒观察,2022(8):90-97
[5] 邓月琴.有声阅读概念探析[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9(6):92-95
[6] 张琴.中国古代的巫及巫术仪式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12:45
[7] 慧皎.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183
[8] 袁文春.休闲文化诱导下的宋代志怪小说虚构倾向[J].文艺评论,2014(8):24-28
[9][16] 李晓晖.宋元“说话”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8:66,33
[10] 工商新语:新式唱片[J].上海总商会月报,1923(6):1
[11] 听唱片·喝咖啡:英茵在家庭中每天拿一元零用钱[N].中国艺坛日报,1941-03-26(3)
[12] 散了课女工们麕集在俱乐部室里听留声机,下棋,看壁报[J].文艺画报,1947(1):25
[13] 赖黎捷,方龙,邱鑫.2021年中国有声书市场的用户画像及触媒分析[M]//颜春龙,申启武,牛存有,等.中国音频传媒发展研究报告(202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266-284
[14] 宋兆麟.巫与巫术[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342
[15] 道宣.续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4:158
[17] 王秋利.宋代说话研究:以北宋东京和南宋临安为考察中心[D].开封:河南大学,2009:44
[18] (宋)孟元老著;李士彪注.东京梦华录[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21-22
[19] 汪英.上海广播与社会生活互动机制研究(1927—1937)[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7:86
[20] 曹国东,刘越飞.能动的身体感:移动阅读中的感官书写与身体经验[J].出版发行研究,2022(3):40-46
[21] [美] 安德鲁·斯特拉桑著;王业伟,赵国新译.身体思想[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 :51
[22] 褚传弘.身体漫游、朗读仪式与文化社群:新型城市读书会的地方情感研究[J].阅江学刊,2021(2):108-118+123
[23] 唐灿灿.文化类电视综艺节目的文化复位与价值探索[J].当代电视,2022(8):54-57+109
[24] Sheller M, Urry J. 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6(38):207-226
[25]比达咨询.2023年度中国移动阅读市场研究报告[EB/OL].[2024-03-26].http://www.bigdata-research.cn/content/202403/1249.html
[26] [美] 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37
[27] 王春红. 移动阅读平台中场景理论的应用研究[D].青岛:青岛科技大学,2023:17-25
[28] Ihdh D. Bodies in Technology[M].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6
[29] 李珍.真实的自我与虚拟的身体:元宇宙中虚拟化身的具身性研究[J].自然辩证法通讯,2023(2):19-27
[30] 简予繁,黄玉波.人机交往中“闻声”与“现形”:智能语音助手化身形象呈现对用户听觉意象的补偿与冲突[J].国际新闻界,2022(10):50-73
[31] [法] 梅洛·庞蒂著;杨大春,张尧均译.行为的结构[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78
[32] 杨沉,张家武,黄仲山.全民阅读视角下新媒体阅读生态重构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7(12):86-93
[33] 李桂华.深阅读:概念构建与路径探索[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7(6):50-62
(收稿日期:2023-08-19;修回日期:2024-0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