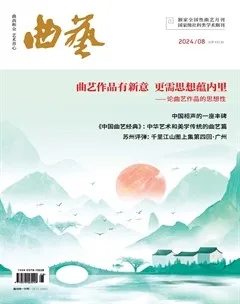“赛博撂地”之我见、我思、我想
相声是起源于民间的艺术,自诞生之初,艺人们便在熙熙攘攘的老北京天桥下与那些杂耍、摔跤、演出戏法的同行一起卖艺,以“撂地画锅”圈出舞台、吸引观众。相声艺人将卖艺时画的圈比作一家老小吃饭的“锅”,“锅”里的人全仗“平地抠饼,对面拿贼”的精湛业务打动过往看客慷慨解囊。这口“锅”既是相声艺人的温饱来源,也是表演舞台。
时移世易,相声演员“锅”的样式也日趋多样,从小到大,从平面到立体,如何不断适应新平台、立足新平台,一直是他们研究的重要课题。
近年来,相当一部分曲艺从业者转战线上,与受众相会“云端”。2023年5月以来,更有相声演员进一步在抖音平台开启相声直播秀,凭借精湛的业务水平和独有的话题性迅速吸引了大量用户的关注和讨论,短短数月间粉丝数量爆涨,多家相声团体和大量个人从业者也顺势而为,相继开立账号加入相声主播的行列。通过直播间表演一段,俨然已成为许多青年相声演员的新玩法,抖音平台上,一场盛大的“赛博撂地”正有声有色地进行着。
我见——机不可失,相声直播正当时
自相声直播被开辟为网络新赛道后,网上就有了各种不同的声音,心平气和讨论者有之,偏激攻讦或支持者亦有之。一种新事物的出现,总会伴随各种不同的讨论声音,这不足为奇。但就笔者个人所见,相声直播、“赛博撂地”应该得到正确的、客观的看待。

从曲艺艺术的发展历史来看,各曲种能传承至今,依靠的正是一代代前辈名家对新事物的接纳与融合。20世纪60年代前后,电台评书造就了万人空巷的火爆场面,东北的评书演员们喊出“要想干,就过电”“广播喇叭一讲,东西南北全响”的口号,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渐普及,相声艺术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大放异彩,经典作品和知名演员不断涌现。由此可见,曲艺艺术紧跟时代齿轮的转动频率,与时代新传媒手段紧密结合,是自身不断发展的有效方式。
从用户数量来看,直播平台也是我们不能轻易放弃的市场。如抖音自2016年上线至今,已相当成熟,日活跃用户高达6亿,是大多数智能手机用户必备的APP。有这样的用户数量作基础,抖音直播的影响力和潜在的群众数量可以想见。目前比较成熟的相声直播团队,近一年来借助抖音直播的势头,积累了大量粉丝,还累计开展了150余场线下巡演。然而粗算他们线下演出服务的观众人次,大剧院单场约1000至1500人次,体育馆单场约2000至5000人次,总计仅15万至25万人次。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们日常直播,单场同时在线人数最高即可达到40万以上,观看人次更是以百万计。
单纯的数字对比不能全面反映线上线下演出的特点,更不能被当作线上直播优于线下演出的“铁证”。但如此直观的数据至少能给广大相声从业者提个醒:有受众的平台才能被称为舞台,以立足舞台、服务受众为目的的相声从业者,不应当忽视直播平台巨大的受众潜力。
我们更加不能忽略的是,直播的出现,为相声艺术带来了全新的审美接受模式和互动形态。网上曾有一段短视频,记录了几位外卖员在等待餐厅出餐的间隙观看相声直播,几分钟后商家出餐了,外卖员便停止观看,出发送餐。生活中像外卖员一样利用碎片时间观看直播的用户不在少数。对于他们来说,随时打开抖音看看喜欢的主播的直播动态、在公屏上打字互动并偶尔打赏,已成为习惯。相声直播就是这一新传播“主河道”的“支流”,可以令许多从未听过相声,甚至从未关注过相声的新媒体用户,成为相声爱好者,进而走进剧场,无形中为相声艺术开疆拓土。
我思——南橘北枳,直播间里大不同
相声在直播平台的发展,需要所有相声从业者共同努力。当前已有大量青年演员旋步接踵,在新媒体平台开立账号,迅速了解、学习、尝试,希望抓住机会重现电台评书、电视相声的辉煌。但据笔者观察,由于缺乏经验,目前许多新晋相声主播都没能充分发挥直播的功能,他们或在剧场演出时直接架起手机“假直播”,或缺乏策划,对直播节目不选择、不改编,此外还有大量违反平台规则、不适应直播模式的情况。这样的“问题直播间”恐怕会对相声的发展带来“逆向效应”,对于演员团队和线下演出的宣传作用都非常有限,更难以收获预期的打赏收入。
(一)作品选择与改编
无论何时,作品都是曲艺工作者的立身之本,也是决定观众关注度的核心要素。以网络为底层架构的直播平台极大地消除了时间、空间等方面的限制,让“剧场空间”容量爆发式增长的同时,也对相关表演者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受众的年龄层次、文化水平、兴趣爱好等十分多元,加上平台本身还有许多词汇上的监测和限制,所以相关表演者在直播间里表演的相声作品不仅要适合大多数观众的共同欣赏偏好,还要符合平台的监管标准。
以相声《大上寿》为例,传统版本当中涉及大量对男女关系的暗示,显然不适合公开直播表演。部分相声演员对其进行改变,有的弱化男女关系,将包袱集中在其他情节上;有的则将整个作品改编为以“柳活”见长的节目,大部分包袱出在“歪唱”中。这些版本的《大上寿》经直播间与观众见面后,获得了较为广泛的称赞。
其实不仅是《大上寿》,许多相声的传统版本由于创作年代的局限性,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糟粕,如有的伦理哏过多,有的表现出对残疾人士的讽刺。也正因为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侯宝林等老一辈相声艺术家顺势而行、主动作为,发起成立了“相声改进小组”,把说“文明相声”作为创、编、演的重点之一。而当前立身于直播平台的众多相声演员对作品“品控”的严格把关,实际上是与老先生的倡导一脉相承,是自觉遵守艺风艺德的规定动作。他们对难以适应直播的作品,要么不演,要么必须提前改编。同时,抖音等的直播平台还会使用AI监测主播内容中是否涉及迷信、烟酒、暴力、医学术语、特殊功效等限制词汇,一旦触及,会立刻限制直播间流量,严重的还会当场强制关播。
因此,每一次相声直播,相声演员都需要慎重选择作品,在确保不触及平台监管红线的同时,更要兼顾作品的演出效果。此外想要长期稳定开播,相声演员还要避免节目重复的问题,这对演员的创作能力、作品储备和现场把控都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
(二)剧场与直播分离
笔者观察到,目前有些相声团体在剧场演出时直接就架起手机进行“直播”。表面上看,这样做似乎效率很高,一场演出满足了线上和线下两个观众群体的需求;但实际上,这种类似传统电视节目式的“直播”,并不能真正有效地利用直播平台的各项功能,也无益于主播与粉丝群体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而只能被看作是“假直播”。
晏子讲“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即使是同一物种,生长在不同环境中,也会发生变异。同样是说相声,剧场表演与网络直播是两种不同形态的演出。想把相声直播做好,相声演员一定要有专门的直播间,即使条件有限,只能使用剧场的舞台,至少要将剧场演出与直播分开进行。因为相声演员在剧场表演时面对的是现场观众,在相声直播时则是线上观众,如果硬要架起手机将两者混在一起做,则一方面使购票观演的现场观众心理失衡,另一方面也很难照顾好线上观众的互动热情,可谓两头不讨好。只有在剧场演出时专心关注现场观众的反馈,直播时专注应对线上观众的互动,才有可能让两者都取得理想的效果,才能进一步讨论线上线下联动的可能性。
而且,各种直播平台以手机为主要载体,为配合用户使用手机的一般习惯,无论视频还是直播都以竖屏模式为主。但相声是舞台艺术,长期以来适应着观众的观演习惯,舞台调度往往以左右横向居多。如今相声要与直播融合,就势必要适应新的“舞台调度”。手机屏幕的左右空间有限,只能容纳两位核心演员并肩出现在画面中,场面桌都只能露出半个。舞台形态的改变对相声主播提出了新的挑战,例如,他们熟悉的横向舞台调度几乎完全失效,需及时将横向调度调整为前后调度,即利用景深实现视觉效果,这也是另一个必须将剧场演出和直播分开的原因。
(三)重视粉丝互动
为提升用户的参与感,直播平台开发了大量促进粉丝与主播互动的功能,而相声演员群体则非常需要及时得到观众对节目的感受和评价,并据此调整作品。从这个角度来看,网络直播重视用户互动与反馈的特质与相声演员的创演需求不谋而合。对于新晋相声主播来说,尽快适应直播平台的强互动性,不仅有助于直播间的流量,还能带来业务能力的快速提升。以抖音为例,目前的互动主要包括两种:直播公屏互动和其他日常互动。
直播中最核心、最重要的互动就是实时反馈的公屏,在线人数和礼物数等数据可以直观体现直播的效果。一般来看,公屏数量暴增,意味着直播间内容获得大量观众的喜爱,抖音会据此将直播推送给更多用户,更多关注和打赏也成为了可能。公屏的内容就更值得研究了,相对剧场观众的笑声和掌声来说,公屏文字能够更加具体、明确地反馈观众的感受和建议,许多公屏直接就可以作为再创作的要点。当然,知易行难,直播中演员一边需要在没有现场观众的情况下全凭心理节奏完成节目,一边还要眼观六路,随时关注直播数据和公屏反馈,对业务能力和即时反应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同时,相声演员要进一步拉近与观众的心理距离,节目之外的日常互动也不容忽视。当前相声直播的头部演员在每场直播中都会单独安排一段“聊天时间”,用于分享生活趣事、预告巡演日程、回答观众提问等,还形成了一个固定环节“神回复”,直面水军自媒体的恶评,引导自己的粉丝群体理性发声,并数次维护同行前辈、反对网络暴力,这一举动使他收获了许多“路人粉”,网友纷纷称赞其大格局。除了直播中的即时互动,日常短视频也是向大众展现自己的重要渠道,类型演员每到一地巡演,都会宣传当地文旅、拜访同行剧场、安排美食探店、分享后台趣事,其团队成员也经常通过vlog分享生活,这些短视频向粉丝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亲切的相声演员,也是对其相声直播的一个重要的辅助。
我想——拥抱变化,主动探索新发展
相声艺术发展至今天,其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已被历史证明。借助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介,相声演员不断探索新的表演形式,推动相声艺术不断向前发展。可以说,一部相声发展史,就是相声演员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历史。当前,相声演员“借船”驶出传统表演形式的“黄海”,逐步驶向相声直播的“蓝海”。如何在这条新赛道上走出一个“通天大道宽又阔”,是每一个相声演员都应该适时思考的问题。
首先是专人做专事。如前所述,线上线下的舞台不同,观众容量、需求也不同,需要相声演员有的放矢、不断开发新作品,也需要专人专用,组建、打造熟谙相声艺术、熟悉网络特点的专业团队,各司其职,将技术、场景、运营和商务等业务做得更精细。
其次是探索相声直播赋能的有效路径,开拓更加立体的发展模式。比如将直播作为导流的手段,平衡不同舞台的受众数量,激发各类表演场所的市场活力,推动相声艺术综合发展。比如可以深入探索线上PK、电商带货变现渠道,不断拓宽相声行业在互联网时代发展的新出路。
最后是尊重直播平台的运作模式。在国家强化网络监管的大背景下,直播平台也在运用各种手段——与监管部门加强合作,大力开发互联网直播内容筛选软件,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动态抓取、分析主播行为和直播内容,倒逼着主播们讲尺度、守规矩,当然也给相声主播画出了“写字”的“字框”。平台的严监管态势在客观上呼应了近些年来中国文联、中国曲协对行风建设的倡议。相声主播们或许可以在直播平台上展示新时代相声从业者的精神风貌,在逐步扭转某些对曲艺界消极印象的同时,更能推动文明相声、健康相声在新时代的新发展。
(责任编辑/马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