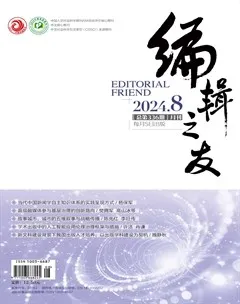媒介融合语境下数据出版知识空间建构研究
【摘要】随着媒介融合的深度发展和智慧技术的持续更迭,以知识为核心生产要素的数据出版朝着知识空间的方向发展。文章围绕数据出版知识空间的建构展开分析,指出在媒介融合语境下数据出版的服务化转型势在必行,服务导向成为数据出版知识空间建构的核心要义。从智慧时代媒介发展趋势和媒介空间性的角度来看,数据出版知识空间的突出特征体现在人媒共生性和空间复合性上。数据出版知识空间建构所遵循的逻辑底色是基于趣缘关系形成的社群。数据出版知识空间的价值通过面向用户需求的情境化知识服务实现,对应用场景的识别与适应、对用户需求的分析与管理、对情感状态的捕捉与计算,都是情境化知识服务的表现形式。从长远来看,媒介融合语境下的数据出版知识空间是一个基于价值共创的泛在空间。人们以趣缘关系为基础,围绕不同主题的内容形成新的社会关系,共同构成虚拟与现实交融、人与媒介共生、知识获取与价值创造并行的智慧生存空间。
【关键词】媒介融合 智慧技术 数据出版 知识服务 知识空间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4)8-054-06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4.8.007
媒介是文明的标志,也是知识的载体和形态。人类的媒介进程既是文明演进的历程,也是人类知识生产和知识消费的历程。随着以算法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突破与发展,整个传媒生态正在发生根本性变革。新的传媒生态深刻影响着事物被感知的方式以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媒介融合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大背景下,数字出版产业也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如何借力媒介融合发展数字出版产业,成为世界各国出版行业日益重视的问题。当下,融合已成为出版业发展的共识、热点及方向,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成为实现我国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对于出版业来说,媒介融合不单单是技术应用、形式创新与业务整合,其本质是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知识产品形态的融合以及知识传播机制的范式转变。在智慧技术的驱动下,以知识为核心生产要素的出版业正经历知识数据化的发展过程,出版业将迎来从数字出版向数据出版的转型升级。
与此同时,在5G、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元宇宙等新技术的赋能下,出版业不断创新内容生产模式与呈现形式,拓展传播渠道,出版的空间转向趋势明显。因此,将出版实践活动放在空间维度进行具体分析,对于出版学科研究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出版空间中交织着真实与虚拟化的符号和景观,承载着大众的自我意识、个性表达方式与心理需求,也在无形中建构着新型的社会关系、文化娱乐方式、新的身份认同方式与新的意识形态。因此,数据出版知识空间的建构问题成为媒介融合语境下出版业转型发展过程中需要予以关切和探索的重要议题。
一、服务化:媒介融合语境下数据出版知识空间的核心要义
从现阶段出版行业转型发展路径看,智慧技术在出版产业链中的应用是基于产业发展惯性而附着在原有出版模式之上的,而非颠覆性的产业业态革新。虽然此种路径依赖的方式更易于新技术的嵌入与渗透,并让出版机构在短期内通过低成本运营和小幅度创新保持稳定发展。但从长远来看,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弱化和限制技术的赋能力以及出版行业的持续发展动力。一直以来,出版行业遵循的是基于图书等有形产品的商品主导逻辑。但从行业划分看,出版业是一种知识服务业,属于服务业的一种。未来,随着产品形态的丰富以及读者互动性的加强,出版行业的服务属性将逐渐凸显。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出版行业如何通过产品和服务满足读者用户的信息和文化需求?如何构建基于出版机构、作者、读者与机器之间关系的虚实融合的生存空间?这都是出版业需要深入探讨的话题。
当前,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过渡和转型。在生产型社会中,消费从属于生产,仅作为整个社会生产活动中的一个环节而存在,消费最终由生产决定。而在让·鲍德里亚所提出的消费社会中,消费不再表现为一种单纯的物质资料的占有,而是转向一种社会关系的主动建构。这种社会关系指的是人与物、人与人、人与集体、人与世界间相互联系所构成的整个社会体系。
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社会转型相适应的,是商品主导逻辑向服务主导逻辑的转化。2004年,斯蒂芬·瓦戈和罗伯特·鲁什两位学者提出一种新的经济交换逻辑——服务主导逻辑。服务主导逻辑的核心是无形服务、交换过程以及关系营销。服务主导逻辑把消费者纳入价值链条中,生产者在通过商品向消费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与消费者产生互动并共同创造价值。从服务主导逻辑入手,重视消费端在内容生产、文化传播与价值创造中的地位和作用,从多元主体协同、虚实环境融合的角度探寻基于价值共创的泛在出版空间的构建,是媒介融合语境下打造全新出版业态的一种有效思路。在当前媒介融合背景下,数据出版的服务化转型势在必行,服务导向成为数据出版知识空间建构的核心要义。
二、数据出版知识空间的总体特征:人媒共生性与空间复合性
智慧技术的发展引发媒介与人类关系的重塑,也让媒介空间在虚拟与现实的交织中得到进一步延展。总体来说,从智慧时代媒介发展趋势和媒介空间性角度看,媒介融合语境下数据出版空间的突出特征体现在人媒共生性和空间复合性上。
首先,人媒共生性强调的是人与媒介从相互弥补和依存走向一体共生。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是人的延伸”将媒介看作人类与外部世界产生接触和关联的中介,认为媒介是人类感官系统的延伸。美国媒介理论家保罗·莱文森则认为,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相较于以往的媒介,都具有功能上的补偿性,媒介进化的过程是人类根据自身需求不断选择的结果。从本质上讲,补偿性媒介理论体现了人与媒介的互补关系。随着媒介技术的进化升级,媒介融合不仅体现为媒介形式的融合,更重要的是人类与媒介在交互和连接的过程中相互渗透和影响,最终走向一体、人媒共生。一方面,人与媒介有了共同决策权。随着智慧技术的介入和人机交互的深化,媒介对人类需求的理解能力逐渐增强,媒介在对内容进行组织、创作和传播的过程中拥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主决策权,在人类接收信息、思考问题和创造价值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参考、论证和引导作用。可以说,未来社会的发展是人类与媒介协同共进的结果。另一方面,人与媒介具备了更强的身心嵌入性。智慧时代媒介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人类感官的全面沉浸。未来,随着脑机接口、生物芯片等新型技术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人类与媒介在身体和心理层面的契合度会进一步提升,人脑与人工智能在多层次上相互连接、相互赋能,最终形成人与媒介深度融合的智慧综合体。
其次,空间复合性强调的是智慧时代的媒介空间从单纯的网络空间转向集物理空间、意义空间与社会空间于一体的复合空间。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人文社科领域空间转向思潮的兴起,空间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视角。法国著名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提出空间生产理论。他将空间划分为物理、精神和社会三种形式,赋予传统意义上的基于物质性的物理空间精神属性和社会属性,认为空间是意识形态与社会关系的产物,空间生产是一种社会性的实践活动,社会空间是一种“由社会生产,同时也生产社会的空间”。[1]其后,爱德华·W.索亚又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进一步提出“第三空间”理论,“第三空间”是既区别于真实和想象、又包容并超越真实和想象的他者化的空间。空间理论研究为探索数据出版知识空间的建构方式提供了理论依据。加拿大传播学者哈罗德·亚当斯·伊尼斯将空间视角引入媒介研究领域,认为媒介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属性。麦克卢汉对伊尼斯的观点进行了延伸,认为媒介技术的发展将带来社会的“内爆”。“内爆”一方面指时间与空间概念的模糊,信息的传递打破了时空的阻隔;另一方面指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间界限的模糊。综合空间理论以及媒介研究中的空间认知可以得出,智慧时代的媒介空间是物理空间、意义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综合体,是人类社会个体存在、符号生产和关系建构的场域,是开放流动、包容万物、虚拟与现实互融、真实与想象并存、个人与公共领域交织的复合式空间。
三、数据出版知识空间的建构逻辑:基于趣缘关系的社群化知识共享
基于趣缘关系形成的社群是数据出版知识空间中多元主体参与价值共创的基本单位,依托同一兴趣爱好展开交互与分享,成为智慧时代一种重要的文化表征。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在其文化美学研究中提出了“区隔”这一概念,并且关注到趣味与社会区隔之间的联系,他认为,消费者的社会等级与社会认可的艺术等级相符,并在每种艺术内部,与社会认可的体裁、流派或时代的等级相符。这就使趣味预先作为等级的特别标志而起作用。文化的获得方式在使用所获文化的方式中继续存在着。[2]借用布尔迪厄的理论,不同的阶层会因趣味的不同而形成具有一定集体性和普遍性的特定趣味空间,个体的文化参与实践是由其所处的阶层决定的,趣味在个体的社会阶层归属划分上起到重要作用,也影响着各层级人群的媒介使用与文化消费惯习。这为数据出版知识空间以因趣缘而区隔的社群为切入点提供了理论基础。具有相近知识水平、阅读偏好和价值取向的读者聚集在同一社群空间中,开展获取信息、分享知识、交流思想等多种形式的文化实践。
在数据出版知识空间的社群关系维系上,要注重建立价值认同与人际信任。影响阅读共同体中个体情感黏性的重要变量是价值观的契合度,阅读者是否具有相对一致的价值取向,是内容能否引发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的关键,也是群体中的个体进行精神文化层面的社会交往并建立人际信任的前提。而人际信任的建立将促进该共同体内信息的流动、延展与裂变,从而形成共享式文化样态。因此,出版机构在进行社群阅读空间构建时,要充分整合与利用知识、创意、人际关系、文化圈层等操纵性资源,力求内容与社群的精准匹配,限定内容组织标准与圈层准入门槛,促进内容价值的持续释放与社群文化的良性发展。
此外,在数据出版知识空间的社群关系维系上,还要关注社群内部差序结构以及外部分众差异。在社群内部,不同个体间由于性格、身份、学识、动机等差异,在社群中的贡献度和参与度也有所区别,分别扮演管理者、领导者、追随者、执行者、贡献者、连接者等角色,从而形成社群内部的用户差序结构。传统意义上的社区是角色分明、层级固化的扁平化结构,伴随着人们在文化参与中便捷性和实时性的提升,价值共创模式下的社群成员受情境、个性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形成相对松散又相互连接的多个子群,各个子群间关联性、交互性和流动性较强。按照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符号消费具有表征性,人们通过消费来彰显个人品位和建构社会身份。“现代消费社会的本质,即在于差异的建构。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客体的物质性,而是差异。”[3]因此,数据出版知识空间社群的构建除了要关注社群内成员之间的个体差异,更要注重不同社群之间的差异性,通过对用户数据的精细化分析,向社群投放符合该圈层生活方式的主题内容,从而不断吸引和聚集处于该圈层和向往进入该圈层的用户,使整个社会形成一个个具有高辨识度、高凝聚力和高生产力的文化社群。
在数据出版知识空间的社群关系维系上,要注意用户的权益保障和利益均衡。在一个群体内部,群体行为包括三种形式:共享、合作和集体行动。从价值共创的角度来说,集体行动是最具难度的一种形式,社群内的成员需制定一致的目标,采取统一的行动,形成共同的决议,并对全体成员具有约束力。在社群内部促成集体行动、广泛激励用户创造价值的关键在于构建起公平、公正的权益保护体系和利益分配机制,尊重全体贡献者的智慧成果,从而为价值共创提供持久的内生动力。
四、数据出版知识空间的价值实现:面向用户需求的情境化知识服务
伴随智慧技术的持续赋能,出版业的知识服务功能进一步放大。从知识内容的生产、传播到消费都将以用户需求为中心,以产品的可供性和情境的适配度为衡量标准,形成技术、知识、场景与用户有效连接的服务生态。
1. 面向时空、行为与心理的自适应场景识别
在数据出版知识空间中,知识服务以用户为中心首先体现在对用户场景体验的关注上。出版产品的设计要以场景为驱动,数据出版赋予场景新的内涵。数据出版模式下的场景是由用户状态、使用场景共同构成的。用户状态包括用户在阅读前、阅读中以及阅读后的行为状态、心理状态等个体特征。使用场景包括用户的使用时间、使用场所、共同在场人、连接设备等环境特征。对场景的识别与适应是出版产品与用户产生有效连接并带来优质知识服务和用户体验的关键环节。
相较于传统出版,数据出版知识空间中的场景识别面临更为复杂和多变的局面。在传统出版模式下,读者的场景信息较为简单和粗放,出版机构只能通过读者购买及阅读后在各种渠道反馈的信息了解读者的状态和感想,而读者使用场景的具体信息相对难以获取或未加以利用,无法在出版活动中发挥其应有的价值。而在数据出版知识空间中,从媒介可供性视角看,数据出版具有生产可供性,即用户在一定范围内可对内容进行编辑、审阅、复制、关联。其用户的可参与性和用户信息的可数据化,使得场景信息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潜在价值。用户在智慧技术所营造的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空间中,可以随着剧情的发展,通过肢体动作、语言和情绪表达等多种方式,与出版产品中的人、物、机器进行实时交互。而数据出版的移动可供性,即可携带、可获取、可定位和可兼容的特点,大大提升了用户调用和编辑知识信息的频度和广度,使用户的使用场景更加丰富。这些场景信息呈现出大体量、分散化、个性化的特点,需要出版机构及时捕捉和收集,进行数据化的处理与分析,并从中发现内容、用户、场景间的关联特征和规律,从而反哺和支撑出版产品的设计、创作和分发。
借助智慧技术识别用户阅读场景、分析用户阅读惯习,是提高出版知识服务精准度的基础。在进行场景识别时,首先,需尽可能细化场景粒度,不仅要关注某个用户群体和用户个人的总体状态,更要关注用户对不同类型产品、不同故事情节的反馈情况,把握在整个阅读过程中以及阅读前后用户的状态和行为变化,通过细节上的体察和比对,精准把握用户需求的特征和差异。其次,要对各个场景要素进行关联分析,例如可以提取出某个用户在某个时间段的常去地点和常用设备,分析与不同的共同在场人进行阅读活动时的不同阅读类型和情绪特征,不同场景要素的交叉碰撞更有助于用户需求的精准匹配。最后,要能够预判隐性需求,可基于日常生活轨迹和阅读行为活动进行数据建模,挖掘和推测用户未被满足的潜在知识内容需求,进而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以适当的形式向用户推送有价值的内容和服务。
2. 基于个体特征与需求的成长型知识管理
随着用户获取知识渠道的日益多元以及消费需求的逐步分化,标准化和大众化的知识服务方式逐渐不能适应用户的需求。作为知识密集型的出版产业,服务的概念被不断强化,出版从单纯的内容供应升级成知识服务。而智慧技术的充分赋能,让每一个体的知识需求显性化,这就为粗线条、普适型的知识服务转向个性化、成长型的知识管理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走向基于个体需求的成长型知识管理,是数据出版知识空间中消费方式向服务化转型的突出体现和有效路径。
首先,数据出版知识空间中的知识服务要适配个体认知惯习。智慧技术之所以被称为“智慧”,一方面体现在智慧技术具有全自动的自学习和自组织能力,且能够全智能地适应、调整、影响和选择环境。因此,数据出版知识空间中的知识服务要基于用户个体信息、认知水平、学习习惯以及实时状态等相关数据,进行科学、综合地分析与预判,从而为用户匹配、调用和组织个性化的学习方案。同时帮助用户查漏补缺,引导用户不断突破自我,获得进阶提升,为用户打造和规划符合甚至高于其预期的系统化、分阶段的成长路径。另一方面,“智慧”体现为机器对人类思维和表达的超强学习与模拟能力。认知智能被认为是人工智能发展的高级阶段。机器认知智能的实现依赖于知识图谱技术,其核心就是让机器具备理解和解释能力。认知智能使得机器具备基本的知识理解、逻辑推理和自主学习能力,并能够用人类易于理解的自然语言方式进行表达。[4]因此,数据出版知识空间通过智慧技术与用户的不断磨合,产出更加符合用户个体需求和特征的高价值信息。ChatGPT在用户的持续使用和反馈过程中,可以根据用户的个人信息以及所处的任务情境,不断细化和调整回复方式及内容,直到为用户提供满意的、更易于接受的知识内容与解决方案。
其次,数据出版知识空间的知识服务要关注用户交互模式。随着媒介融合的发展和智慧技术的进阶,知识服务在保证知识准确和有效传递的基础上,需从交互体验的便利性和自然性方面展开探索,充分利用多模态技术,突破语言和文字的限制,将用户个体的眼动、手势、语气、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等作为交互的触发方式进行精准捕捉。融合式的交互模式能让机器更加细腻地感知用户的根本需求和真实反馈,便于机器更准确地分析用户特点,描绘用户画像,从而提供更加个性化的知识服务。同时,利用人类在获取知识过程中所产生的语言、文字、行为和心理等全方位数据,持续对机器进行喂养,是训练和提升机器模拟人类思维能力的有效方式。机器能以更加拟人化的语言和更加符合人类信息接收习惯的方式与人类进行交流,更好地促进知识与文化的有效传播。而脑机接口、静默交流等技术的实现将从根本上变革人类与机器的交互模式,人类将借助智慧技术与外部世界产生更全面而深刻的物理连接。在未来,知识服务的概念可能面临消解,演进为人类与机器共生环境下公共知识空间与私有化知识领域的叠加和交织。数据出版知识空间的知识服务也要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交互模式的革新,思考知识的生产、沉淀与传承,发挥人类在知识创造、规则设定、知识管理等方面的主体作用。
3. 情感计算驱动下的主动式精神陪伴
互联网的崛起和普及为人们情感的释放和宣泄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畅通的出口,情感成为媒介发展中的重要元素。美国学者罗莎琳德·皮卡德在1997年提出了“情感计算”的概念,认为“情感计算就是针对人类的外在表现,能够进行测量和分析并能对情感施加影响的计算”。[5]情感计算主要是让机器能够准确捕捉和深刻理解人类丰富的情感表达与情绪变化,从而以更加契合的方式达成人机交互。多模态的融合算法可以智能接收、监测和处理多元化的情感信息,包括文字、语言、语气、语调、语速、表情、眼动、手势、动作、心率、血压、脑波等。经过对情感信息的综合分析之后,机器可以对人类的情感状态进行推断,从而进一步合成并输出符合用户心理特征、带有情感倾向、具有不同风格的语音、表情和动作组合。机器通过识别、理解和学习的过程,逐步模拟人类的沟通与表达方式,以更加自然、细腻和亲切的形式,与人类建立情感层面的连接。情感计算的介入充分借助其计算优势,赋予机器更加鲜明的人格化特征,让人类与机器的交流更有深度和温度,弥补了机器在反馈与表达时过于机械化和程式化的不足。情感计算使机器具备了超强的情感体察与共情能力,为营造和谐的人机共生生态奠定了基础,也为知识服务拓展更高质量的服务内容和形式创造了可能。
情感元素的融入是数据出版向服务化转型的重要体现,意味着出版行业从单纯提供信息内容向提供全方位精神陪伴进阶,人们的幸福感提升。对于出版业而言,作为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在提供精神与情感陪伴方面拥有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内容资源优势。出版机构可以借助情感计算,深入理解用户个性化、实时化的文化需求与情感需要,适时组织、匹配和推送短小精练或系统深刻的多模态内容。而产品富有感情的表达方式,能更直接、有力地触达用户内心世界,并进一步放大阅读内容本身所带来的愉悦、疗愈、减压、振奋、满足等作用。
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的类人化发展趋势以及自主意识的生成,以往的社会交往秩序被重塑,在数据出版知识服务提供精神陪伴的同时,需注意防范人类主体性的缺失以及机器不良诱导行为的发生。人类在“主我”与外界的交往中通过不断内化对“客我”的评价,逐渐完成自我的形塑和价值观的形成。随着人工智能对社会生活的深入渗透,人类在对机器进行拟人化训练的同时,也必然会在无形中吸收和内化机器对人类的反馈与评价。人与机器的关系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转变为相互影响和作用的主体间性关系。这就可能导致机器模仿人类的同时,人类也越来越趋同于机器,呈现社会交往工具理性化的特点,即重视逻辑与规则而忽视情感与主观意识。这进一步论证了情感计算的重要意义,提示出版机构在情感陪伴的过程中要不断细化情感计算的粒度,尽可能全面地捕捉各种充满跳跃性和不确定性的情感与心理变化。与此同时,也需注意情感陪伴的尺度,避免造成情感依赖的心理问题、有悖伦理的失范行为以及危害生命的危险行为。据报道,一位比利时男子由于焦虑而寻求智能聊天机器人艾丽莎的帮助,但在与机器人深度交流六周后,该男子在其诱导下选择结束生命。因此,未来在借助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社会的同时,要重视社会交往秩序与伦理框架的构建,确保人工智能的可塑性与可控性并行。
五、数据出版知识空间的未来走向:基于价值共创的泛在空间
总体来说,媒介融合语境下的数据出版知识空间是一个基于价值共创的泛在空间。数据出版知识空间以泛在网络为基础,以内容为连接点,依托智慧技术让虚拟与现实世界中的人与物产生广泛而紧密的联系,从而形塑自我、建构社会、创造价值。数据出版知识空间的泛在性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网络连接泛在。具体是指自然人、数字人、实体物品、虚拟物品、物理空间、虚拟场景等都处于一种实时互联、无缝衔接的状态,空间中的各个主体可以通过泛在网络实现动态、连续的信息传递与交互,而整个信息传播、接收、决策和行为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会被记录和分析。二是知识资源泛在。根据价值共创理论,价值创造的前提和基础是对知识、技能、经验、智慧等操作性资源进行充分整合,形成具有延展性和关联性的知识资源体系。三是实践活动泛在。数据出版知识空间的价值创造是在个体、社群或不同的社会力量开展的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文化参与和价值博弈。四是嵌入智能泛在。数据出版知识空间中知识的生成与传播是在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智慧技术进行需求理解、情境感知、数据分析、知识组织的基础上完成的。数据出版知识空间中所创造的价值是人类智慧与机器智慧协作的成果。五是反馈控制泛在。数据出版知识空间中各个要素可交互的特点,对泛在空间反馈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可控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从人的主体性角度出发,在规则设定上对人工智能的全面监管与控制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六是服务系统泛在。在价值共创理论视角下,数据出版知识空间的服务生态系统构建至关重要,要将数据出版知识空间中的价值创造主体,如自然人作者、虚拟作者、编辑、数字人、出版机构等,在整个社会结构中进行延展和关联,借助智慧技术的赋能和规则机制的构建,整合多元异质资源,满足多元主体需求,形成利益增值循环,从而实现泛在的共建、共享与共创。
参考文献:
[1] 陆扬,王毅. 文化研究导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359.
[2] 皮埃尔·布尔迪厄. 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上册)[M]. 刘晖,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
[3] 让·鲍得里亚. 消费社会[M]. 刘成富,全志钢,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9.
[4] 易龙. 从数字出版到智能出版:知识封装方式的演进[J]. 出版科学,2023(1):81-90.
[5] 罗莎琳德·皮卡德. 情感计算[M]. 罗森林,译.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62.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Space in Data Publishing in the Context of Media Convergence
GUO Jia(Digital Review Center of Editorial Office, WANFANG DATA, Beij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ep development of media convergence and the continuous change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data publishing with knowledge as the core production element is developing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knowledge spac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data publishing knowledge space, and proposes that in the media convergence environment, the service transformation of data publishing is imperative, and service orientation becomes the core ess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data publishing knowledge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edia development trend and media space in the intelligent era, the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of data publishing knowledge space are reflected in the symbiosis between human, media and the spatial complexity. The logical structur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data publishing knowledge space is the community formed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of interest. The value of data publishing knowledge space is realized through the situational knowledge service for user needs. The identification and adaptation of application scenarios, the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of user needs, and the capture and calculation of emotional states are all the manifestations of situational knowledge service. In the long run, the data publishing knowledge space in the context of media convergence is a ubiquitous space based on value co-creation. People form new social relationships around different topics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of interest, and form a smart living space where virtual and reality blend, where human and media symbiosis,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value creation go hand in hand.
Key words: media convergence; intelligent technology; data publishing; knowledge service; knowledge space
(责任编辑:武)
作者信息:郭嘉(1986— ),女,山东济南人,博士,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编审办公室数字审读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数字出版、文化创意与文化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