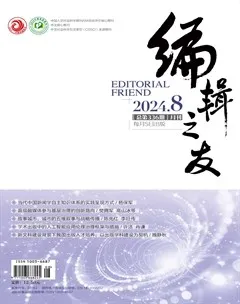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呈现方式
【摘要】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实践指向,决定了自主知识体系必然要呈现在实践领域。文章认为,实践呈现方式是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呈现的重要方式之一,且具有终极呈现的意义。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呈现方式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呈现或体现于国家层面的新闻路线、方针、政策中;呈现或实现于国家层面的新闻制度规范中;呈现或体现于所有新闻实践主体的新闻实践观念中;呈现或实现于所有新闻活动主体直接感性的新闻实践活动中。
【关键词】当代中国新闻学 自主知识体系 实践呈现方式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4)8-005-09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4.8.001
知识源于实践,又回到实践。知识在形式表现上是一种话语,但不限于学术话语,或者说,知识话语、学术话语会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呈现出来。“人类不仅在他们的言语和文本、他们的话语和著作中,而且在制度、实践、技术和他们生产的对象中曾‘想说’什么”。[1]知识的目的不限于知识范围,不限于解释世界,更在于追求知识的实践目标,实现改造世界的目的。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实践指向,是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业建设服务,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服务,因而,自主知识体系必然要体现或实现于国家层面的新闻路线、方针、政策中,体现于国家层面的新闻制度规范中(也即制度实践中),体现于新闻实践观念中,更会直接呈现或实现于感性的新闻实践活动中。本文就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呈现方式展开比较系统的论述,至于自主知识体系的其他呈现方式,笔者将另文专论。
一、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新闻路线、方针、政策呈现方式
当代中国新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是党和政府作为领导主体构建的自主知识体系,[2]是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业乃至整体现代化事业服务的知识体系。也就是说,知识体系构建的目标并不是构建纯粹的理论知识体系、学术体系,它会通过一定的中介方式转换为指导、规制、约束新闻活动的路线方针和制度规范。这意味着,自主的知识体系必然会体现在党和政府关于新闻领域、新闻事业的相关路线、方针、政策中,体现在各种相关法律、行政管理、伦理道德、新闻舆论工作的纪律规范中。这实际上也是体现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产生实际社会作用的重要途径。下面,我们先来讨论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新闻路线、方针、政策呈现方式。
党和国家用来指导新闻舆论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可以看作当代中国社会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软制度”或“软规范”,它们实际上构成了新闻舆论工作领域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精神灵魂,支配着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立场,决定着新闻舆论工作的价值定位,指导着新闻舆论工作的总体方向与目标。依据我们讨论的议题,这里的主要问题是:在知识论视野中,新闻舆论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是从哪里来的?制定或确立它们的根据是什么?问题的实质是:新闻舆论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等与新闻学知识生产、知识体系有着怎样的内在关系?
新闻舆论工作路线、方针、政策等的制定与确立,需要诸多的依据和条件,一定的组织机构保障和诸多的程序与环节,①但这不是我们此处要讨论的重点问题。我们想指出的是,在所有制定和确立新闻舆论工作路线、方针、政策的依据和条件中,最基本的依据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实际情况,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业的实际情况,即最重要的根据是新闻舆论工作的实际情况,以及党、国家和人民群众对新闻舆论工作的期望和需要。客观实际与主观愿望的统一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总体依据。也就是说,只有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党、国家和人民群众对新闻舆论工作期望和需要的路线、方针、政策,才有可能科学合理地指导和引导新闻舆论实践的优良运行和发展。但进一步的也是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怎样才能了解和把握实际情况,如何才能了解党、政府与人民的合理愿望与需要,这也正是探讨新闻知识生产、知识体系呈现的关键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业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党和国家对新闻舆论工作的期望和需要是什么,都是需要进行科学研究和实际考察的基础问题。也就是说,对实际情况、实际需要的把握,有赖于新闻认识活动、学术研究活动。对新闻舆论活动实际表现、基本特征、内在规律的探索和揭示正是新闻研究的任务,也是新闻学知识生产和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说新闻舆论工作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有赖于实际情况,直接意义上就是有赖于新闻学研究形成的科学认识成果,有赖于新闻学形成的正确知识体系。当然,新闻学知识体系不会直接也不会整体转化为新闻舆论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但知识体系却会以整体方式为新闻舆论工作路线、方针、政策的设计与制定提供知识支持。也就是说,知识体系经过一定的中介化方式,②会呈现、蕴藏在党和国家关于新闻事业、新闻舆论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可见新闻知识生产、知识体系构建对于社会新闻活动、新闻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当前形势下,党和国家要制定出能够适应当前数字环境、智能环境中新闻舆论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须高度重视学术共同体的建设,积极支持引导科研队伍展开探索和研究,且要特别重视国内外学术界对新现象、新事物、新实践的研究成果,采取有效措施和方法将相关优秀成果吸纳、转化、体现在新闻舆论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党和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在当今知识时代,信息化、媒介化社会中,新闻传播学研究(当然不限于新闻传播学研究)对于科学合理的新闻舆论工作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进一步说,党和国家对新闻舆论工作的功能作用、意义价值总是拥有自身的特别期望与需要,但需注意的是,不能仅仅凭借自身的愿望和理想去制定路线、方针、政策,而是要尊重新闻工作、新闻舆论工作的特征和规律,③即路线、方针、政策只有建立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业实际发展情况的基础上,建立在新的媒介环境、新闻生态变革发展的基础上,其需要才可能是合理的,期望也才有可能实现。从知识论角度说,就是要求党和国家尊重新闻认识形成的认识成果,将认识成果反映和体现在新闻舆论工作路线、方针、政策中,这样才能真正体现新闻学研究的实践意义和价值。如果新闻学研究成果、形成的知识体系,仅仅是解释新闻现象的思想体系、理论体系,不被党和国家所重视和运用,那新闻学研究就真的成了学者们的“自娱自乐”。认识的价值不仅在于说明世界、解释世界,更在于改善世界、改变世界。对此,马克思早就有过精彩的论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
从理论上说,新闻舆论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只有达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也就是既符合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又能满足党和政府的需要与愿望,才能说路线、方针和政策是科学的、合理的、可行的。优良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有效实现,需要一定的中介手段,对中介手段的探寻同样需要新闻学的探索和研究。由此可见,合理、可行的新闻舆论工作路线、方针、政策的设计与制定,必须以新闻学的知识体系为基础。反过来说,新闻学的知识体系在宏观层面上就呈现或实现于指导新闻舆论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之中。事实上,知识生产、理论研究往往并不是直接指导具体的新闻生产活动、新闻舆论工作,而是以理论方式、知识方式影响相关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这可以说是更大、更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二、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制度规范呈现方式
一个领域、一种事业稳定而持久的发展,总是需要相关制度、规范的保障。依据既有经验,优良制度、优良规范的形成与制定,需要许多条件和程序来保证,但最为基础的必然是对制度、规范指向领域实际情况的准确把握。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要比较好地完成这一任务,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对制度、规范指向的领域展开全面、系统、深入的现代科学研究。针对一定领域、一定实践活动方式的科学系统认识,也就是针对一定领域、一定实践活动方式的知识生产与知识体系构建,这是相关制度建设、规范制定的基本前提或事实根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定领域范围内的制度建设、规范制定必然需要一定领域范围内的相关知识支持,而体系化的制度建设、规范制定,必然需要体系化的知识生产、知识支持。知识体系经过一定的中介化方式,会自然呈现、蕴含在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制度、规范之中。因而,我们可以说,制度规范是一定知识体系的重要呈现方式。
按照上述逻辑,新闻领域的制度建设或规范制定,诸如新闻法律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组织领导制度等的建设,新闻伦理道德规范、新闻宣传工作或新闻舆论工作的纪律规范等的制定,首先需要对新闻领域实际情况进行准确、系统、深入、全面的认知和把握,这也是一项需要实事求是展开科学调查研究的工作。只有通过科学研究获得相对比较准确的认识,构建起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才能保障制度建设、规范制定的有效展开。即如果我们要制定出针对我国新闻舆论工作领域的各种优良制度规范,最基本的条件是对我国新闻舆论领域的实际情况有一个全面、系统准确的认识和把握。
随着“后新闻业时代”的快速发展,新闻活动领域产生出大量的新现象、新事物、新问题、新矛盾,亟须以新的法律规范、伦理道德规范、宣传纪律规范等进行调节和约束,而这些规范的形成与制定,特别是这些规范本身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可行性的基础保证,都需要新闻学与其他学科的科学研究提供基础支持,这样的支持就是知识的支持、知识体系的支持。也就是说,如果新闻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生产、知识体系构建能够准确反映实际,适应时代要求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那么其认知成果就可以按照一定的需要经过一定的程序转换为相关的法律、行政、伦理、道德等规范。显然,这些规范形式是知识体系的呈现方式、实现方式。总而言之,如果我们把知识生产、知识体系构建当作前提,那就完全可以说,优良的制度和规范实际上就是知识体系在某种程度上的呈现或实现方式。
在现实社会中,就知识生产、知识体系与制度规范之间的关系而言,我们甚至可以说各种类型的制度规范是知识体系更为稳定、持久、权威的呈现方式。由此可以进一步指出,制度规范方式也是知识体系重要的呈现方式。制度规范是路线、方针、政策的规范化存在方式、表现方式,它们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但制度规范具有更为直接、明确的约束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知识或知识体系一旦经过一定的中介方式转化成相关的法律规范、行政规范、纪律规范、技术规范、伦理道德规范等,就不可能随意变动,而是会保持一定阶段甚至一定历史时期的稳定性、持续性,以保证人们对一定领域活动的稳定预期,从而形成制度规范的权威性。在知识论视野中,作为正确知识的真理,其权威性就可以通过制度规范的方式呈现出来,以形成知识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和指导。这里再次反映出,知识生产、知识体系构建对于一个国家、社会规范运行的重要性,这也是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原因。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不管是路线、方针、政策,还是各种类型、层次的制度和规范,它们不仅是一定知识体系的呈现方式,也是促进知识生产、知识体系构建的动力。如前所述,当代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业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总是要面临不断变化的新现象、新问题、新情况,需要制定新的或完善已有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制度、规范,使其转化为动力,促使研究者积极探索实际,解决问题,从而促进新闻学的知识生产和知识体系构建。也就是说,在知识体系与路线、方针、政策及制度、规范之间,实际上是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关系。知识、理论一经产生,往往并不能指导直接的、具体的实践感性活动,而是要转换为具有指导意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转换为更具约束性的制度与规范。需指出的是,关于知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讨论,视野不能过于狭窄,也不能落于过度的直接实用主义层次。事实上,知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实现于不同的层次和范围,不同的知识、理论,有着不同的重点指向。
三、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观念呈现方式
作为知识体系,本体性的呈现方式是学术方式。但任何知识生产、知识体系的构建,从原则上说都不会停留在理论知识范围内,而是要进入相关的实践领域,根据一定的需要,依据一定的中介手段,转化为指导相关实践活动的观念,使理论知识真正形成对实践活动的支持或指导。对于应用性极强的新闻学科来说,就更是这样了。在新闻实践中,理论化的新闻学知识体系会以规范化的方式、实践观念化的形式呈现出来,转换为指导新闻活动的实践观念。这意味着,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只有转换为直接指导新闻实践活动的实践观念、应用观念,才能真正产生知识体系的功能作用。
在知识论视野中,尽管知识本身包含各种具体的类型,但就现代社会而言,知识最主要的形态是由科学认识方式形成的理论知识。理论知识(理论观念)要想指导直接的实践活动,必须依据主体的需要和一定的可行性条件转换为实践观念。我国著名哲学家夏甄陶指出:“科学合理的实践观念,就是被人们掌握和理解了的理论观念的客观内容和自己的愿望、意志、情感等主观精神的创造性综合,应该是指向未来的理想,是反映着人们对真理和价值相统一或真、善、美相统一的对象的追求。”[4]主体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坚持什么样的实践观念,用什么样的实践观念指导自己的行动,这绝不是小事,而是至关重要的大事。用不同的观念指导实践活动,就有可能造成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果。
这里所说的实践观念就是用来直接指导感性实践活动的观念,对实践活动的展开方式及其实现结果有着直接的作用。新闻理论知识、理论观念,只有转换为作为实践观念的新闻观念,才能直接指导新闻实践活动。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尽管新闻理论观念、理论知识是新闻实践观念得以生成的前提条件,但新闻实践观念对于新闻实践活动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人们要想真正理解主体的新闻观念系统,上至一个国家、政党,中到一个媒体组织或社会机构平台,下至独立的个体,尽管需要弄清楚其持有的新闻理论观念,但最核心的其实要看其坚守的新闻实践观念是什么。[5]
新闻学领域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类型的新闻学,存在着不同类型的新闻理论,存在着不同类型的新闻学知识体系。就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实际情况来看,最典型的、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性质不同的新闻学是中国式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特色新闻学)和西方式自由主义新闻学(西方专业主义新闻学),它们拥有各自的核心观念和理论体系,也就是说,它们拥有各自不同的知识体系。①一个国家、社会到底选择什么样的新闻学知识体系作为知识基础构建自身的新闻实践观念,对于造就什么样的新闻实践图景、形成什么样的新闻世界、发挥什么样的新闻价值有着前提性的作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不同的新闻观念之间尽管可以相互学习借鉴,但它们之间的冲突是不可否认的,甚至是不可调和的。我们不可能用相互冲突的新闻观念去指导我们的新闻实践活动,这样会造成精神分裂症式的新闻现象。
我们所讲的自主知识体系,就是由中国人以自己的立场、智慧、方式构建的知识体系,它自然具有典型的中国性或中国特色。对于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而言,我们一再强调,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新闻学知识体系,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新闻学知识体系,是以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党媒实践经验为根基的知识体系,是在吸纳国内外现代新闻学优秀成果基础之上的知识体系,是基于现实、面向未来的知识体系。而其中的灵魂所在,是当代中国新闻学在理论性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构建的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新闻学知识体系。也就是说,当代中国新闻实践以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新闻学知识体系为基础,因而在总体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就成为指导当代中国新闻实践的主导观念。这样,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观念与中国新闻实际相结合,就成为中国新闻领域、新闻舆论工作始终关注和探索的重大问题。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当代中国新闻的精神内核。
无论是在历史维度还是在现实构成上,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观念都是一个庞大、丰富且不断更新发展的观念体系,①这一体系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主导知识体系。这样的知识体系,为当代中国新闻事业、新闻舆论工作提供了理论基础、知识基础,提供了一系列不同于其他性质新闻学的标识性观念。②比如,中国共产党的党性观念、人民观念,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观念,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观念,坚持正面报道为主与舆论监督相统一的观念,坚持尊重新闻规律、按照新闻规律办事的观念等,都是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内容、理论观念。所有这些重要的理论观念不会封闭在知识体系之中,而是要转化为指导新闻舆论工作的实践观念。这些源于实践的理论观念,只有以实践观念的方式“回流”到新的新闻实践中,才能真正体现出知识作为知识、知识体系作为知识体系的力量和影响。
更具体一些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念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起源观念、新闻本原观念、新闻本质观念、新闻真实观念、新闻价值观念、新闻传播观念、新闻自由观念、新闻道德观念、新闻事业观念、新闻技术(媒介)观念等一系列观念构成的,所有这些观念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关于新闻起源问题、新闻本源问题、新闻本质问题、新闻真实问题、新闻价值问题、新闻传播问题、新闻自由问题、新闻道德问题、新闻事业问题、新闻技术(媒介)问题等一系列问题认识成果的体现。这一系列观念正是用来指导当代中国新闻实践的观念,中国新闻世界的实际图景、实际面貌到底为何,新闻所产生的实际功能作用到底如何,其实主要是由这一系列的新闻实践观念决定的。
落实在微观层面上,可以说,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的知识体系,特别是历史新闻学、理论新闻学知识体系,会转换为指导当代中国新闻宣传工作、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的、基本的实践观念,也就是说,知识体系会体现、呈现在新闻实践活动之中。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已经形成富有自身特色的概念体系,形成自身的一些标识性概念。比如新闻概念体系中的正面新闻概念,新闻真实概念体系中的整体真实概念,舆论概念体系中的新闻舆论、舆论引导概念,媒体及新媒体概念体系中的党媒、媒体融合概念等。这样的概念及其所反映的观念,在与新闻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当代中国新闻舆论工作中一系列具有内在关系的实践观念,诸如当代中国新闻实践,特别是以党媒体系为主的新闻实践,拥有一套独特的观念体系,像正面事实、正面新闻观念,整体真实观念(整体真实与个别真实相统一的观念),新闻价值观念中的关系价值观念、新闻时间观念中的时效观念,舆论引导观念,媒体融合观念等。③所有这些用来指导新闻实际工作的实践观念,都是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体现。可以说,有什么样的自主知识体系,就会有什么样的自主新闻实践观念,自主知识体系与自主实践的观念体系本质上是统一的。
与历史新闻学、理论新闻学知识体系相比,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的应用新闻学知识体系,更是广泛地体现、实现于自身的新闻舆论工作之中,成为指导新闻舆论实践工作的重要知识来源。新闻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有众多的分支,每一分支都有自身的知识体系,包括自身的历史知识体系、理论知识体系和应用知识体系。分支领域更强调实践性或应用性,其知识体系构建的过程本就是观察、分析、研究实践的过程和结果,同时也是研究成果不断回馈实践、实现于实践的过程。
四、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直接实践呈现方式
从一般意义上说,公共性是知识的基本属性,知识是人们可以共享、分享的认识成果。对于一定领域的知识而言,参与领域活动的人们原则上都是创造知识、分享知识、运用知识的主体。因而,一定领域的知识会通过人们的相关活动呈现出来,或者说知识会呈现、体现、实现于人们的相关活动中。
新闻活动是人固有的活动,新闻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这意味着所有人(历史上的人、现实中的人和未来的人)都是新闻活动主体,他们在新闻活动中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创造新闻知识、分享新闻知识、运用新闻知识。新闻知识会以不同方式呈现在人们不同的新闻活动中。对于人类来说,知识不是死的东西,而是活的存在,是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对象化的存在,工具便是知识客观呈现出来的方式,诚如斯蒂格勒所言,“知识是一种效应,而效应是通过器具、劳动工具和技术来实现的”。[6](195)新闻知识不仅可以呈现在新闻实践活动中,也可以呈现在各种新闻活动工具中,呈现在对各种新闻工具、媒介技术工具的运用中。由于在现实的新闻活动中,不同的人、不同的主体承担着不同的角色或身份,所以,新闻知识也会以不同的主体方式呈现出来。下面,我们针对当前中国新闻的实际情况,加以简要分析和阐释。
首先,新闻知识体系会呈现在职业新闻主体的新闻生产传播实践中,这是新闻知识、知识体系得以呈现的主导实践方式。尽管互联网已成为社会运行的基础设施,数字技术、智能技术激活了所有社会主体的新闻生产传播能力与热情,但不管是在人类整体意义上还是就一定社会来看,其日常的新闻图景依然主要是由职业新闻机构与职业新闻工作者塑造的,因而,职业新闻主体的新闻实践观念、新闻知识体系,与其他类型的新闻生产传播主体相比,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传统新闻学的知识体系本身就是以职业新闻活动、传统新闻业为主要对象生产构建起来的。人们通过对职业新闻活动的长期考察、研究,形成了关于新闻业和职业新闻活动的系统认识成果,这样的理论认识成果或知识体系经过一系列的中介化方式,反过来成为指导职业新闻活动的实践观念,从而使新闻认识成果、知识体系体现在职业主体的新闻生产实践活动中。可以说,新闻学知识体系与职业新闻实践具有一种内在的互生关系。
从一般意义上,人们不难看到中外新闻研究形成的大量理论成果,诸如新闻事实论成果、新闻真实论成果、新闻价值论成果、新闻传播原则论成果、新闻事业论成果、新闻媒介论(技术论)成果、新闻责任论成果、新闻自由论成果、新闻道德论成果等,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在职业新闻机构、职业新闻工作者常态的新闻生产实践中。以新闻传播原则论成果为例,传统新闻学经过长期探索和研究,形成关于职业新闻传播原则相对比较成熟的体系化认识成果或系统化基本观念,诸如新闻传播必须遵循真实原则、客观原则、全面原则、公正原则、及时原则、公开原则等。①这些原则,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所有专业新闻机构和职业新闻工作者观念上认可、行动上遵循的基本原则。应该说,这些原则的实现尽管不够理想,但已经体现在职业新闻活动主体(包括组织主体和职业工作者)的新闻生产传播实践中。至少可以说,这些理论原则诉诸的基本要求已得到职业新闻领域的普遍认可和接受,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及不同的社会环境、新闻环境中以不同的程度和方式体现在新闻生产传播实践活动中。
而随着媒介环境、新闻生态的整体性变革,新闻研究也在与时俱进,在新闻生产传播原则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新的认识成果,如在互联网背景下,在数字新闻环境中,职业新闻传播要想赢得社会大众的信任、形成良好的社会影响力,就须在遵循传统新闻传播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遵循新闻生产传播中的透明原则、对话原则。②透明成了保证新闻真实与信任的基础方法,不透明往往成了阴暗、虚假甚至阴谋的代名词,“当代公共话语中没有哪个词比‘透明’更高高在上,地位超然,人们对它孜孜以求,这首先与信息自由息息相关”。[7]同样,对话成为时髦词汇,没有对话就没有真实,没有对话就不可能揭示和呈现全面的真实,我们“可以将新闻的本质理解为建立在公共协商基础上的文化实践”。[8]可以想象,伴随智能新闻、人—机新闻的迅速勃兴,一些新的新闻生产传播机制和规律将被揭示出来,一些新的新闻生产传播原则将被确立起来,并逐步体现在智能时代的职业新闻生产传播实践中。
就当代中国新闻生产传播领域的实际情况来看,党媒体系以及党媒体系中的从业者构成了新闻舆论工作的主导性或核心性主体。这意味着,现实中国社会的新闻图景、新闻舆论景象主要是由党媒体系及其所属的工作者塑造、构建的。因而,党媒体系在新闻生产传播实践中依托的知识体系、奉行的实践观念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①就知识、观念到实际、实践这一逻辑关系而言,可以说,当代中国新闻生产传播实践之所以是人们看到的图景或景象,是作为新闻舆论工作核心主体的党媒体系,在新闻舆论工作实践中依托的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知识体系,呈现的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念的要求。其核心是,党媒体系展开的新闻舆论工作,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化、时代化的党媒(党报)思想、党媒(党报)理论。②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有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知识体系,有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念体系,有什么样的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闻舆论思想体系、知识体系,就会有什么样的新闻舆论实践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新闻图景和新闻舆论景象,后者不过是前者的实践呈现方式、实现方式。当然,从实际、实践到知识、观念的逻辑关系中,知识、观念来源于实际、实践,且这是更为根本的关系,但这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核心问题。
其次,新闻活动主体本身就是多元的,在现代新闻业产生之后,不同类型的新闻活动主体形成了系统的以职业新闻主体为核心的新闻活动主体结构方式,③共同塑造一定社会的新闻图景。而在当今媒介环境中,新闻活动主体类型及其不同类型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传统的以职业新闻主体为核心的结构方式受到了冲击甚至被解构。因而,新闻知识体系会以更为丰富、复杂的方式呈现在新闻活动主体特别是非职业新闻活动主体的多元化新闻活动中。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新闻学知识、知识体系会呈现在所有社会主体(包括各种类型的组织主体、一般群体和个体)的新闻活动中。就像新闻活动属于人们普遍的社会活动方式一样,新闻知识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知识,它的专业性相对弱一些,门槛相对低一些,易被社会大众理解和运用。
在传统新闻业时代,职业新闻主体之外的其他社会主体在新闻活动中主要承担的是新闻收受者、新闻消费者的角色,很少以生产者、传播者的身份参与到职业新闻生产传播中,参与到大众化、公共化的新闻生产传播活动中。与此相应,新闻学也主要是从新闻收受角度、消费角度来关注社会大众、研究社会大众的。这样的研究,除了为职业新闻主体实现更为有效的新闻生产传播服务之外,也为社会大众如何提高基本的媒介素养和新闻素养服务。媒介素养、新闻素养研究实际上是期望社会大众能够在常识基础上更好地理解新闻的基本属性和功能作用,更好地理解新闻媒体新闻生产传播的基本原则和机制,从而能够以比较理性的方式、反思批判的方式对待职业新闻主体生产传播的新闻,也就是能够把有限的新闻知识体现并运用到日常的新闻收受活动、消费运用中。
但在当今数字环境和深度媒介化社会背景下,社会大众的新闻活动角色或身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技术赋能、技术赋权的大环境中,整个人类的新闻活动进入“后新闻业时代”,新闻生产传播的“共时代”成为基本事实,④新的社会化生产模式形成,[9]“民众新闻”(民间新闻)、“日常新闻”已成为普遍现象,⑤新闻生活已成为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的基本构成部分,并广泛渗透在其他社会活动中,一个不同于传统新闻时代的新的新闻世界正在形成。这种景象在新闻活动领域最为典型的表现是:传受主体角色一体化的态势已形成,职业新闻主体之外的多元化新闻生产传播主体生态结构已形成。①这意味着,新闻知识已经成为更加普遍的社会知识,成为社会大众日常经验常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新闻专业知识常识化的典型表现。不难看出,传统新闻时代属于职业新闻主体的基本新闻观念,属于职业新闻主体运用的新闻知识、专业技能,已经成为社会大众普遍拥有的观念、普遍运用的知识和技能。相比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新闻知识甚至是新闻知识体系,是普通社会大众相对更为熟悉的知识,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理解新闻的本质,以及新闻生产传播的基本原则和内在精神。尽管非职业新闻总体质量参差不齐,但有一些非职业的新闻生产传播主体(包括群体和个体),也能够像职业新闻主体一样,生产传播出高质量的专业化新闻。不可否认,职业新闻主体与非职业新闻主体共同反映呈现、塑造构建的新闻世界,比起由职业新闻主体单一描述的新闻世界更加丰富全面,人们通过这样的新闻符号世界可以了解到一个更加真实的现实世界。从新闻知识(体系)与这些主体新闻活动间的关系看,职业新闻主体之外的各种社会主体,是新闻知识得以呈现的广泛社会主体,且是越来越重要的主体。如果我们把大量的平台媒体、机构媒体纳入观察的视野,发现它们不仅是新闻知识体系的运用者、呈现者,还是新闻知识生产者、创造者,是新闻知识体系的构建者。
再进一步观察分析智能时代开启后的新闻生产传播活动,那就不得不说,与自然人主体相对应的人工智能体,正在成为越来越普遍、越来越重要的新闻生产传播主体(准主体或拟主体)。[10-11]在智能新闻生产活动中,智能体“是以主体的姿态参与其中……新闻从业者和算法技术以彼此可以理解的方式进行互动和合作,共同塑造了智能新闻生产的底层逻辑”。[12]随着智能技术日新月异的进化升级,智能体相对自主独立的新闻信息采集能力、制作编辑能力、分发传播能力、反馈信息获取能力加速提高,其工作效率远远超过人类主体。人类主体所创造的新闻知识、所构建的新闻知识体系、所追求的新闻伦理价值倾向等(当然不限于新闻知识领域、价值领域),正日益(以恰当的、不恰当的或介乎其间的方式)呈现在人工智能体的新闻生产传播活动中。一种与人类并驾齐驱的拟主体形式正在以基础设施的方式规模化、系统化地展现着人类的知识与智慧,其中就包含人类主体所创造、构建的新闻知识体系。智能体本身就是人类的某种化身,它正在乐观与悲观的各种喧嚣中沿着自身的逻辑不确定地演进着,但其背后的深层动力依然是人类主体的知识创造能力、知识运用实现能力,“人工智能还没有聪明到让我们放弃思考的地步,或者更准确地说,还不具备足够的想象力或创造力”。[13]
再次,新闻知识体系会呈现在领导主体、管理(治理)主体的新闻领导、管理(治理)、控制活动中(可以把领导主体、管理主体、控制主体统一简称为控制主体)。新闻学知识不仅会体现在专业新闻工作者的新闻实践活动中,体现在非职业新闻活动主体的相关新闻活动中,也会呈现在一个国家、社会新闻领域的领导、管理(治理)和控制活动中。实事求是地说,新闻控制主体对新闻知识的运用比起其他类型主体对新闻知识的运用更加重要,控制主体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一定社会现实的新闻局面。
新闻活动是重要的社会活动形式和活动领域,新闻生产、传播对一个国家、社会的正常运行与发展有着特殊的作用和影响,尤其是在人类整体步入信息社会之后,新闻活动的重要性更是前所未有,有人不无夸张地说,“如今的政治家越来越是舆论的管理者”。[6](140)如何领导、管理、控制新闻生产传播活动,如何维护优良的信息秩序、新闻秩序,几乎成了所有国家、社会必须摆在战略地位的优先事项。我们看到,在西方社会,一直宣称没有媒介、没有新闻,就没有民主,足以见出新闻对于整个社会运行的重要作用和价值。在新时代的中国,党和国家把新闻能力看作重要的执政能力,把新闻舆论工作看作“治国理政、立国安邦” 的大事,[14](345)是“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14](322)因此,高度重视新闻知识生产、新闻知识体系构建就是必然的事情。
高度重视新闻知识生产、重视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当然不是纯粹的知识论问题,而是知识生产与知识运用相统一的问题。党和国家要想科学合理有效地领导、管理新闻活动,就得依赖对新闻舆论领域历史、现实的准确认识和把握,依赖对新闻活动领域未来变化发展趋势比较真实准确的认知和预判。这样才能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相关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制定和确立科学合理的各种制度规范。也就是说,关于新闻舆论领域的认识成果、构建的知识体系,一定会体现、呈现、实现于领导、管理新闻舆论的活动中。
结语
基于以上论述,可以说,总体上新闻学的知识体系必然会呈现在整体的新闻文化体系之中,也就是说,新闻文化体系是新闻学知识体系的系统呈现方式。一般说来,新闻文化也像一般文化一样,主要是由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大层次构成的,因而,新闻学知识体系就会呈现在新闻媒介、新闻媒体、新闻技术系统之中,呈现在各种新闻制度规范之中,呈现在新闻思想、新闻观念和新闻精神系统之中,呈现在各种社会主体的新闻实践活动之中。相比知识体系的学术呈现方式、教育教学呈现方式,不同形式的实践呈现方式是知识体系的终极呈现方式,实践呈现方式使知识体系产生改变世界的意义和价值,而不再囿于解释世界的范围内。
新闻实践活动、新闻舆论活动是活的历史活动,同样,“知识不能超越时间,它不是永恒或不朽的”,[6](157)新闻知识生产、新闻知识体系构建也是活的历史过程,前者是后者的根源所在,但后者又始终呈现在前者之中,这就是它们之间最为稳定的基本互动关系。新闻知识、新闻知识体系只有“回流”到作为实践存在的新闻活动中,呈现在新闻实践活动之中,新闻知识生产、新闻学的知识体系构建才是有真实意义和价值的,这是当代中国新闻学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过程中必须自觉的基本道理。
参考文献:
[1] 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M]. 董树宝,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140.
[2] 杨保军. 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构成及其关系[J]. 当代传播,2023(1):4-11.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1.
[4] 王永昌. 实践观念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2.
[5] 杨保军. 论作为“实践观念”的当代中国新闻观[J]. 新闻大学,2023(1):51-59,120-121.
[6] 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 迷失方向[M]. 赵和平,印螺,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7] 韩炳哲. 透明社会[M]. 吴琼,译.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1.
[8] 卡琳·沃尔-乔根森,托马斯·哈尼奇. 当代新闻学核心[M]. 张小娅,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14.
[9] 杨保军,李泓江. 新闻学的范式转换:从职业性到社会性[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8):5-25,126.
[10] 杨保军,孙新. 论新世纪以来新闻生产主体的结构变迁[J]. 未来传播,2021(4):2-13,120.
[11] 杨保军,孙新. 论人主体新闻与智能体新闻的关系[J]. 新闻界,2022(8):4-13,57.
[12] 吴璟薇. 人工智能如何改变新闻:技术、媒介物质性与人机融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74.
[13] 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 观念的跃升:20万年人类思想史[M]. 赵竞欧,译.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3:487.
[1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The Practical Orientation for Materializing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Journalism
YANG Bao-jun1,2(1.Center for Journalism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ese, Beijing 100872, China; 2.School of Journalis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ese,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practical orient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journalism determines that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must be deeply rooted in actual practic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practical approach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journalism, and it has the significance of being the ultimate orientation and approach. There are four main ways for this practice-oriented approach to be materialized: adhering to and embodying the news lines, guidelines and policies at the national level; being materialized or implemented according to the norms of the press system at the national level; being demonstrated or embodied in the concept of journalism practice for all subjects of journalism; and virtually being realized in the direct and perceptual journalistic practice activities for all news subjects.
Key words: contemporary Chinese journalism;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practical orientation and materialization
(责任编辑:侯苗苗)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研究”(22JJD860018)
作者信息:杨保军(1962— ),男,陕西富平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新闻理论。
①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一定活动领域路线、方针、政策等的制定与确立,首先依赖国家发展的整体大政方针,是对整体发展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贯彻和落实;其次依赖一定领域的实际情况,这是制定相关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再次是通过一定的组织机构展开工作;最后要经过科学合理的程序和方法,还需要积极借鉴世界各地的相关知识和智慧。
② 所谓中介化方式iOJBfZdsqqgfGXUGQydYeBxIRSJAehGRxvY6MVnbwGc=,是指从知识到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确立,有一个转化的过程或环节。作为对实际情况真理性揭示的理论成果,可以指导人们根据实际需要、理想愿望,并结合各种可行性条件,制定出有效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③ 关于当代中国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规律问题,可重点参阅杨保军《新闻规律论》第七章“党媒视野中的特殊规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80-332页)。
① 当然,作为新闻学知识体系,它们拥有诸多共同的概念、问题和内容。
① 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念体系的构成问题,可参阅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参阅杨保军《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观念及其基本关系》(《新闻大学》,2017年第4期,第18-25、40、146页)。
③ 关于这些实践观念,可参阅杨保军及其合作研究者关于当代中国新闻实践观念的系列论文:杨保军《论作为“实践观念”的当代中国新闻观》(《新闻大学》2023年第1期,第51-59、120-121页);杨保军《当代中国新闻的“事实观念”》(《编辑之友》,2023年第7期,第19-28页);杨保军、叶倩茹《作为实践观念的当代中国新闻“时间观”》(《当代传播》,2023年第6期,第11-18页);杨保军《准确理解新闻的“整体真实”》(《新闻界》,2020年第4期,第35-42、5页);杨保军《准确理解“党媒”新闻报道“全面”观念与“正面为主”观念之间的关系》(《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119-124页)。
① 职业新闻传播要遵循这些基本原则,是因为只有遵循这些基本原则,才有可能实现新闻要为社会公众服务、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的基本目标。这种目标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选择,即人类在长期的新闻活动过程中,赋予新闻活动特别是职业新闻活动这样的社会职责和使命。事实上,每一社会领域的基本功能、每一种职业的基本职责,都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这是社会演进过程中的历史选择。
② 关于透明原则、对话原则的基本内涵与要求,可参阅杨保军《新闻理论教程(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28-132页)。
① 需特别说明的是,党媒体系在新闻舆论工作中所依托的知识体系、观念体系不限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知识体系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念体系,原则上其所依托的是整体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和观念体系。
② 中国共产党的党报思想、党报理论实际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主体内容,且随着历史的演进,党报思想、党报理论也在不断更新和发展,形成了时代化的表现方式。如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就形成了新时代新闻舆论思想体系。
③ 在基本类型上,新闻活动主体主要是由新闻信源主体、新闻传播主体、新闻收受主体、新闻控制主体和新闻影响主体构成的。参阅杨保军《新闻主体论》第一章“新闻主体”第二节“新闻主体的构成”中的相关论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32-34页)。
④ 参阅杨保军《“共”时代的开创——试论新闻传播主体“三元”类型结构形成的新闻学意义》(《新闻记者》,2013年第12期,第32-41页)。还需注意的是,民众新闻、民间新闻或日常新闻是贯通历史的存在,并不是网络时代、数字环境下的产物,只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日常新闻的非日常化、公共化变得更加容易,使日常新闻与非日常新闻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
⑤ 参阅杨保军《简论网络语境下的民间新闻》(《新闻记者》,2008年第3期,第20-23页);杨保军《简论新闻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第133-139页);杨保军、张博《论日常新闻的实质特征与功能意义》(《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第36-47页)。
① 就当前的现实看,在新闻生产传播端,已经形成了职业主体、机构主体、平台主体、自媒体主体和智能体主体(拟主体或准主体)共同构成的新闻生产传播主体生态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