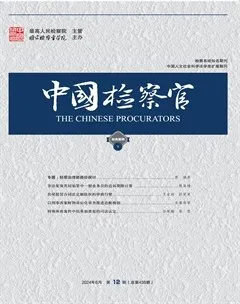相约自杀中的帮助、欺骗行为如何定性
关键词:相约自杀 欺骗自杀 故意杀人罪 间接正犯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何某为寻求观看他人上吊窒息状态而产生的畸形快感,在网上找到有自杀意愿,但没有勇气选择自杀的被害人孙某(女,殁年21岁)。何某隐瞒其真实意图,谎称自己也要自杀,引导、欺骗孙某确定与其一起采用上吊的方式自杀。两人在网上确定自杀的具体时间、地点及工具等,由何某预订客房、购买上吊用的凳子、丝巾等物品,绳子各自携带。2022年7月9日晚,何某和孙某在宁波市某区某宾馆一房间内,采用将绳子绑在客房楼梯上,再将丝巾绑在绳子上的方式上吊自杀。何某帮助孙某绑了一个死结,而自己在上吊后绑了一个活结,后自行解脱,观看孙某上吊临死时的状态,满足自己畸形快感。孙某因颈部受力致机械性窒息死亡。案发后,被告人何某打电话报警,并在现场等候处理,但报警时仅称其与他人相约自杀,后被查实系引导、欺骗孙某自杀。
二、分歧意见
孙某在何某帮助、诱导下自杀,何某是否承担刑事责任是本案的争议焦点。首先要厘清自杀是否构成犯罪。自杀是指“在被害人事前知道自己行为结果的前提下,直接或间接地由其自己实施的作为或不作为所引起的死亡”。自杀是自己对自己所为的杀害行为,系自己加害自己、自己实施放弃法益的自暴自弃行为。自杀是当事人自我处分生命的行为,自杀分为违法说、无罪说和法外空间说。近年来,法外空间说成为有力观点,即“自杀不是法律领域的负价值行为,而仅仅是属于法律上不考虑违法、有责判断的法律空白领域之内的放任行为”。本文不纠结学说争论,笔者认为,目前至少有一点可以达成共识,即自杀行为虽然道德上不提倡,但是刑法评价上不构成犯罪。其次,要厘清自杀相关联的行为,尤其是相约自杀中帮助、欺骗自杀的行为,在刑法上如何处理。我国刑法对故意杀人罪规定的比较简单。《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没有单独规定帮助自杀罪、欺骗自杀罪。“利用、控制、操纵被害人使其实施自杀行为,利用者本人就可能是间接正犯,犯罪结果就要归责于利用者。”帮助、欺骗自杀是否属于故意杀人罪的射程范围,需要结合案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案中,存在二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何某不构成犯罪。基于被害人自我答责原则,生命处分权属于自己决定权的范畴,是人的权利和自由,本案中孙某上吊自杀是基于本人意思所实施的自杀行为,属于完全自由地处置自己生命的行为。尽管何某存在帮助、欺骗孙某了结自己生命的行为,这属于取得被害人同意之后对其法益造成一定损害的行为,并不是刑法上的杀人行为。故何某不构成犯罪,孙某对死亡结果自行承担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何某构成故意杀人罪。本案中被害人对死亡的动机存在认识错误,没有何某的伪装和引导,孙某根本没有勇气选择自杀。在自杀过程中,何某上吊后自行解脱,观看孙某上吊临死时状态,没有及时救助孙某,导致死亡结果发生。何某是故意杀人罪间接正犯,同时也构成不作为杀人,应当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此外,何某尽管报警并在现场等待,但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不成立自首,不能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主要理由如下:
(一)被害人自杀的承诺必须没有瑕疵,受欺骗的承诺无效
被害人的有效承诺,必须是被害人意思处于自由的状态,对承诺的事项能够独立作出决定,对相关的行为及后果能够清楚判断。自杀者的承诺不能有瑕疵,否则不能成立自杀。司法实践中,有学者认为,缘于生命法益的高度人身专属性、不可流转性的因素考量,基于行为人自主程度和承诺程度的不同,自杀分为自主性自杀和非自主性自杀两种样态。笔者认同此种划分。自主性自杀是个人自我决定权的完整体现,不存在法益损害的空间,自然不应当禁止。比如,被害人主动将自己砍成致命伤、亲自服下毒药、自己跳楼或者投湖等场合中,均是以自己的行为造成了死亡的后果,应当自我担责。非自主性自杀并非个人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在自杀过程中介入了自杀关联行为,比如欺骗、教唆、帮助他人自杀,类似大量非自主意愿充斥自杀过程,并非个人真实意愿表现,此时认定自杀关联行为无罪,不合法也难以为人民群众所接受。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对介入自杀的行为有所规定,在受邪教组织帮助、欺骗自杀的情况下,个人尽管对于结束生命有所认知,但对死亡意义有着明显错误认识,属于被害人的无效承诺,应当认定邪教的组织人员实施故意杀人行为,以间接正犯(把被害人当成杀害他自己的工具)定罪处理。尽管在其他帮助、欺骗自杀的案件中,行为人对被害人的控制不如邪教组织那么强,但不可否认的是,若他人故意介入会现实地或高度危险地影响自杀者内在意思形成的自由,导致自杀并非完全是自主、自治的结果,应当考虑追究帮助自杀、欺骗自杀行为人的责任。
帮助、欺骗自杀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应当受刑法评价。实施帮助、欺骗的行为人不是在心理影响上增强了他人的自杀意图,就是于外在物理意义上助力介入,自杀者对于自杀行为完整流程的自主支配受到了干扰,国家法律应当介入并干预这些行为。在本案中,通过孙某就医记录显示,孙某近两年曾有数十次到医院就诊,其患有抑郁症,并长期服用药物治疗,性格、情绪波动比较大。何某的供述与辩解可知,“何某先是在跟孙某聊天的过程中伪装成有同样自杀想法的人,骗取她的信任,然后慢慢把她诱导到现实中见面,然后配合她的想法让她心甘情愿去上吊死亡。”从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可知,孙某原本没有勇气自杀,也不愿意自杀。何某为满足变态的性癖好(观看他人自杀得到快感),在网络上撒网式搜索目标,与孙某线上接触后,非但没有劝阻开导,反而采取引诱、帮助、欺骗等手段,为孙某提供上吊用的板凳、丝巾等自杀工具并租赁自杀场地,同时在精神上鼓励孙某自杀,导致孙某产生了何某欲与其一同赴死的错误认识,从而做出了在何某帮助下上吊自杀的行为。孙某的承诺系无效承诺,孙某被何某当成了杀害自己的工具,应当以间接正犯追究何某刑事法律责任。因此,第一种意见并不合理。
(二)帮助、欺骗自杀构成故意杀人罪要结合主客观事实综合认定
自杀除了主观方面要求被害人纯粹自主自愿,认识并意欲死亡结果发生,客观方面上还必须完整支配着直接导致死亡的行为,在不可逆转地造成死亡结果的最后关键时刻自己控制着事物的发展。那么,认定帮助、欺骗自杀构成故意杀人罪,主观方面要考虑行为人影响被害人的程度(前文已述),客观方面还要考虑行为人是否直接控制着被害人自杀的进程。若行为人控制被害人自杀进程,则应当追究行为人责任;若被害人在通往死亡最后一刻,仍然掌握决定权,却依然选择走向死亡,则成立自杀,行为人无需承担责任。德国有一个案例,行为人与被害人共同自杀,行为人将一根橡皮管连接排气管并通过车窗接入车厢,然后行为人与被害人共同坐在车里(车门可自由打开),行为人启动汽车并持续怠速,最终行为人因吸入二氧化碳昏迷不醒,被害人因吸入过量二氧化碳死亡。在这个案件中,被害人完全可以打开车门避免死亡结果的发生,但依然选择坐在车里吸入二氧化碳,自己跨向了通往死亡的关键一步,应当认定为自杀,而行为人不应当承担责任。这个案例给我们的启示是,构成自杀的必要条件是自杀者在最后关头掌握、支配着事态的发展。
本案中,何某控制了孙某的死亡进程,并最终以不作为的方式导致孙某死亡结果的发生。何某为孙某绑了一个死结并帮助孙某上吊,而何某自己绑了一个活结,随时可以挣脱危险。何某实际上控制着孙某的死亡走向,而非孙某掌握着死亡走向,与上述德国案例存在区别。此外,何某、孙某在相对封闭空间中一同赴死的行为,形成了危险共同体关系。危险共同体义务,是指虽然不属于法律明文规定,但是当事人之间基于一定事实形成了社会上通常认为的对危险应当予以共同承担、相互照顾的关系。处于危险共同体关系的成员,在发现其他成员陷入危险后,都有救助、排除危险义务。共同实施合法行为,比如一起爬山,发生雪崩,危险共同体的成员之间有救助义务。共同实施违法行为(共同吸毒)形成的危险共同体关系,当成员陷入危险后,也一样有救助义务。如前文所述,共同自杀虽不被提倡,但至少不是刑法意义上的违法行为,双方共同自杀,当何某自行解脱、终止自杀行为后,就产生了救助孙某义务。但是何某的供述与辩解,“我希望能找到女孩,因为在国外色情网站上就有这种上吊自杀的情节,我就希望能按照这样的情节做来满足自己的快感,女孩在上吊时挣扎,我在旁边看着,这样我心理上能得到最大的满足”(案发前的想法),“看到女孩子上吊死亡的过程我很兴奋,内心再一次得到满足根本没有想过要救她,看她死亡的过程也是在我的计划之内”(案发时的心理活动)。由此看出,何某不仅不帮助孙某脱离危险,反而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选择袖手旁观,观看孙某上吊临死时的状态,导致孙某最终死亡。何某既是故意杀人罪的间接正犯,又支配着被害人死亡进程,同时违反了危险共同体关系中的救助义务,以不作为方式产生了被害人死亡后果,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尽管事后何某拨打电话报警,但隐瞒了帮助、欺骗自杀的事实,不能认定自首,无法从轻、减轻处罚。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人的生命具有极端重要性,一般情况下个人不会放弃自己的生命,对于自杀的认定要严格谨慎。自杀者必须清醒认识并且意欲死亡结果发生,意思表示不能有瑕疵,另外自杀者还必须事实上支配死亡进程。只有满足这两点,才构成自杀,帮助、欺骗自杀者才可以免责。而当帮助、欺骗自杀者的行为造成了自杀者产生严重的认识错误,且客观上又主导自杀者的死亡进程,则应当认定帮助、欺骗自杀者为故意杀人罪的间接正犯,结合案情认定其以作为或者不作为方式产生被害人死亡的后果。
最终,法院判决何某成立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孙某母亲经济损失人民币2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