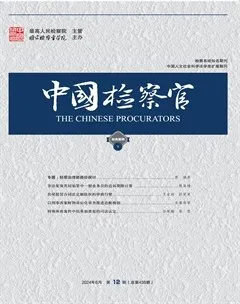非法集资共同犯罪中一般业务员的追诉期限计算
关键词:共同犯罪 追诉期限 分别评价 连带评价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条,犯罪是否超过追诉期限,关乎能否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是刑事司法的基础性问题。在追诉期限的适用中,追诉期限的起算点、追诉期限的延长等问题,理论与实务一直争议不断,上述问题在共同犯罪中的分歧更大。本文以实务中常见的非法集资共同犯罪中一般业务员的追诉期限计算为例,对上述争议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释疑。
一、非法集资共同犯罪中一般业务员追诉期限认定的争议
[基本案情]在陈某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陈某实际控制的中某公司自2013年2月至2019年4月间以投资股权融资、众筹等项目为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金额1亿余元。中某公司理财经理张某于2014年3月入职,2018年1月离职,在职期间参与中某公司非法吸收资金数额200万元。2019年4月,公安机关对中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并抓获陈某等嫌疑人,但未对张某采取强制措施。2018年1月,张某离职后回老家工作。2023年2月,公安机关将张某抓捕到案。对于中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事实,检察机关和法院均认为,由于中某公司设立后,以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为主要活动,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单位犯罪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不以单位犯罪论处,陈某等人成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共同犯罪。检察机关综合张某的犯罪数额、退赃退赔、从犯、认罪认罚等情节,对张某作出相对不起诉。
根据《刑法》第87条、第176条和最高法《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张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犯罪数额200万元,对应的法定刑档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追诉期限为5年。对于张某是否已经超过追诉期限,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张某2018年1月从中某公司离职时,其犯罪事实已经终了,应当自2018年1月起开始计算追诉期限,至2023年1月经过5年,且张某在此期间并无逃避侦查行为,不能适用追诉期限延长的规定,因此,2023年2月公安机关将张某抓捕到案时,张某的犯罪已经超过追诉期限。另一种观点认为,张某的犯罪未超过追诉期限。对此有两种论证思路:一种思路认为,应当从涉案中某公司犯罪事实终了之日即2019年4月起开始计算张某的追诉期限,因此,2023年2月公安机关将张某抓捕到案时,尚未超过5年的追诉期限;另一种思路认为,即使从张某离开中某公司的2018年1月开始计算其追诉期限,2019年4月,公安机关对中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后,张某的追诉期限延长,2023年2月公安机关将张某抓捕到案时,尚未超过追诉期限。
以上不同观点,集中体现了共同犯罪中共犯追诉期限的计算问题。为准确认定张某的追诉期限问题,需要明确三个问题:共同犯罪中共犯追诉期限应当连带评价还是分别评价、共同犯罪中共犯的追诉期限起算点认定和共同犯罪中共犯追诉期限的延长问题。
二、共犯追诉期限应当分别评价
(一)共犯追诉期限应当连带评价还是分别评价的不同观点
对于共同犯罪中共犯追诉期限应当连带评价还是分别评价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从共同犯罪追诉的一体性以及保证诉讼程序完整性的要求出发,对于共同犯罪,确定从犯追诉期限所适用的法律条款与确定主犯追诉期限所适用的法律条款应当同一,不论从犯的参与程度,即使从犯有从轻、减轻情节,其追诉期限与主犯的追诉期限应当一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共同犯罪并非适用统一的追诉期限标准,而是应当按照各共犯人应当适用的法定刑幅度,分别计算追诉期限。
笔者认为,追诉期限是依照法律规定对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的期限,是“对人”的单独评价,共同犯罪的场合,对共犯人追诉期限的判断,应当针对各共犯具体情况进行分别评价,而不能按照“部分实行全部责任”连带评价。因此,共同犯罪中各共犯的追诉期限应当根据各共犯所犯罪行对应的法定最高刑分别确定。
(二)共犯追诉期限分别评价的主要理由
一般来说,由于共同犯罪采取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各共犯所适用的法定量刑幅度是一致的,即法定最高刑相同,适用的追诉期限也应当是相同的。但也存在共犯法定量刑幅度不同的情形,一是成立共同犯罪但罪名不同的场合,二是成立共同犯罪但适用不同法定刑档的场合。在共犯法定量刑幅度不同时,应当根据各自的法定最高刑分别确定共犯的追诉期限。因此,可能出现部分共犯超过追诉期限、部分共犯没有超过追诉期限的情形。当然,应当根据各共犯的法定刑而非宣告刑确定各共犯的追诉期限,例如,共犯可能具有从犯、自首等减轻处罚情节的,不影响其追诉期限的认定。
在非法集资共同犯罪案件中,非法集资整体事实的犯罪数额往往特别巨大,虽然普通业务员与涉案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高管等人员成立共同犯罪,但普通业务员作为从事吸收资金行为的最低层级人员,仅对自己实际参与吸收的全部金额承担刑事责任,而不对整体非法集资犯罪事实的全额负责。因此,作为共犯的普通业务员认定的犯罪数额与主犯不同,适用的法定量刑幅度不同,应当分别确定各共犯的追诉期限。这一分别评价的思路,也符合非法集资案件中分层处理的司法逻辑。本案中,陈某等人可能适用“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张某的行为属于“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法定刑档,应当按照张某的犯罪数额所处法定刑档的法定最高刑确定对张某涉案犯罪行为的追诉期限,其追诉期限为5年。
三、共犯追诉期限的起算点
根据《刑法》第89条规定,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共同犯罪不是各共犯参与行为的“简单相加”,而是形成共同故意下的共同行为,因此,共犯的共同犯罪行为终了之日一般应当是同一的。当然,如果部分共犯成立犯罪中止,则从其脱离共同犯罪之日起计算其犯罪行为终了之日。
(一)非法集资共犯追诉期限起算点争议
在非法集资案件中,如本案中的张某,在整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事实终了之日前离职的,究竟是以其离职时间还是以整体非法集资犯罪事实结束之日起计算张某的追诉期限,存在一定争议。
这一争议实际源于非法集资案件中对一般业务员犯罪数额的认定规则。按照共同犯罪的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共犯应当对其参与的整体犯罪事实、犯罪数额承担刑事责任。但非法集资案件中,一般业务员仅对其任职期间实际参与吸收的全部金额而非全案犯罪数额承担刑事责任。从承继共犯的角度看,一般业务员自其参与非法集资犯罪事实之日参与非法集资共同犯罪较容易解释,但为何其无需对离职后的犯罪数额承担责任,以及为何对其任职期间未直接参与的其他共犯非法集资犯罪事实不承担责任?这其实是基于一般业务员在非法集资共同犯罪中的特殊认定思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共同犯罪行为,是不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连续犯罪行为,一般业务员作为底层直接参与非法吸收资金的人员,仅对其直接参与吸收的金额承担共同犯罪的责任。因此,其离职行为切断了其犯罪行为与整体非法集资犯罪事实的因果关系,具有共同犯罪的犯罪中止效果。
(二)区分不同层级人员分别认定“犯罪行为终了之日”
基于对各共犯分别确定追诉期限的思路,前述认定一般业务员刑事责任的认定思路,会对一般业务员的犯罪事实终了之日的认定产生影响。换言之,认定各共犯刑事责任的逻辑与确定各共犯追诉期限起算点的逻辑应当统一,即应当区分不同层级人员,分别认定犯罪行为终了之日。
对于主犯,如涉案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员,因为其一般要对整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事实承担刑事责任,即使其提前离职,但不成立犯罪中止的情况下,根据共同犯罪基本原理,应当以共同犯罪终了之日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整体犯罪事实结束之日起算其追诉期限。对于一般业务员,因为追究其刑事责任时,是以其任职期间实际参与吸收资金的共同犯罪事实部分为基础的,因此,应当以其离职之日作为其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算其追诉期限。本案中,应当以2018年1月张某离职之日起计算其追诉期限。
四、共犯追诉期限的延长问题
根据《刑法》第88条第1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共同犯罪中,共犯是否符合追诉期限延长条件,一是要根据各共犯的具体情形分别评价,而不能以主犯连带评价。二是需要对“已立案或受理案件”和“逃避侦查或者审判”进行准确解读。
(一)根据共犯具体情况分别判断追诉期限是否延长
共同犯罪中,不同共犯追诉期限的延长具有相对独立性,各共犯是否符合追诉期限延长条件,应当根据具体情形个别判断。关于是否受追诉期限的限制,无论是1979年《刑法》第77条规定的“采取强制措施以后”,还是1997年《刑法》第88条第1款规定的“立案侦查或者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都需要判断犯罪分子是否“逃避侦查或者审判”,这显然是对人的具体评价。因此,共同犯罪中,共犯追诉期限是否延长,应当根据共犯具体情况分别判断。例如,在刑事审判参考第1200号袁某祥、王某恩故意杀人案中,袁某祥、王某恩系共同犯罪,二人作案后,王某恩在被批捕的情况下一直负案潜逃,袁某祥未逃避侦查,法院认为,王某恩符合追诉期限延长条件,其犯罪不受追诉期限限制,但共犯袁某祥仍然要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二)实质判断是否延长共犯的追诉期限
共同犯罪中,无论是“对事立案”还是对“对人(单位)立案”,都需要考虑共犯是否“逃避侦查或者审判”,进而实质判断是否延长共犯的追诉期限。
第一,在追诉期限制度中理解“立案”,不应排除“对事立案”,但应实质判断侦查机关立案后是否指向具体犯罪嫌疑人。例如,最高检2015年发布的指导性案例——蔡某星、陈某辉等(抢劫)不核准追诉案中,明确指出由于案发后公安机关在追诉期限内仅发现了李某忠等3人,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蔡某星、陈某辉,且2人在案发后没有再犯罪,因此2人已超过追诉期限。该案系典型的“以事立案”,由于司法机关在追诉期限内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蔡某星、陈某辉,2人的追诉期限当然要受到限制。但如果在“对事立案”后,侦查机关已经发现、指向特定犯罪嫌疑人的,则应进一步判断特定犯罪嫌疑人是否逃避侦查。
在经济犯罪尤其是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中,公安机关接到集资参与人报案时,既可能对“事”立案,如XX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也可能对“人(单位)”立案,如XX公司、XX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时,可能出现部分涉案人员已离职,或者当时的证据无法证实部分人员构成犯罪,后期公安机关又追捕到案等复杂情形,需要结合具体情况综合、实质判断。本案中,公安机关对中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这属于对人(单位)立案,也指向了涉案公司的相关人员,之后分批、分层次打击涉案人员,符合此类案件的一般侦查实践,在公安机关没有怠于侦查的情况下,应当认为该立案对于中某公司涉案人员包括张某等,产生了“立案”效果。需要说明,对单位立案后续认定为共同犯罪的,不影响“立案”的认定。
第二,认定“立案”后,应当结合犯罪嫌疑人“是否逃避侦查与审判”综合判断,是否应当延长追诉期限。关于“逃避侦查与审判”存在不同观点,主要分歧在于:是仅限于积极、主动的逃避行为,还是也包括如未主动投案、未如实供述等消极行为。笔者认为,“逃避”应限于积极、主动的逃避行为,要看犯罪嫌疑人的逃避行为是否干扰了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是否影响了国家侦查权的有效行使。因为从追诉期限制度的立法宗旨而言,如果犯罪嫌疑人长时间没有再犯罪,也没有积极、主动逃避司法追究,从改善效果来看,犯罪嫌疑人特殊预防的必要性大大降低,应受追诉期限限制。反之,如果犯罪嫌疑人积极、主动逃避司法追究,证明其特殊预防必要性没有降低,应当延长其追诉期限,避免其从逃避行为中获利。如果行为人没有逃避侦查或者审判,但有关机关因自身原因长期不开展侦查、起诉、审判工作,导致案件长期悬而未决,明显超过追诉期限的,不应将该怠于侦查效果加诸于犯罪嫌疑人,仍应受追诉期限的限制。需要注意,目前公民身份信息实名制较为普遍,公民的银行账户、出行、住宿等均需要实名信息,如公安机关对该人采取强制措施(如上网追逃)后,该人长时间较为异常地未使用任何可追溯行踪、联系的方式,可以推定其具有逃避侦查的行为。
本案中,公安机关对中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后,张某追诉期限是否延长,应当根据其具体情况个别判断,即需要判断公安机关是否发现张某涉嫌犯罪,以及张某是否有积极、主动的逃避侦查行为,进而判断是否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而不能径行认为张某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