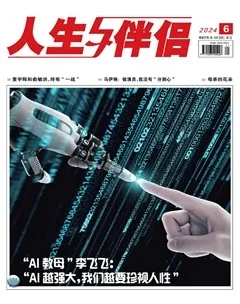夫妻忠诚协议的法律效力研究

一、问题提出的背景
家庭制度的核心在于“婚姻”,家庭稳定则社会稳定。因此,努力构建和睦、文明、幸福的家庭不仅是婚姻双方主体所追求的,也是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目标。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2021年7月发布的第七次(2020年)人口普查报告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53%,相较第六次(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的年均增长率 0.57%,总体呈下降趋势。2023年我国的育龄妇女生育水平持续下降,初婚人数八年减半。出生率、生育率的下降,除了人口总量下降、育龄推迟、疫情短期冲击等客观原因外,婚姻观的改变、市场经济下的经济成本分析、法律意识的提高等影响个人主观选择的因素也应被纳入讨论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2023年度民事一审案件情况显示,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占总数的12.41%。以上各项数据都表明,为我国适龄人口的婚姻问题提供有效且可被执行的建议是维护社会稳定、保持人口竞争力的当务之急。
2024年3月,江苏法院家事审判白皮书公布,离婚案件占比超7成,直言婚姻当事人对婚姻的宽容度和忠诚度逐渐降低是离婚率逐年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对自由的追求、两性观念开放、婚内出轨试错成本低等文化环境对夫妻间忠诚义务的履行影响不容小觑。因此,许多有意愿结为夫妻的双方当事人为了保证自己在婚后的权利,会选择以书面的形式签订夫妻忠诚(忠实)协议,而夫妻忠诚协议的法律效力之争在理论界此起彼伏,实务中的裁判也大相径庭,为此,本文旨在探讨夫妻忠诚协议是否应该纳入《民法典》层面进行效力判定以及应当采用何种方式进行分析,以期保护婚姻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促进家庭生态文明,为当下适龄群体的婚姻困境提供一些思考路径。
二、夫妻忠诚协议基础问题的厘定
(一)夫妻忠诚协议的概念及特征
夫妻忠诚协议是具有合法婚姻关系的夫妻双方基于自愿原则签订的夫妻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互尽忠诚义务,若一方由于不忠诚行为导致婚姻破裂,需承担一定后果的协议。大多数夫妻忠诚协议的内容都涉及主体需为发生不忠行为所导致的后果支付一定数额赔偿金或对其限定权利进行“剥夺”。夫妻“忠诚协议”这一概念最关键的点在于对“忠诚”的理解。婚姻家庭领域中的“忠诚”一词可做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上的“忠诚”包含夫妻间不得遗弃配偶、不得容许第三方侵害婚姻当事人的利益、互尽陪伴义务、不得互相隐瞒等要求。而狭义的“忠诚”仅指夫妻间性义务的专一性、排他性,不得与婚外第三方发生性行为。因广义上的“忠诚”不属于婚姻家庭的范围,且若无限扩大“忠诚”的语义会导致法律适用不清,概念界定不明的情况,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狭义上的“忠诚”。
此前提下的夫妻忠诚协议应当有三个主要特征:(1.)基于特定身份关系,双方主体需拥有合法的婚姻关系;(2.)协议订立基于自由意愿;(3.)内容特定,即未履行忠诚义务的一方需承担一定后果。
(二)夫妻忠诚协议产生的法经济学分析
为何当下越来越多的夫妻双方会选择签订夫妻忠诚协议?这还要从“婚姻”的本质出发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婚姻的本质是基于特殊身份的契约关系。不管是早期的群婚制、血缘婚、对偶婚等,还是如今的一夫一妻制,本质上是对社会中不同性别人群的社会分工、合作形式做出调整。
而家庭模式之所以保存至今,也是因为其有难以替代的经济效能。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当下大部分国家都主要实行市场经济,辅之以宏观调控,在经济学理论中,默认每个市场主体都是“经济人”,而经济人所做出的行为都基于理性分析。若把婚姻看作一种特殊身份关系下的契约,则婚姻中的当事人必定会对婚姻的成本及其收益做出分析。婚姻会形成家庭,而家庭作为市场中的消费者和生产者,是需要投入成本以获取收益的。除了投入以金钱换取的食品、药品、家具等有形物品,温暖、爱、陪伴等无形物品的投入也不容忽视,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投入就是,为了养育下一代和维护家庭稳定所付出的时间,尤其是传统家庭模式中妻子一方的时间。孩子作为家庭这个经济主体最主要的“产品”,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于婚姻的选择。根据波斯纳的成本经济分析在家庭与性当中的应用可知,随着医疗科学的进步,婴儿的死亡率明显下降,使得一对夫妻想要拥有更多孩子意愿降低;而养育一个孩子所需投入的成本,相较于养育多个孩子的平均成本明显增高;并且伴随着社会廉价劳动力大量涌现以及高效的家务替代型机器的出现,妇女在市场上工作的成本降低,从而增加了雇主对于她们服务的需求;服务增加使得妇女在市场上能赚取的净收入增多,此时若一个妇女选择退出市场竞争而参与家庭管理,其服务于家庭的机会成本增高,这种机会成本转化为养育的子女的影子价格;孩子的影子成本升高,降低对于孩子的需求,最终导致人们对于婚姻的需求降低。
婚姻这种契约模式区别于市场中其他商业主体契约模式的主要点在于,规范、指导婚姻内分工和行为的机制并非“员工守则”,而是“爱”,在经济学中称之为“利他主义”,促进了夫妻双方的合作。而随着社会婚姻观念的不断变化,人们对于自我利益的追求,对于自由的无条件追求,导致人们对于爱情的忠诚度,对伴侣的包容度已经大不如前。婚外情、嫖娼等一系列婚内不忠行为都使得监督夫妻双方履行义务的道德基石受到严重打击,于是,为了能够弥补“利他主义”日渐缺位带来的婚姻危机加重,人们试图用法律的武器来作为捍卫婚姻中合法权益的“救命稻草”,夫妻忠诚协议就此进入婚姻家庭法的视野。
(三)夫妻忠诚协议的界定及类型
夫妻忠诚协议所涉及的内容可谓是“五花八门”,我们无法穷尽所有主体在婚姻中对配偶的个性化需求,因此按照内容划分类型未免有所疏漏。这里笔者更认同孙若军教授的观点,按照《民法典》构建的民事权益体系和民事权益位阶作为依据更为合理。而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明确了,夫妻忠诚协议的主要范围是围绕夫妻间性的专一义务,由此,根据《民法典》第五章民事权利的相关区分,笔者认为在认识类型和实际裁判上需要进行不同方式的划分。在泛化认识夫妻忠诚协议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将忠诚协议概括为三个类型,即人身关系型、财产关系型、人身财产关系混合型。而裁判中则需要根据民事权益位阶针对协议内容进行更细致的划分,此部分将在后文阐述。
人身关系型忠诚协议,是指夫妻任何一方在整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做出违反忠诚义务的行为,会导致过错方人身性权利义务关系发生变化。在内容上可能表现为过错方需自残、罚跪、道歉等行为;或涉及人身自由在一定程度上的剥夺;对子女抚养权的放弃、探视权的限制等。
财产关系型忠诚协议,是指夫妻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若有不忠诚行为,过错方需向无过错方支付损害赔偿,离婚时财产分割需少分甚至“净身出户”等惩罚性财产措施。
人身财产关系混合型忠诚协议,兼具人身型和财产型协议的特点,在内容上往往过错方既需要承担人身关系的变化,也要承担财产上的不利损失。
三、夫妻忠诚协议的法律效力分析
(一)夫妻忠诚协议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
关于夫妻忠诚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学界大致有四种学说,分别是有效说、无效说、自然债说、中间说。
有效说认为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条的立法精神,夫妻忠诚协议具象化了关于“夫妻应当互相忠实”的倡导性规定,使忠实义务具有可诉性。无效说则认为,忠诚协议属于道德规范的要求,属于“法外空间”,不应当由法律规制。自然债说认为忠诚义务属于情谊行为,当事人自愿履行时不应当干涉,但当事人以违反忠诚协议之由提起诉讼时,法院也不应当以强制力要求其执行。中间说认为应当视其内容,区分对待其效力。
笔者认为,忠诚协议的内容若不违背法律,不违反公序良俗,则应当有效。《民法典》的编纂体系里使婚姻家庭单独成编,且在第一千零四十三条明确规定了“夫妻应当互相忠实”,足见其立法目的在于促进夫妻关系和谐融洽,弘扬家庭美德,维护社会稳定。有学者认为,《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条是倡导性、宣誓性条款,并不会直接产生请求权。但是通过《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了关于无过错方的权利救济和离婚时的诉讼请求权可知,“忠诚”义务并非只属于道德规制的范畴。且从《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来看,夫妻忠诚协议属于合法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有学者认为,夫妻双方在签订忠诚协议时,未必都处于冷静、理智的状态,一方可能是基于欺骗对方、避免事态升级、敷衍对方等动机之下签订的,不能视为其有真实的意愿表示。然而,笔者认为,行为人在签署忠诚协议时,若非被强迫、威胁或其他影响其做出真实意愿表示的客观原因,其动机并不会影响对于忠诚协议内容的判断,不能因此认为当事人并非真实的意思表示,且动机不应该成为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与否的判断标准。在过错方能够举证自己签订协议时存在影响其做出真实意愿表达的情况时,应由法官自主裁量,是否采纳证据。
夫妻忠诚协议内容的不同,使得其涉及的权利类型也不一样。在忠诚协议里有关于“放弃抚养权”“放弃探视权”的约定,由于这类权利属于法定权利且权利位阶较高,不可以被人为约定剥夺,因此该种条款无效。某些忠诚协议涉及财产权利,如违约需支付的金额、关于离婚后夫妻财产的分割,以及过错方需额外支付给无过错方的损害赔偿,诸如“精神损失费”甚至“净身出户”等条款,应在秉持“显失公平”的原则下,认定有效。混合型忠诚协议同理,应兼顾前述两种协议的处理原则。综上,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应当被法律认可,其中不合理的条款无效不意味着协议整体无效。
(二)夫妻忠诚协议的法律适用规则
《民法典》第四百六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架起了婚姻家庭编与合同编的桥梁,而第四百六十七条、第五百零八条的规定也架起了合同编与总则编的沟通桥梁,使民法典的运用更具体化。关于夫妻忠诚协议的法律适用,应当首先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确定协议的性质和目的。在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首先按照价值位阶排除不应当由主体约定限制的人身权利条款,再按照忠诚协议的性质,根据《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七条的规定,适用合同编通则的规定。具体而言,若忠诚协议约定不忠行为会导致离婚的后果,涉及财产分割的问题可以适用《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的规定;若过错方行为符合《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包含的兜底性规定,则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86条的规定适用。涉及侵权损害的,按照侵权责任编相关条款适用,同时兼顾过错方经济能力,涉及子女利益的,应以子女利益最大化为原则适用。
四、结语
随着社会发展和婚姻观念的转变,人们对婚姻存续期间内的权利意识越来越高,夫妻忠诚协议在很长时间内都属于被回避的话题,然而,回避或者使其成为“法外空间”都不是应对当下婚姻家庭问题的有效手段。《民法典》最大的立法原则就是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而夫妻忠诚协议正是基于双方合意订立的可参照合同条款适用的协议,应当被纳入合法的范畴内,更加精细化、精准化地适用法律规范,为家事治理提供新的思考路径。
(作者单位:吉首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