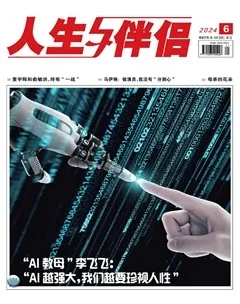人到中年,我也成了没有朋友的“妈妈”

每天晚餐后,父亲都会进入忘情的“网聊”阶段。他总是神神秘秘地关上自己的卧室门,接下来的一两个小时内都不出来,只能听到他房间时而传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母亲总是一边吐槽他,“人都已经退休了,还整天和‘狐朋狗友’聊那些无聊的工作”,一边在沙发上选个舒适的位置,坐下来打开手机,沉浸式开刷。
在我们面前一向唠唠叨叨的母亲,打发时间的方式反而是安静的。除了偶尔和外婆通电话,或者是和忙着带孙子的姨妈发几条信息外,更多时间她都是一言不发地网购或者看短剧。
当然,这是父母随着我到了我所生活的城市之后的节奏。如果回到老家的话,无论是退休前还是退休后,父亲有很多时间都是存在于家人的电话里和别人的生活中。而母亲呢,无论生活在哪座城市,她的行踪都是有迹可循的,退休前“单位——菜市场——家”三点一线,退休后成了“菜市场(商场)——家”的两点一线。当我仔细回想,从我记忆中有母亲那天起,她好像就过着这样没有任何变数的生活。
母亲是家里的长女。跨省工作的外公因突发心脏病在异乡辞世后,当时只有17岁的母亲义不容辞地担起了和外公所在单位对接后事的任务,将外公的遗体运回了故乡。为了外婆和弟弟妹妹们的生计,母亲只身一人远赴他乡。与父亲的婚姻,可能于当时的她来说,算是一个避风港,但是,也是一所时常漏雨的避风港。
父亲那一代的男人,他们时常会互相打趣对方为“妻管严”,但实际生活中,他们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大男子主义。我的父亲也不例外,他时常会以通知的形式,告知母亲自己的哪些朋友要来家里做客,需要母亲提前采购好食材。对此母亲也是牢骚不断,但她的抱怨从未成功改变过事情的最终走向。周末的时候,客厅里烟雾缭绕,餐桌上摆放满了饭菜和酒杯,父亲自然是坐在沙发中间劝菜劝酒的那个。母亲呢,她除了给刚到家的朋友们打招呼和上菜之外,几乎没有出现在客厅。就连吃饭,都是在厨房里匆匆解决。我和姐姐时常不顾父亲示意我们赶紧出去的眼色,赖在客厅里找个角落,聆听着男人们之间的交谈。他们谈工作,谈晋升,谈最新款的摩托车,谈打麻将,却从未谈及做出这顿大餐的女人,身在何处。
沉浸于父亲和他的朋友们营造出来的热烈氛围里的我,至少在成年前,也从未想起过厨房里的母亲。直到现在,我依然能对父亲的朋友们如数家珍,但是我却不知道母亲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朋友,我几乎回忆不起来她曾经和什么样的人关系密切过。如果非要列举一个母亲的亲密朋友的话,我脑海中只有一个人选,就是我们的邻居阿姨,她同时也是父亲朋友的妻子。
不过比起父亲的朋友们来家里做客时的阵势,母亲和邻居阿姨的交往则充满着隐秘性和随意性。我从来不知道阿姨什么时候来的,更不知道她何时离开的。她俩不会坐在客厅里,一板一眼地交流人生。偶尔瞥到她们时,她们也是坐在院子里的某个角落,或者在厨房这样连一张板凳都没有的地方,低声说着什么。
从来没有人像招待父亲的朋友那般,去招待这位邻居阿姨。我甚至从头到尾都不知道阿姨到底姓什么,因为小时候我们都称她为刘阿姨,而刘是她丈夫的姓。自从我们搬离那个小院子后,我便再也没有见过有人特意上门来找母亲。就连那位曾经的邻居,虽然偶尔从母亲为数不多的来电上曾听到过她的声音,但她的身影再也没有出现过。
小孩子大约都有一些慕强心理,面对着一边是事业有成,朋友缘很好的父亲,一边是工作上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同时也没有任何社交的母亲时,我内心的天平自然偏向了父亲。母亲遭遇到的困境,在我看来是可以通过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和社交能力而改变的境况。我质疑母亲的不努力,但随着自己年龄渐长,尤其是结婚生孩子后,可以称为朋友的人数几乎掉到个位数后,才意识到,我也陷入到了同样的困境中。
某次当我和先生因为他过于频繁的社交而爆发争吵时,先生突然来了一句:“我从来没有阻拦你见朋友吧?你现在就去社交啊,今天孩子我来带。”当我赌气地打开微信,却发现不知道该联系谁。通讯录里经常热聊的大多只能算是云朋友,线下同年龄段的朋友几乎都和我一样,处在见一面都要提前几天打招呼的阶段。预约制社交,早已成为“妈妈朋友们”之间心照不宣的规则。即便是提前约好了,也会因家里的各种突发情况而临时取消。
其实我也算是远嫁,大学毕业后,我随着先生来到了他读书和工作的城市。这座城市距离母亲的娘家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所以我一度有一种被命运安排的感觉。不过这样的神奇感并没有持续多久,另一种熟悉的命运已经在不远处等待着。在过了爱情的最初阶段,我才意识到,在这座城市里,除了先生之外,我甚至都没有一个能相约一起出去逛街的朋友。
当时的我首先想到的是融入先生的社交圈,从他那里获得一些现成的朋友。先生的主要社交有两类,工作前的朋友和工作后的朋友。第一类朋友,他们聚会时不会邀请自己的女友或妻子一同前来,整个行程也是简单粗暴。要不就是网吧开黑,要不就是球场相见,接下来的目标也很明确,喝酒撸串。这类聚会我自然参与不进去。第二类朋友则是同事,出席这样的聚会,考虑到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先生的职场风评,连我都得带着几分表演的性质。时间长了,我不但没有获得一个朋友,反而开始抗拒参加这样的聚餐,甘愿成为那个待在家里的人。

后来,我尝试和自己单位的伙伴们建立起一种接近朋友的关系。就在我找到了还算是兴趣比较相投的目标人物,并且两人相处得还算不错时,这位朋友跳槽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跳槽的公司影响了我们可能继续发展的友谊,总之我们开始渐行渐远。一开始我们偶尔还会小聚,但每次见面时,她都会娴熟地从包里掏出一份她和她老公投保的单据,顺便送我一些诸如洗菜盆、打火机之类的小物件,真诚而热情地劝我买同款保险时,坐在身边的我都如坐针毡。后来她又主动约过我几次,但都被我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推掉了。
当然,我也不总是那个主动远离友谊的一方,我也曾尝试过经营友谊。比如说去年春节返回故乡的时候,我主动联系了一位高中时的朋友。当年我们之间的关系亲密到什么程度了呢?双方的父母都知道对方的存在,只要是对方的邀约,父母都会很放心地答应我们出门去。大学后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我结婚前。从那以后,总是因为工作安排或者两人中的某一人在怀孕、需要带孩子、要陪家人等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没有再见过。
我试图从我们的聊天里捕捉到一丝被友尽的蛛丝马迹,但平平淡淡的对话告诉我“无可奉告”。如果回到学生时代,我肯定会因为朋友突然的断交而伤神,甚至会通过给对方写小作文这样的方式来弥补双方的关系,但对已经进入成人世界的我来说,已经熟谙朋友之间的交往不能死缠烂打的道理,况且被工作、家庭琐事缠身的我,也没有时间再去为朋友的来来去去而黯然神伤了。
无论是结交新朋友,还是维系旧友谊,对我来说都有些力不从心,我惊喜地发现远在天边近在手机里的线上闺蜜群,才是最坚不可摧的存在。这个群里的朋友们身处不同的城市,目前的工作和婚姻状态也都不尽相同,最初大家还曾幻想过,像大学时那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闺蜜之旅。随着群里的朋友们一个个结婚、生子,大家都开始默契地回避这个话题。不再背负必须依靠定期见面才能维系友谊的隐形规则后,大家默认为远离自己现实生活的群友们,可以作为最安全的树洞,只管在群里自顾自地分享或者是吐槽。线上闺蜜群俨然是一个源于生活,但已经脱离真实生活的小世界了。
电影《阳光姐妹淘》里讲述了七个学生时代的闺蜜,时隔25年后的重逢,让年少时的友谊得以再次被延续。我虽然为之感动,但我实在无法想象,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已经接受了任何人可能在任何时间离开的现实。甚至,如果能够和学生时代的闺蜜重聚,我也不确定产生于特定环境的友情,是否能经得住现实的考验。
孩子们看待世界的目光很简单,自然不懂在远嫁后的交友这条路上我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陪伴孩子们的时间明显多于先生的我,最近就遇到了儿子的灵魂追问:“爸爸经常见朋友,妈妈为什么不见朋友?”儿子眼中的我,或许已经与我眼中的母亲相重合,我们都成了没有朋友的“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