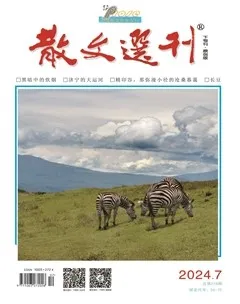吃生活
金宇澄小说《繁花》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礼拜天下午,小毛在家罚写字,却被沪生带去荡马路,直到黄昏才回家。兰兰看到小毛说,肯定要吃生活了。果然,刚踏进房间,小毛娘一把拖过来,头上一记麻栗子。小毛娘说,侬个小赤佬,死哪里去了?
其实一记麻栗子,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小儿科了,哪里算得上“吃生活”。我们小的时候,因为淘气,因为不听话,“吃生活”是家常便饭。上树掏鸟窝,下河摸鱼虾,果园里偷葡萄,实在有点儿调皮。父亲看不惯,恨铁不成钢,痛骂不行索性痛打。
“吃生活”的场面总是伴着号哭大叫和歇斯底里。一天,我与小伙伴们在城墙根捉迷藏,那里是一大片向日葵地。后来,不知道谁出的主意,我们把还没有成熟的向日葵花盘全部摘了下来。傍晚时,邻居老太太找上门来,向父亲告状。我父亲气不打一处来,紧绷着脸,对我怒目而视。我知道一顿暴打就要降临,赶紧拔腿而跑。父亲一把捉住了我脏兮兮的手臂。我转过身,对着父亲手狠狠咬了一口,这更让父亲火上浇油。于是像拎小鸡似的将我拎到院子里,捡起一根竹乌箫。一乌箫抽下来,火辣辣钻心的疼痛,我的号叫声立刻响彻村庄。腰背上、屁股上,顷刻就爬满了一条条蚯蚓似的血痕。
父亲每抽一乌箫,就会厉声地问我:“以后去不去讨债了?”开始,我只是高声哭喊,绝不回答,就像地下党面对刽子手似的。再几乌箫抽下来,在父亲的追问声中,我丧气腾腾地嘶吼一声:“不去了。”父亲再问:“有没有记牢?”我一边哭一边大声地回答:“记牢啦!”然后父亲的怒气消下来,我终于得以解放。我的脸上挂满了泪水,我的皮肉早已血痕道道。
在我们村里,“打是亲,骂是爱”,父母打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他们让我们吃米饭,当然也有权给我们“吃生活”。“棍棒le0P+b00FrrF1e5l6sn7CcVSDiPiF+qhjnjcjB2u16Q=底下出孝子”的古训,是大人打孩子的理论依据。我们的父母,父母的父母,当他们也是孩子的时候,其实也吃过无数次“生活”。等到他们自己做了父母,完全忘了儿时的痛,于是薪火相承,打骂孩子的传统在我们的村子里生生不息。有的孩子顽劣成性,调皮捣蛋,年长的人就会摇着头说,“是大人不打的缘故”。
孩子的玩性远强过记性,我们总是“吃过肚饥,打过忘记”。三天不打,父母的教导成为耳旁的一阵风,就会故伎重演,上房揭瓦,于是,夹杂着鸡飞狗跳的打骂便隔三岔五卷土重来。
其实,父亲是绝不会往死里打我们的,毕竟被打的孩子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更多的时候是掀开裤子打屁股,或在手脚上做些文章,那都不是身体的关键部位,任鞭子在那里抽打,也不碍事。其实,打在孩子身上的鞭子,肉痛的是父亲自己。打的时候是解恨的,打过后就又后悔了。
记忆中,我有无数次“吃生活”的经历,如今重温那时的皮肉之痛,我丝毫没有憎恨我父亲的意思。我知道,我们小时“吃生活”毕竟只有一点点皮肉之痛,而我们的父母,为了家庭操心操肺,还要承受身心的重重折磨。只是,当我们真正理解他们痛楚的时候,他们再也打不动我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