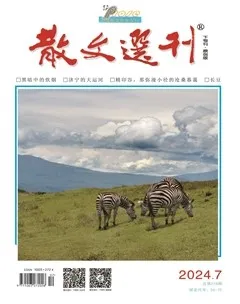姑姑
姑姑是家中当时唯一的女娃,兄妹七个,她是最中间那个。
80 年代,二十出头的姑姑,说小不小的年纪,在鹅毛大雪覆住整个村庄的那天,穿着一身亮得刺眼的红衣,出嫁了,嫁去了山的另一边。
八百块钱,十尺布,便是全部彩礼。绑了红丝带的自行车,两个人推着,晃晃悠悠。“当时只见过你姑父一面,你爷爷说他是家里唯一的儿子,去了能享福,我也就应了下来。”这是姑姑后来告诉我的。
姑姑出嫁后的日子过得并不好,没有像爷爷说的那样享到福。相反,姑姑的快乐与幸福似乎在出嫁那天随着雪中一袭红衣逐渐隐去,最终销声匿迹。
打我记事起,姑姑总是头上包一块头巾,脚上一双布鞋,身上一条永远沾着泥土的裤子。她总是家里最不得闲的那个,从嫁进去的那刻开始,一家老小就指靠她了。婆婆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问:“饭做好了吗?衣服洗没洗?”她的丈夫,也便是我的姑父,是个暴脾气,也是赌场的常客,总是凶神恶煞地冲进院子里大喊:“地里的庄稼怎样了?圈里那几头牲畜今天有没有放出去吃草?”得到满意的回答后,他像个打了胜仗的将军,扭头骑上刚买来的二手摩托车沿着镇上赌场的方向,疾驰而去。最后,还有那个还未出阁的小姑子,过来指指点点,似乎是为了彰显她在这个家里的地位高于姑姑。姑姑如果不作声,她还不忘嘲讽一句:“哑巴了吗?”
姑姑知道,她的确哑了,彻底哑了,不是嗓子,是那颗心。
村里人总能看到姑姑在忙。姑姑在地里耕种,姑姑拿着笤帚在院子里扫地,姑姑给牛羊倒草料。厨房里的烟囱冒出黑烟,他们就会说:“看呀,他们家那个勤快媳妇儿开始做饭了。”
姑姑忙了大半辈子,为婆婆忙,为丈夫忙,为孩子忙,为圈里的猪和羊忙,为地里的庄稼忙,唯独没有为自己忙。就像她身上那件穿了三十几年,早就破烂的灰色短袖嫁衣,一辈子都耗费在别人身上。
姑姑终于有了不用劳动的几天,是在2019 年冬天,因为爷爷去世了。这是出嫁后的姑姑第一次出远门——参加她父亲的葬礼。
姑姑回到娘家时,还是那身打扮,一条头巾,一双布鞋,一条裤子,但衣服却干净得出奇。夜里,万物已安睡,世界似乎也在沉睡中死去,姑姑却开口诉起过往,我也随她在回忆里穿梭。
“你爷爷就我一个女儿,他心疼我,怕我吃苦,才把我许配给你姑父。刚进门那年,我就被他们一家人轮流打,用棍子打,用铁锹打,我疼,但不敢说。”
我心头一震:“为什么不说?”
“我不想你爷爷担心,只要他以为我过得好,就够了。”姑姑睡了,我却毫无倦意。
爷爷坟前,姑姑的哭声擂天倒地,椎心泣血,震得我的心生疼,疼得我和姑姑一样,不顾一切地哭。哭声中,有姑姑与至亲阴阳两隔的不舍,有三十多年忍气吞声,饱受打骂却手足无措的痛苦,更是诉说命运不公,对上天的埋怨。
之后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不曾见过姑姑,听说姑姑有了儿媳,还抱上孙子。直至去年暑期,我完成了阶段学业,寻得时机去往山那边的姑姑家。
车子沿着山路行驶,绕着山一圈儿又一圈儿,像我的思绪碾压着我的胸膛,一圈儿又一圈儿,喘不过气。下了车,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山这边的太阳那样炙热,像个火球,几十年如一日炙烤着大地,把姑姑烤得黝黑,把她的一颗心烤出沟壑。显而易见,姑姑老了,更瘦了,风一吹便能看到衣服下她的骨架。但她的生活还是如常,只是由照顾婆婆变成照顾孙子。
在姑姑家,我停留了大概十天,我只是个旁观者,她的一幕幕场景却要在眼前上演,每一幕都化成一把利剑向我刺来。我躲不开,却什么也做不了,像沉溺在梦境中瘫软无力,只好选择逃离。
离开时,姑姑送我到山口。她叮嘱我路上小心后,便转头匆匆离去。我知道姑姑怕我看到她伤心的样子。不觉中,泪水纵横在我的脸上。我哭她一辈子被困在山这边,哭她一辈子太苦,哭她逆来顺受。
看着姑姑的身影逐渐模糊,我突然有些害怕,怕她终究会在时间的洪流里,在大山的压迫下悄然隐去。
(本文作者系山西财经大学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