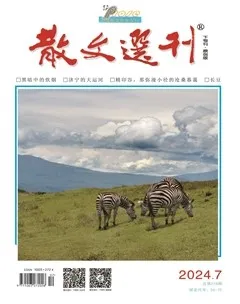我的姥爷姥娘
我的姥爷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种了一辈子地,是种地的老把式,勤劳、朴实、老实、节俭,所有赞扬农民的词用在他身上都不过分。他像路边的小草,像庄稼地里的一棵矮小的禾苗,但是,他却是一名老党员。
在我印象中,有两次比较深刻:一次是我五六岁的时候,在他家吃完晚饭睡了,姥娘把我从床上喊起来,让姥爷把我送回家,我不想走路,姥爷就背着我走。我们家和姥爷家是一个村子的,从村南到村北大概三四里路的样子,我竟然趴在姥爷的背上睡着了。那时,姥爷的背已经有些驼了,但是却很坚实温暖。后来,姥爷的背驼得更厉害了,我走到他面前,他只能仰着脸看我,然后微笑着喊着我的小名,把我让到堂屋里。现在回想,姥爷一生很少生病,即使有个头疼脑热的小病也会很快好的。
另一次是我都结婚生子了,回老家,姥爷知道了,佝偻着身子,步履蹒跚地来了,手里还拎着一条大鲤鱼。还未等我上前去扶,姥爷不小心一脚踩在了淌水沟里,一下子滑倒了,我们吓坏了,我和母亲忙去把他扶起来,找了椅子让他坐下。只见膝盖处渗出了殷红的鲜血,母亲忙端来清水给姥爷擦了擦,又涂抹了碘伏,用纱布给包裹上了。我问姥爷疼不疼,姥爷仍旧微笑着说:“不疼。”幸好没伤着骨头,因为姥爷那时已经有八十多岁了。姥爷不善言谈,坐了一会儿就要走,我和母亲挽留,但是姥爷说:“年龄大了,能走动来闺女家看看就知足了,人老了不能在闺女家住。”姥爷就拄着拐杖晃悠悠地走了,看着姥爷远去的背影,我的鼻尖感到一阵子酸楚。
后来,姥爷活了八十六岁就去世了。
我的姥娘个头儿不高,是很精干的那种,先前当过八路军,也算是老革命。姥娘也是受了一辈子罪,没享过几天福,晚年得了各种病,不到七十就飞升瑶池了。
由于姥爷家门户大,舅多姨也多,母亲一忙就把我送到姥娘家里,反正会有人照看的。姥娘平时做的饭都是粗茶淡饭,但是只要我去,姥娘肯定会做好吃的给我吃。上小学时,我放了学不回自个儿的家,一溜小跑就去了姥娘家,姥娘便围上围裙去小草屋(厨房)里生火做饭。有时我饿急了想先吃点儿东西,姥娘就会拿出一张她自己烙的煎饼再卷上白砂糖让我先吃,姥娘怕糖漏了,就用白线把煎饼的一头绑住,我就从另一头开始吃。那个味道,现在想想都很甜、很香。
在孙子辈里面,姥娘还是比较疼爱我的。我隔三岔五地问姥娘要点儿零花钱,买个雪糕,买个零食,买个西瓜啥的。姥娘每次都会给,多则一块,少则一毛。那时候,买根老冰棍才五分钱。姥娘弄点儿好吃的也会拄着拐杖送到闺女家,比如自家树上结的大枣、栗子、柿子啥的,姥娘会挎着小提篮,里面装得满满的,送过来。
去年给姥爷上三年坟的时候,在他们的老房子的墙上看到挂着的发霉的老照片,姥娘年轻时长得也很俊俏的,五官清秀,目光炯炯,不让须眉;姥爷平头正脸,目光平和,朴实无华。他们很平常,与中国大多数的老百姓一样,悄无声息地来,悄无声息地去。他们热爱那片土地,最终还是那片土地收留了他们。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