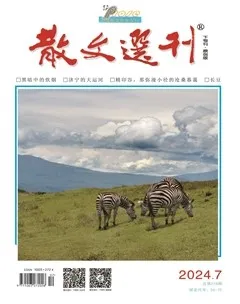在袁隆平墓前
清明时节,我随“爷爷的水稻田”发起人曾松亭博士一行在长沙拜访了袁隆平院士的夫人邓则后,去袁院士墓敬献了花篮。
袁院士的墓坐落于长沙市唐人万寿园陵,鲜花簇拥的墓前铸有两只瓷碗,分别盛着金黄的稻子和白花花的大米。“人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袁隆平院士生前手书的这几个大字,被雕刻在一块巨石上,矗立在墓后。
石刻右边的草坪上,静静地竖立着一把老人家喜爱的小提琴,左边立着一幅卡通画,满脸笑容的袁院士怀抱一大把沉甸甸的稻穗,画面上有他生前题字:“爷爷的水稻田”。袁老生前嘱托自己的学生曾松亭博士就此开展以水稻为主题的公益活动,培养青少年“爱粮食、爱劳动、爱科学”的优秀品质。
一碗稻子,一碗大米,一把小提琴,一幅“爷爷的水稻田”卡通画,袁隆平院士墓边的四样物品,既是他生活的记录,也是亲人对他的怀念,更是他一生为之奋斗与追求的目标和期许。
都说“民以食为天”,可在杂交水稻尚未研制成功及普遍栽种之前,国人却一直被吃饭问题深深困扰。在我的成长经历中,就存留着与粮食相关的难忘记忆。
在我国处于计划经济的上世纪70 年代,粮食是按农村人口与城镇居民进行分配和供应的。时年因父亲下放农村,我一家七口人中,除爷爷奶奶和父亲为农业户,口粮由所在生产队按劳分配,母亲和我们三兄弟属于城镇户口,俗称吃“国家粮”。每月拿“国家城镇居民粮油供应证”去指定的粮店购买定量大米。
那时因稻种问题,农民常年广种薄收。极低的水稻产量,导致大米每年供不应求。人民吃不饱饭,成为存在于我国的普遍现象。
有年父亲所在的村子遭遇旱灾,粮食严重歉收。农村所得加上我们城镇居民户口每人每月定量供应的28 斤大米,远远不够一家七口人糊口度日。为填饱肚子,爷爷和父亲也和当地村民一起去高山界挖葛当粮。他们天不见亮就扛着锄头出门,天黑才各自挑着一担沉重的黄葛回家。在那些大雪封门的冬日,我们一家人围坐在火塘边用柴刀和菜刀刮去葛皮,洗净放在一口石臼里用沉重的木槌砸碎后浸入隔着篾筛子的大水缸里反复搓洗,让葛粉沉于缸底。放置两天后把缸里的水慢慢倒掉,下面就出现一层黏糊糊的淀粉。爷爷和父亲将淀粉做成葛粑粑或葛糊糊给家人充饥,吃得人面黄肌瘦。
记得母亲从家乡调至紧挨某军工厂的一所农村小学任教那年,我们的粮油供应点也暂时划到了军工厂内部粮店。根据当时政策,粮店出台了每本粮册一次性购买七斤以上大米需搭配一斤杂粮的规定。为规避杂粮搭配,我和二弟想出个办法,每人拿个口袋去粮店轮流排队买米。先由我拿粮册购买七斤大米,然后将粮册交给在门外等候的二弟,再由他用同一本粮册排队购买七斤大米。这样,14 斤大米就逃掉了杂粮搭配。前两次做得还算顺利,后来被粮店工作人员发现并将我们扣了下来。他们打电话到当地政府声称有人蓄意破坏国家粮食政策,把我们吓出一身冷汗。直到天黑后公社派人到粮店调查并没收了我们购买的大米方得以放行。
我们上中学后,母亲调到二弟所在中学附近的村小任教。去粮店买米的任务由此落到了二弟头上。某天,二弟不慎弄丢了粮册,这意味着丢了一家四口人的饭碗。急得母亲四处张贴悬赏公告,承诺给予拾到并归还者十元人民币的奖赏。不几天,有人上门送回粮册,母亲兑现了奖赏。当年,母亲的月工资仅三十几元,十元人民币已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后来,随着袁隆平先生杂交水稻的成功研制并在广大农村普遍栽种,水稻产量得以大幅度增长。人民群众吃不饱饭和吃不好饭的现象才从根本上得到圆满解决。国家也取消了粮食定量供应的政策,撤销了设立在各地的粮油供应站点。但当年的缺粮情景,却像一道烙印,留存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深处。
如今,袁隆平院士虽已带着他梦中的“种子”离我们远去,但这位用毕生精力让14 亿中国人乃至世界人民“端牢饭碗”的功臣,留给人们的除了吃不完的粮食,还有宝贵的精神“种子”。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