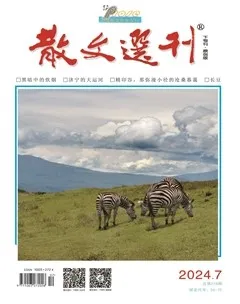精印谷,那弥漫小径的沧桑暮霭
人老了,站在属于自己的高度,看自己能看懂的风景。游北京西山,要走八大处的精印谷,那里有一番弥漫着乡野、青草、情怀的风味,特别是傍晚。
夕阳下行,我从八大处公园的六处逐级而下走,高高山腰,微风从耳边划过,好像在窃窃私语;路上没有人、没有车辆,静谧的小路上只有蟋蟀在草丛里低沉地叫。驻足仔细倾听:翠微山微风潇潇,松涛阵阵,分外凉爽,远山近黛被晚霞涂上了红色。独自走在蜿蜒曲折的山间路上,是一个容易产生思想的时刻。寂寞的小路,路有多远,思想就能走多远。当然,对于大思想家来说,没有路也能思考。2000 多年前,哲学家苏格拉底被囚禁在监狱里,他依然在与专制、暴君抗争,他说过一句话:“思想,能把四壁推向遥远的天涯!”他的话是在2000 多年前讲的,我们现在还能屏息听到,只有深邃思想像耀眼的流星,能够长久地在不尽的时空中穿行,爆发出炫目的光亮。可见,目前能在时间隧道里穿行的,哪怕隔着千层历史迷雾,也只有知识和思想了。也听说过有人设计超过光速的设备,但始终停留在科幻小说的层面上。
走过一道小桥,沿石板路逐级而下,便走进一条长长的山谷。这便是“精印谷”。走在露水湿过的石阶,望望被山峦掩dwiMGo7tuMd1rgtmKCDONQ==盖的夕阳,天空成了碧海,黄黄的一线天,让人看得胆寒。这大概是第四纪冰川期的杰作,巨大的冰川压力和地应力联袂,将大山撕裂,形成了这条鬼斧神工的深壑。“精印谷”蜿蜒向下延伸,我看到,天色更晚了,深谷两侧山坡的石头上、大树下,不时有小松鼠在跳跃、嬉戏。傍晚,是它们快乐的时光。高高的树尖上,归巢的鸟在叫,大声呼唤着同伴。近年来,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加强,山中的小动物也多起来。这无疑是个喜讯。
进入深谷,信步游、粗略看,映入眼帘的是依石而凿的大小篆刻印章。大小不一、错落有致。依山而建,依石而凿,印章大小有异,小如巴掌大如牛。字形、字体则随年代更替凿刻:秦印区、汉印区、唐印区、宋印区、元印区、明清印区……中国的印章,起源于殷商,发展于秦、汉。皇帝用的叫“玺”,老百姓用的叫“印”。“印”是一种诚信的标识。你盖上了自己的章,就表示你愿意承担责任。在唐朝,是不允许随便刻章的,人们也能自觉遵守。不像现在,时有“刻章办证”的小广告。
在前秦印区,出自老子的“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的篆刻引起我注意,其大意是,在顾全黑时,也要注意到其相反的颜色。观察问题,解决问题,也要注意事物的两个极端,他的话,充满了老庄哲学,也反映了印章的精髓所在。西方的油画,讲究背景衬托,而中国画则讲究留白。留白中有很深的内容,就像佛教中的禅,只能悟,不能说,一说就错。中国文化中的这种思想,反映到印章上格外明显,所有空白的地方,应置于与文字同等重要的位置。这实际上讲的是平衡,任何事情都不能走极端,走了极端就会出乱子。
漫步中,走过汉印区,来到“四度泉”边,十几年前,我到这里来过,当时杂草丛生、怪石林立,我从下而上,走得好苦,不得不知难而退。如今,这里干净、敞亮,附近几个巨大的石块,好像刚刚用水洗过一样,泉水边还修了石板路,供游人往返。巨石下的泉水边,正有一老者用舀子慢慢舀水,然后灌进水壶里。泉水很少,需要耐心等待,他不急不乱,慢慢舀,慢慢倒。我大声问:“打一次水,够喝几天啊?”
老者抬起沧桑的脸:“也是乐趣吧。”
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故事和乐趣,好一个豁达、开朗的老人。这一定是个有故事的人。在有生之年,能够找到这种乐趣,也算是大彻大悟了。我极其敬佩地告别了他,继续往下走。弥漫一径的沧桑暮霭很快丢在身后。
走过明清印区不远,便看到门柱上“中华精印谷”几个大字。穿过门柱,便出了山谷,眼前是一条宽敞的柏油路,通向山下。我忽然有些茫然,从秦、汉、唐、宋、元、明、清,直至现代,也就一会儿工夫,正在思索,忽然看到路边有一巨石,被围栏保护。我矗立在围栏边,端详冰山漂砾,许久许久。这块灰色的巨石,300 多万年前,因冰块的挤压,从山上滑落,它身上的擦痕成了历史的见证。也就是在那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地球变冷,进入大冰河时期,随着气候的急剧降温,冰川从南极和北极不断向赤道延伸,苍茫大地,包括北京地区被冰山雪地覆盖,不知覆盖了几百万年。大冰河时期,对于地球上的动物,无疑是灭顶之灾。它使原来温和,从未有过冰雪的温暖时期,转变成寒冷的严冬。大量的动物因饥饿和寒冷死亡。生活在温暖时代的类人猿,突然遇到漫长的寒夜,不但身体无法承受,而且也找不到食物,大量死亡。但也有少数在劫难中找到了求生之路,正是这些劫后余生者,成为未来的智慧人。这件事,学者恩格斯在《劳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作过详细的描述。冰河时期,对于人类的祖先是浩劫,也是涅槃。
近年来,自然界的平衡因人类活动而受到损害,气温不断升高。目前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气温的升高,会使南极、北极的冰川融化,提高海平面,甚至于将地球变为泽国。到那时,人类会有挪亚方舟吗?在考古学上,也有一个“断代工程”,类人猿突然在近百万年的时间里没有了踪迹,有人推想,类人猿因为环境的变化,被迫进入海里,成为“海猿”。这有很多证据,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人类的皮肤,依然可以看到鱼鳞退化的痕迹。但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增加了智能,却丧失了在海里生活的本领,辽阔的大海,已经成为祖先的梦。
走过冰山漂砾,又是一座小桥,路,渐渐平坦,游人也多起来,“三山庵”亭台楼榭已经影影绰绰,能看到卖小吃、卖饮料的小摊儿和听到笑语,烟火气就在远处四散开来。
路过的永远是风景,留下的却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