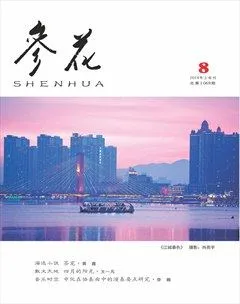童年相册
网知了
进入夏天,天气慢慢热起来了,知了也渐渐多起来了,村前屋后的树木上日夜不停地“大合唱”。白天,歌声给地里劳动的乡亲们解困、解乏;晚上,歌声像催眠曲,伴着乡亲们进入甜蜜的梦乡。
学校放暑假了,我和伙伴快乐极了,嚷叫着“网知了去”。于是伙伴们把家门口晒衣服的竹竿取下来,又拿着一把柴刀,猫着腰钻进村后的一片竹林里,砍来一根细长的竹条,把它压弯成一个椭圆形,用细铁线或绳子牢牢地捆扎在竹竿头上,然后举着竹竿去村里的墙角找蜘蛛网。找到蜘蛛网后,转动手中的竹竿使蜘蛛网缠绕在椭圆形的竹条上,做成网。我们挺有经验的,专找刚织的新鲜的蜘蛛网,因为刚织的蜘蛛网黏性特好,知了一旦上网,想挣脱简直是白日做梦。
只要听到知了的叫声,我们顾不上炎热,举着缠有蜘蛛网的竹竿一溜烟儿似的跑到村前的树底下,抬头屏息,仔细观察,树不算高,可是叶子长得茂盛,密不透风,只闻其声不见其影,一双双眼睛在每一根树枝上认真搜寻,好不容易发现了一只知了趴在枝条上,扇动着翅膀。
这时,谁最先用手一指,知了就归谁了。只见一根竹竿缓缓地伸过去,徐徐靠近知了的头部,近了,伙伴心跳加速,全神贯注;更近了,用竹竿快速地罩过去,知了看到竹竿靠过来,感到情况不妙,想躲避危机,张开翅膀向前方猛冲过去,正好撞在蜘蛛网上。它拼尽全身力气挣扎,可是一切晚矣。看到知了在网上扑腾,伙伴们围了上去,双手捉住它,把它放进一个事先带来的玻璃瓶子里(瓶盖上有一个个的小孔),知了刚开始一副很不服气的样子,在瓶子里一边嘶叫,一边横冲直撞,想冲出去,过了一会儿,许是累了,不叫了,也不撞了,乖乖地趴在瓶底上,一动不动,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通常情况下,每个伙伴都能网到知了,多的时候能网到五六只,少时也有一两只。
凡事讲究技巧,网知了也一样。发现知了后,伙伴们用竹竿悄悄靠近它的头部,因为知了有一个特点,一有动静或发现危险时一般都会往前方冲出去逃走,所以容易网中。我们屡试不爽后,知了也许是摸清了我们的“常规战术”,之后变得异常地精明,不向前飞,而是忽东忽西,让人琢磨不透。
伙伴们凑在一起,商量如何应对。
“来个四面包围。”伙伴们一合计,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此后,只要一听到“歌声”,伙伴们便举着竹竿飞快地跑到树旁边,把整棵树包围起来,这样最保险,任凭知了从哪个方向逃跑,都很难逃出包围圈。
多次“实战”后,证明这个办法管用。
对于高大一点的树,竹竿够不到,我们也有办法,在脚下垫一个小木凳子,人站在凳子上网知了。
听村里的老中医说,知了晒干后可入药,具有祛风散热、利咽、明目之功效。网到了知了,伙伴们有时平分,各自装进玻璃瓶里供人观赏;有时卖给村里一位老中医,换成钱后再平分,用于买文具盒之类的学习用品,或留着开学交学费。当然,嘴馋的伙伴也用来买零食吃。
伙伴们天天在村前的树上网知了,许是知了受到了惊吓,树上知了一天比一天少了。后来我们发现知了转移到村后的大杨树上,继续不知疲倦地“大合唱”。知了贼精贼精的,知道这里相对安全些,愈聚愈多,可是那么高的杨树,竹竿怎么能够得到呢?有伙伴提议,把两根竹竿接在一起,用绳子扎紧,可是一比画,还是够不到。“那就接三根竹竿吧。”又有人说。可是三根竹竿接在一起,竹竿太沉了,哪有那么大的力气举起来呢?伙伴们傻了眼,透过枝叶看到知了,像排队一样,心里猴急猴急的,巴不得一网打尽。
“我来!”就在伙伴们面面相觑,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叫小兵的伙伴,把鞋子一脱,扔在一边,双手摊开,往手上吐一点儿唾沫,双手来回搓动几下,抱紧树,双脚夹住树干,双手往树上爬,那个样子让人想起雨后在地上爬行的蚯蚓。眨眼间,小兵爬上了树,站在一个树杈处往树上张望,一脸的自豪感,因为他看到知了近在咫尺,短竹竿都能够得到。
“把竹竿给我。”他扶着树干,挥着手,压低声音对树下的伙伴们说。
网到了知了,小兵把竹竿慢慢放下来,树下的伙伴赶紧把一只布袋子揉成一个布团儿,用力抛给他。这时他只管往布袋里装知了,毕了,把布袋打一个结,系在裤腰带上。
“左边还有一只。”
“右前头有一只大的。”
…………
伙伴们在树下小声地指点着,生怕惊飞了知了。因为站在树上和树下看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树下伙伴发现了知了,树上的小兵不一定能看得到,所以伙伴们在树下面指挥他。
忙活了一阵子,布袋子里沉沉的,知了不甘就擒,就在里面一个劲儿地扑腾、鸣叫。
这种合作网到的知了,我们大多卖给村里的老中医,这时众人都会说,小兵该得双份。小兵却笑着摇头说,不要不要,平分平分!
现在想来,当年网知了不仅点缀了我们枯燥的少年生活,而且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乐趣。
浇鱼
浇鱼,就是找一口水塘,用脸盆把水塘里的水“浇”干,然后捉鱼。
我小时候居住的村庄紧挨着一条大土坝,坝外是奔腾不息的潦河,河边有一口口大小不一的水塘。准确地说,大的,我们管它叫塘;小的,叫水沟或水坑。
那时生态环境非常好,加上捕鱼工具少,所以鱼儿特别多,潦河的小沟、水坑、水塘都可以看到鱼儿游动或跳出水面的身影,有时村民在水田里耕地都能抓到鱼。
春季天气暖和,鱼儿活动频繁,我们大多选择春季浇鱼。下午放学,我们邀上几个要好的伙伴,拿着脸盆和木桶像蝴蝶一样飞过土坝,来到潦河边。由于放学后临近黄昏,找水塘浇鱼时间来不及。我们讲究“速战速决”,只得专找水沟和水坑浇,碰上水沟长的,用泥土把它拦成一段一段的,用脸盆一段一段地浇,浇完一段,抬头看看天色,天色还早的话,再浇另一段。晚了,就披着夜幕回家。那时几乎每次都是满“桶”而归。
节假日是浇鱼的好时候,时间充足,可以找水塘浇鱼。我们把村庄里年龄差不多大的小伙伴都召集起来,推选出一位“浇鱼能手”当队长。当队长可不容易啊,必须符合三个条件:力气大、能吃苦、能吃亏。队长权力也蛮大的,有分工权,谁带铁锹,谁带脸盆、桶子等由队长说了算,另外,还有一个权力是劳动成果决定权,浇得的鱼是分,还是卖,也由队长做主。
水塘浇鱼不比水沟、水坑,面积大,工作量也大,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我们在水塘地势低的地方挖一条水沟,把水塘里的水引出去一部分,同时根据水塘面积大小分成两小块或三小块,中间用泥土筑一条小路,也叫“间路”。谈起筑间路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不光要筑结实,还不能有丝毫的间隙,一旦渗水或倒塌,那麻烦可就大了,辛辛苦苦浇了半天的水等于白干了。同时间路还要高出水面至少一尺,这样便于储水。筑间路是关键环节,队长带头挥锹铲泥土,先筑一条雏形的小路,然后同伴一起动手,用手抓泥土把间路加宽加高,一边挖,一边筑,为防渗水,不时用脚板把间路踩实踩紧,现在回忆起来,那场面够热闹的。
间路筑好了,伙伴们一字排开,卷起衣袖,手拿脸盆,把水一盆一盆浇过间路。记得那时我们还举行浇鱼比赛,队长一声令下“开始”,接着大声数着“一二三四……”看谁气力足,浇的次数多,伙伴们谁也不服输,憋足了劲,汗水流到嘴角边上也顾不上擦拭。队长见状,大声说“歇一会儿”,伙伴们这才抬起头来,把双手在水塘里洗干净,再擦擦汗水。几个回合之后,我们发现,以间路为界,塘里的水位一边低,一边高。
队长开始巡视间路,不时用警惕的目光在间路上扫来扫去。他最担心的是间路倒塌。
尽管队长小心加细心,每次浇鱼近尾声时,因为水压力大,间路两边的水位一高一低,总会发生一两次间路倒塌的情况,伙伴们纷纷丢下脸盆,拿起铁锹挖泥土修补间路,那场面虽然没有洪水冲垮大坝那样气势汹涌,但是也够惊心动魄的。
间路修好了,伙伴们加油干,塘水越来越少了,鱼儿着急了,纷纷跳出水面,令人眼花缭乱。开始是一两条,接着是一群。当水位没过脚背的时候,大鱼在水里时而乱窜,时而跃出水面,耳畔不时传来“啪啪”或“咚咚”的声音,溅起星星点点的泥水, 弄得伙伴们一身泥点和泥水;小鱼似乎没有什么力气,只是在伙伴们的脚边游来游去,弄得脚趾痒痒的。“开始捉鱼呀!”队长大声叫嚷着。伙伴们有的提着捞兜捕鱼,有的干脆低着头,双手在水里摸索,抓到大黑鱼或巴掌大的鲫鱼都会惊叫:“我抓到鱼王了!”伙伴们抬起头向他投去羡慕的目光。也有伙伴抓到一条大鱼,高兴得不得了,刚想显摆显摆,鱼儿用力一挣扎,手没捉住,“咚”的一声,一头扎进水里跑了,随即传来“哎呀,多可惜呀”的惋惜声。
直到水面平静了,水里的鱼儿捉得差不多了,队长用手指着间路另一边的水塘说:“现在浇这边。”只见他挥动铁锹把间路挖开一个口子,口子前面放上捞兜,防止鱼儿跑出去,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了,又用泥土把口子封住。伙伴们釆用同样的办法浇鱼,我们把这种浇鱼的方法叫“分割浇鱼”。
浇鱼最后一个环节是分享劳动成果。当我们把装有一条条鱼儿的木桶摆放在草地上时,队长忙开了,先把大鱼、小鱼分开,再按鲫鱼、黑鱼、鲢鱼……分成几类,最后按人头把大小鱼儿平均分给伙伴们,多少人即多少份。
记得浇这种大面积的水塘,每人大概分到十多斤鱼,甚至二三十斤,根本吃不了。有的伙伴拿到集市上去卖,有的晒干鱼吃……
潦河边鱼儿最多的时候是涨春水,退水时,水沟、水坑、水塘里半边鱼,半边水,只要一弯腰,随手一抓就能抓到鱼,连妇女在塘边洗衣服都能抓到鱼,你说鱼儿多不多。可惜,如今潦河边的水塘有的被推土机填平了,有的被杂草覆盖了,即便有几口水塘也不见鱼儿的影子……
拾稻穗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的孩子几乎都拾过稻穗。平时学校老师也经常教育我们,珍惜粮食,和我们一起朗读“……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到秋收季节,学校放秋收假了,小伙伴们像笼子里的小鸟一样快活地冲出笼口飞向田间地头。那时生产队有规定:收割完的田,稻穗被挑到打谷场上,才可以下田拾稻穗。那时没有实现农业机械化,乡亲们用镰刀收割稻穗,尽管收割得仔细,但每收割一块稻田,总有一些割不干净的稻穗掉在田里,村民耕地时就会把稻穗埋在地里,怪可惜的。所以天麻麻亮时,小伙伴三五成群挎着小箩筐去拾稻穗。乡亲们在田里耕地,扶着犁耙,扬着牛鞭,嘴里吆喝着“驾——驾——”。牛在鞭子和吆喝声的双重驱赶下,奋力向前耕,掀起一块块的土块,像顽皮的孩子在翻跟头,又像花卷一般整齐地排成一排,一股泥土的清香散发在空气中。田里的鸟儿忽飞忽落,鸟鸣嘤嘤,好不热闹;伙伴们正弯腰一根根拾稻穗,装满小箩筐后,坐在田间小路上,一边哼着无名小曲,一边把稻穗拿出来,放在路边,用手把金黄的稻谷一粒一粒地剥脱下来,放进小箩筐里,稻秆随手扔在田地当肥料;偶尔也有挑稻穗的乡亲们不小心踩到放倒在地的稻穗,稻谷熟了,一踩就脱落,掉落在田里,这儿几粒,那儿几粒,十分显眼。我们蹲下身,从小箩筐里拿出一把筅帚,把稻谷粒扫聚在一起,然后用五个手指头一撮,放进小箩筐里。通常一次撮不干净,再用筅帚扫聚一处,再撮,如此反复,直到颗粒归筐为止。
拾稻穗我们是守规矩的,没有收割的稻田,不去;正在收割,稻穗没有挑走的田里,也不去。那个年代,拾稻穗有时也会碰上危险的事。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田里拾稻穗时,看到田角有几棵稻穗,伙伴们高兴极了,一起飞奔过去,跑在最前面的一个伙伴,快速地弯下腰,生怕同伴抢走稻穗,可是刚拾起来,“呀”的一声,把稻穗扔在地上,吓得双手发抖,脸色苍白,不由得后退几步,被稻穗桩子绊倒在地,我们惊呆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伙伴指着前面的稻穗说:“蛇……蛇。”果然,一条黑色的小蛇扭动着细长的身子,从稻穗里爬了出来,溜到路边的水渠里去了。
那之后我们拾稻穗时格外小心,每人手拿着一根小棍子,只要看到几棵稻穗在一起时,先小心翼翼地用小棍子轻轻地拨开,看看里面是否藏着蛇之类的东西,确定无异常,再上前。当然,拾稻穗也有惊喜的时候,运气好的话,能抓到白色或灰色的小兔子。
拾稻穗其实是件很快乐的事。小箩筐装满了稻穗后,我们就在田里捉蚱蜢玩。蚱蜢有绿色和黄褐色两种,腿细长如丝,在稻桩间蹦蹦跳跳,还会短距离飞行,单靠个人力量往往难以捉住它,因为它太机敏了。我们也有对策,看到蚱蜢在蹦跳,少则七八个伙伴,多则十来个,围成一圈,脱去上衣,趴在地上,像侦察兵一样慢慢向蚱蜢靠近,近了,伙伴们大呼“捉蚱蜢呀!”大家一跃而起,双手举着衣服,像撒一张巨大的网一样罩过去……
拾稻穗虽然是时代的产物,但是我还是十分怀念那段美好而愉快的时光。
(责任编辑 葛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