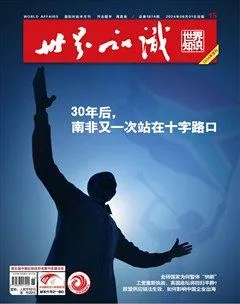特朗普拥有广泛刑事豁免权对美国意味着什么
7月1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3的票数对“特朗普诉美国案”(Trump v. United States,简称“特朗普案”)做出裁定,认为在“干涉2020年大选案”中,作为总统的特朗普拥有广泛的刑事豁免权,即总统在公职行为上拥有刑事豁免权。
2023年8月,因涉嫌推翻2020年联邦总统选举结果,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对特朗普发起四项刑事指控。该起案件又被称为“干涉2020年大选案”。但在庭审前,特朗普律师团队提出了审前动议。该动议称,作为前总统,特朗普在任期间的行为应享有绝对豁免权(absolute presidential immunity)。对此,作为初审法院的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断然予以了否决。此后特朗普又向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上诉法院同样对该动议予以了驳回。2004年2月12日,特朗普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上诉,申请撤销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最高法院于2月28日受理了此案。
最高法院的此次判决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美国最高法院虽然在1982年的“尼克松诉菲茨杰拉德案”中裁定,总统在公职行为中享有绝对的民事豁免权,但一直没有对总统是否拥有刑事豁免权做出解释。在“特朗普案”中,最高法院做出总统在公职行为上拥有刑事豁免权的裁定,不仅将影响特朗普个人的政治前途,也会对美国宪政史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总统豁免权的法理依据
美国宪法只规定了总统可以被弹劾,但并未明文规定总统可以被起诉。美国总统豁免权是最高法院大法官在解释宪法特定条款过程中,创立并逐渐发展出来的。总统豁免权是指总统在任期内,因其行使宪法权力而采取的某些行为,可以免除民事和刑事起诉,且免除其因该行为而带来的法律责任。1985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米切尔诉福赛思案”中提出,豁免权的核心在于,拥有豁免权的个人或机构不需要在法庭上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在法律诉讼中免除责任。作为三权分立的一支,总统具有超然于其他权力部门的特殊宪法地位。从法理来说,总统享有豁免权主要基于以下几个理由:
一是确保总统有效履行职责。总统的职责繁重且复杂,涵盖国家安全、国际关系、经济政策等广泛领域。如果总统频繁面临司法诉讼,可能会严重干扰其履行职责的能力。豁免权确保总统能够专注于国家事务,而不必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应对法律纠纷。
二是确保行政分支的独立性。总统作为行政部门的最高首长,需要在行使行政权力时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豁免权可防止其他政府部门或个人通过诉讼影响总统的决策和行动,从而维护行政权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三是防止滥诉。如果总统不享有职务行为的司法豁免权,可能会遭到大量基于政治动机的诉讼,这不仅浪费司法资源,还可能被用作政治工具来削弱总统的权威和信誉。司法豁免权有助于防止这种滥用法律程序的行为 。
四是美国历史和法律先例。美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关于总统职务行为豁免权的法律争议和判例。例如,美国内战期间,林肯不顾宪法约束,颁布行政命令,下令暂时中止一些不稳定地区的人身保护权,授权军方可以任意逮捕他们怀疑与南方“叛军”有关联的人。尽管首席大法官做出了不利于林肯的判决,但是林肯依旧推行他的战时政策,并最终获得了国会授权。关于总统豁免权的解释,也已有几个法律先例。例如,1982年的“尼克松诉菲茨杰拉德案”裁定总统具有民事豁免权;1997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克林顿诉琼斯案”中进一步明确了总统在公职行为方面有绝对豁免权,但如果涉及其个人行为,仍然可以在其任期内被民事起诉。这些判例强调了维持政府运作的连续性和效率的重要性。
甄别工作将非常困难
2023年8月,因涉嫌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史密斯对特朗普发起四项刑事指控。在起诉书中,史密斯对特朗普干预大选的行为分为四类:一是特朗普“伙同”他的代理司法部长、司法部其他高官以及白宫高官等“同谋者”,一起调查所谓的拜登阵营“选举欺诈”,并向一些州发出了信函,要求彻查此类“选举欺诈”;二是特朗普向副总统彭斯“施压”,让他在阻止国会对拜登胜选进行认证中发挥作用;三是特朗普与联邦行政部门之外的人互动,“共谋推翻大选结果”,这些人包括州级官员、私人代表、律师以及一些州的公众等;四是在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山骚乱”中,特朗普的种种行为,包括向他的众多粉丝发布了一系列推文,“怂恿、蛊惑”他的支持者在当天前往华盛顿特区,导致了骚乱的发生。

“特朗普案”的历史贡献之一就是根据总统的行为是否属于公职行为,把豁免权分为以下三类:一是美国总统权力的本质是总统行使决定性和排他性的宪法职权时享有免受刑事诉讼的绝对豁免权。特朗普同他的代理司法部长等一众高官调查大选中的欺诈行为是总统的职责所在,有宪法依据,该行为享有“绝对豁免权”。二是总统任期期间还至少应享有对其所有公职行为的推定豁免权(presumptive immunity),特朗普“施压”彭斯阻止国会对拜登胜选认证的行为目前暂时推定为具有豁免权。特朗普“施压”彭斯的行为比较复杂,是否属于公职行为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甄别。三是总统的非公职行为则无豁免权。特朗普与联邦行政部门之外的人的互动,以及特朗普在“国会山骚乱”中种种行为,是否属于公职行为,需要仔细而科学地甄别,如果是非公职行为则无刑事豁免权。
在“特朗普案”中,多数派大法官把甄别特朗普公职行为的难题推给了初审法院,使得初审法院法官塔尼娅·丘特坎面临巨大的压力。她必须重启“干预2020年大选案”的审理,甄别特别检察官起诉书中的哪些指控构成公职行为,从而可能根据最高法院裁决免于起诉;哪些行为不属于公职行为,可以被起诉。丘特坎这项剥丝抽茧的审理工作将备受瞩目,甄别工作需要数月时间,这也就意味着今年大选日前,特朗普不大可能因为该案件而被审判。
甄别工作确实非常困难,主要存在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公职行为与非公职行为界限模糊。2020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特朗普诉玛泽会计公司案”中也承认:“总统个人行为与公职行为界限并不总是清晰的”。二是要求陪审团甄别总统行为存在一定风险。一般来说,美国的刑事案件,特别是重罪案,一般都有陪审团参与审理,“特朗普案”也不例外,这是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所规定的。在“特朗普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多数意见认为,允许检察官要求或建议陪审团探究总统享有豁免权的公职行为,将引发一个“独特的风险”,即陪审员的审查将因其对总统在任期间的政策和表现的看法而受到个人偏见的影响。而且,甄别总统的行为是否属于公职行为,涉及宪法解释和政治问题,这超出了陪审团的能力范围。
是“捍卫宪法”还是“对民主的践踏”?
“特朗普案”的裁决又一次体现了美国最高法院内部保守派阵营与自由派阵营的对决。索托马约尔代表三名自由派大法官撰写了少数意见,猛烈抨击六名保守派大法官撰写的多数意见,称其创造了一种“脱离文本、无历史依据且无法证明的豁免权,将总统置于法律之上”,表达了他们对民主的担忧。然而,保守派大法官认为,赋予总统一定程度的刑事豁免权不是要庇护特朗普,而是要保护总统行政分支,这恰恰捍卫了美国宪政体制。如果总统不享有刑事豁免权,每位继任的总统可以自由起诉他的前任,将使得在任总统因为害怕自己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而无法大胆地履行职责……这种党派纷争的循环所导致的总统和整个政府的弱化,或许正是制宪者意图避免的。因此,代表保守派的罗伯茨大法官认为,自由派大法官“发出了令人不寒而栗的厄运之音,与法院今天的实际做法完全不相称”,自由派大法官“在极端假设的基础上散布恐惧”,且法理依据薄弱。
在当今政治极化背景下,美国最高法院已深陷两党无休止的政治恶斗中。两党党争严重危及了美国民主。早在1796年,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在其总统告别演讲中曾提出警告:“党派之争的精神,可以在自由的政府中被视为一种威胁。它从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但政府需要采取措施防止其过度的增长。党派精神会造成偏见、仇恨和复仇的恶性循环,损害公共利益,破坏政府的权威。”华盛顿当年的告诫正在今天的美国上演。
美国党派恶斗涉及政治理念、政策优先事项和选举策略,这些是立法和行政部门的职责范围,法院无法通过判决改变政党的行为或理念分歧。然而,面对两党恶斗,法院却又难以置身度外,司法沦为美国两党推行己方政策、打击对手的工具。从2000年的“小布什诉戈尔案”到“特朗普案”,美国最高法院迈过“政治荆棘丛”,充当了解决两党政治纷争的角色。而最高法院在美国政治制度中的角色是保持司法独立和中立,其裁决应基于法律和宪法,而不是党派利益。如果最高法院卷入党派斗争,它的中立性和公信力将受到损害。就像在“特朗普案”中那样,尽管保守派多数意见不断强调,基于总统的公职行为赋予总统一定程度的刑事豁免权,是为了避免总统遭受滥诉与报复,让总统安心履职,旨在捍卫宪政,但是出于对最高法院中立性和公信力的质疑,民主党阵营的官员和民众很难相信,做出该判决不是基于党派利益。
(作者为南京审计大学法学院、国际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