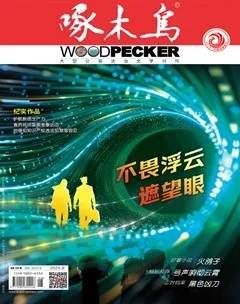水中的奥菲利亚

我采访过她。大约是七八年前吧,那时她就算大龄剩女了,有独立的事业,勤奋自律,还有天赋。而我,则是个刚出道的记者,懵懵懂懂,满脑子不切实际的幻想。采访期间我时不时神游天外,想象着奋斗多少年才能成为她的样子。
至今我也没有能够成为她。不幸,也万幸——她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警方还没搞清楚,现场没有遗书,也没有发现明显的他杀迹象。这就是秋生把我找来的原因,他想知道我们还有没有交往,是否了解她近期的生活状态。
可惜,我对她的了解仅限于社交媒体,而这方面,我知道的恐怕还不如警方多。我们互留了微信,却从没真正意义上聊过天,更谈不上见面了。我只是在朋友圈里看到她的动态,美食、时装、旅游,背景是卢浮宫、梵蒂冈或帝国大厦……永远是她刻意展示给别人的风景,永远是她一个人的身影。
面对秋生的询问,我只能表示爱莫能助。但我提出了一个不情之请——能不能去看看她死去的地方,算是一种凭吊吧,为她,也为我自己。
现场勘查已经结束,她的遗体也送去检验了。迎面碰上两个刚刚清理完现场的民警,擦肩而过的时候,我听见他们的聊天,大意是从没见过这么干净的现场,死者太勤快了,仿佛担心死后给别人添麻烦,事先把所有东西都归了位。“你能想象吗?”其中一个民警感叹,“浴室的镜子上,竟然连一星儿牙膏沫都没溅到。”
或者溅到了,但被她随手擦掉了。正是我记忆中的她该有的样子。警方没有在公寓里发现第二个人存在的迹象:浴室里的牙具只有一套;鞋柜里的鞋都是女式的,哪怕是拖鞋,也只有适合她自己的尺码。至少从表面上看,不但没有人和她一起住,连上门拜访的客人恐怕也没有——她甚至没准备自己尺码以外的拖鞋。
同事们对她的评价是敬业投入,还有开朗乐观包容和团队精神,总之,一个领导的全部优点她都具备。可工作以外,没有任何同事了解她的私生活。而此刻,在她的生命逝去之后,我试图发现她不愿展示出来的另一面。
我能想象出她躺在浴缸里的样子——哦,对了,她是死在浴缸里的,表情平静恬淡,没有挣扎的痛苦,就像水中的奥菲利亚,只是头上的花环变成了一对蓝牙耳机。顺便提一下,这是我一直梦想拥有的按摩浴缸,要说贵也真不算贵,至少我负担得起。我负担不起的是容纳浴缸的空间,这个浴缸比我的床还大,而浴室的面积完全匹配得上她独自居住的大平层,尽管一个人住实在是太大了。我怀疑除了客厅卧室和浴室,其他房间她是不是都进去过——据她的同事说,她每晚至少工作到十点以后,第二天上班总是第一个到,周末都很少休息;而她休假大半在国外,哪有时间熟悉这么多房间呢?如果警方发现这个大平层里同时住着一个和她互不干扰甚至互不知晓的室友,我都不会感到意外。
手机就放在浴缸边缘延伸出来的台面上,屏幕如同浴室的镜子一样光洁。解除锁屏后,显示出来的是依旧处于打开状态的QQ音乐界面。还有酒杯,也在那个台面上,她伸手就能够到的位置。原来她喝酒,而她的同事说她滴酒不沾。
那是一个锥形高脚杯,里面只剩一点儿残酒。我猜应该是鸡尾酒,什么杯子喝什么酒,她在细节上一向是一丝不苟的。果然,警方的鉴定结论是马提尼,里面掺了安眠药,但远远不到致死剂量。在卧室的床头柜里也发现了安眠药,还有医生的处方。因此,依然不能确定是自杀还是他杀——酒杯和手机上只有她自己的指纹,放置酒杯和手机的台面上,甚至没有留下一丝印痕,就像浴室的镜子,都被她(当然也可能是凶手)擦干净了。又或者,既不是自杀也不是他杀,她只是想洗完澡马上就能进入睡眠状态,所以提前吃了安眠药,却没想到药效发作得这么快……这也符合尸检结果,她的确是在睡梦中被淹死的。
然而,开朗乐观敬业的她,不但喝酒,还失眠。我心里怀着遗憾和歉意,酝酿着下一篇报道的主题,那一定是一个迎合大众口味的主题,嗯……痛斥资本推动的消费主义导致的剩女现象怎么样?比如此刻,梦想着拥有一个能够安放大号按摩浴缸的浴室空间的我,正准备再消费她一次,哪怕她已经死了。
但是等等,这个主题的前提是,她必须是自杀的,至少也是一场事故。但如果是他杀呢?我这篇稿子就又成了千篇一律的案件报道了。我第一次意识到,居然有比报道杀人案更容易上头条的题材。
那么,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呢?读者朋友,您知道吗?
(8月31日截止答案,参考答案见第9期,“八月侦探榜”见第10期)
责任编辑/季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