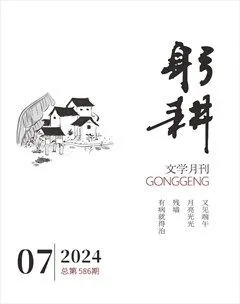黄河泥
我的书房里,放着一块很特别的石头。它是在黄河河道里偶然捡到的,个头只有摊开的手掌大小,整体呈椭圆形,浑身包裹着土褐色的干泥,边缘略微显出深黄的石头底色,好似裸露着的骨骼,恰与河底泥沙同色;如果仔细看,一圈圈不规则的浅黄纹路若隐若现,如河面荡起的水波纹。
别看它“土”得掉渣,我却视为珍宝。捧着它轻抚,就觉得满架书香,都不如泥土独特的味道。那不时散发的氤氲香气,是发自灵魂的。因为正是邂逅“黄河泥”,才让我真正了解了母亲河——黄河。
“黄河水,黄又黄,黄河岸边是故乡……”身为一个河南人,我却没有近距离见过黄河。渐渐地,无数次擦肩而过的遗憾,促使我专程为看黄河而来。车穿行在莽莽苍苍的山间,峻拔奇伟的太行山麓,王屋、黛眉二山环伺北围,又微微隐没于云间。仲夏的山上植被茂密,流水潺潺,我们要去的地方正是黄河三峡尽头的一个小镇。
一进洛阳新安县境,我就掩饰不住激动的心情。杜甫《新安吏》中的诗句“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马上跃入脑际。当年老杜路过新安,看到官府征兵的愤懑和感喟,早已淹没在过往的尘埃中,留下的“新安道”让我们钩沉那段伤痛的历史。也许,只有在这里,诗的灵魂才能得以重现吧。
车还没有停稳,不知谁叫了一声:“快看,黄河!”同车的人一齐伸长脖子,向深涧下张望,哪有黄河的影子?只有掩映在花间和树丛中的苍莽罢了。
俗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一个雨后的黄昏,我和几个同伴约好到黄河的“荒坡古渡”。这里地处石井镇,在黄河小浪底大坝上游,是八里峡的出口。既是峡谷出口,又是多雨季节,河水该是一汪碧水,还是滔滔涌流呢?要不怎么会有“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的气魄!这个码头在黄河和清河的交汇处,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你是否能想象当年万船齐发,掀起的滔天巨浪?又有多少战马嘶鸣、狼烟四起的场景一次次不停上演?还有多少商贾游客在这里穿梭,更有多少人凝望远走的亲人和朋友?
近了,近了,很远就看见一个荒坡下斜卧着一弯浅滩,近乎干涸的河床像一条巨大的黄蟒,在淅淅沥沥的小雨飘洒中,曲曲弯弯地伸向天边。河滩里仅横着两三只小船,仿佛在等着什么。河水呢?呈现在眼前的怎么只剩下一汪,或者说只是一掬,难道这就是我日思夜想的黄河?拨开坡上的杂草,仍能寻见乱石丛中寂寞的铁链和残存的砖石遗迹,是在昭示它作为渡口的明证吗?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它孤独地静默着,静默得让人不可置信。
我不免有些失望,可就这样打道回府,似乎心有不甘。心想,干脆探探黄河道,也算是不虚此行了。我们找了根木棍拄着,攀着铁索,慢慢探身下去,行走在她曾经奔流不息的河道上,贪婪地呼吸着来自三千多年前的气息。河床里泥土龟裂,有的略略鼓起成一个个马蹄的印迹,好像有马队经过一样。我们仔细辨认着,轻嗅泥土中散发的特殊味道。不久,一个同伴瞬间有了新发现:淤泥中竟然有一股羊屎味儿!
大家猜测,黄河岸边或河道里放牧过羊群,河水暴涨时,羊粪被冲刷下来,久而久之就淤积在河道里了。先前看到的蹄印应该是羊蹄印,是河道快干涸时羊群留下来的吧。我出神地想着群羊你推我挤的画面,一个人竟走到了河道中间。突然身子猛地趔趄一下,右脚一下子陷了进去,大家一齐惊呼起来。幸亏我握紧手里的木棍,看见脚边有块石头,就借助棍子的力量,“嗨”地拔出一只脚,正踏在那块石头上,大家赶紧来拉我,这才转危为安。从深陷在淤泥中的棍子判断,河底泥沙至少能没膝了。
定了定神,回过头,看见那块救命石头,已被我踩得深陷在松软的泥里,只露出半个头,根本不见“庐山真面目”,倒更像个顽皮的孩子,正在探头探脑地张望什么。我爱怜地蹲下,把它拔出来,抚摸着满身泥泞的它,找片大树叶包好。不知什么时候,雨停了,天色暗了下来,大家也不再停留,攀着荒坡上的藤蔓又上了岸。
路上,我不时轻轻触摸石头上的河泥,感觉犹如婴儿皮肤一般,细腻光滑,好像还有直立感。用手捏一下,明显觉得土质和普通的稀泥不同,应该能制作泥塑。同伴告诉我,这种泥是做“澄泥砚”的原料,叫“黄河泥”。“澄泥砚”烧制工艺十分讲究,不仅要把河底泥沙中的细泥过滤、澄清、晾干,放入模具中成型,还要用竹刀雕琢图案或花色,放进窑内烧制,方可完成。
哦,黄河泥,还有这个用途!
看着附着在石头上的泥巴,不禁心生敬意:在数千里黄河流域的怀抱里,孕育和沉淀着独特的艺术瑰宝——黄河澄泥砚。她任凭河床被无数遍冲刷,用特有的执着和坚守,用自己的隐忍,蕴含着黄河的精华和力量,默默沉积下来。经过岁月的洗礼和自然的筛选,泥质逐渐变得纯净、细腻,内心也变得坚硬起来,既有韧劲儿又有黏性,最终成就她沉稳、内敛的品质,这是在黄河汹涌澎湃的河道和温度极高的烧窑中双重锻造后,才凝聚成的灵魂香气啊!这和人一样,经过千般淬炼,万般打磨,才能磨砺出人生最美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