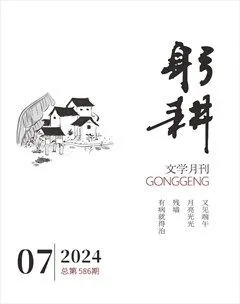月亮光光(二题)
月亮光光,把牛吆到房上。
房上没草,吆到沟垴,沟垴有狼哩,吆到花场哩。
花场里拾了一把野鸡毛,拿到河坝摆去了,河坝老鼠撵来了。
老鼠哩?猫吃了。
猫儿哩?狗吃了。
狗儿哩?钻山了。
山哩?河拽了。
河哩?日头姥姥晒干了。
——童谣
应是一个大雪天。麦村陷入寂静,偶有脚步声,从巷道深处走过。雪,起初落在瓦片上,落在院子,落在瘦路上,落在一只鸡的薄梦里。后来,雪,就只落在雪上了。
炕洞里,青烟冒出,带着几分幽蓝,袅袅升起,融于白雪,不见了。
我在被窝里,如一只兔子,蹲着,只留出脑袋在被外。炕有点烙,被窝温热。寒冷在屋外流淌。祖母给我念起了这首叫《月亮光光》的童谣——月亮光光,把牛吆到房上。房上没草,吆到沟垴,沟垴有狼哩,吆到花场哩……那时,我家养着两头秦川牛,毛色栗红而光滑,眼睛鼓圆而湿润,它性格温驯,喜好啃食灰菜。在祖母的童谣里,我似乎看到了自己在月光之下,把牛吆赶到了屋顶,月光照着我的额头,照着牛的脊背。瓦片灰蓝,层层叠叠,没有一根青草,我又吆赶着牛,去了山沟里,山沟深远幽静,月光照不到的地方,满是漆黑,我隐约听见狼叫……恐惧袭来,我抬头,看到了祖母的白发,和窗外的白雪,一样白。
多年以后,祖母离我们而去,长眠于黄土之下。有好长时间,祖母离去的空缺,如同有人在心坎上凿去了一块,风吹来,总有疼痛之感。
而在另外一个夏天。午后,燥热依旧,我们赶着牲口,去放牧。那是一块河滩。不久之前,河里水波荡漾,草鱼出没。但后来,河干枯了,鱼只把篦子状的骨刺留于泥土。那块河滩,青草茂盛,有齐腰高,是放牧的理想之地。
伙伴们把牲口赶进河滩,去捉蚂蚱了。
我坐于树下,看着青草深处的牛,脊梁如一道桥,供昆虫们来来回回走着。空气里,只有牛粗重的呼吸声和扯着青草的撕裂声。风把蚂蚱的叫声吹向了东边。葵花金黄,盛大而辽阔,把脸统一朝向西边。
后来,灰爷赶着自己的两头灰毛驴来了。驴进河滩,他和我并排坐于树下。树荫披在我们肩头。我们说起蚂蚱,说起莓子,说起河流的秘密,当然,很多时候,都是他说,我听。最后,他说到了我的高祖。一个长工,力气很大,能把一百二十斤的麻袋抱起,丢于肩头,腰杆一伸,走了。后来,土匪作乱,拍马提刀来到麦村。村人皆已逃往堡子避难,高祖未来得及逃离,被土匪迎脖子一刀,差点被砍掉脑袋,仅靠食管“藕断丝连”。高祖扯一圈锅盖上的麦草,缠于脖颈,不顾鲜血直流,一手扶起已歪斜的脑袋,一手翻墙而逃。高祖,活了下来。
那个午后,在灰爷的讲述里,我两鬓冒汗,不知是树下闷热而致,还是那惨烈的场面带来的惊惧所致。但我清晰地闻到,血腥从青草缝隙中,升腾而起,弥漫了童年。
我曾想,已入古稀之年的灰爷,掌握着我家族更多的往事。若有机会,我想知道更多。然而,终是遗憾,我再也没有和灰爷共同拥有一个午后。我们也曾多次照面,但多是寥寥数语,然后各自散去。那个遥远的夏日午后,也成了某种回忆。
还是后来,灰爷病故。他家的灰毛驴,也卖给了驴贩。那个河滩,依旧铺平于沟壑之间,夏天,青草茂盛,秋天,蓼花灿烂。只是再也没有牲口,从草丛中伸起头颅,长长出一口气,然后打个饱嗝。它的眼里,装满夕阳。那些河边的树,依旧把阴影投下来,破碎的光斑,如漏网之鱼,从树叶间弹下来,曾落在一个少年和老人的头顶。就像一些时光,裂出的斑驳碎片。
春天刚来,父亲就去兰州拉架子车。
那时我们年幼,不谙世事,对于父亲远去他乡,并不当回事。应是凌晨四点。我被父亲和母亲的谈话吵醒,尽管他们把声音压得很低。屋子灯亮着,蜡黄的光,昏暗,虚幻。我歪过脑袋,看到父亲在地上,正往化肥袋中装被褥,被褥太厚,用绳捆绑着,勒出了一圈圈“赘肉”。母亲从厨房进来,放好碗筷,帮父亲把被褥塞进袋中。父亲端起碗,坐在椅子上,把饭吃毕,瞅了一眼墙上的钟表,起身,背起化肥袋,出门时,发现我醒着,走过来,摸摸我头,说,听你妈的话。然后出了屋子,母亲跟在身后,提着布包,包里装着熟鸡蛋,去送父亲。天还很黑,如同陷阱。父母的脚步声叩打着那黑,在大门哐当一声后,消弭于更大的黑了。
母亲送完父亲回来,顶着满头夜色。她舀一碗饭,给我吃。摇醒妹妹,也舀一碗。洋芋粉条烩菜,有肉片,有荷包蛋,油很旺,撒了葱花。很香。这是母亲能做得最好的伙食了。
之后的日子,很长很长,我们没有父亲陪伴。春种夏收、起早贪黑都是母亲的。
父亲去兰州拉煤了。村里有不少人去兰州拉煤。在煤场,把煤块装进架子车,然后送到所需要的人家,挣点人工费。去兰州拉煤的人,有些已立稳脚跟,租了房子,安家落户,带走了妻子儿女。某一天,那些和我在同一个教室念书的不来了,后来才知,去兰州了。有些如同我父亲,候鸟一般。立稳脚跟的人,从此,也就不用回麦村了。他们出走多年,也带去了亲戚朋友,让更多的人,在黄河的泡沫里寻觅生活。他们走后,院落空旷,大门紧闭。不用几年,那屋舍也坍塌了。
关于他们的生活,当父亲跟母亲谈及时,我略有耳闻。他们对父亲,很是热情,常会叫他去吃饭。然而他们终究于我,是模糊的,他们的生活,也并非如意,那些煤火中的光焰,并未照亮他们的日子。在这种不如意里,时间,就如同父亲要去打工的那个凌晨,恍惚,虚幻,甚至遥远。
到了秋天,村里人并没有等到他的消息。
寒雨撤身而退,山川潮湿,枝叶腐烂。白霜很快就来。而他的亲人要赶在白霜之前,找到他,哪怕找到他的一缕消息。不能再等了。
一群人离开麦村,去了远方,湖北、河南,甚至更远,都是麦村人不能了解的世界。然而,当他们回来时,只带来了一个虚幻的消息。那个在外地谋生的人,没有了。他究竟是否存活于世,人们多方打探,筋疲力尽,还是不得而知,最后只能在一场大雨里无功而返。
一个人莫名消失了。一个人是否真的存在过,都值得怀疑。
我依旧记得他的相貌。中等个,脸色白净,梳一个中分,爱穿西装。他比我大几岁,我上小学,他已是初三毕业。毕业后,去了外地打工。一去多年,只在逢年过节或亲人丧事中,来过几次。沉默寡言,淹没于或悲或喜的人群中,偶尔叼一根烟,耷拉在嘴皮上,似吸非吸。节后,或丧事一毕,他便离开了麦村。究竟去了哪里,也说不清,总之是外地。
人们回来后,渐渐地,村里多了一些传言。大多是说他早已不在人世。于是那个秋天,树叶红得伤神,很早就落了。村庄陷入了巨大的不安,有一种浮若游丝的恐惧在村庄的每一个缝隙里弥漫,最后,人们在午夜听到了某种怪异的叫声,在秋雨迷蒙中看到了某个模糊的背影,在午后看到了一片瓦莫名跌落摔成碎片。
于是,白霜,在某个黎明,落了下来。
日子就是这般,春夏秋冬,又是一个春夏秋冬。慢慢地,很多人走了,还有一些人即将走了。他们走了,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品性,他们所秉承的习俗,也便通通消失了。除了麦村人和他的亲朋,再没有人记得他曾存在过。而就连麦村人和他的亲朋,也在不久以后,将他淡忘了。没有什么将他记录并留存,平凡者是无法拥有历史的。
于是,很多个日子,我常常念及那些离我们而去的人,或者,游荡于麦村的每一户人家门前。他们已成往事,在一个人的记忆中,被尘土满满覆盖。他们有的紧锁门户,有的房屋倒塌,有的仅留出一片空地,成为遗址,有的已被荒草遮蔽,了无痕迹。可以前,他们真的存在于此,他们日出下地,雨来关窗,养满鸡鸭,种满庄稼。他们在灶台前下面,在供桌前屈膝,在土炕上生儿育女,在西北的风沙中打骂,在爱恨的泥淖里滚爬。
可他们都去了哪里?
在好多时候,我都问自己这个问题。我把麦村翻开,如同翻出一袋洋芋,一颗颗数下来。那一户户人家,逐渐清晰,像有人打着灯盏,把一颗颗洋芋照亮。他们的往事和归宿,在微光下,隐隐浮现。几十年了,那离我们而去的人和人家,或搬迁走了,或因事故殁了,或病亡了,或悄然失踪了,或来了又走了,等等。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最后弥散在大地之上,只留下一段回忆、一抔黄土、一片草木。
细细数来,有些人已模糊不清,有些往事已随风而散,那就这样吧。而能想起的,除了回忆,也需要别人来补充和佐证,好在最后有了一个轮廓。而同时,我想如果真实的麦村不是有近百户人家,而是有二三十户,这二三十户就是这些已不存在的人家,他们组成了另一个麦村。那么,如今麦村是不是早已不存在了?是的。
在这片辽阔而斑驳的大地上,定是有这么一个麦村的。我在一个堡子里见过,几十户人家,都已不存在。堡子宽厚的手臂,拦着这个村庄。院落废弃,屋顶塌陷,黄土砌成的墙,被风雨剥蚀得七零八落,只有一个牧羊人,赶着盛大的羊群,在村里晃荡。我同样在一个山顶见过,还是几十户人家,都已搬离。黄昏时分,参天的洋槐把天空遮住,地上留着黏稠得发绿的阴影。我在巷道里走了不远,便退了出来。寂静,连风吹树叶的声音都没有,让人恐惧。
那就让这些消失的人家共同组成另一个麦村吧。而我,就写下他们或平淡无奇或轰轰烈烈的历史吧。
在另一个春夏秋冬,他们依然蓬勃地生长着。在纸上,而不是田野里。
月光电影
五月,细嫩的风,滑过田野,村庄安详,最后一抹黄昏静静褪去,有鸟,落上柔软的枝头,弹起一缕尘埃。炊烟绵长,牛羊飘进院门。
饭后,母亲说,今晚有电影,早点去看吧。一想,已经十多年,没有在村里看过电影了。
忙完琐事,推门而出,一袭夜色披满山坡。有风吹过,洋槐、杏树、白杨的叶子,拍掌而歌,或许在互说心事。目光所及,七八点灯光,像橘,挑在夜空的手指上。脚踏三两声犬吠,高低不平,来到村西头,我们叫“钢磨院”的土台上。
土台一米多高,台子四周长满野草,台下堆满砖瓦。电影早已开始,荧幕挂在一面土崖上,正好,崖面平整陡峭,有如刀切,高三五丈,荧幕挂上,视野开阔。土台上,或坐、或站、或骑在树上,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老人手持烟锅,坐在小凳上,像安静的雕塑,偶尔会憋气抽一口烟,火星一明一灭,浓稠的烟喷出口鼻,随之飘散。妇女,怀抱小孩,多挤在一起,会说说笑笑,荧幕的亮光洒在脸上,面容恬静,神色舒展,褪下了白昼的疲倦。偶尔有小孩哭泣,说瞌睡、说害怕。妇女哄哄,不哭了,接着看一阵,还哭,就略带怨气地回了家。最高兴的莫过于孩子们,或数人骑坐在树上,或挤一堆,蹲在砖头上,打打闹闹,像猴。看到惊险处,会尖叫,看到搞笑处,会哄笑。尤其一双双眼睛,蓄满了月光,通透明亮,充满好奇。
第一个影片没有看到片名,讲母子两人,相依为命,儿子失明后,性格变得古怪,和母亲充满矛盾。母亲要为其换眼角膜,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无法如愿,想捐献自己的眼角膜给儿子,但医院没有同意,后来,儿子知道了母亲的苦衷,体会到母亲的关爱之后,两人和好。就在失明的儿子学会绘画,举办画展,作为给母亲的礼物时,母亲,却因为癌症,与世长辞,按照她的遗嘱,眼角膜给了儿子。
其实影片故事简单,缺少悬念,更没有夸张的特技、造型,唯独讲述母亲和奉献精神,是人类伟大的力量。在场的人似乎也不在意情节,只是想于清凉如水的夜晚,洗去疲乏,放下担子,坐在月光里,看看别处的人和事而已。也许,虚构的生活已不足以打动他们沉重的日子了,他们的日子,比影片,更加跌宕起伏,更加充满悲伤和感动。
现在放映机小多了,支起,也刚到我膝盖处。一束光线,笔直射出,投到荧幕上。小飞虫、蛾子,会在光束里,翩翩起舞,像在聚光灯下,婀娜多姿的舞女,轻盈、幽静,甚至忘我。还有细细的尘埃,也一起跳跃,像一场聚会。
月光轻柔,如水,擦洗着夜空,透过树叶的缝隙,像筛落在地的碎银。村庄静谧,被四处飘散的花香包围,看电影的人,被浓浓的夜色包裹。空气中,泥土的气息上升,月光落下。更远处,熟透的油菜爆裂,把孩子藏进泥土;葵花舒展腰身,把梦轻轻打开;胡麻拥抱,诉说着蓝色心事。
正是十六,月亮丰盈,像脸盘,慈祥、恬淡。从东缓缓而来,向西步行,或许也在看电影,或许在看看电影的人。
第二个影片是动画片,大人多已回家,只留下了孩子们,这是他们的最爱。世界清静,万物入眠,清澈的风藏在草丛,安心入睡。只有孩子们睁大双眼,瞅着荧幕,心被故事揪着,时而大笑,时而叹息,忘了夜色已浓,月眠柳梢。只是还有顽皮的鸟,蹲在树枝上,陪孩子们,它们似乎也入迷了,眼珠溜圆,毫无倦意,忘了脚趾的酸麻。
电影演毕,已快凌晨,孩子们怏怏而散。夜空碧蓝,如一湾湖泊,星星点点,闪闪烁烁,月亮手拢如玉脸庞,卧在一枚叶片上,入睡已久了。
小时候,村子里穷,家家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孩子们没有玩具,电视也屈指可数,全是十几英寸,黑白的,多数时间为了省电,不开,偶尔播节目,泥猴一样的孩子们塞满了屋子,其实看不懂,图稀奇。而到晚上,捉迷藏、打枪仗,便成了为数不多的游戏。单调、纯粹,被快乐和月光塞满了整个贫瘠的童年。
看电影,便成了最期待的事,也成了改变玩耍口味的一剂调味品。但是,演电影的次数,也是寥寥无几。
那时候,电影有公演和包演两种形式。电影演不演,消息很早就会传来,对于孩子们,充满了诱惑,像猫爪,在心上挠。因为一演电影,作业就可以不做,可以看大荧幕上比我们高大许多的人,打仗、比武,甚是新鲜、刺激。还可以玩很晚,家长不会用鸡毛掸子打屁股。
确定了演电影的时间,那天晚上,饭囫囵吞枣一吃,就早早来到电影场,或追打嬉戏,或看放映员装机子,那时候,总是搞不懂,为什么和大人一般高的机器,装上车轮一样的胶卷,会发一束光,投到白布上,人就出现了,而且是活的。这些,一直没有人告诉我们原因,由于好奇,总是你推我搡地围在机器边,放映员会将我们赶开,害怕机器被撞翻。
不知道谁说的,那机器发的光,不能动,沾上会死的。于是,大家对那束光充满了恐惧和好奇。
那时,一到晚上,串门聊天和睡觉是大人唯一的两件事,看电影,就成了全村人的盛会。不像现在,看电视、打麻将、喝酒,消遣的方式已经很多了,不再是漫漫长夜,而是夜色短暂,不够寻乐。
公演电影不要钱,多在“钢磨院”或大场这些公共场所上演,全村三四百口人,提凳子,抱木桩,搀老携幼,像赶集一样,说说笑笑,往电影场涌去。大家簇拥而坐,空气中飘荡着嘈杂、汗腥、哭喊、尘土,还有难以入眠的飞蛾。电影开演,光束一射,荧幕一亮,人群瞬间安静,声音突然蒸发,呼吸也似乎停止了。我们孩子,多看不懂情节,有枪战、武打的精彩场面会安下心,眼皮不挤地看一会儿。有拥抱或者亲嘴的镜头,人群中会爆发一阵骚动,嘘声、口哨、咒骂声煮成了一锅粥。我们会喊,羞羞、羞羞,把眼睛捂住,从指头缝里看伙伴们在偷看没。要是没有打打杀杀,我们多会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或者在荧幕后面,看那些人的后背,奇怪的是,他们没有后背,跟从前面看一样,只是方向相反,风一吹,荧幕波动,那些人的身体像是软的,来回动荡,可吓坏了我们。
其实,我们最爱看的是包演,包演要钱,每人两毛,都在人家院子里。人家花钱把电影包下,再收门票,或许能赚一点儿。包演多会演武打的,这是我们爱看的原因。只是,那时孩子们连钱渣渣都没有,别说两毛了。但电影不能不看,要是没看,第二天,伙伴们讲起来自己一无所知,很丢人。于是我们早早来到演电影的院子,先玩,等快开演之前,就偷偷藏起来,钻到人家洋芋窖里,或者躲在麦仓里,也有的缩到厨房的案板下。他们清场时,我们已经神不知鬼不觉,躲藏妥当,等电影开演了一会儿。我们像老鼠一样,一只只才溜出来。
而这样的躲藏总会发生很多搞笑事件。有一次,伙伴赵小军钻到人家缸里藏着,时间一长,睡着了。刘三妈刚洗完锅,不知道情况,把半锅面汤倒了进去,差点没把赵小军烫熟,当时他一声尖叫,还把刘三妈吓出了心脏病。还有一次,傻了吧唧的赵二炮藏到人家厕所的横梁上,下来时,一失脚,掉进了茅坑里,爬出来后,臭味惊动了满院人。像这样的事,数不胜数,有藏在牛肚子下面被牛踩的,有挂到屋顶下不来的,只要谁家包演电影,谁家就被我们整个底朝天。钱一分没掏,电影是不落一场的。
那时候,没有人外出打工,村里多年轻人。一场电影后,大人们总会说,谁家的儿子在麦草堆后面学着电影中的人,抱了谁家姑娘,还亲人家的嘴,这是谁撒尿时发现的。谁家的男人鬼鬼祟祟,在人堆里,摸了一把赵寡妇的圆屁股,被赵寡妇一转头,唾了一口。还有谁家的老母鸡那天晚上丢了一只,结果女主人一大早骂了半天人,后来才发现被黄鼠狼偷吃了……听了几句,就被大人赶走了。那时候,月光清明,星辰灿烂,夜空似乎很高,像一口井,藏着望不穿舀不完的秘密。人们的笑声也来得容易,电影上,随便一个动作,一句话,大家都会哄笑半天,把山林里的野鸟都能惊飞。
现在想来,能记住的影片只有《大渡河》《南北少林》等为数不多的几部,虽然内容忘了,但玉兰花瓣一样的月光下,几百人围在一起,看影片的场景,还依旧历历在目。
电影演完后的第二天一大早,我必定会早早到电影场,去捡那些裁掉的胶片,三指宽的黑胶片,举到太阳下看,会变成茶色,上面还有小人儿,不过为什么头发会是红色的?脸为什么会是绿色的?他们会是谁呢?是不是电影上那些人的魂?我很纳闷。当然,起个大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看看能不能捡到昨晚别人被挤落的一两毛钱,据说有人捡到过,整整五毛呢,但我没那福气,这可是我一直没有告诉伙伴们的秘密哦!
老早前,在天水,有两家电影院,一是南湖影院,一是岷山文化宫。
在七里墩上师范时,周末我们有从学校往中心广场步行的习惯,那是舍不得花八毛钱坐公交。途中,过七里墩大桥、经面粉厂、到岷山厂,厂对面就是岷山文化宫。虽为文化宫,但被私人承包,多演电影。每次经过,总看到铁栅栏外面的一块铁皮上,用红漆写着影片名,字迹有时龙飞凤舞、有时藏头露尾,可能是所谓的艺术字吧。院里一栋陈旧的楼,楼顶焊着“岷山文化宫”几个红字。但从未进去看过,还是害怕花钱,何况那时也没有多少钱。后来,放电影没有了生意,便倒灶了。
南湖影院,在南大桥边,影院边上有南湖车站、南湖饭店,所以人流量大,口音繁杂,容貌各异。看电影的、无家可归借宿的、等车的全挤进影院,于是生意还好。后来,影院拆掉,那地方被开发了。
物是人非,流年碎影。我于这两个地方没有什么过深的感情。没拆的,依旧经历风霜,如古稀老人,不言不语,静等尘埃如雪,覆盖往事。拆掉的,只是破旧时光,如已逝之人,不知不觉,淹没红尘深处,直至忘记。
后来,在南湖影院所在处,盖起了商业楼,里面便新开了影院,据说是天水第一家数字影城。第一次去看,还是和向向同学,这中间还有个故事。
那是去年十月份,我在武山采访,有陌生号码发短信说,记者节快乐。便礼尚往来,回复了一句。结果那人便回信息说我所写的东西,他读过。这样你来我往多说了几句。临终他说,请我看电影,我回复,感谢,回市里后电话联系。看着这些短信,一头雾水,貌似此人认识我,又好像素未谋面,会是谁呢?不知道。回去后,晚上他打电话说,八点的电影,票已买好,正在一楼电梯口等我。我过去后,找了半天,没见人影,电话联系,声音陌生,说他来找我。这样折腾了几次,最后在另一个电梯门口遇上。初见,那人瘦高,有打枣杆之态,面色黝黑,甚于我三分,说话有股稚气。他踢我一脚,说,不认识吧。我挠头,纳闷,不认识,初次见面,还给我一脚作为见面礼。后来到六楼影城,电影尚未开始,我们便到二楼咖啡屋,坐下F/dUuXN+vWPnV8WURC4OgA==,他要了果汁,我要了咖啡,好像吧,现在记不清了。随便聊了半天,但仍不知其姓名,也不好冒昧询问。那晚电影是动画片,环保题材吧。3D,这便是第一次看传说中的3D电影,一个男人与另一个陌生男人,初次见面,人约黄昏后,去看动画片,有意思吧?哈哈。
之后才知道那兄名叫薛向荣,报纸上读到其诗歌,知其小名,向向。三十而立之人,剩男呵。后来一起还看过好多电影,多为他请我,一打电话,一嘴夹生的秦安口音,说,看电影,走!都成模式了。将初次见面之事说与小宜姐听,她笑着说,你们两个大男生,还挺浪漫的,要是一男一女就更有意思了。
后来,自己有了电脑,在学校,没有拉网线,便从朋友处拿来了近五十张碟,基本保持每晚一部。后来才发现自己电影知识贫乏,所看影片也是寥寥可数,算是恶补一番吧。
关于电影,或者看电影,也就如此,简单,如同我的生活,无波无澜,缺少离奇的故事、扣人心弦的情节,其实这样,也何尝不好,人生,最好不要像电影那样,跌宕起伏、险象环生、充满悲剧。平静、健康就是自己为自己导的最好的影片吧。让风景在别处,你是赏花人,这样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