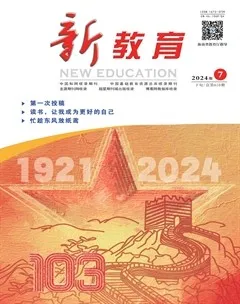第一次投稿
我的文章第一次变成铅字发表是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那年暑假,我们一家三口回老家四川乐山探亲。我们每次探亲都少不了游览名胜古迹。从四川回到武汉,我写了一篇《游乐山大佛》,我爸帮我修改后,鼓励我把它投给《武钢工人报》。
那时“武钢”可是一个有十几万职工的大型钢铁企业,武钢把它的工业区、生活区打造成了一座小城市:那里有职工医院、子弟学校、影剧院、百货商店、农贸市场……还有自己出版的报纸和期刊。当时我上的是武钢第十三子弟小学。每周我们每个人都会拿到一份《武钢工人报》(学生版),上面会刊登学生的文章。
那是1987年,投稿可不是用电脑,那时我们都不知道电脑为何物,更没有互联网。投稿需要将文章写在方格子的文稿纸上—我自然是一笔一画,小心翼翼将草稿上的文字誊抄在文稿纸上,生怕抄错一个字。我抄好后,在文末写上自己的姓名及所在学校、班级,然后把稿纸装入信封内,在信封上写好报社的通讯地址,仔细核对没问题之后,才将信封封口,贴上邮票,去邮局把信封投入邮筒。
我记得邮局有两个邮筒,一个在邮局里面,是长方体半人高的木质邮箱;另一个在邮局外面,是圆柱体的更高一些的铁质邮筒,两个油筒都是绿色。第一次投稿,我将信封郑重塞进木质邮筒,听到它“啪”的一声落地,我的心里便升腾起几分期待,也有几分慌乱。我想我当时凝望邮筒的眼神一定是厚重的。
投稿后,我对《武钢工人报》便有了牵挂,总盼着学校发报纸。我一拿到报纸,心就开始慌乱。我直接翻到第四版(学生习作一般都在那一版)扫视上面的文章,没看到自己的文章,自然有些失望,但很快又安慰自己:三个月呢,再等等—报纸上有申明:自留底稿,不退稿,三个月未见发表可自行处理底稿。
一天放学回家,我爸递给我一份报纸说:“你那篇文章发表了。”一向严肃的他眼里带着笑。我接过报纸一看,可不是嘛!正是我那篇文章,题目下面赫然写着我的姓名、学校、班级。那是我第一次深刻体会到“欣喜若狂”这个词的意思。我爸见我的反应后,立刻收起笑意,说:“不要骄傲!这篇文章能发表,一来是因为像你这样有机会出去旅游的孩子比较少,二来稿件我帮你修改过。这算不得你的真本事。”我立马识趣地点头,随即拿着报纸钻进自己的房间坐在书桌前一遍又一遍读自己的文章,我猜我当时嘴角肯定是挂着笑的。我晚上睡觉时心想:这期的报纸学校怎么还没发呢?不会不发吧,如果不发怎么办,我要不要告诉老师和同学我的文章发表了呢?如果说,他们会不会觉得我是在炫耀呢……一连串的问题搅得我半天睡不着。
第二天,我每个课间都溜到班主任杨老师的办公室门口探头探脑,看有没有报纸送过来,每次都失望。终于,杨老师发现了我的奇怪行为,问:“你有事吗?”我慌乱地摇头,想跑但又不敢。“有什么事你就说,别怕。”杨老师鼓励我。估计是那篇文章给了我勇气,平日里见到老师都躲的我居然迎着老师的目光嗫嚅地说:“我的文章在《武钢工人报》发表了。”“啊?!你再说一遍!”杨老师不知是没听清还是不敢相信。我提高音量又重复了一遍。“你确定?你看到报纸了?”杨老师问。“看到了,我爸昨天从单位带回来的,他们单位也有《武钢工人报》。”杨老师摸摸我的头说:“太好了!太好了!”她眼里的欣喜和脸上的笑像蜜汁似的流进我的心里。同学们很快也知道了这事,纷纷围着我问:“你的文章登报了,真的吗?”“你写的什么呀?”“文章题目是什么呀?”“学校的报纸啥时候能送来呀?”往常在班里几乎是“小透明”的我,突然有了众星捧月的感觉,人都有点晕乎乎了。
又过了几天,报纸终于来了。当杨老师抱着一摞报纸走进教室时,我的心跳莫名加快。有同学问:“老师,是有刊登周羽文章的报纸吗?”杨老师笑眯眯地点头。“哗—”班里发出欢呼声,几个同学冲上讲台抢着发报纸。拿到报纸的同学迅速找到了我的文章,举着说:“这里,周羽的文章在这里!”他们似乎比我还兴奋。我害羞地低下头看桌上那份新报纸,却不好意思看自己的文章。我的眼睛盯着报纸,耳朵却在敏锐地捕捉着教室里的声音:有同学在小声读我的文章,有同学在说“这一段写得真好”,有同学说“作家,我们班出作家了”……杨老师问:“周羽的这篇文章写得好不好?”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好!”“咱们为她鼓掌吧,这是我们学校第一个发表作品的同学,希望大家向她学习……”教室里热烈的掌声真是比过年的鞭炮声还响亮,我内心的“小鞭炮”炸得四处散开,以致于烧到了耳根子,好幸福哟!
大约一年后,我写了一首诗,自我感觉挺好,所以没给我爸过目,也没告诉任何人,自己悄悄投稿。很快,那首诗也发表了。那一次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我写作的积极性越来越高,文章陆续发表。我没有因此而骄傲,我觉得“文字”是能让我内心沉静下来的朋友,也是能引领我不断探寻的良师。
现在的我仍然坚持投稿,仍然会有发表的喜悦和未能发表的失落,我愿意牵着文字的手,一直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