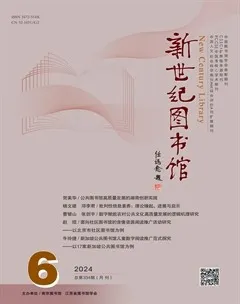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机理研究
摘 要 数字技术是赋能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新型驱动路径。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机理在于能够优化农村公共文化内容、促进多元主体协同供给、促进文化更好传承发展、激发文化建设经济效应。在实践中,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面临缺乏统一数字文化建设规划、考核制度不足、文化建设主体单一、在地文化资源数字化不足、农民群体数字素养不足等现实挑战。在政策层面,需要从数字文化建设制度、机制、内容、主体等方面协同发力。
关键词 数字赋能;数字文化;农村公共文化;文化建设
分类号 G249.27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24.06.007
Resarch on the Logical mechanism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Public Culture With Digital Empowerment
Cao Yinshan, Zhang Jianyu
Abstract Digital technology is a new driving path to enabl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public culture. The logical mechanism of digital enabl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public culture is that it can optimize the content of rural public culture,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supply of multiple subjects, promote the better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stimulate the economic effect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practic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digitally empowered rural public culture faces realistic challenges such as lack of unified digital culture construction planning, insufficient assessment system, single cultural construction subject, insufficient digitization of local cultural resources, and insufficient digital literacy of farmers. At the policy level,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concerted efforts from the aspects of digital culture construction system, mechanism, content and main body.
Keywords Digital empowerment. Digital culture. Rural public culture. Cultural construction.
0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文化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与有力支撑,推动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成为新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农村作为我国重要地理空间与群众生活空间,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在农村公共文化发展过程中,广泛存在内容同质现象严重[2]、阅读资源供需不匹配[3]、公共性消解、文化空心化[4]等现实困境。近年来,数字技术迅猛发展,驱动着农村公共文化体系深刻变革。学者围绕数字技术赋能农村公共文化发展进行了探索,现有研究成果基本可以归纳为如下三个层面。一是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文化发展的运作优势。数字技术能够重塑文化理念、扩展参与主体范围、变革供给思维、实现城乡文化共享[5]。二是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文化发展的问题。学者们主要立足于供需适配角度,认为当前发展过程中存在数字化平台推广、线下工作配合等现实问题[6],造成数字文化服务的相关性、可及性、质量性以及相适性不高,影响公众的整体满意度[7]。三是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文化发展的建议。基于供需平衡角度,以主体协同、平台驱动等为策略的公共文化服务共同生产是推动农村公共文化发展的重要路径[8]。此外,在宏观层面,要从完善财政补贴制度、建设数字文化服务标准制度、细化人才培养制度等方面着手[9]。
现有研究成果从供给侧改革角度,为我们认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然而,高质量发展是高质量供给和高质量需求相统一的发展[10]。一方面,现有研究成果聚焦于文化由外而内嵌入,而缺乏对农村本地内生型文化挖掘的关注,因此存在进一步阐释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空间。另一方面,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效能是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然而,现有成果主要聚焦于数字技术在农村文化发展中的功能,而对文化与经济功能的关联性分析缺乏重视,因而使得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蕴涵阐释的全面性不足。由此构成了本文的研究空间与分析进路,即在阐明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核心蕴含的基础上,阐释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机理,继而指出现行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不足,并据此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1 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机理
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解决农村公共文化发展过程中供需不匹配、供给体制机制不畅等问题,是实现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数字技术为解决长久以来的痼疾提供了新的解题思路。“数字赋能”是指运用各种新兴数字技术,通过提供平台、场景改造等方式,积极创造条件,激发和促进行动主体解决过去所不能解决的问题[11]。概括而言,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主要体现在优化文化内容、供给方式、促进文化发展传承、激发文化经济效应四大层面。
1.1 数字化文化传播:优化农村公共文化内容
能否有效满足农民群众各类多元文化需求,是衡量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准。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农村发展滞后于城市,农民精神文化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此外,统一的公共文化服务决策机制往往忽视各个地方差异化的发展水平、民风习俗、文化需求,致使文化供需难以有效衔接[12]。而数字化文化传播功能,则能促进优质文化高效向农村传播,从而优化农村公共文化内容。
在公共文化内容选择层面,数字技术能够精准匹配农民公共文化需求。农村居民能够在线访问和学习以数字图书馆、在线文化资源平台为载体的数字文化资源库,可以自由选择感兴趣的电子书籍、音乐、电影等。借助问卷星调查、微信小程序等各类数字平台,农民可以主动表达文化需求。政府部门、企业组织等主体对数据进行采集分析,便可以修正决策,为农村农民精准供给文化项目。借助数字技术平台,农村公共文化供给模式由“要我接受”变为“我要点单”。此外,各类数字平台能够通过对农民个人行为数据的收集与分析,透视农民公共文化需求,从而能够为农民提供个性化文化服务。比如,手机伏羲云App便汇聚了数千家文化机构优质、海量的数字文化资源,农民通过下载、注册便可以针对性享受自身所需要的文化服务。同时,智能平台的云计算、知识标引等数字技术,会不断通过用户的行为数据“投喂”,修正数据模型,主动为用户提供更为精准、前瞻的文化服务。在文化供给层面,数字技术能够大大降低文化建设成本,从而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持续发展。数字化文化资源的存储和分发成本通常较低。相对于传统的印刷品和实体介质,数字内容可以便宜地存储在云端服务器上,并通过互联网广泛传播,无需大量的物理空间和物流成本。数字化文化传播方式通常比传统的面对面培训更经济实惠。通过在线学习平台提供培训和教育课程,可以节省场地、材料和交通等方面的成本。
1.2 数字化参与互动:促进多元主体协同供给
从现实来看,政府行政包揽式文化供给模式,正是过去农村公共文化缺乏活力、出现供给失灵现象的症结所在。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分层分类协同供给体系,是推动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尽管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双方都存在问题,但现有矛盾主要在供给方[13],而数字技术能够利用数据要素优化治理流程,搭建集中式交互平台,从而能够促进多元主体协同供给农村公共文化。
一方面,数字技术平台能够供文化机构、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企业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文化供给。这些平台可以提供协作工具、资源共享和信息交流渠道,促进各方之间的合作和沟通。比如,“顺义公共文化云”平台统筹整合以文化中心“三馆一院”(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大剧院)为中心、镇街综合文化中心为纽带、村社文化活动室为支撑的三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大数据,促进跨地区、跨部门文化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公众可以在线预定公共文化活动项目,后台数据便可以驱使各部门、社会组织等主体合作供给民众所需文化。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和网络社群等数字技术提供了一个参与互动平台,让文化机构、艺术家、文化爱好者和农民能够分享文化活动信息、互相联系,并协同组织文化活动。各大文化主体能够基于自身兴趣,通过视频、聊天讨论等形式,共同参与到农村公共文化生产中来,从而从根本上激活农村公共文化内生发展动力。例如,永春县岵山社区大学根据各村村民兴趣,广泛引导建立非遗文化、学堂教学等各类微信群,定期通知举办各类文化活动,促进村民自主开展文化交流学习。
1.3 数字化资源建设:促进文化更好传承发展
从内容上来看,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不仅要将外部先进文化植入乡村社会,更要注重对本土在地文化的深度开发与创造性转化,是“外引”与“内生”的辩证统一。数字技术是一种强大的工具,可以帮助保护和传承乡村文化资源。数字技术能够通过在地文化资源数字化,对农村传统文化、农耕文化等资源起到保护、传承与传播接续作用。传统乡村民俗文化、手工艺文化、乡村文物古迹、特色建筑等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是农村公共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人工智能、短视频、音频、AI成像等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发展为农村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提供了新的平台与技术支撑。三维扫描建模、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能够实现传统文化的数字孪生,建立物理文化产品与虚拟文化空间的映射关系,实现文化遗产的存档、展览、传播、管理、虚拟体验。例如,2018年10月,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正式上线。目前,已上线将近1000个村落。该数字平台以全景漫游、三维实景等方式,全方位展示传统村落文化形态。即便未来传统村落消失了,民众借助网络,也能感受到传统公共文化的魅力。
1.4 数字化创意产业:激发文化建设经济效应
农村公共文化效能转化机制不畅,往往导致农民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不高[14]。同时,文化建设难以转化为经济效益,不断加大政府财政负担,使得公共文化建设难以可持续发展。上述双重困境严重制约着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数字技术能够实现农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经由各类数字化创意产业提升文化建设的溢价效应,增强农村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将农村公共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成为提升群众参与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积极性、确保农村公共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路径。
一方面,数字技术能够带动文化产品对外销售。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农村创意性文化产品、手工艺品往往是稀缺资源。抖音直播、淘宝等各类数字平台,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难题,畅通农村文化产品的对外销售。例如,博主“茶三姐”通过抖音数字平台讲解茶知识,不仅带动更多人群了解当地特色茶文化,同时带动了茶叶及周边产品销售。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能够实现本地特色文化增值。例如,湘西凤凰县山江镇利用GIS和VR等数字技术,构建乡村文化的“廊道—建筑—展馆—商品”四维联动的数字化体验平台,借助VR漫游、数字展馆等体验形式,促进线上文化遗产旅游,带动线下文化产品销售,将文化发展转化为社会经济效益,真正实现农村公共文化的高质量发展。同时,借助各类数字平台,外地游客能够了解到本地特色文化,吸引游客前来体验当地特色文化。游客不仅为特色文化本身付费,无形中进一步带动了民宿、餐饮等各类行业的发展,促进农村增收致富。通过数字化创意产业,不仅促进了文化建设,而且激发了文化的经济效应,增强了农民参与文化建设的内生动力,真正赋能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
2 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挑战
数字技术与农村公共文化发展有着天然的内在逻辑契合。然而,数字技术发展、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并非一蹴而就,两者必然需要经历磨合交互的过程。就当前来看,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主要面临着规划不足、建设主体单一、在地文化资源数字化程度不足、农民群体数字素养不足等现实挑战。
2.1 政府缺乏统一数字文化建设规划,数字供给考核制度不足
数字文化资源只有统一规划、协同应用,完善前期、中期、后期数字文化资源全生命周期管控,才能真正激发数字文化资源效能[15]。然而,数字化作为一种新兴手段运用于农村公共文化建设领域,普遍存在缺乏统一规划、考核制度不足的问题,严重制约着农村文化发展效能。
其一,公共数字文化平台不兼容,建设运营缺乏制度保障。当前,我国地方各级政府、各部门在推进数字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往往各自为政,分散推进。受科层理性与政绩驱动双重逻辑影响,各部门争先进行数字技术创新,造成各类数字平台交叉性强、协同性弱[16]。而公共数字文化平台要发挥知识发现、知识利用功能,就必须提供整合、联通的知识管道[17]。以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为例,从省级到县级政府自建网站数量繁多,共享程度低,并且缺乏统一检索入口。目前国家层面尚未出台数字文化平台建设运营的相关法律法规,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往往各行其是。例如,各类数字文化平台日常运行和管理维护不到位现象屡见不鲜,网页信息陈旧、无效链接较为严重。由于政府缺乏统一数字文化建设规划,造成数字文化平台不兼容、建设运营缺乏相关制度保障,严重制约着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
其二,数字文化供给考核制度不足,导致服务效能反馈修正机制不畅。绩效评估是检验服务效能的重要手段,评估结果是提升服务效能的重要依据[18]。然而,各地在数字化公共文化建设过程中呈现出自上而下的推广逻辑,而对农民群众的需求及主观评价重视不足。缺乏自下而上的服务效能评价机制,导致各地在数字化公共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数字形式主义”现象,片面以数字软件建设数量、下载率作为评价标准,严重忽视了农民群众真实的文化需求。数字技术嵌入农村公共文化发展未将群众需求、满意度纳入评价标准,导致数字文化内容偏离农村实际情况而长期得不到有效修正。
2.2 数字化公共文化建设主体单一,企业与社会组织参与不足
当前,数字化公共文化建设机制不完善,主要表现为建设主体单一,企业与社会组织参与严重不足。在价值链维度上,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要体现为偏重于层级型的单一治理模式,政府与市场、社会协同互动的网络型治理模式还远未形成[19]。
其一,政府行政思维主导导致数字化公共文化建设主体单一。在数字化公共文化发展初期,企业及社会组织往往出于成本、短期收益考虑,难以看到盈利点,普遍不愿参与数字化公共文化建设中来。因此,公共数字文化及传统公共文化的数字化转型,往往需要政府主导的层级型控制来加以推动。在实践中,具体体现为政府将数字化公共文化建设标准、考核要求等各项事务纳入基层政府职责清单,以便推动基层政府及相关事业单位全面参与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的生产和经营。然而,行政惯性思维导致政府难以在适当环节引入企业、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数字化公共文化建设,最终影响公共文化发展质量。
其二,缺乏利益协调机制导致企业与社会组织参与不足。目前在农村数字化公共文化建设过程中,作为主导者的政府尚未制定明确的利益分配机制。企业和社会组织担心投入不会得到合理回报,或者不清楚如何分享项目利益,所以参与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积极性较低。同时,企业作为盈利组织,更倾向于追求短期利润。然而,数字化公共文化建设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看到明确的经济回报。因此,企业主动参与农村数字化公共文化建设的积极性更低。此外,信息不对称阻碍着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数字化公共文化建设。由于政府倾向于行政主导,忽视引入社会力量,企业和社会组织难以找到合理参与的渠道。
2.3 在地文化资源数字化不足,文产数字化融合程度有待提升
目前大多数农村地区文化资源数字化程度不足,严重制约着文化资源保护与传播。一是经费普遍不足。与实体文化书籍资料建设不同的是,文化资源尤其是文物资源数字化对于高科技技术和设备的要求较高,导致其成本偏高。文化部门系统所提供的经费支持显然不足,尤其是在县级层面,普遍面临有心无力的局面。贵州省东南部地区有着大量的侗族和苗族聚居村落,现存大量珍贵的少数民族建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各县由于开展文化资源数字化的经费不足,只能选择部分重点文物加以数字化,而大量为民众喜闻乐见的习俗、古迹等正在逐步走向消亡。二是综合性跨界人才不足。由于基层待遇与发展机会限制,县级文化工作部门往往难以招考到高素质的文化工作专业性人才。同时,农村丰富在地文化资源难以在短期内转化为经济效益,文化公司不愿入场进行文化资源数字化开发。上述双重困境进一步加剧了在地文化资源数字化的不足。三是缺乏相关文化资源数字化成果转化的法律法规。由于国家和地方各级尚未出台较完备的文化资源数字化开发的知识产权法规,致使侵权行为界定、收益共享等不明。尽管部分影视工业、文旅、互联网等行业有着对各地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开发的愿望,但由于知识产权限制而难以进行。
文产融合程度不够,严重制约着农村公共文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化和文化产业的融合作为一个全新领域,能够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带来巨大机遇。然而,目前数字化文产融合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中的应用还存在诸多不足。一方面,数字化文产融合的应用仍然比较有限。许多农村地区的文化产业仍然停留在传统模式下,缺乏数字化和互联网思维的应用,导致这些地区的文化产业无法跟上数字化时代的步伐,缺少竞争力。以数字文旅为例,与机票、酒店等行业数字化相比,文化景区、文化活动体验等行业的数字化程度极低,对于线上内容介绍等项目则更是阙如。由于农村文化资源数字化程度不够,自然难以吸引人群前来付费体验,不利于农村文化的长远发展。另一方面,数字化文产融合的应用需要更多的资源和支持。数字化和文化产业的融合需要具备一定的技术和人才基础,但许多农村地区的人才和技术资源相对匮乏。以抖音“新农人”为例,大多数农村地区研学项目、付费体验艺术品制作等抖音博主点赞量、成交量均不高。其重要原因在于缺乏专业的团队运作,机械化的讲解往往难以捕获市场流量。
2.4 农民群体数字素养不足,农村公共文化缺乏内生发展动力
农民群体是农村公共文化的重要创造者,也是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主体性力量[20]。农民主体性是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在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离开了农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也就无从谈起。在数字技术成为农村公共文化活动重要载体的同时,具备良好的数字素养成为参与文化建设的基础。然而,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农民受教育程度较低,数字技术运用能力则更为匮乏。截至2021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较之2007年的7%翻了一番,标志着我国已由轻度老龄化社会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21]。由于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以及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年轻人外出务工使得不少农村地区成为“空心村”,留守在村的多为老年人。
一方面,农村老人数字素养不足,导致其无法参与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对于知识素养、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老年人而言,听力、视力、理解能力、判断能力、反应能力等均在不同程度地退化。这一困境导致老年群体面对眼花缭绕的操作界面,存在着较大的使用困难,难以快速操作阅读、影视欣赏等数字文化应用。另一方面,各类数字技术软件存在“困老性”,脱离农民兴趣,导致农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内生动力不足。在注意力稀缺时代,政府、企业开发数字技术功能,往往聚焦于青年群体的兴趣点,难以兼顾到数字技术软件的适老性。腾讯公司《老年用户移动互联网报告》显示,基础性操作是老年人面临的最大障碍,其中应用使用与功能操作障碍占比46.7%,系统设置与维护障碍占比41.2%。在农村公共文化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字化设备功能繁多且不断迭代升级,却未能很好地兼顾到农村老年人这一主体,导致广大农民群众缺乏兴趣,因此不愿意参与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中来。
3 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因应
在数字技术加持下,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迎来了新的契机。农村公共文化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复杂多元的框架体系,必须要坚持系统性、整体性改革思维。基于农村公共文化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可以从制度、机制、内容、主体四大维度,构建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优化路径。
3.1 制度维度:统一规划数字平台,建立数字文化发展考评制度
政府是推动农村公共文化发展的主体与主导力量,是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责任承担者。从运作模式来看,政府主导的文化下乡是重构农村文化生态与乡土社会的主要实践,撑起了农村公共文化发展过程[22]。从制度维度来看,政府亟需统一规划数字平台,建立数字文化发展考评制度。
高位推动数字文化平台建设。分散化、碎片化的数字文化平台成为信息壁垒、信息孤岛,严重制约着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因此,加快建立集约化的数字化文化平台,成为推动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前设条件。一方面,要通过立法与政府内部流程重塑,以整体性政府理念推进数字平台建设。以立法规定各级公共文化发展机构将文化资源链接进入一体化的数字文化平台,构建起省市县乡村五级共建共享的数字文化服务网络。例如,地方各级政府可以以法律法规形式,规定各级文化部门在“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上接入地方特色文化,并积极更新维护。各级政府要进一步细化公共文化覆盖面,在数字平台中设置适合各地的、适老的资源板块。另一方面,要提升数据采集与利用的通约性。通过设置统一的数据接口标准以及共享流程,提高数据资源利用效率。例如,农民需求侧数据、文化部门供给侧数据资源经过脱敏处理后,可以共享给相应市场、社会组织部门。而相关主体则可以根据已有信息,在数字平台上精准推出独特性的、创新性的文化资源。
建立数字文化发展考评制度。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要兼顾农村个性化需求与普遍性公共利益,因此需要构建制度化的绩效评价机制。一方面,在过程中,要通过征询群众意见推动公共文化发展。政府部门要定期开展深入访谈,对农村公共文化发展层次和偏好进行细分,根据群众意见,对政策不到位的地方进行完善,从而使普适性的公共文化服务向更加精细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在结果上,要畅通农民需求表达渠道。通过在数字平台中嵌入问卷调查、意见反馈功能,确保评价主体多元化,以便实时改进农村公共文化发展过程。就根本而言,引入文化发展考评制度,是确保农村公共文化发展不脱离农民日常生活场域、契合农村乡土气息的根本保障。同时,要开展专题调研,确保农村公共文化数字化发展过程中不存在违规收费、数字不友好等情况,确保农村公共文化数字化健康长远发展。
3.2 机制维度:构建利益合作机制,引入多元数字文化建设主体
构建一个既有分工又有协作、既有竞争又有整合的有机运转的良性协作系统,是推动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保障。在实践中,各主体的职责分工与权力边界则体现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合作[23]。通过构建农村公共文化发展的多元行动主体,能够促使各行动主体平等对话、良性竞争、有序合作,在此基础上实现公共文化资源的有序供给与分配。
第一,广泛采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明确规定“国家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形式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政府要充分利用公共服务采购的形式,引导具备资质的企业、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到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中来。例如,在数字文化平台研发、数字图书更新、线下文体活动举办等各环节,均可以充分采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形式。第二,广泛采取公私资本合作(PPP)形式。PPP是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建立的优化融资与实施模式,具有降低政社双方风险、社会效益好等特点[24]。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在文化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正式肯定PPP模式适用于文化建设领域。例如,在农村数字文化图书馆建设、非遗文化数字化推广、文创产品数字化销售等各项目中,均可以由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负责筹资、建设及经营,并以“使用者付费、政府补贴”等多种形式,允许投资者获得合理利益回报。第三,广泛吸纳慈善投资、志愿者参与乡村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企业作为社会主体,往往有着承担社会责任的使命感。同时,要积极发动志愿者,尤其是在地文化志愿者,组织他们广泛参与到技能培训、数字文化平台推广等各个环节中来。通过动员多元主体共建共享,强化政社多元主体持续性协同合作,从而在数字文化建设机制上保障农村公共文化长远高质量发展。
3.3 内容维度:推进在线在场互联,以数字化助推文产深度融合
借助数字化打造线上与线下、在场与缺场交互统一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成为当前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的突d14YS294E1mYhN2ADH1C2dh+eDR1eFo/Djvmsuil1Ao=破口。线上虚拟场景构建与线下公共文化空间营造深度融合,能够使感官“深度卷入”,从而助推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第一,打造数字文化场景。利用数字技术,创新公共文化展示模式。以文化公园、非遗场所等为内容,利用数字技术终端展示丰富多样的农村生活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公众借助手机、展示屏等数字终端,便可以轻松进入农村公共文化数字空间,能够低成本、便捷地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第二,积极利用VR等技术,使各类文化“活化”。数字文化场景尽管能够满足群众对各类文化空间的视觉需求,但缺乏对各类非物质文化的深度体验。借助VR等技术,群众可以虚拟体验戏曲、传统刺绣等各类文化手工艺。通过沉浸式体验,群众能够身临其境,提升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感。第三,积极利用AR等增强现实技术,实现文化内容可视化、情景化。AR技术将文化行业带入三维时代,比平面二维更具有立体感、真实感,互动性更强[25]。在农村文化礼堂、文化展馆等公共文化空间中,可以利用文字、图片、3D动画、全息模型投影等展示文化内容,不仅能够降低导游、讲解成本,避免文物遭到破坏,打破时空条件对游客人数的限制,同时能够使群众深度体验各类文化,同步提升文化参与感与满意度。
文产融合既是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第一,要利用数字技术,加强文产研发生产方面的融合。要积极挖掘开发当地的红色、非遗、信仰等方面独特性、价值性高的文化,文化创作者可以利用数字工具创作和制作数字化的工艺作品、音乐、电影等。利用各种数字技术,研发出不同的数字文化呈现形式,形成不同的数字文产资源,推进文化产业创新。第二,要利用数字技术,加强文产销售方面的融合。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内容创作和传播。同时,数字平台和社交媒体提供了广泛的传播渠道,可以扩大文化产品传播途径。农村地区文化主管者和工作者要积极在数字文化平台、抖音直播、快手等平台进行创意性引流,捕捉流量。第三,要利用数字技术,加强文产消费方面的融合。利用数字技术提供在线预订和导览服务,为城市居民创造更多的公共文化消费需求。通过VR、AR等技术,可以为游客提供丰富的农村文化体验,包括参观农田、体验传统农业工艺等。通过延长文化产业链条,逐步探索农村公共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长远道路。
3.4 主体维度: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增强数字文化建设内生动力
农民群体是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主体,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农民群体的深度参与。提升农民群体数字素养,使其具备参与数字化公共文化活动的能力,才能从根本上增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内生动力。由于老年群体受教育程度、身体机能等多方面原因限制,对电子设备终端的运用仅限于通讯层面,对数字化公共文化认知水平较低。
一方面,要积极提升农民群体的数字技能。基层政府作为推动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责任主体,要积极承担责任,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县级文化部门、乡镇党委政府可以依托乡镇文化站,督促各村组建数字文化技能培训组织。各行政村组织党员干部、大学生志愿者、退休乡贤访组入户,上门针对性为老年群体提供数字技能培训服务。同时,要积极倡导家庭代际反哺。鼓励在家子女积极向老年人普及数字知识,提供精细化、精准化培训服务,从而缩小老年农民群体的“数字鸿沟”。另一方面,要通过数字文化运用,增强农民群体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内生动力。基层政府要积极建设数字文化示范基地,通过实际案例向农民展示数字技术在文化及产业发展中的应用。提供培训和实践机会,让农民亲自学习并体验数字技术;同时,政府要打造农村数字文化活动平台,组织农村数字文化活动。通过举办数字艺术展览、电影放映、线上文化演出等活动,让农民亲身参与和体验数字文化的魅力。同时,鼓励农民自己创作和分享数字文化内容,如农民摄影比赛、农村微电影制作等。通过技能培训与场景运用两个维度协同发力,真正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并增强农民群体参与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内生动力。
4 结语
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题中之义,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有力抓手。数字技术因其内在特征,能够赋能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主要体现为数字化文化传播能够优化农村公共文化内容;数字化参与互动能够促进多元主体协同供给;数字化资源建设能够促进文化更好传承发展;数字化创意产业能够激发文化建设经济效应。可见,数字赋能成为新时代背景下农村公共文化发展转型的必由之路。然而,数字技术与农村公共文化融合发展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在实践中不可避免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政府缺乏统一数字文化建设规划,数字供给考核制度不足;数字化公共文化建设主体单一,企业与社会组织参与不足;在地文化资源数字化不足,文产数字化融合程度有待提升;农民群体数字素养不足,农村公共文化缺乏内生发展动力。上述困境严重制约着数字技术赋能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接下来要从数字文化建设制度、机制、内容、主体四个维度着手。具体体现为:统一规划数字平台,建立数字文化发展考评制度;构建利益合作机制,引入多元数字文化建设主体;推进在线在场互联,以数字化助推文产深度融合;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增强数字文化建设内生动力。
参考文献: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28.
司蒙蒙,孙宁,陈雅.长三角公共文化服务高质
量发展逻辑与路径研究[J].新世纪图书馆,2022
(6):63-69.
王春梅,刘春洋,王春黎.农村居民公共阅读资
源供需矛盾探析[J].新世纪图书馆,2023(1):16-20, 70.
耿达.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演进与逻辑理路[J].图书馆,2022(11):1-7, 15.
邵明华,刘鹏.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供给:价值意蕴、动力机制与路径创新[J].图书馆论坛,2023,43(1):40-48.
杨芳,王晓辉.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契合作用机理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J].图书与情报,2021(1):62-69.
陶成煦,沈超,完颜邓邓.供需适配性理论视域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满意度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21,65(17):57-68.
汤资岚.数字赋能共同生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新范式[J].新世纪图书馆,2023(5):5-9, 76.
戴艳清,刘杨庆.公共数字文化均衡化发展制度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22(1):18-24.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问题[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0:214.
李燕凌,陈梦雅.数字赋能如何促进乡村自主
治理 基于“映山红”计划的案例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3):65-74.
董帅兵,邱星.供给侧视角下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振兴:基于全国31省267个村庄的调查分析[J].图书馆学研究,2021(2):30-36.
李燕凌,高猛.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结构
视域、内在逻辑与现实进路[J].行政论坛,2021,
28(1):18-27.
曹银山,刘义强.面向共同富裕的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理论契合、现实挑战与政策因应[J].图书馆,2023(10):1-6.
杨滟,田吉明.基于科技与人文融合的数字文
化治理体系建设研究[J].现代情报,2020,40(10):
43-51.
曹银山,刘义强.技术适配性:基层数字治理“内卷化”的生发逻辑及超越之道[J].当代经济管理,2023(6):35-40.
邵长娜.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建设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J].图书馆界,2016(2):60-63.
戴艳清,何晓霞,郑燃.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效能
提升的制度优化[J].图书馆论坛,2021,41(8):26-33.
陈世香,徐小丰.“政策工具—价值链”视角下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2023(3):68-77.
汪圣,聂玉霞.地方性知识的张扬:乡村文化振
兴的应有之义及其实现[J].图书馆,2022(5):1-6, 31.
胡春艳.养老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N].中国青年报,2023-03-24(006).
陈建.从重构到涵养:乡村振兴中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转变研究[J].图书馆,2022(11):8-15.
程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多元供给系统的构建:以江苏省为例[J].编辑之友,2018(9):16-22,42.
陈瑜.乡村振兴与农村公共阅读空间的多维构建:以政社合作为视角[J].图书馆,2022(7):49-57.
李海英.AR技术在出版中的应用与实例分析[J].青年记者,2020(23):101.
曹银山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
张剑宇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江苏南京,210000。
(收稿日期:2023-05-18 编校:左静远,曹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