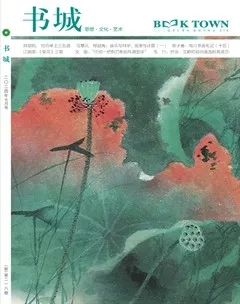牡丹亭上三生路
一
《牡丹亭》是一部伟大的文学杰作,更是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一颗璀璨明珠。作者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江西抚州临川人,阳明学泰州学派大师罗汝芳的入室弟子,一代诗文大家。除诗词歌赋卓有成就之外,最为人所称道的就是他的戏曲作品“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他也因此被文学史家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临川四梦”中的《牡丹亭》,又名《还魂记》或《还魂梦》,长达五十五出,剧情跌宕起伏,更以辞藻优美著称。
《牡丹亭》在明代万历年间甫一问世,就备受瞩目,使当时文坛与剧坛惊艳不已。见多识广的沈德符(1578-1642)在《万历野获编》中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袁宏道评《玉茗堂传奇》则说:“《还魂》,笔无不展之锋,文无不酣之兴,真是文入妙来无过熟也。”他们都惊叹《牡丹亭》的文辞美妙,是足以流传千古的文学经典。也有人虽然赞扬汤显祖剧本文辞美妙,却批评其音律方面有许多不合乎“吴音”之处,与昆腔水磨调有所扞格,指之为“案头之书,非筵上之曲”,因而出现一些草率的改编本,“以便吴歌”。经过明清曲家的努力,以及舞台伶人的实践,以调整曲牌及集曲整合的方式,保持原作不动,终于成为昆曲表演艺术中家喻户晓的保留剧目。《牡丹亭》经历了四百个春秋的花开花落、人世沧桑,一直上演到今天,依然是最受欢迎的昆曲剧目,并在二十一世纪的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
要理解《牡丹亭》为何在千百部明传奇中脱颖而出,成为最辉煌的戏曲杰作,必须从三个面向来理解。首先,是思想内涵与文学想象。要知道作者汤显祖写作的历史文化背景、动机与寓意,如何以美妙文辞构筑出他心目中的想象世界,向往自由开放,追求理想幸福,才能深刻认识到不朽作品为什么可以超越时代,历久弥新,让千百年后的人们为之感染同情,观之兴叹。其次,是舞台表演的审美境界。《牡丹亭》不仅是伟大的文学作品(“案头之书”),也是在舞台上粉墨登场的戏曲表演(“筵上之曲”),这就需要理解从南戏到昆曲的演剧传统,知道明传奇编剧与昆曲演出的互动关系,如何展示了中国舞台表演最精致优美的审美境界,以诗歌演唱的写意手法,展示人间悲欢离合的百态。第三,是昆曲音乐的优美绝伦。《牡丹亭》在不同剧种中都可以演出,而最优雅的艺术呈现形式则是昆曲,关键是昆曲婉转细腻又优美动听的音乐,恰如其分地显示了《牡丹亭》的雅韵高标,辅以精雕细磨的“四功五法”,最能给人“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的忘情感受。我总是指出,昆曲在戏曲传统中独占鳌头的原因,就是艺术跨界三结合的成就:剧本文学雅致如诗、舞台表演精彩如画、音乐优美细腻如沐春风,三者结合为一,浑然天成,成就了中国传统演艺的巅峰,《牡丹亭》就是其中最优秀的典范。
二
《明史·汤显祖传》对汤显祖登上历史舞台,强调的是他的政治生涯,涉及文学成就的只有几个字,完全不提他对戏曲艺术的贡献:“汤显祖,字若士,临川人。少善属文,有时名。张居正欲其子及第,罗海内名士以张之。闻显祖及沈懋学名,命诸子延致。显祖谢弗往,懋学遂与居正子嗣修偕及第。显祖至万历十一年始成进士。”很隐晦地指出,汤显祖少年俊才,闻名遐迩,以至于首席大学士张居正想要罗致于门下,与他的儿子们一同去应试科举。谁知道汤显祖居然恃才傲物,拒人于千里之外,显示了年轻人狷介不群的气骨。后果则是连续落第,直到张居正逝世之后,“至万历十一年始成进士”,而煊赫一时的张家此时已遭抄家处分而覆败。
汤显祖狷介的傲骨来自罗汝芳的教导,笃信阳明良知学说,相信人性向善,应该发挥“赤子良知”的精神,以臻圣贤之道。他不满张居正专断独行,肃清言路,订定禁止讲学、打击探讨心性之学的政策,禁锢了罗汝芳一脉的思想传播。由不肯依附张居正的经历,可以看到汤显祖耿介与狂狷的性格,如何从萌发到成形,再经过长时间的淬炼与磨砺,终于造就了独立自主的个性。终其一生,秉性刚毅决绝,像他笔下创造的杜丽娘,坚持理想初心,九死而未悔,追求梦中理想的“至情”人生,成为思想孑然独立的大文学家。
阳明学派在明代中晚期兴起,宣扬个人本体良知自主性的重要,所以要有源于自己的内在体悟,要“致良知”,要“知行合一”。这个内在体悟,跟个人的心性本体有关,跟个人的人格发展有关,强调的是个体心性的自主与自由,到了罗汝芳就提出“解缆放帆”,让人人各指本心。社会上出现了个人心性自由化的潮流,引起张居正的担忧,开始限制罗汝芳传布发抒个人主体性的自由追求,以维持官方正统思想的稳定性。作为罗汝芳的忠实弟子,汤显祖坚信老师教导“天机泠如”的取态,反对以官方律令压制阳明圣学思想自由的“活泼泼地”特性,就对张居正滥用权威的行为不满,这也是汤显祖拒绝张居正罗致的思想与时代背景。
汤显祖两次拒绝张居正的笼络,反映了他独立自主的个性,对当权者显示了自己狷介不移的性格,其间还因张居正夺情事件的扰攘,对官场斗争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而张居正死后的清算抄家,更使得汤显祖看清政治斗争的残酷。汤显祖考上进士之后,坚决要求到南京做个不参与实际政治的闲官。万历十四年(1586),汤显祖三十七岁生日时,在南京写了《三十七》一诗,回顾半生的经历,透露出“中年危机”的困扰,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有所向往,也显示了无奈的怅惘。他在诗中说,“神州虽大局,数着亦可毕。了此足高谢,别有烟霞质”,希望通过思想追求与文学创作,探索性命所系的终极目标。此时他已经开始写作以霍小玉故事为题材的《紫箫记》,因为官场的流言蜚语,说他在剧中讽刺朝廷,迫使他封笔。后来他再以同样题材,写了《紫钗记》,在想象世界里批评权臣弄国,揭露官场的攀缘勾结,抨击时政的龌龊腐败。
万历十九年(1591),汤显祖四十二岁,终于借着前一年天象示警,皇帝批评言官欺下瞒上的时机,上了《论辅臣科臣疏》,批评首相申时行弄权谋私,科道重臣贪污受贿。汤显祖上疏,造成了官场大地震,申时行辞官以表心迹,更多人上书辩解,攻击汤显祖此举是私怨泄愤。最后的结果是,皇帝下诏:“汤显祖以南部为散局,不遂己志,敢假借国事攻击元辅。本当重究,姑从轻处了。”贬谪了汤显祖,降为“徐闻县典史添注”,赶到天涯海角,不给任何工作职务,从此杜绝了汤显祖飞黄腾达之路。“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汤显祖这一趟雷州半岛贬谪之行,前后经历不到一年,却让他翻越梅关,进入岭南海陬,像苏东坡一样,远赴雷州与海南。这番深入瘴疠之地的远行,让汤显祖亲历岭南风光,是他从未接触过的异乡情调,为他提供了撰写《牡丹亭》岭南场景的背景知识。他笔下的男主角柳梦梅就是岭南人士,在广州生活成长,而女主角杜丽娘则生长在梅关旁边的南安府衙。
汤显祖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与他自己的人生历验及生命思考是息息相关的。他的戏剧作品,呈现了不同角色的世间处境,同时揭示了不同人物的自我选择,反映了人物性格、自主意志与生命意义的关系,也间接反映了他自己的理念,一生坚持展现自我的价值与意义。汤显祖在官场上的坎坷,与他本人性格狷介有关,更与他性格中永葆艺术想象的天真有关。为了维护自身秉性的纯净,他以身家性命来抗拒俗世的污秽。在他的作品中,权相是批评的主要对象,官场是污浊不堪的场地,这在《南柯记》与《邯郸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至情”人物,坚守爱情与理想的角色,则是汤显祖歌颂的对象,这在《紫钗记》霍小玉身上已经可以看到,《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更为后世塑造了千古不朽的美丽形象。
三
汤显祖被贬谪岭南之后,虽然得以重回官场,却遭到当权者的白眼,沦落到浙江偏僻的山区遂昌当县令,一待就是五年,不得升迁。最后在不忿之下,汤显祖弃官回乡。他在遂昌为官,生活清净闲暇,开始了《牡丹亭》的创作。弃官之后,回到家乡临川,在一五九八年秋天完成了全剧。在第一出《标目》中,写了《蝶恋花》一词:“忙处抛人闲处住。百计思量,没个为欢处。白日消磨肠断句,世间只有情难诉。玉茗堂前朝复暮,红烛迎人,俊得江山助。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表达了他深感岁月蹉跎,经世济民的理想难以实现,又厌倦官场现实的蝇营狗苟。汤显祖弃官回乡之后,千思万想,焚膏继晷,通过文学创作,追求心目中的至情境界。《牡丹亭》一剧,借着杜丽娘寻觅梦中的理想情人与生命意义,发挥阳明学坚持“赤子之心”的理念,显示了追求理想,不惜出生入死,百折不挠的决心。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特别指出,他撰写此剧,蕴含着深刻的思想性,不是一般的才子佳人团圆剧:“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关键是标出杜丽娘突破生死肯綮,追求至情,肯定自我本体,逆袭当时“存天理,去人欲”的理学意识形态,至少在文学艺术的想象世界中,实现梦寐以求的爱情幸福与人生理想。
汤显祖在创作《牡丹亭》及塑造杜丽娘这个角色时,清楚认识到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分际,思考了如何以虚构超越现实的命题,构筑了艺术创造的“梦”,如何成为历史文化血脉的“真”。他在《题词》中,明确指出“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也就是说,舞台上展现的人世处境与感情,可以是真挚而真实的,则人物与情节即使虚构,也能传递这种真实的情感经验,为人接受,而成为历史现实中的经验与记忆。学者历来征引《题词》的结尾,作为汤显祖以情抗理、创作《牡丹亭》的思想基础。近代思想史家如侯外庐,则在汤显祖剧作中发现了以青春自由冲决道德桎梏的呼唤,算是思想解放的宣言。从文艺创作的角度来看,《牡丹亭》超越虚构与真实,让理想(梦)跨越生死之际,化作世世代代文化记忆(真)的一环。他说:“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这里说的“人世”,是指汤显祖生活的历史现实,也就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现实人生,生活其中,不能逾越宋明理学所构筑的“理”,杜丽娘超越生死的追求,显然是说不通的。因此,汤显祖要在《牡丹亭》中以“情”来代之。这里拈出的“情”是上升到普遍哲思的情,或曰“至情”,涉及世世代代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记忆。在历史文化的长河中,在人类思维的演化进程中,虚构与真实因记忆的延续与转化也会产生变化,甚至调换位置,使十六世纪创造的《牡丹亭》虚构世界,经历几个世纪的淘洗,在二十一世纪成为文化记忆中最真实的人类情感经验。而当时真实的社会现实,到了二十一世纪已经随风而逝,在文化记忆中成了虚幻的“过去”。
对这种虚构转化为真实的历史吊诡性,汤显祖虽然在哲学思辨上没做过仔细分析,却十分着意,并深有所感。他在为罗汝芳诗集写序时说:“古之人若有其诗可诵,而其人尚有未可知者,以待论其世而后知。夫世之为世,古之为古也。古之为古,即其人之所以为人也。故夫论古之世,而后知古之人。非其世何以有其人?然非其人亦何以有其世?”这段话探讨了人与时代的关系,要了解一个人的诗,必须了解他的时代背景。然而,时代与人的关系,不是当时的时代可以决定一切,而是互动的。时代影响人,人也可以创造时代。也就是这种人可以创造时代、可以改变历史的愿景,使得汤显祖在塑造杜丽娘时,让她在梦中创造真实,创造了梦,还要锲而不舍地去追梦,去寻梦,上穷碧落下黄泉,一梦而亡,因梦而生。“牡丹亭上三生路”,不单是追寻真实爱情的故事,也是创造文化记忆中历史真实的探索。在舞台上,杜丽娘起死回生,是活生生的人物;在历史文化记忆中,她也从虚构化为真实,千古不朽。
《牡丹亭》刻画的杜丽娘,从《游园》所展现的青春向往、《惊梦》感受的爱情滋润,到《寻梦》时的缠绵情思,一层一层显示了丽娘内心幽微的感情纠结。面对冷酷无情的现实生活,她在世间追求幸福理想的美梦,只有无限的艰辛与挫折,只能冀望于来生。从《写真》《闹殇》到《冥判》《魂游》,显示为达生命意义必须奋不顾身,死里求生。柳梦梅的出现,是梦寐理想的活化,有柳梦梅在《拾画》、《玩真》(亦称《叫画》)的借力,展示冥冥中两人心灵相通,才有《幽媾》《冥誓》的情投意合,实现《回生》从梦境与幽冥回到真实世界的可能。《牡丹亭》的结尾,与一般才子佳人大团圆不同之处,在于强调夫妻牵手同心,在传统人伦格局中,努力争取应得的认可。
若是只看《牡丹亭》的表面情节,似一部才子佳人大团圆的故事,但其内涵却丰富缤纷,层次繁复。特别是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通过幽深杳渺的华美文辞,探索了女性个人情欲的自由解放,及其与人伦社会道德规约的冲突,在当时有如石破天惊,冲击了保守派道德主义的藩篱,时有禁令限制阅读与演出。《牡丹亭》肯定女性情欲意识,冲击了保守派的道德底线,以致出现许多传闻故事来诋毁汤显祖,如明末苏州文人徐树丕(1596-1683),算不上极端派的卫道人士,在《识小录》书中居然说:“闻若士死时,手足尽堕,非以绮语受恶报,则嘲谑仙真,亦应得此报也。”道听途说,散布谣言,诅咒汤显祖惨死是报应。其实,当时流传“手足尽堕”而死的人是屠隆,来自汤显祖慰问他病情的一首诗《长卿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屠隆可能得了痛风症,又有消渴症(糖尿病),而非后世猜测的梅毒,因此“筋骨段坏”,总之,与汤显祖死于绮语报应无关。到了清代,汤显祖因写《牡丹亭》而在地狱中身荷铁枷受苦的故事,在劝善书中更是广为流传,如道光年间黄正元的《欲海慈航》就说:
昔有人入冥府,见一囚身荷重枷,肢体零落,因问何人。狱卒曰:“汝在生时,曾阅《还魂记》否?”曰:“少年时曾阅过。”狱卒曰:“此即作《还魂记》者也。此词一出,使天下多少闺女失节,上帝震怒,罚入此狱中。”问:“几时得遇赦出狱?”狱卒曰:“直待此世界中更无一人歌此词曲者,彼乃得解脱耳。”
清代中央及地方政府,经常公布禁令,设局收毁“有伤风化”的小说淫词,如道光年间《劝毁淫书征信录》就把《牡丹亭》列为淫书,必须禁毁。同治年间江苏巡抚丁日昌下令严禁淫词小说,就把《牡丹亭》《红楼梦》与《金瓶梅》《绣榻野史》《如意君传》等并列,一律严禁。在当时官府眼中,只要涉及男女谈情说爱,就有可能败坏善良风俗,必须坚壁清野,扫除绮思。
传统卫道人士为何如此嫉恨《牡丹亭》这类涉及情色的文学与戏曲作品,禁书毁版、禁止演出而唯恐不及,从保守顽固的人伦道德角度来看,是为了坚守“三从四德”的社会规范(闺范),要求妇女谨守妇道,保证男性社会的主导权威。《牡丹亭》的故事主脉,以杜丽娘春心萌发的一场梦,发展到不惜生生死死,上天下地追寻自主决定的爱情,不但挑战了以父权为代表的男性中心权威,甚至蔑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规范,结尾居然还暗示,皇帝的政治权威也得符合天心人意,认可这一段出生入死的爱情与婚姻。
《牡丹亭》的剧情梗概,在第一出的《汉宫春》词中,汤显祖就做了剧透:“杜宝黄堂,生丽娘小姐,爱踏春阳。感梦书生折柳,竟为情伤。写真留记,葬梅花道院凄凉。三年上,有梦梅柳子,于此赴高唐。果尔回生定配。赴临安取试,寇起淮扬。正把杜公围困,小姐惊惶。教柳郎行探,反遭疑激恼平章。风流况,施行正苦,报中状元郎。” 从故事主脉看来,领衔演出的是女主角杜丽娘,陪衬的是男主角柳梦梅。情节发展是杜丽娘小姐出生入死,由死回生,再努力肯定生存价值的三段过程。全剧五十五出,情节跌宕起伏,要完全忠实原剧,从头到尾展现舞台演出,恐怕要演上半个月之久。因此,近代演出一般出现三种串演方式,按演出时段酌情删减唱段:一是串联《惊梦》《寻梦》《写真》《闹殇》的杜丽娘因情而死的一晚演出(三小时),二是加上《闺塾》《冥判》《拾画》《玩真》《幽媾》《冥誓》《回生》的两晚演出(六小时),三是近来流行所谓“全本《牡丹亭》”的三晚演出(九小时)。
《牡丹亭》的剧情,若按三段过程分解,可以大体浓缩如下:
第一段:南安太守杜宝的女儿杜丽娘进入青春期,父亲安排了老儒陈最良设席教书。开讲是《诗经·关雎》,聪慧的丽娘在侍女春香闹学的过程中,对男女之情有所领会,情窦初开。在春香诱使之下,丽娘到废弃的大花园中游耍,看到废弃的花园在春光中绽放姹紫嫣红,感到自己年岁渐长,芳华虚度,不禁感伤“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回房休息,在梦中遇到了书生柳梦梅,并在牡丹亭中欢会好合,留下美好的回忆与怅惘。醒来后春情难忘,次日到花园中寻梦,思念理想的梦中情人而不可得,从此郁郁寡欢,以致相思而死。死前为自己的容貌写真题诗,嘱咐春香藏在花园的假山之下,葬身大梅树下,以待来日机缘。
第二段:丽娘到了阴曹地府,判官查出她阳寿未尽,让她鬼魂回到阳世,寻觅她未来的夫婿。三年后,岭南柳梦梅赴临安赶考,途经南安,病倒风雪之中,在埋葬丽娘的梅花观中养病,无意中发现了假山下的丽娘遗像,为之神魂颠倒,终日呼唤佳人现身。丽娘鬼魂出现,以邻女的身份前来陪伴,两人情投意合,欢好无限,誓盟为夫妻。最后鬼魂告知原委,嘱托柳梦梅在石道姑的协助下,掘开墓穴,让她还阳回生。
第三段:剧情再下一步的发展,是丽娘回生之后恢复人伦至情,为追寻理想爱情与婚姻自由的实现,得到父母认可,获取社会道德规约的合法性。她先让母亲与春香相信了自己回生,母女相聚,亲情流露,再让柳梦梅到淮扬前线寻找抗敌的父亲。此时杜宝退敌获胜,庆功宴上来了自称女婿的柳梦梅,不禁使深信女儿已死三年的杜宝愤懑填膺,吊打撞上前来的骗徒。正好朝廷昭告柳梦梅中了状元,四处寻觅不得,主考官闯入杜宝衙门,救下了吊在梁上的柳梦梅。翁婿闹得不可开交,丽娘、杜母、春香赶到,杜宝却以为她们都是鬼魂化作人身,乱上加乱,一直闹到金銮殿上。皇帝命令取出秦朝照胆镜,辨明丽娘确是人身,并非鬼魂,一场闹剧终于以喜剧收场。
汤显祖此剧的思想内容,反映了阳明学派肯定自我良知,追求个人理想幸福才是趋向圣贤之道的信念,通过爱情与亲情的展现,汤显祖创作了一部超越生死的不朽著作,就像他在《牡丹亭·题词》里的总结:“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这出戏经历了四百年舞台演出,而能永葆青春,获得现代观众共鸣,并感到无比钦佩,是因为文学想象的境界高超,在华丽的辞藻背后,蕴含沛然难以抵御的生命活力,展现了女性追求自身爱情与幸福的无畏精神,可谓女性主义肯定自我主体的萌芽,具有历史文化的前瞻性。
本文是为《牡丹亭》新注释本所写导读。新版注释者俞为民,主编胡晓镜,即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