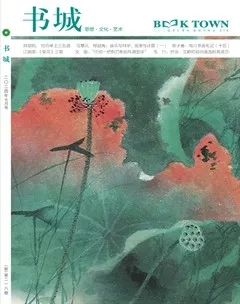哭还是不哭,这是个问题
帕尔马的《秘鲁传说》说,古代秘鲁的利马城里有所谓的“哭丧婆”,是一群满脸皱纹、比穷人身上的虱子还干瘪的老太婆。她们的职业是抽噎哭泣,大把大把地甩眼泪。这些人都像巫婆和老鸨一样,老得不能再老,丑得不能再丑。凡能留下一笔可供办起一场体面丧事的财产的人寿终正寝,遗嘱执行人和死者眷属便会走街串巷,寻访最有名的哭丧婆,由她再去雇佣陪她一起哭丧的伙伴。报酬是首席哭丧婆四个比索,陪哭者每人两个比索。当办丧人装出一副慷慨大方的样子,除正价外多给几个小钱时,哭丧婆们也得有点额外举动。所谓额外举动,就是一边号哭一边顿足捶胸,像发羊痫风一样抽搐和揪头发。她们和那些手拿蜡烛前去吊丧的所谓“穷光蛋”一起,在教堂门口等着遗体抬进抬出,尽情发泄她们那出卖的悲痛。要说利马有什么有利可图的职业,那就是受雇哭丧婆这一行了。在所有哭丧婆里,有一个高级哭丧婆,她是这类人中的至高无上者,只有为总督、大主教或最显贵人物举行丧礼,她才屈尊到场。她与众不同,雅号叫“圣星期五的受雇哭丧婆”。所以才有了这种说法:“某某先生的葬礼真是登峰造极了。你听啊亲爱的,连圣星期五的受雇哭丧婆都光临教堂门口了。”(《圣星期五的受雇哭丧婆》)
“哭丧婆”当然不仅仅是古代才有,马尔克斯也写过现代的“哭丧婆”。“哭丧—这项活动在大西洋沿岸地区又派生出许多有趣而又荒唐的细小区别—在拉谢尔佩镇土生土长的居民心目中,是一种职业,它不应当由死者的家人从事,而是要交给一个女人,一个无论从素质上还是从经验上都堪称专业的哭丧婆。”“哭丧婆们不是来哭死人的,而是来向来宾当中的显贵人物致敬的。当人们发现某个因为富甲一方而被当成有特殊贡献的重要人物将要登场,便会有人通知值班的哭丧婆。接下来的情节就非常有戏剧性了……哭丧婆双臂高举,脸戏剧性地抽搐着准备放声大哭。随着一声长长的呼啸,刚刚到来的人听到了整个故事—听到了死者的走运时光,也听到了他的倒霉岁月,听到了他的优点,也听到了他的缺点,还有他的快乐、他的痛苦;而故事的主人公此时正仰面朝天躺在一个角落里渐渐腐烂,身边不是猪就是鸡,身下垫着两块木板。”(《拉谢尔佩镇的奇异偶像崇拜》)秘鲁在太平洋沿岸,这里是大西洋沿岸,可见得在两大洋之间的美洲都有这一行当。在富恩特斯的《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中,写到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临终时,想象人们会雇一些哭丧婆来哭他,可见墨西哥也有哭丧婆这一行当。
之所以会有这一行当,无非是因为有需要。死人是必须有人哭的,否则显得活人没感情,更显得死人没面子。尤其是死者的亲人,特别是死者的儿女,不哭更是大逆不道,有违社会良善风俗。也就是说,哭有两种基本的功能,一种是满足感情的需要,一种是满足社会的需要。“哭丧婆”满足的是后一种需要。
哭的两种基本功能,在《红楼梦》里的贾珍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第十三回写其儿媳秦可卿死了,作为公公的贾珍“哭的泪人一般”,“说着又哭起来”,“恨不能代秦氏之死”,甲戌本批云:“可笑!如丧考妣,此作者刺心笔也。”贾珍这里的哭满足的是感情的需要,显示了其对秦氏异乎寻常的不伦之情。到了第六十三回,贾珍的父亲贾敬为服药求道所误而死,停柩在铁槛寺。贾珍父子闻了此信,即忙告假,星夜驰回。半路遇见家人,问家中如何料理。家人汇报说,怕家内无人,接了亲家母和两个姨娘在书房住着。听见两个姨娘来了,贾珍父子相顾一笑,贾珍忙说了几声“妥当”—两个姨娘就是尤二姐和尤三姐,与贾珍父子都有一腿的。到了铁槛寺,已是四更天气。“贾珍下了马,和贾蓉放声大哭,从大门外便跪爬进来,至棺前稽颡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咙都哑了方住。尤氏等都一齐见过。贾珍父子忙按礼换了凶服,在棺前俯伏。无奈自要理事,竟不能目不视物、耳不闻声,少不得减些悲切,好指挥众人。”联系此前路上的关心和后来服丧期间的表现,贾珍这里的“跪爬进来”“稽颡泣血”就全成了表演,连“竟不能目不视物、耳不闻声”也是辛辣的讽刺了。贾珍这里的哭满足的是社会的需要,与他对秦氏发乎不伦之情的痛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如果社会的需要不被满足,也就是该哭的时候不哭,又会怎样呢?那甚至是会招来杀身之祸的。谓予不信,请看加缪的《局外人》。辩护律师对“我”说,预审推事们了解到“我”在妈妈下葬的那天“表现得无动于衷”,如果做不出什么解释的话,这将成为起诉“我”的一条重要依据。果然,在法庭上,所有人都做证说,在“我”妈妈死后,“我”的所有言行都有违社会常识。养老院院长说,他对“我”在下葬那天的平静深感惊讶,说“我”不愿意看妈妈的遗容,没有哭过一次,下葬之后立刻就走了,没有在坟前默哀。还有一件事也使他感到惊讶,那就是殡仪馆的人告诉他,“我”不知道妈妈的具体岁数。说到这里,大厅里一时鸦雀无声。养老院的门房做证说,“我”不想见妈妈的遗容,“我”在守灵时抽了烟、睡了觉、喝了牛奶咖啡。这时,“我”感到有某种东西激起了全大厅的愤怒,“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真正有罪。养老院的老人做证说,他没有看见“我”哭。检察官也揭发说:“陪审团的先生们,此人在自己母亲下葬的第二天,就去游泳,就去开始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就去看滑稽电影、放声大笑,我用不着再向诸位说什么了。”最后,检察官声嘶力竭地喊道:“我控告这人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这一声宣判,显然对全体听众,当然也对陪审团,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时“我”才感到,自己大事不妙了。庭长宣布审判结果:将要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在一个广场上将“我”斩首示众。—“我”只因没有满足社会的需要、在妈妈的葬礼上没有哭而被处决!
正因为出于满足社会的需要,在葬礼上哭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哭丧婆不仅秘鲁有,哥伦比亚有,包括中国在内,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不仅古代有,现代也有,现在甚至有用录音代替活人、代替哭丧婆的。科塔萨尔的《为您效劳》(收入《秘密武器》),写了一位现代版的哭丧婆,是发生在法国巴黎的故事,很有讽刺意义和喜剧色彩。弗朗西内太太受雇去冒充一个死者的母亲,来求她的罗塞老爷难以启齿、吞吞吐吐地说:“这位先生……是位非常著名的时装设计师……他孑然一身,也就是说,远离家人。您理解吗?除了朋友之外,他无依无靠……作为他的朋友,我们考虑,为了葬礼能达到恰当的效果……我们认为,举行一个仪式,只有他的朋友们,只有很少的几位朋友参加……以这位先生的情况,还不够庄重……也无法诠释他的辞世给人带来的沉痛……您理解吗?我们觉得您也许能出席追悼会,自然还有葬礼……我们假设您以逝者亲戚的身份……您懂我的意思吗?很近的亲戚……比如他的姨妈……甚至我斗胆建议……我们觉得您可以作为……请您谅解……我的意思是,作为逝者的母亲出现……请允许我向您解释清楚……母亲刚刚知道儿子过世,从诺曼底赶来陪伴儿子,看他入葬……那么自然,您一到那儿,就应该做出样子……您明白的……痛苦,绝望……主要是做给来宾们看的,在我们面前,您保持沉默就行了。”(按,省略号除个别外都是小说原有)弗朗西内太太带着心理矛盾和对报酬的渴望接受了这个差事:“要我装成那位过世的时装设计师的母亲是不对的,因为这种事情是不应该假装的,也不应该欺骗别人。但也要考虑来宾的感受,如果葬礼上没有逝者的母亲,甚至连一位姨妈或者姐妹也没有,仪式就显不出它的意义,也无法诠释他的辞世给人带来的沉痛。”然而巧合的是,死者恰巧是以前她在罗塞老爷家干活时,所有人里唯一尊重她、对她好的人,还说她一看就是好人,像是一个乡下的姨妈。这下她的悲痛就不必装了,她真的大哭起来,还哭得情真意切,哭得罗塞老爷表情古怪,对她说没必要继续装了,不知道她这根本就不是装的……“天真的弗朗西内太太一面讲述,一面让读者领略那个道德极度沦丧、极其腐化的社会,它隐藏在每一句话的背后……身在其中的人得维护自己的面子,得伪装,要是真正的母亲并不存在或是没有到场,还得创造出一个母亲来:只要能贯彻完成那些维护它、支持它、捍卫它的仪式和礼节,这个社会就绝不会犹豫半分。”(科塔萨尔《文学课》)
科塔萨尔还有一篇《葬礼上的举止》(收入《克罗诺皮奥和法玛的故事》之《奇特职业》),写有户人家专门挑战虚伪的葬礼:“我们不是为了茴香酒,也不是因为不得不去。有人已经猜出来了:我们去是因为无法忍受各式各样最狡诈的虚伪。我年纪最大的堂姐负责了解葬礼的性质,如果是真的,如果人们哭泣是因为在晚香玉和咖啡的香味中男男女女们除了哭泣再无他想,我们就会留在家里,在远处陪伴他们。顶多我的母亲会过去一下,以全家人的名义道个恼;我们不喜欢强行加入他人与阴影的对话之中,那是傲慢无礼的行为。但是,如果我堂姐通过不慌不忙的调查,怀疑在带顶庭院或是客厅里出现了虚伪的征兆,那么全家人会立即穿上最好的衣服,等待葬礼开始,无可阻挡地逐一登场。”他们到虚伪的葬礼上去轮番痛哭,让虚情假意的死者家属原形毕露,其战略战术及作战效果颇堪发噱。这是传统哭丧婆形象和功能的大翻转:本来是帮助虚情假意的死者家属的道具,却成了揭露死者家属的虚情假意的利器。
后来,马尔克斯为科塔萨尔写的悼词,深得科塔萨尔此类小说的神髓:“不过,大胆设想一下,假若死者还能再死一次,那么,眼下这种举世皆为他的辞世而悲的场景,恐怕会让他无地自容,再死一次。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书里,谁也不像他那样惧怕身后的哀荣、奢华的葬礼……所以,正因为了解他,深爱他,我才拒绝出席科塔萨尔的一切治丧活动。”(1984年2月22日在墨西哥城美术馆的演讲《人见人爱的阿根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