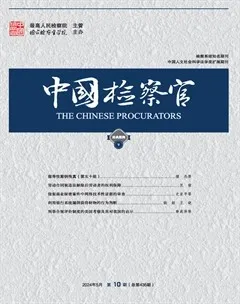骗取型贪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再理解
邓骏伟 赵天文
摘 要:骗取型贪污行为应当符合骗取行为本质特征,即行为人事先未占有、控制、支配公共财物。现行司法解释对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界定过窄,与法律规定、司法实践和骗取行为特征不协调。结合骗取手段转移公共财物的间接性和贪污行为所侵害的职务廉洁性,骗取型贪污中的职务便利是指行为人的职权或履职事项对公共财物处分权人具有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可以是纵向的、基于行政关系的领导力,也可以是横向的、基于工作流程的控制力。
关键词:贪污罪 骗取手段 职务便利
《刑法》第382条第1款明确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为贪污罪的构成要件要素。通说认为,贪污罪侵犯的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以及公共财产权。[1]而职务便利正是体现职务行为廉洁性的行为要素,因此在适用贪污罪评价犯罪行为时,需要关注对职务便利的解释。笔者在审查起诉案件中发现,贪污犯罪事实愈发复杂,犯罪行为愈发隐蔽,呈现出从单独犯罪向共同犯罪发展的趋势,犯罪手段从单一行为侵吞、窃取型向复合行为骗取型演化,犯罪流程从单一节点实施向多阶段贯穿演变。最高检1999年9月16日公布施行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立案标准》)中明确了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概念内涵,但在骗取型贪污中,该概念界定存在范围过窄的问题,尤其是难以应对相互衔接的工作流程中国家工作人员共谋骗取公款类的案件。
一、相互衔接工作流程中共谋骗取公款“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认定存在的问题
[基本案情]某军队单位财务部门负责人甲,人力资源部门负责档案工作的乙、负责兵员工作的丙,工薪助理员丁等四人共谋通过篡改复员军士入伍前户口性质套取复员费。[2]乙伪造数名复员军士档案材料,将其中户口性质由城镇篡改为农业;丙根据篡改后的档案材料,制作虚假的复员费结算通知书;甲安排丁根据前述结算通知书编制虚假经费结算单、复员军士退役经费汇总表等材料,其中虚增复员费数十万余元。丁将钱款冒领套现,后由四人分赃。[3]
在上述改编案例中,复员军士入伍前户籍性质认定和复员费计发为前后衔接的工作流程,即后者需以前者为依据。然而根据岗位职责,乙、丙均不具有主管、管理、经手复员费的权力或方便条件,只有甲、丁对复员费具有主管、管理职权。如果严格按照《立案标准》对职务便利的界定,则案件事实应当归纳为:乙和丙分别利用档案业务经办人、兵员业务经办人的岗位便利[4],在复员费结算工作期间时将数名复员军士户口性质由城镇改为农业,并通过甲、丁作为财务部门负责人、工薪助理员的职务便利,骗取复员费,即认为本案中利用职务便利的行为仅是甲安排丁在制作复员费银行代发材料时虚增复员费。然而,这种事实归纳方式无法从本质上区分骗取型贪污罪和诈骗罪。假设本案没有甲、丁的参与,或言甲、丁在正常履职过程中,根据乙、丙提供的篡改材料,错误地多发了复员费,按照上述归纳方式,乙、丙篡改户口性质的行为并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即使骗取单位公款也只能评价为诈骗。那么,仅仅是有无财务人员参与的区别,罪名认定就不相同,难免带来参与犯罪的职能环节越多、犯罪的隐蔽性越强,反而罪责更轻的直观法感。因此,笔者尝试对骗取型贪污罪中职务便利解释作轻缓扩张,将国家工作人员履职事项在工作流程上的影响力也评价为职务便利。
二、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适用困境
虽然《立案标准》明确了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定义,但这种定义与骗取行为特征、刑法贪污罪的立法精神不相适应,司法实践中对骗取型贪污中职务便利的理解认定也并非与《立案标准》规定完全一致。
(一)司法解释对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内涵的界定
《立案标准》明确,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务上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及方便条件。最高法2012年9月18日发布的第11号指导性案例——“杨延虎等贪污案”裁判要点对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也做出相同解释,并进一步明确这种职务便利既包括本人职务上的便利,也包括职务上有隶属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因此,并非国家工作人员的任何职权或方便条件都构成贪污罪中的职务便利,而要求这种职务便利应当直接关联公共财物,或者垂直指向公共财物,这是由贪污罪的经济性和职务性复合特点决定的,与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无关的职权、职务便利,不能构成贪污罪中的职务便利。
对于“主管”“管理”“经手”,有关机关在办案实践中进一步归纳,认为“主管”一般是指行为人不具体管理、经手公共财物,也不控制、占有公共财物,人财相对分离,但具有公共财物的处置决定权,主管人包括部门负责人、上级对口领导、本单位领导,也包括领导层中由于工作协作分工而对公共财物职能部门协管的非主管领导;“管理”是指行为人具有日常管控、监督、监守、保管公共财物的职权,管理人可能控制、占有公共财物,也可能不控制、占有公共财物但对公共财物具有调度或安排等支配职权;“经手”是指因执行公务而具有的领取或者支出公共财物的职权,具体实施公共财物的日常运转和使用,经手人通常控制、占有公共财物。[5]
(二)上述内涵界定与法律规定的不协调
《刑法》第183条第2款规定,国有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和国有保险公司委派到非国有保险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故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进行虚假理赔,骗取保险金归自己所有的,依照贪污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国有保险公司委派到非国有保险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并非天然具有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或方便条件,其职务行为即编造保险事故的行为只是最终处分权人错误行使处分权的原因。对于该款规定是注意规定还是法律拟制,存在不同理解,如果理解为注意规定,则贪污罪的骗取手段不要求行为人具有对公共财物的垂直管控地位,即使行为人没有对公共财物的最终处分权,但其基于职务处理的有关公共财物的事项使其具有实质上公共财物处分人的地位;如果理解为法律拟制,则几乎只有该款规定的情形可能成立骗取型贪污。[6]前一种理解突破了《立案标准》界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后一种理解则使《刑法》第382条第1款关于骗取型贪污的规定几乎成为具文。
(三)上述内涵界定与司法实践的不协调
当前司法实践对贪污罪中的职务便利以及骗取手段理解、认定不一,部分判决对职务便利的理解并不完全符合《立案标准》规定。如在孙威力贪污案[7]中,孙威力作为民政助理的工作职责是审核上报优抚对象信息,并不具有主管、管理或经手公共财物的权或方便条件,其职责并不会直接导致公共财产所有权力或占有的转移,孙威力并非单位领导或财务业务链条上的领导、负责人,也不存在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的空间,故孙威力并不具有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或方便条件,其工作职责和取财结果之间只是横向的工作流程先后关系。
(四)上述内涵界定与骗取行为特征的不协调
如不考虑量刑上的不均衡,大体可以认为,骗取型贪污罪是诈骗罪的特别法条,前者在行为对象、行为主体方面需要具备特别要素。[8]那么,骗取型贪污应当符合普通诈骗的一般行为特征,在这个意义上,骗取和诈骗二词文义上并无明显区分。诈骗的行为特征是财产处分权人因为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产生错误认识,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因而导致占有转移,即在骗取行为中,行为人事先并不占有、控制、支配被骗取的财物。在国家工作人员对公共财物具有管理、经手权力或方便条件的情况下,如果其已经占有、控制、支配[9]了公共财物,则根本没有成立骗取的空间。对自己单独或与他人共同占有、控制、支配的公共财物,即使在据为己有的过程中存在欺骗的方式、手段,对行为整体仍只能评价为侵占或窃取。如军队财务部门的出纳人员,伪造其保管的现金保险柜被砸、现金被盗取的假象,实际将柜内现金据为己有的,虽形式上有欺骗行为,但这个过程中没有产生任何公共财物占有转移,所以仍属于侵吞型贪污罪,其伪造现场的行为,目的在于掩饰其侵吞行为。
《立案标准》中的“管理”“经手”,指向的是行为人已经全部或部分占有、控制、支配公共财物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讲,《立案标准》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理解与骗取行为特征具有天然的矛盾。究其原因,在于贪污罪中的“侵吞”“窃取”“骗取”以及“其他手段”本身具有形式和实质上的差异,对应的职务便利范围也有所不同,而这正是《立案标准》没有区分的,这种不加区分的后果,就是不当限缩贪污罪尤其是骗取型贪污罪的范围。[10]
三、对骗取型贪污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再理解
《立案标准》属于现行有效的司法解释,在承认其对司法实践具有法定适用效力的同时,也有必要关注贪污罪中职务便利的共性和骗取型贪污罪中职务便利的特殊性。笔者认为,结合骗取行为本质特征,对骗取型贪污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应当理解、解释为利用职权范围或具体履职行为对公共财产处分权人形成影响,即除纵向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外,还应涵盖横向利用工作流程下游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当然,后一种情况还要求该工作流程以处分公共财物为目的。
(一)骗取型贪污侵犯公共财产权的间接性
如前所述,骗取型贪污罪中的公共财产权是以间接转移的方式被侵犯的,而侵吞、窃取型贪污罪中的公共财产权是以直接转移的方式被侵犯的,这是骗取型贪污罪与侵吞、窃取型贪污罪在手段层面的本质区别,这种间接性体现在行为人本身并不占有、控制、支配公共财物。换言之,较之于侵吞、窃取型贪污,骗取型贪污在职务行为和取财结果之间,多了一层介入因素,即处分权人的处分行为。
本文案例中,乙、丙本不具有公共财物处分权限,而是通过甲、丁公共财物处分权人虚增数额的处分行为,实现取财目的,这正是骗取型贪污侵财间接性的现实体现。
(二)骗取型贪污中职务行为的指向性
根据《立案标准》,职务便利应当直接关联公共财物(管理、经手),或者垂直指向公共财物(主管)。前文已经论述,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国家工作人员难以成立骗取型贪污罪,因此在《立案标准》列明的范围内,能够成立骗取型贪污罪的通常是主管公共财物的国家工作人员,即骗取型贪污罪中职务行为垂直指向公共财物处分行为。然而,还应当注意到,涉及最终处分公共财物的工作流程中,除了纵向审批流程之外,还有横向的跨部门传递、衔接流程,正如本文案例中,财务部门结算、发放复员费用,需以人力资源部门对军(工)龄、级别、岗位等的认定为依据。在横向流程中,当在前认定环节作为在后处分行为依据时,前者即具有了对后者的实质影响力。换言之,当在前环节工作人员基于职务做出涉及处分公共财物的认定时,其职务行为就产生对公共财物处分的实质影响力。
(三)骗取型贪污中被侵犯的职务廉洁性法益
职务廉洁性法益是区分骗取型贪污罪和诈骗罪的关键,也是骗取型贪污罪相较于诈骗罪多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构成要件要素的根本原因。骗取型贪污中的职务行为与取财结果之间介入了公共财物处分权人的处分行为,即骗取型贪污罪中的职务行为并不直接作用于公共财物之上,而只能作用于处分权人之上,这种作用就是骗取型贪污行为人的职务行为对公共财产处分权人的影响力。如果行为人没有利用职务行为影响处分权人,或者利用了职务行为但是没有影响到处分权人,即使获得了处分权人所管控的公共财物,这个过程中职务行为就没有发挥作用,不能评价为职务廉洁性受到侵犯。
同时,这种影响力既应当包括纵向的领导力,也应当包括横向的流程控制力。因为国家工作人员一旦利用职务行为影响公共财物处分权人做出错误处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即遭破坏,而这种破坏与影响力的方向是无关的。
本文案例中,甲作为财务部门负责人,对该部门具有实质上的领导职权,故同属该部门的丁与甲具有实质上的职务隶属关系,而且甲正是利用了作为财务部门负责人的职务便利,向丁交代、安排虚增、取现事宜,才使得套取复员费的流程得以实现;乙、丙同属于人力资源部门工作人员,在部队复转退工作中,户口性质是费用结算的重要依据,且户口信息由人力资源部门认定后传递至财务部门,财务部门以此为据直接套用计发标准而不再实质审查户口信息真实性,此时应当认为,在与户口性质相关的复员费用计发项目中,档案业务、兵员业务人员对相关款项具有横向工作流程上的实质上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能够作用于工作流程下游具有公共财物处分权人。甲、乙、丙、丁利用各自职权篡改复员军士户口性质、虚增计发费用,从而谋取不法利益的行为当然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
(四)对骗取型贪污罪中职务便利解释的轻缓扩张
综合骗取型贪污罪本身包含的骗取方式和利用职务贪利特性[11],骗取型贪污罪应当具有“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行为人利用职务行为——对自己以外的公共财物处分权人产生影响——处分权人陷入错误认识——处分权人因错误认识处分公共财物——行为人因此取得公共财产”的典型构造,同时,只要行为人的职权范围或者具体履职事项在地位或流程上足以影响处分权人做出处分决定,即可认为职务便利产生了影响力。相较于《立案标准》,该种解释的轻缓扩张在于将履职事项在工作流程上的影响力也评价为职务便利。
贪污罪保护的是职务廉洁性和公共财产权双重法益。骗取型贪污罪中的职务廉洁性法益对应的就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构成要件要素,公共财产权法益对应的就是利用“骗取”手段构成要件要素。那么,对骗取型贪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解释就应以保护职务廉洁性目的为指导。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行为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12],意即具有职务行为外观,但背离公共利益,同时对公共财物处分权人产生影响的行为,即可认定为骗取型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便利的行为。不可否认的是,对于可能存在职务外观的行为,其同时具有公共利益目的和个人目的的,如“搭车”虚增申报金额,此时仅需将其中虚增部分对应的行为评价为利用职务便利行为。
本文案例中,犯罪行为流程是“篡改档案户口性质——篡改结算通知户口性质——虚增复员费”,篡改信息经过层层传递,最终由不知情的出纳人员开具了含有虚增数额的代发复员费转账支票。这个过程中出纳作为对复员费具有处分权限的人,被丁直接欺骗,受此影响产生错误认识,处分了单位公款,而丁对出纳的欺骗也正是基于之前乙、丙的篡改行为得以实现的,即乙、丙实施了虚构复员军士户口性质的行为,丁实施了虚增复员费的行为,且上述行为均足以影响出纳处分公共财产的决定,与出纳陷入错误认识和处分公共财物具有因果关系,故从整个行为流程看,既符合骗取行为的构造,又体现了职务便利影响。当然,丁作为工薪助理员,单纯从其工作职责看,本身对公共财产具有管理职权,按照前文论述,如果独立评价其虚增复员费数额的手段,应当属于侵吞或窃取,但丁的行为是全案犯罪流程的组成部分,因此将全案行为手段整体评价为骗取也是合适的。
(五)该种扩张解释的法理依据
上述认定骗取型贪污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路径,虽与《立案标准》中的界定存在出入,但并未违背《立案标准》的原则立场,回归骗取行为、职务便利的本质特征,既可弥补《立案标准》中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界定过窄的不足,同时由于指明了职务便利的作用对象、影响力方向,也能避免不当扩大骗取型贪污罪的成立范围。此外,上述认定路径只是针对《立案标准》中职务行为与公共财产的直接关系的突破,这种突破事实上是一种法教义学上的修正,笔者仍然认为骗取型贪污罪中的职务便利须与公共财物至少具有间接关系,并未切断职务便利与公共财物的关联性,也不违背贪污罪的经济性和职务性复合特点,而且在法益保护、行为特征方面,仍然与贪污罪条文本身表述是融洽的,契合《刑法》第183条第2款规定的立法精神。
至此,笔者认为,在骗取型贪污中,只要行为人的履职事项能够对公共财物处分权人形成影响力,并且行为人实际利用了这种影响力,即可认定行为人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本文案例案件事实的归纳可以表述为:甲、乙、丙、丁等四人共谋套取军士复员费,分别利用甲作为财务部门负责人、乙作为档案业务经办人、丙作为兵员业务经办人、丁作为工薪业务经办人的职务便利,在结算复员费时将数名复员军士户口性质由城镇篡改为农业,骗取复员费数十万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