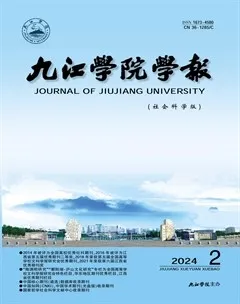隋代骁果与府兵在建置与布局上的差异性分析
摘要:骁果与府兵同属府兵制中央军府系统,具有相似的制度结构。但是,二者在建置方式上存在差异。骁果不具有乡土品质,不囿限于关陇地域。炀帝组建骁果,旨在抛开乡土地域的束缚,将骁果作为一类对早期府兵制原型的超越形式而加以利用。二者在江都权力空间布局上亦有差异。江都之变爆发前,与皇帝关系近密的给使驻防殿中禁内,其外以少量十二卫府兵驻防宫内禁外,最具实力的骁果则驻防在宫外城内。骁果武力布置在江都城权力布局的外层,将以府兵为中心的“重内轻外”之局转成以骁果为中心的“外重内轻”之局,最终促发了江都之变。
关键词:骁果;府兵;乡土品质;江都之变;外重内轻
中图分类号:K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580(2024)02-0065-(07)
DOI:10.19717/j.cnki.jjus.2024.02.012
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定令时,以左右翊卫、左右骁骑卫、左右武卫、左右屯卫、左右御卫、左右候卫等十二卫统领府兵,合以左右备身府、左右监门府,共同构成了府兵制中央军府系统——十六卫府。大业九年(613)募民为骁果,骁果被归入左右备身府,与十二卫府兵同属中央军府系统。学术界考察了隋代骁果与府兵之间的关系。谷霁光在《府兵制度考释》中指出,隋代宿卫分内外,禁卫综合,内外相维,府兵与骁果在内外宿卫之间存在矛盾与争夺,炀帝不断扩充骁果,将其列入禁卫并参与内宿卫,是隋府兵解体的重要因素[1]。气贺泽保规在《以骁果制为中心论隋炀帝时代的兵制》一文中指出,骁果是在原有府兵暴露出已无法发挥有效军事机能的弊病之后于左右备身府之下组建的,骁果制的出现意味着炀帝试图以新的形式来解决府兵制所面临的问题。骁果制从上到下都采用了与府兵系统完全一样的组织形态,炀帝并没有让骁果制从府兵制中独立出来,两者是互补关系[2]。黄永年在《说隋末的骁果——兼论我国中古兵制的变革》一文中指出,以农耕为业的府兵不愿背井离乡长期远征,所以需要在府兵之外招募一支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新军,骁果便应运而生[3]。综上所述,隋代骁果与府兵之间究竟是一种对立关系?互补关系?还是替代关系?就此问题,仍有进一步研讨的必要。
一、隋代骁果与府兵建置方式的差异
早期府兵制在吸纳地方武力时,主要通过“募”的形式,如西魏大统九年(543)广募关陇豪右以补充军队,北周建德三年(574),改军士为侍官,募集百姓以充之。随着战争日渐白热化,对于大量兵员的需求使得原来的“募”兵逐渐为“征”的形式所代替。然而,在“征”兵之外,仍然存在“募”的现象,如北周建德五年(576),武帝大举讨伐北齐,宇文弼乃“募三辅豪侠少年数百人,以为别队,从帝攻拔晋州”[4]。所募之“三辅豪侠”并未进入北周正式军事编制之中,而以“别队”的方式参加这场战争,体现了这支部队特殊的军事性质。隋朝实现南北统一之后,“征”成为主要的兵员征集形式,如隋炀帝第二次远征高丽时,首先“征天下兵”,之后才组建骁果武力,而在组建骁果时,又重新利用了“募”的形式。
所谓“募”兵,体现的是一种交易关系,一个愿买,一个愿卖,在双方谈好合适价钱之后达成交易,亦可能是事后“付款”。因为古代战争多为掠夺性质,于是才有应募及“别队”,甚至还有跟随着去捡“便宜”的。大业九年(613),隋炀帝改革原有军事制度,开始募集并组建了骁果,支付给骁果想要获得的丰厚政治和经济利益,而皇帝想要获得的则是骁果在战场上拼杀的实际能力。
“骁果”一词用来状物时,本意在形容某人的骁勇果敢,如称某人“勇力骁果”“勇决骁果”“志气骁果”等。炀帝组建的骁果作为国家军队的一部分,其身份相比府兵更为特殊,如府兵的卫士名衔不会出现在墓志铭中,不会作为加重墓主身份的符号进行书写,然而骁果名衔则不同,它能够以一类职衔的方式被写入墓志铭中。如《刘世恭墓志》记载:“大隋京兆郡大兴县进贤乡左备身府故骁果刘世恭,以今年十月廿日,于河南郡崩逝,以大业十一年岁次乙亥十一月乙丑朔十四日壬寅,葬于城东白鹿原浐川乡之原。”[5]骁果成为了墓主政治身份的表征,说明了骁果在隋朝地位的特殊性。
气贺泽保规认为,隋炀帝的骁果制是对府兵制的补充,并非是针对府兵制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的解决办法。骁果隶属于左右备身府,并不是脱离府兵系统而建立的独立军事制度。骁果的主帅多来自于炀帝大业十二卫军府系统职官,骁果并未从府兵系统中脱胎出来,骁果是对府兵制最初原点的回归。那么,府兵制的最初原点是什么?按气贺泽氏的说法,骁果举家被蠲免了赋役,有类于府兵系统早期的兵户制;骁果的上下级关系,带有私人性质,则类似于府兵系统早期的乡团。从这些方面看,骁果与早期府兵制相当接近,从本质上来说,骁果是向早期府兵制这一原点的回归[6]。早期府兵制,就其年代来说,应属西魏创建之初的府兵制。气贺泽氏所说的原点,主要指西魏府兵制的建置机制,它是一种吸纳具有“豪侠”性格之人物的机制。换言之,气贺泽氏认为骁果所“募”之豪侠,与早期府兵制所“募”之豪侠,在社会气质上具有一致性,因此认为骁果即是对早期府兵制的一种回归。
西魏府兵制是一种吸纳具有“豪侠”性格之人物的机制,它能够将两种乡里武力(武川集团与关中豪右)纳入共同的制度系统。其中,通过府兵制吸纳的武川集团,是所谓的“武川豪杰”,他们在各自军镇扮演着乡里领袖的角色,具有“豪侠”精神,喜欢与自己气质相类的人物相交通(所谓“交通轻侠”);而通过府兵制吸纳的“关中豪右”,他们在各自地方也扮演着乡里领袖的角色,同样拥有着“豪侠”精神,也乐于与自己气质相类的人物建立密切联系。通过府兵制度系统,武川集团与关中豪右一同成为了府兵系统人物。
隋炀帝所募集的骁果,具有与上述府兵系统人物相类似的豪侠精神,如公孙武达,“雍州栎阳人也,少有膂力,称为豪侠,在隋为骁果。”[7]又沈光,“少骁捷,善戏马,为天下之最。……常慕立功名,不拘小节,家甚贫窭,父兄并以佣书为事,光独跅弛,交通轻侠,为京师恶少年之所朋附。……大业中,炀帝征天下骁果之士以伐辽左,光预焉。”[8]公孙武达、沈光都是豪侠一类的人物,其中,沈光身手了得,时人称其为“肉飞仙”,喜好“交通轻侠”,平素“不拘小节”。既然西魏北周府兵制是一种能够吸纳“豪侠”性格之人物的机制,骁果制也具有吸纳“豪侠”人物的机制与功能,不正说明早期府兵制与隋朝骁果制在制度结构上具有同质性而非异质性么?那么,是不是气贺泽氏的论断便完全成立了呢?
笔者以为,尽管府兵系统人物(武川豪杰、关中豪右)与骁果人物同为“豪侠”,但二者之间仍有差异。首先考察武川豪杰与关中豪右之武力形成过程,武川豪杰是自北魏以来军镇制度设计安排的结果,其中人物皆为职业军人,依托于军镇地域形成乡里结构,作为乡里领袖的豪杰人物,既是职业军人,又是乡里豪杰。两种角色相辅相成,这些豪杰的豪侠精神是无法脱离军镇体制编制的。武川人物以行军征战作为主要职业,依凭自身所具有的军事才能,有着打造“良好”秩序的政治抱负,即所谓的“反门阀主义”。由武川豪杰所结成的武力,是一类具有政治志向的武力。关中豪右则处在地方州郡制度的安排下,所居住的乡里原本是基层行政的政治末梢,当君主无暇顾及地方时,或面临外部势力侵扰时,地方人物将此种乡里结构转化成地方武力的基本组织形式,地方豪右成为地方武力的领袖,他们为防范外部敌人的侵犯而结集,有着捍卫“良好”乡土秩序的意志。豪右的豪侠精神无法离开本乡本土的地域,具有捍卫乡土的自觉意识。由乡里豪右所结集的武力,是一类具有乡土志向的武力。尽管两种武力所要达至的目标与志向不尽相同,却都是以乡里结构来加以形塑的,依托乡里,维护着乡里社会的各自利益。
西魏府兵制能够吸纳两类地方武力,调和两类人物不同的利益取向及政治目标,而该制度的基础,则在于对两类人物乡里结构的维护与肯定上。统治者将府兵制作为一种制度工具,收到了相辅相成的两种效果:第一,使府兵军将与兵士逐渐土著化;第二,使地方土著势力逐渐府兵化。两方面的相互运作,表明的正是一种“融冶”的政治力量。其目的在于将分散于各乡里的武力加以融合,将两种乡里武力纳入共同的军政制度框架中。
西魏府兵制的政治运作,是适应关中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是一种具有乡土品质的制度形态,其所扎根的乡土正是关中地域。关中既是西魏北周国家的基本疆界,是武川豪杰实现政治理想的主要场所,又是关中豪右生活的乡土地域,是他们需要努力捍卫的生存空间。早期府兵制凝聚武川集团与地方武力,使之发展为关陇集团,将关中与陇右锻成一个整体,与其他空间地域之间便有了内外区分。西魏府兵制权力支配的基本原理是以关中为其本位或中心,将其作为权力运作的政治核心区,府兵军府大量聚集于该地域,由政治核心区中心向外扩散与辐射。越靠近中央,其控制力逾强,越远离这一中心,则其控制力逾弱,呈现出中心与边缘的政治布局,以此收内外相维、重首轻足的政治效果。因此,早期府兵系统人物是以乡土地域为依托的人物。
然而,骁果在武力形成过程中与府兵系统人物不同。隋炀帝远征高丽时,据《隋书·沈光传》载称,“同类数万人,皆出其下。”[9]当时远征高丽的兵士有百万之众,主体部分是府兵,材料中提到的“同类数万人”,独自分群,则是骁果。隋炀帝最初从关陇地域募集骁果,所募骁果,作为直接听命于皇帝的侍卫亲军,接受皇帝直接指挥,随驾在全国各地。而当第二次远征高丽失败、内乱加剧时,在江都扈从炀帝的骁果仍有众多出身自关中,“炀帝惧,留淮左,不敢还都。从驾骁果多关中人。”[10]由于隋炀帝的穷兵黩武,两次远征高丽的战争消耗了大量府兵,剩下部分的府兵主要用于守卫隋朝政治核心区──关陇地域与首都大兴城。大部分府兵难以从关陇地域抽调出来,而散布于全国各地的民众起义,又使那些力量不断削弱的府兵呈现出分散化的趋势,导致府兵分身乏术。于是,隋炀帝在其政权统治后期,大力扩充的乃是骁果。
骁果与关中或关陇地域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从关中募集的骁果亦可脱离乡土,作为一支专职为皇帝和皇权利益服务的武装力量。换言之,骁果虽由具有“豪侠”性格之人物组成,但缺乏府兵那样对特定政治区域的羁绊与联系。如骁果常单身随驾,家口不在侧近,是皇帝身边的侍从部队。在远离故乡的情况下,为稳固骁果的思乡情绪,他们成家立室的具体情况,需要皇帝亲自过问。
时从驾骁果数有逃散,帝忧之,以问矩。矩答曰:“方今车驾留此,已经二年。骁果之徒,尽无家口,人无匹合,则不能久安。臣请听兵士于此纳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计也。”因令矩检校为将士等娶妻。矩召江都境内寡妇及未嫁女,皆集宫监,又召将帅及兵等恣其所取,因听自首,先有奸通妇女及尼、女冠等,并即配之。由是骁果等悦,咸相谓曰:“裴公之惠也。”[11]
从驾骁果驻留江都两年,无家口妻儿,人心难安,故裴矩为炀帝谋划久安之策,要在江都境内为骁果娶妻,目的在于使骁果能顺利扎根江都。“由是骁果等悦”,因感裴矩之恩,在“江都之难”中,更极力保护裴矩,使之幸免于难。
炀帝远征高丽失败,暂留江都,民怨鼎沸,政治形势严峻。时李密占据洛口,兵势甚盛,炀帝欲返关中需要经过李密的势力范围,若与之正面冲突则有整体倾覆的危险,不得已在江都长期驻留,等待机会。之后,骁果参与江都叛乱,以关中骁果为主,除了“多关中人,久客羁旅,见帝无西意,谋欲叛归”外,仍有其他因素促发之。其一,表现为关中骁果与“南人”之间政治利益的冲突。司马德戡曾授意许弘仁、张恺扇惑骁果:“君可入备身府,告识者,言陛下闻说骁果欲叛,多醖毒酒,因享会尽鸩杀之,独与南人留此。”[12]炀帝后期日益倚重南方人物,引起了北方军将与骁果的强烈不满。其二,因“时江都粮尽,将士离心”,骁果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和粮食,军粮乃由朝廷直接供给。为解决因“粮尽”而引发的现实问题,内史侍郎虞世基、秘书监袁充等“多劝帝幸丹阳”[13],但最终并未成行,而“江都粮尽”,使骁果自身的经济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隋末骁果之数量约计十五万之众,其最初部分主要由关中募集。关中骁果之一部,乃扈从炀帝进驻江都,江都之“从驾骁果多关中人”;另一部则仍镇守在关中,其众约数万,后来屈突通乃用此骁果兵以抵抗李渊的太原兵。
为适应政治局面的变化,隋末骁果武力不断地扩充,其所募集的范围便不再局限于关中。炀帝“幸太原,为突厥围于雁门。突厥寻散,遽还洛阳,募益骁果,以充旧数”[14]。由本则材料可知,炀帝在洛阳时曾募集骁果,这批洛阳骁果,后来则为王世充所获得,王世充更据此骁果以对抗李密。又江都之骁果虽多为关中人,其中仍有不少骁果是从南方募集的。如《隋书》记载宇文化及渡河时遭遇李密,数战不利,“其将陈智略率岭南骁果万余人,张童儿率江东骁果数千人,皆叛归李密。”[15]则知炀帝在南方的岭南及江东等地均募有骁果之兵。江都之变后,一部分南方骁果从江都返回南方,为割据南方的萧铣所吸收。史云:“会旧骁果从江都还者,审知隋灭,遂以州从铣。”[16]而前述“独与南人留此”中的“南人”,似应包括南方籍的骁果人物。
由此可见,炀帝当时招募之骁果,与府兵在建置方式上确有差异,它并未囿限于关中或关陇地域,其军事力量的布局,也未能在“关中本位政策”下体现以关中或关陇地域为政治核心区自中心向外辐射的样态。炀帝根据后期政治形势的需要,更将骁果分散布列在全国多个重要的政治区域中,由此推动了骁果在全国各区域的发展。总之,隋代骁果作为府兵制度系统的一种发展,隋炀帝并非以西魏府兵制作为建置原型,而是作为对早期府兵制原型的一种超越形式,尝试抛开关中乡土本位的束缚,将政治目光放在对隋帝国全领域的控制上。
二、隋代骁果与府兵权力布局的差异
隋朝中央军府系统之左右备身府建立后,其职责在维护皇帝本人及皇室的安全。因此,左右备身府之备身郎将与直斋系统中诸侍从之官如千牛左右、司射左右等,“掌侍卫左右”,护卫皇帝及皇室生命安全。左右备身府之折冲郎将与果毅郎将系统设置比较晚,乃后于骁果的出现而建立,更非与备身郎将与直斋系统同时设置。其中,骁果最早出现在炀帝大业九年(613),《隋书·炀帝纪》云:“九年春正月丁丑,征天下兵,募民为骁果,集于涿郡。……辛卯,置折冲、果毅、武勇、雄武等郎将官,以领骁果。” [17]炀帝既“募民为骁果”,又为统领这些新募集的骁果,乃在同月辛卯日,组建折冲郎将与果毅郎将等郎将官统领骁果的军事组织关系,使骁果直隶于左右备身府。
设置骁果的目的,在于通过招募骁勇果敢的兵士以支持炀帝远征高丽的大规模战争。据《隋书·沈光传》称:“大业中,炀帝征天下骁果之士以伐辽左,光预焉。”[18]骁果之立,既隶属于左右备身府,则主要以维护君王利益展开行动;然而,骁果并非如千牛与备身等员以番上宿卫为职责,而是快速转化为一支以征伐为目的,由皇帝直接掌领,具有机动性的国家军队。总之,骁果是通过主动攻击外敌的方式,达至维护与巩固皇权统治的目的,因此骁果武力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皇帝侍卫亲军的性质。
炀帝大力扶植骁果,大业九年八月“甲辰,制骁果之家蠲免赋税”,改善骁果原有家庭的经济条件,提高骁果的经济待遇,又不断扩充骁果的数量与规模。气贺泽保规认为,隋末骁果之数可达十五万之众。谷霁光认为:“如果说大业八年前着重扩充十二卫,那么大业八年后是着重扩充左右备身府。”[19]扩充左右备身府组织系统,正是适应骁果迅速壮大的需要。骁果不断扩充与壮大,迅速成长为皇帝可直接倚仗的军事力量,“骁果虽不完全用以宿卫,然而炀帝巡游江都,骁果在扈从军中占极重要的地位,宇文化及便是以骁果发动政变的,主谋司马德戡统左右备身骁果,裴虔通系监门直阁,当时骁果万人营于城内,卫士寡弱,皇帝最亲信的左右备身府、左右监门府乃在政变中扮演了主要角色。”[20]掌控骁果与否,在江都政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据《隋书·司马德戡传》记载:
司马德戡,扶风雍人也。……以勋授仪同三司。大业三年,为鹰扬郎将。从讨辽左,进位正议大夫,迁武贲郎将。炀帝甚昵之。从至江都,领左右备身骁果万人,营于城内。因隋末大乱,乃率骁果谋反。[21]
在宇文化及的策动下,司马德戡统领骁果在江都发动政变,弑杀了炀帝,历史上称作“江都之变”。此次政变给隋末政局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上引材料中,值得关注的是司马德戡的仕途经历与职官变动。如在大业三年(607)时,司马德戡担任的职官是鹰扬郎将,属府兵制地方军府系统——鹰扬府;后迁升至武贲郎将,则跻身于府兵中央军府系统——十二卫府,武贲郎将是大将军、将军的副贰之官,所统率的兵士本应是卫士,而当时的司马德戡却能以武贲郎将的身份统领左右备身府的万名备身骁果,取代了原本应属于左右备身府中折冲郎将与果毅郎将等郎将官的权责,“在正史上留下名字的骁果统帅大多都是十二卫系统的长官,而不是备身府骁果系统的长官。”[22]其中不免让人疑惑,武贲郎将既然可以统领备身骁果,那么,原本应掌领骁果的左右备身府长官折冲郎将又充当着怎样的角色呢?对此,《隋书·沈光传》中记载了一段时任折冲郎将一职的沈光的事迹:
炀帝征天下骁果之士以伐辽左,光预焉。……帝望见壮异之,驰召与语,大悦,即日拜朝请大夫,赐宝刀良马,恒致左右,亲顾渐密,未几,以为折冲郎将,赏遇优重,帝每推食鲜衣以赐之,同辈莫与为比。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怀竭节。及江都之难,潜构义勇,将为帝复仇,先是帝宠昵官奴,名为给使,宇文化及以光骁勇,方任之,令其总统,营于禁内。时孟才、钱杰等阴图化及,因谓光曰:“我等荷国厚恩,不能死难,以卫社稷,斯则古人之所耻也。今又俛首事雠,受其驱率,有腼面目,何用生为,吾必欲杀之,死无所恨。公义士也,肯从我乎?”光泣下沾衿曰:“是所望于将军也,仆领给使数百人,并荷先帝恩遇,今在化及内营,以此复仇,如鹰鹯之逐鸟雀,万世之功在此一举,愿将军勉之。”孟才为将军,领江淮之众数千人,期以营将发时晨起袭化及,光语泄,陈谦告其事,化及大惧曰:“此麦铁杖子也,及沈光者并勇决不可当,须避其锋。”是夜即与腹心走出营外,留人告司马德戡等遣领兵马逮捕孟才。光闻营内喧声,知事发,不及被甲即袭化及营,空无所获。值舍人元敏,数而斩之。遇德戡兵入,四面围合,光大呼溃围,给使齐奋斩首数十级,贼皆披靡。德戡辄复遣骑持弓弩翼而射之,光身无介胄,遂为所害。麾下数百人皆斗而死,一无降者。[23]
由上述材料可见,沈光最初以骁果的身份远征高丽,在战场上表现异常突出,深得炀帝赏识,很快便由普通的一员骁果升任为骁果的最高军事长官──折冲郎将,当司马德戡以武贲郎将的身份,在江都城内设营统领数万备身骁果时,沈光却以备身府折冲郎将的身份,在江都“禁内”置营,统领着比骁果更为炀帝所宠昵的官奴部众,其名曰“给使”,其部众约数百人。骁果与给使的区分,可由各自主要活动的政治区域──“城中”与“禁内”空间位置的不同管窥得之。
身处“禁内”的给使深得炀帝信任,其待遇极优,“帝选骁健官奴数百人置玄武门,谓之给使,以备非常,待遇优厚,至以宫人赐之。”[24]玄武门是隋宫城北门,由此北门进入则为禁内,给使置营于玄武门,其目的正是护卫皇帝及皇室的安全。然而,这支重要的皇帝侍从军力量却在江都政变发生时离奇地离开了玄武门驻地,未能真正履行护卫皇帝及皇室的职责:“司宫魏氏为帝所信,化及等结之使为内应。是日,魏氏矫诏悉听给使出外,仓猝际制无一人在者,德戡等引兵自玄武门入。”[25]司马德勘与司宫魏氏里应外合,魏氏矫诏将给使调离“禁内”防区,使炀帝直接暴露在“城中”骁果的兵锋之下。炀帝被弑杀之后,宇文化及则将给使营由炀帝的“禁内”纳入到自己的内营之中,使给使成为自己的侍从军,而司马德戡所统领的骁果反而被置于宇文化及营外,由此可知给使相比骁果,在隋末政局中地位更为特殊。
值得注意的是,骁果武力原本是以卫宫部队的形式组建的,然其武力不断地扩充,也使之不断向宫廷以外的方向发展。与骁果不同,炀帝带到江都的十二卫府兵,其实际兵力并不多,主要承担在江都宫诸门与宫殿宿卫的政治任务;而不断扩充实力的骁果,则由于人数众多,规模巨大,逐渐发展为以“卫城”为目的的中军(中央军)。
江都政局中,府兵与骁果在军事力量、地位与职责等方面发生易位,这在江都政变的发动过程中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到,据《资治通鉴》“高祖武德元年三月己酉”条载称:
天未明,德戡授裴虔通兵,以代诸门卫士。虔通自门将数百骑至成象殿,宿卫者传呼有贼,虔通乃还,闭诸门,独开东门,驱殿内宿卫者令出,皆投杖而走。右屯卫将军独孤盛……不及披甲,与左右十余人拒战,为乱兵所杀。[26]
骁果驻扎在江都城内,并没有追随在皇帝左右,而是以“卫城”为其主职。直接负责皇帝和皇室安全的最内层交给了给使,政变当日则被司宫魏氏诱骗出外,不在皇宫禁内,数百之众并没有直接参与与骁果的对抗行动。其外少量的十二卫府兵(“诸门卫士”)以守卫宫廷及宫门为职责,当宇文化及、宇文智及及司马德戡等由“城”入“宫”,其所统领的骁果能够轻易地换掉守卫诸宫门的卫士,又裴虔通仅带上数百骑骁果便驱除了正在殿内宿卫的卫士,说明当时府兵力量的薄弱。在整个政变中,仅有零星战斗发生,而当时右屯卫将军独孤盛与入宫骁果拒战时,身旁仅有“左右十余人”。在数万骁果面前,府兵数百之众的反抗无异于“螳臂当车”。
从当时江都城权力空间布局看来,骁果作为“卫城”的中军,其兵力已远在十二卫府兵之上了。陪侍皇帝左右的任务,交给了皇帝更为亲近的官奴──给使,府兵与给使当时的数量都很少。骁果既成长为中军,则走出宫廷,走向城中。而左右备身府并未与骁果武力的迅猛发展相配伍,其主要机构和军府官员仍然留在皇宫禁内,左右备身府的备身郎将与直斋系统仍以卫护皇帝及皇室安全为目标,而折冲郎将与果毅郎将系统则与给使进行了组合,折冲郎将与果毅郎将统领着给使,给使则行使着原属骁果“侍从左右”的侍从官职责,上引材料中,沈光便是以折冲郎将的身份统领着“禁内”的给使部众。
然而,左右备身府作为骁果管理机构的事实并没有改变,江都政变时司马德戡想要扇惑骁果叛乱,则需要通过备身府机构方能逞其意。如据《隋书·宇文化及传》略云:
义宁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宣言告众,恐以人心未一,更思谲诈以胁骁果,谓许弘仁、张恺曰:“君是良医,国家任使,出言惑众,众必信。君可入备身府,告识者,言陛下闻说骁果欲叛,多酝毒酒,因享会尽鸩杀之,独与南人留此。”弘仁等宣布此言,骁果闻之,递相告语,谋叛逾急。德戡知计既行,遂以十日总召故人,谕以所为。众皆伏曰:“唯将军命。”[27]
由此材料可知,义宁二年(618),司马德戡欲胁迫骁果谋反,则让许弘仁、张恺二人在备身府中制造谣言,而这些消息很快便传入骁果耳中,是因为备身府本是骁果的直接领导机构,由此府传布、扩散消息最为迅速、便捷。骁果武力在人事关系上仍隶属于左右备身府,只是从宫廷中走出,由十二卫府兵军府系统高级武官加以统领,卫护整个江都的安全,履行着中军的职责。原以“卫城”为目的的府兵,则因其力量的弱小,转而变成了宫内的宿卫军。
如此,在江都军政权力空间布局中,依与皇帝远近关系观之,则以给使营为最核心,给使陪侍在皇帝左右,与皇帝有近密的私人关系,主要驻防在殿中禁内,护卫着皇帝及皇室的生命安全,计有数百人;其外则以少量的中央十二卫府兵分管江都宫城内宿卫及诸宫门,驻防在宫内禁外,计有数百人;而最具实力的骁果营,约有数万人之众,与皇帝政治空间距离最远,驻防在宫外城内,于江都城内布防。骁果武力布置在江都权力空局布局的外层,则与西魏北周及隋初以府兵内外宿卫为中心“重内轻外”的政治格局调换了位置,产生以骁果为中心“外重内轻”的政治新局势。这种政治新格局中,使得原本处在权力外层的野心家却因此掌握重兵,使之能够凭藉骁果武力,比较轻易地弑杀处在深宫中的炀帝。
在江都之变时,给使虽然肩负起骁果“陪侍左右”职能,却并非与骁果同类。给使由皇帝身边的官奴所组成,是一类身份地位极为低下,却与皇帝更为昵近的私人关系的团体,是皇帝的私人武装,官奴对皇帝具有很强的人身依附性。而骁果是地方社会中想要建功立业,具有豪侠精神的人物,是由皇帝通过“募”的形式招集而来,是在国家政治结构规定下组建形成的,是以府兵军府制度系统为其胚胎的。骁果虽然直接为皇帝的利益服务,然而这种服务性质,已然被赋予了一种“公”利的政治品质,是以其自身所具有的军事才干换取未来的个人功业,与皇帝之间并不存在牢固的人身依附关系。因此,就公私关系而论,骁果与府兵更为接近,而与给使在身份角色上有所不同。
三、结语
隋代骁果与府兵同属府兵制中央军府系统,皆置府以统兵,骁果可视作一类具有特殊身份的府兵,两者在制度结构上有相似之处,骁果人物与早期府兵系统人物一样,都具有豪侠精神。但是,二者在建置方式上仍存在差异。不同于府兵的“征”,骁果是一类募兵,它不具有乡土品质,不以守护关中或关陇地域为政治目标。隋炀帝组建骁果,旨在打破关中乡土本位的束缚,将骁果作为对早期府兵制原型的一种超越形式而加以利用,欲通过扩充骁果武力以实现对隋帝国全领域的控制。又,二者在军政权力布局上亦有差异。在江都之变爆发前,与皇帝关系近密的给使驻防在殿中禁内,守御宫城北门玄武门;其外少量府兵驻防在宫内禁外,守御宫内诸门;而武力强大的骁果则驻防在宫外城内,守御整个江都城。在江都政变中,骁果处在江都军政权力空间布局的最外层,形成了“外重内轻”的政治局势,这为实际掌握骁果的野心家们带来了可趁之机,也最终促发了江都之变。
参考文献:
[1][19][20]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1:111-116.
[2][6]气贺泽保规,辛德勇.以骁果制为中心论隋炀帝时代的兵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1):94-103.
[3]黄永年.文史探微:黄永年自选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0:119-137.
[4][8][9][10][11][12][13][14][15][17][18][21][23][27]魏征,令狐德棻,长孙无忌,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1389,1513,1513,1888,1583,1889,1541,688,1891,83,1513,1893,1514,1889.
[5]俞伟超.西安白鹿原墓葬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56(3):52-53.
[7][16]刘昫,张昭远,贾纬,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2300-2325.
[22]蒙曼.唐前期北衙禁军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出版社,2005:181.
[24][25][26]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5779-5780.
(责任编辑 程荣荣)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隋唐府兵制变革与社会结构的演化”(编号LS20102)。
收稿日期:2023-11-06
作者简介:熊伟(1980—),男,江西新建人,历史学博士,九江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北朝隋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