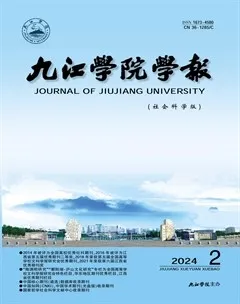庙堂与山林:王士对陶渊明及其诗歌的接受
摘要:王士禛是清初康熙文坛大家,治学博综该洽,重视陶诗。从其诗话、笔记、年谱等著作可以看出,王士禛对陶渊明及其诗歌均有颇多论述,他推崇陶渊明的五言古诗,尤以田园题材为最,赞赏其古澹闲远和沉着痛快的诗风。但由于诗论主张和人生际遇的不同,王士禛对陶诗及其人生路径呈现了选择性接受和替代性接受的倾向。他以旁观视角效仿陶渊明的田园书写,展现了其心向山林与身处庙堂的矛盾感。这种接受方式并非孤立现象,隐含了文人们选择与动机的多样性,也愈见陶渊明及其诗歌的自然纯粹以及无可替代的经典地位。
关键词:王士禛;陶渊明;古澹诗风;田园书写;归隐意志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580(2024)02-0012-(06)
DOI:10.19717/j.cnki.jjus.2024.02.003
明末清初的时代背景下,陶渊明“变不失贞,穷不陨节”的遗民诗人形象及其超逸古雅的诗歌风格再度成为文坛焦点,论陶、和陶诗、集陶诗、仿陶诗等现象迭出,展现了文坛对陶渊明的关注与尊崇,清初诗人王士禛即是其中重要代表之一。
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1]。他提倡典雅正宗,以“神韵说”主盟康熙诗坛,诗宗王孟,多山水田园之作,风格清新俊逸、冲和淡远。但其博学广识又使得他的诗论和诗作不会局限于王孟,实是集前人之大成[2]。他激赏陶诗的古澹闲远、自然真诚,但由于政治际遇和人生理想的不同,他对陶渊明及其诗歌呈现诗歌层面的选择性接受,以及人生层面的替代性接受倾向,即以内心之纯诚淡泊替代归隐田园的行为之淡泊,展现了身处儒林与庙堂的文人们拟陶效陶的普遍选择和现实实践路径。
一、“佳句多从五字求”:古澹闲远与沉着痛快的诗风选择
王士禛对陶渊明在古诗创作中的地位颇为认可,《渔洋文》卷十四载:“渊明之谊,卓绝后先,三百篇之遗也。”[3]谓陶渊明有古人遗风,与魏晋间其他诗人殊然不同,且其中尤以五言古诗为最佳。《池北偶谈》谈“魏晋宋诗”一条记:
偶读《严沧浪诗话》云:“黄初之后,惟阮公咏怀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晋人舍阮嗣宗、陶渊明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时,陆士衡独在诸人之下。”又云:“颜不如鲍,鲍不如谢。”与予意略同。[4]
王士禛赞同《沧浪诗话》的说法,认为晋人之中陶渊明的诗歌是卓绝一时的佳作,并在编选《古诗选》时别于晋代诸家,令陶诗独为一卷,收录其三十首五言古诗。从编选五言古诗的诗作类型来看,王士禛较推崇陶渊明的山水田园之作,其中收录不乏《游斜川》《饮酒》《归园田居》《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这样的代表性诗作。在王士禛看来,陶渊明的山水田园诗和韦庄、王维的诗歌属于同一类审美风格范畴,他在《然灯记闻》中谈道:“为诗各有体格,不可泥一。如说田园之乐,自是陶、韦、摩诘。”从他诗宗王孟、标举“神韵” 的诗歌主张,以及诗歌风格淡远清雅来看,他最欣赏的是陶渊明古澹闲远、平淡自然的诗歌。
王士禛常在诗话、笔记中以风格清真古澹评陶诗。并以自身“神韵”说的诗论主张为基准,在论诗时将陶渊明与谢灵运、王维、柳宗元、韦庄四人并置提及。他在《分甘余话》中谈道:
东坡谓柳柳州诗在陶彭泽下,韦苏州上,此言误矣。余更其语曰:韦诗在陶彭泽下,柳柳州上。余昔在扬州,作《论诗绝句》,有云:“风怀澄淡推韦柳,佳句多从五字求。解识无声弦指妙,柳州那得并苏州?”又尝谓陶如佛语、韦如菩萨语、王右丞如祖师语也。[5]
王士禛反驳了苏轼对韦庄和柳宗元二人诗歌地位的排序,但对于陶渊明居二者之上是赞同的,三人诗风皆澄淡和雅,其中首推陶渊明。并以佛语比陶诗,菩萨语比韦诗,祖师语比王维诗,根据佛教角色的师承与层次,指出陶、韦、王诗各自的特点,他认为三人中仅陶诗达到了觉悟的高度和解脱的境界,拥有人生智慧,其淡泊超逸诗风极类佛语。对于此种诗风和诗境造化,王士禛在《蚕尾文》“蒙木集序”一条评道:“才之不能相兼也,自古然矣。谢之不能为陶也,顔之不能为谢也。”[6]陶谢诗风虽相近,但陶诗之古澹和陶渊明之诗才是无可替代的。
王士禛亦将古澹闲远风格作为评诗论诗的标准,以陶诗为依据,评点其他诗人诗作,并关注诗风背后隐逸生活的创作来源。《蚕尾续文》“金素公问学集序”一条记:“金子于诗尤工古选,予喜其闲适古澹,类自陶韦门庭中来。”[7]该句不仅可见王士禛心中树立的诗歌风格衡量尺度,更可见其审美趣味的选择倾向,言明其本身对闲适古澹一类诗风的偏好,而非陶渊明诗名在外。《池北偶谈》卷十“王方伯”记:“罢官归,足迹不入城市,常衣布袍行田间,人不知其二品大僚也。年逾八十乃卒。五言诗清真古澹,有陶、韦风,与石湖邢昉相上下,足称逸品。”[8]除了称赞王庭还归乡野、怡然自得的日常生活以外,更欣赏他诗如其人的古澹闲远,五言诗颇有陶、韦的风格。足见其在对诗歌风格的品评以外,还包含了对诗品背后的人品的关注。诗歌偏好是评点者主观精神世界和理想生活状态的一隅,在古澹闲远的诗风中,王士禛的目光聚焦在诗人隐逸生活的诗性来源之上。
尽管王士禛推崇陶渊明五言诗作的闲远古澹,亦称颂陶渊明的隐逸生活,但其评点中却存有作为后世评点者追忆伟大诗人的距离感,陶渊明和他的诗歌更像一个文化符号,只可被效仿,却难再被超越。他在《池北偶谈》卷十九“梦山诗”中说:“海丰杨梦山宫保太宰(巍)有存家稿八卷,五言最简古,得陶体,明人所少。”[9]明人力倡复古、真性真情,却也少有如陶诗这样简古的作品。同时,王士禛的评点既立足于诗歌发展的事实,也将陶渊明作为五言古诗创作的高峰象征,称其为“风雅宗”,一边透露了对陶诗成就的称赞,一边展现了由于文化环境变迁风雅难再、诗歌盛世已逝的仰望心态和现实无力感。例如王士禛创作的以下诗歌:
最忆同游陶谢手,永嘉南去万峰昏。(《读西樵九青游诗因怀开来》)
高咏岂殊陶谢手,少文潦倒愧同游。(《遥和严颢亭施愚山秋日登华不注之作》)
五字追陶谢,千秋过郑边。(《题高苏门集》)
左司寂寞襄阳远,陶谢千秋不可追。(《寄陈伯玑金陵二首》)
远志希嵇阮,近思慕陶韦。(《江上读韦诗作二首》)
陶谢风雅宗,名不惭烈祖。(《谢灵运》)
述作思陶谢,幽寻怅莫从。(《答愚山耦长西山见怀之作》)[10]
陶渊明、谢灵运和韦庄皆工于山水景物描写,恬淡雅致的风格相类,因此王士禛多次将“陶谢”“陶韦”并置于诗句中,显示了他对陶渊明五古创作成就的肯定。然而思及陶谢,诗句中却多了不少“最忆”“千秋”“不可追”“怅莫从”等颇有怅惘失落感的字眼。王士禛是以眺望者的姿态看陶诗的,间隔千秋,世殊事异,时空距离和人生际遇都成为后来效仿者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也成为王士禛在人生道路中选择庙堂而非山林的重要原因。
陶诗除了古澹闲远的主体风格,更有沉着痛快的一面,王士禛也关注到这一点。他在《芝廛集序》中论及:“沈着痛快,非惟李、杜、昌黎有之,乃陶、谢、王、孟而下莫不有之。”[11]此处提及的沉着痛快,一方面可以理解为直爽的风格,一方面可以看作诗歌情感的充沛性,即《文心雕龙·明诗》所云“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可以说,诗歌语言上表现出的酣畅痛快,就是真实情感充分流露的自然表现。但是在传统诗歌的审美范畴中又讲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情感的过度宣泄会损伤诗性,因此平衡文与质、保持情感的恰当表达尤为重要。通过《陶菴诗选序》,我们能够看到王士禛对陶渊明沉着痛快的诗风的理解:
昭明称:“陶诗跌宕昭彰,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故后之论者,以为外枯中腴,犹未为知陶者也。君古诗大抵原本于陶,而杂采诸家之美,此其能自名一家,而可传于世不疑也。古诗之绝响久矣,规模者工形似,驰骋者偭规矩。[12]
王士禛赞同萧统的评价,认为陶渊明的诗歌情感真醇之余,亦具备抑扬爽朗的语言形式,只有理解陶诗的人才能领会其跌宕抑扬藏之于中的高妙。
然而,尽管王士禛对沉着痛快的风格亦加赞许,但在学陶效陶上,却多选择其古澹闲远一面的诗歌。一方面与其本身的诗歌审美有关,其幼时学诗于西樵,“神韵”诗风奠基于此,且从兄弟徐夜诗尚陶、韦,兄弟几人常作诗赠答,家学环境下王孟韦柳之诗风逐渐成型。另一方面,相较乱世背景下生存的遗民诗人,他所处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使其欠缺充分的情感体验,笔下少有以充沛情感为基础的沉着痛快风格的诗歌作品。这也成为他的“神韵说”和诗作被后世诟病的地方,诗歌关注点泰半停留在古澹闲远的诗歌风格上,注重清词丽句的打造,使得五言作品愈“开平庸之渐”[13],诗歌流于空泛。
二、“槛内人”情牵“槛外人”:田园山水诗的仿效与系联
宋荦在《诰授资政大夫经筵讲官、刑部尚书阮亭王公暨元配诰赠夫人张夫人合葬墓志铭》中,对王士禛的诗歌评论道:“其为诗备诸体,不名一家,自汉、魏以下兼综而集其成。大抵以神韵为标准,以自然为极则,风味在陶、韦、王、孟间,正始之遗音也。”[14]王士禛的部分诗歌确得陶诗风味意趣,从触景及情地化用陶句和陶诗意象的诗歌,到触景及人地访陶渊明故里所写下的诗歌,都能看到陶渊明对王士禛诗作所产生的影响。
王士禛学陶之作主要是五言古诗,以田园题材为主。他曾对弟子说:“五七言诗有二体,田园邱壑当学陶韦,铺叙感慨当学杜子美北征等篇也。”[15]尽管王士禛身在仕途,对田园生活却存有向往。例如化用陶句的《访宾公大谷山居》:“春原麦争秀,斜日雉交飞。涧水寒犹浅,村烟望不稀。田家驱犊返,仄径负樵归。想见南窗下,看山杜德机。”[16]根据《居易录》卷五记,此时王士禛游长白山,拜访隐居在此的内兄张实居[17]。他有感于田园隐逸生活,化用陶渊明《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句式作结,案头宦务繁琐和仕途的机心,在此处都得到了平息,麦秀、雉飞、涧水、村烟、归人的田家景象描写,自然闲远,展现了他对田园生活的喜爱。再如《扶风道中》:“北望回龙薄,西行过马嵬。侠游无柳市,史笔阙兰台。老鬓愁中改,秋风陇上催。田园情话好,何事不归来。”[18]化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悦亲戚之情话”,田园的宁静自然,吸引着倦游的人归去,整诗朴实自然。
尽管古澹闲远的题材和风格颇相类,但从王士禛创作的环境、情感触发点、角度等方面来看,其诗作常常得其形,而不得其神。他以一种观看、欣赏的视角效仿陶诗对日常的书写,难与山水田园产生真正的共鸣,这种弊端集中体现在对景物的化用中。
陶诗中的菊、南山、酒、桑、鸡犬等农家田园景象与诗作一起逐渐经典化,生成的文化内涵固化为象征隐逸的文化符号。这种后天生成的意象,一方面给王士禛仿写的相关诗歌赋予超逸古雅的意趣,另一方面却也妨碍了诗人自身情感的真实显露。代表隐逸文化的意象先入为主,限定了诗歌的表达效果。例如化用菊意象的诗歌:
南圃梅犹涩,东篱花已阑。(《冬日谢送菊》)
松菊庐荒径未锄,云霄地远梦全疏。(《作家书后戏题纸尾寄吏部西樵给事北山两兄》)
问讯东园菊,吴山日夕佳。(《奉常烟客先生八十初度寄呈兼寄端士异公怿民虹友藻儒诸兄弟四首》)
小春风气佳,晚菊有余芳。(《述书赠刘公勇吏部》)
三径荒芜忆故林,何来松菊草堂阴。凭将笠泽高人笔,写出柴桑处士心。(《题王勤中松菊图》)
结庐背城市,绕径幽兰馥。扁舟练川至,复载东篱菊。(《题门人朱翠庭载菊图》)
忽见东篱人,更忆东篱菊。对雪一清吟,萧寥满空谷。(《赵君书来求东篱诗雪后赋答》)
野人久狭东篱菊,不爱铺堂富贵花。(《书宋刘跛子传后》)[19]
王士禛对菊意象的使用,多和东篱、松意象连用,明显化用自《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和《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二句。东篱菊和松菊在陶渊明的笔下是归隐田园的日常生活景象,也是隐逸闲适生活意趣的体现。这些田园生活中的现实景物,不需要搜肠刮肚,篱笆边的菊花、院子里的松菊均是信手拈来之物,是陶渊明真诚自然的情感书写。王士禛的化用之句,以陶诗塑造的意象为基础,触景及情,由朱翠庭画中之菊、王勤中松菊图、东园之菊等,勾起对陶诗菊意象乃至整首诗歌的联想,与梅、兰、雪、扁舟、空谷等景象一同表意抒情,诗句闲雅清丽。
从诗题可知,王士禛写菊并不是为咏叹自然、享受隐逸闲适的生活而作,情感的出发点在事在人,而不在景。不论是题诗、戏赠,还是答谢,王士禛在书写东篱菊、松菊时都是站在交游来往的尘世中的,由菊触发对陶渊明及其诗歌的效仿。因此这种对菊的书写,并不是日常心态,与陶渊明的由景及己不同,王士禛是由景及陶,诗歌中使用的是陶渊明搭建起来的田园隐逸生活描写范式和意象内涵,因此风格相似,但诗意尚浅。
据《北归志》记载,康熙二十四年,王士禛奉命祭告南海,五月渡彭蠡湖、谒张巡庙、登望湖亭,与友人孙枝蔚游庐山,途经三峡涧、观音亭、玉渊诸、玉京山、万杉寺,来到彭泽县。因有感于景色和人事,他先后写下《万杉寺》《开先瀑布》《招隐桥》《万竹亭》《佛印松》《青玉峡》《寄题三叠泉》《彭泽雨泊有怀陶公》等山水诗[20],诗歌收录在《南海集》。先看《万杉寺》一诗:“朝过玉京山,缅想陶公里。溪回得寺门,曲折杉松里。雨中念佛鸟,交语清人耳。风吹修竹林,下有寒泉水。”[21]诗歌由缅怀陶渊明起,却没有落入怀古的哀伤叹息中,后半部分转入对寺庙风光的描写,词句清丽脱俗,有王孟诗歌的禅意。再看《彭泽雨泊有怀陶公》:“陶公令彭泽,柴桑一舍耳。犹对匡庐山,共饮西江水。一朝悟昨非,扁舟归栗里。笑指故山云,吾心亦如此。我来彭泽县,秫田没沙觜。急雨送寒潮,三叹颜延诔。”[22]王士禛身处彭泽,风雨寒潮中独对匡庐山,触景及人,缅怀陶渊明。诗中使用大量与陶渊明相关的要素,“柴桑”“悟昨非”“栗里”“颜延诔”,由这些关键词构建起对陶渊明生平的追忆。尽管诗歌聚焦于陶渊明的故居和旧迹,但或简要一提,或掠过生平,作为繁忙公务中的匆匆一瞥,难以达到与陶渊明一般同自然山水共鸣的程度。
在王士禛看来,陶诗自然淳朴的田园诗境源自对自我的真实表达,诗如其人,纯粹真挚。《梅厓诗意序》记:“窃谓诗以言志古之作者,如陶靖节、谢康乐、王右丞、杜工部、韦苏州之属,其诗具在,尝试以平生岀处考之,莫不各肖其为人。”[23]陶渊明生于斯,长于斯,对田园风光的描绘和眷念是自然且呼之欲出的,通过“田园将芜胡不归”的自问和对“形役”的厌倦,可见他笔下之景和情的真切诚实。钟惺评价陶渊明:“陶公山水朋友诗文之乐,即从田园耕凿中一段忧勤讨出,不别作一副旷达之语,所以为真旷达也。”置身田园,诗可容纳万物,万物皆是诗歌,不是身处其中,笔下难有田园真意。王士禛在和弟子论诗时谈及“五古句法宜宗何人,从何人入手简易”的问题,他直言:“陶渊明纯任真率,自写胸臆,亦不易学。”[24]他意识到了陶诗的难以仿效,但仕宦生活的繁忙让他不得不短暂地寄情田园,寻求宁静淡泊,化用陶句,关注山林,却处处跳脱山林,其旁观姿态和寄赠酬答都意味着与世情的勾连。如果说陶诗已到达宁静淡泊之境,那么王诗则是走在追寻的路上,作为“槛内人”向“槛外人”投去歆羡的目光。
三、“守拙归园田”与“故山归未得”:归隐意志的履践与宣泄
王士禛诗歌层面的选择性接受,透露着他身处庙堂与心向山林的矛盾,这种矛盾来自倦游的心态和强烈的归隐意志。《古欢录自序》记:
山人少无宦情,虽在周行,时有灭景云栖之志。幼读诗至《秦风·蒹葭》,辄流连三复,掩卷旁皇久之。至《考槃》《衡门》《十亩之间》,未尝不想见其人,冀将旦暮遇也。徒以祖父督课,从事科举,弱冠从政,回翔中外,忽四十年,夙昔之愿,纡郁未申,然不能须臾忘也。[25]
王士禛出身官宦之家,父辈、祖辈皆是明朝重臣,自己也官至刑部尚书,可谓仕途亨通,且名气显扬,蜚声康熙文坛。尽管荣华名利加身,但隐逸山林的心愿却贯穿他的仕途生涯。他多次在诗歌中言及此憾,可见“不能须臾忘”一句乃平静真诚的独白,并不是既得利益者的故作姿态。《凌云杂咏五首·其五》中有“故山归未得,空和渊明诗”[26],又《彭泽雨泊有怀陶公》中有“一朝悟昨非,扁舟归栗里。笑指故山云,吾心亦如此”,两度提出“故山”,通过这个意象表达内心对远离俗尘、归隐山林的向往。《同沈绎堂程周量题项参政倦鸟亭图是戴务旃画三首》云:“自得陶家意,吾庐只数椽。曲栏斜钓艇,饥鹤啄秋田。暧暧郊原树,依依墟里烟。未须笑褴褛,饮酒岂徒然。”[27]该诗是为友人的倦鸟亭图而题,笔下是题倦鸟亭,而题画之人亦是倦游鸟,王士禛化用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首句“自得陶家意”与陶句“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遥相呼应。《过长沮桀溺耦耕处》中也直言道:“曾读陶公传,尞尞沮溺心。耦耕余故迹,流水抱寒岑。鸟下日将夕,云归山半阴。从来避世者,不厌入林深。”[28]诗歌引用长沮、桀溺古隐士的典故,化用《归去来兮辞》“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陈说对陶渊明自由闲适的归隐生活的向往。
同时,在其人际交往上,他喜爱结交布衣和隐士。王士禛在《渔洋诗话》中谈道:“余在广陵五年,多布衣交。”[29]布衣即平民,与之相反则是达官显贵,表达了自己对官场的厌倦,与平民交游的融洽。同时,他与隐士徐夜、孙枝蔚等交往甚密,常相互吟诗赠答,《渔洋诗话》谈及从兄弟徐夜:“予目之为‘涧松露鹤。”[30]表现了对其隐士身份与行为的认同。
在诗歌和诗话作品中,王士禛宣泄着自己久困于俗世的无奈与倦怠,但相较于陶渊明对“守拙归园田”的最终选择,王士禛却并未仿其行迹,而是选择站在庙堂这一边。一则可能与遗民心态相关。陶渊明坚守晋遗民的政治节操已有较多研究,不再论述,而王士禛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不是遗民诗人,尽管对陶渊明的遗民身份和气节有所关注,但缺乏充分的情感认同[31],因此不太可能如此坚决地抛下新朝、选择归隐。二则与诚之以求真的人生行思相联系[32]。在山林与庙堂的两难抉择间,两人都有过挣扎。陶渊明几度出仕,又几度罢官归去,他对官场的抗拒从行动上看要远超于王士禛。他反复确认内心的想法,用“悟已往”的方式审视渴求自由的本性。他在人生道路中做选择的纠结,表现了普通人面临困境时的普遍心态,这时候他是一个极普通的人,而当他真实诚挚地在诗歌中写下这些前人未曾触及的普通话题,并用一生去践履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极伟大的人。他在为官过程中明辨本性,提出“质性自然”“性本爱丘山”“富贵非吾愿”,觉察“心为形役”后,果断抛开“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等欲望。此间的踌躇,从《连雨独酌》提及的“僶俛四十年”可知,他用了人生泰半时间去敦行信念,隐居山林。
这种诚之以求真的行思态度,是王士禛诗歌中存有,但行动上缺失的。他在《和苏诗二集序》中探讨仕与不仕,说道:“吾谓渊明为其易,而文忠为其难。渊明之不仕也,楚狂接舆荷莜丈人之类也。”[33]认为陶渊明的选择很简单,但实际上任真自然、渴望归隐表达起来容易,真切抛下尘俗去践行才最为困难和可贵。又《香祖笔记》中提出“气以诚为主”,从诗歌中袒露的情感而言,王士禛对归隐的渴望确实诚挚自然,但却并不效仿陶渊明的归隐之行,只是通过内心的纯然淡泊替代归隐田园的行为淡泊。考察历代文人,王士禛的此类替代性接受并不是孤立现象,疾呼归隐和选择归隐背后分别有着繁多的理由和动机[34],隐含了身处儒林的文人们对于庙堂和山林选择的态度和人生策略,也从中愈见陶渊明的纯隐选择和田园诗作登峰造极、难被企及的原因。
四、结语
王士禛自言少时深喜钟嵘《诗品》,后认为其中谬误颇多,并对诗人品级作了调整,“中品之刘琨、郭璞、陶潜、鲍照、谢朓、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35]可见他对陶渊明诗歌的欣赏,并且从其诗话笔记、编选类书目、自撰年谱和诗歌作品,以及门人友人的著述中,亦可知他对陶渊明及其作品的称道。他认可并效仿陶渊明田园诗的古澹闲远之风,将陶诗作为评诗论诗的典范,同时聚焦诗歌背后渊明低调隐逸生活的诗性来源。
但论诗易,笃行难,尽管王士禛多次透露倦游的心态和强烈的归隐意志,却依旧在庙堂和山林间选择了仕宦生活,以内心的淡泊替代归隐行为的淡泊。这就使其诗歌虽闲远清丽,但欠缺田园生活的情感体验和日常感;另外,其以局外人的目光注视田园山水,缺乏充足情感,亦造成空疏的弊病。山水田园,或是王士禛在繁忙公务中的匆匆一瞥,或是盛世之下隐逸情怀的装点,均与陶渊明将其视作生命和灵魂的寄托之境界相差甚远。透过王士禛对陶渊明及其诗歌的接受方式,也得见尽管陶诗及其人生境界不易效仿,但由之形成的士人隐逸文化和逍遥自在的生命模式,为在俗世纷扰和仕途倦怠中迷失自我的文人乃至普通世人,开辟出一方澄明之境,滋养了无数后人心灵中的山水田园。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232.
[2]孙康宜,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252.
[3][4][5][6][7][8][9][10][11][12][16][17][18][19][21][22][23][25][26][27][28][29][30][33][35]王士禛.王士禛全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7:172-5006.
[13]沈德潜.清诗别裁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5:62.
[14]王士禛.王士禛年谱[M].孙言诚,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7-102.
[15][24]郎廷槐.诗友师传录[M].钦定四库全书本影印本.
[20]蒋寅.王渔洋事迹征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228-312.
[31]李剑锋.陶渊明接受通史[M].济南:齐鲁书社,2020:876-877.
[32]刘奕.诚与真:陶渊明考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41.
[34]吴在庆.谈唐代隐士的隐逸动机与归隐之路[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4(4):26-29.
(责任编辑 吴国富)
收稿日期:2023-11-17
作者简介:陈曾媛(1999—),女,四川成都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