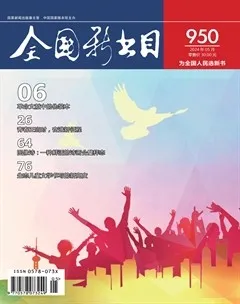生态儿童文学书写的新高度
苏勇


这是一部以动植物视角反映人与自然千年来和谐共生的生态童话。云梯山植物王国即将开展树王竞选大会,千年古树们摩拳擦掌,消失多年的珍稀动物也探出头来。唐枫、唐楠、古罗汉等十位古树候选人的代言人赤狐、金铁豺、蟒蛇等轮流演讲,诉说十位树王候选人阅尽千年的沧桑和与人为善的动人故事。一场场精彩的演讲既是惜树传统的文化课,也是森林命运的故事会,串连起云梯山区动植物与人类相互依存的历史图景,生动反映了生态环保的主题。
《树王选战正酣》
刘华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23.12/28.00元
刘华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曾任江西省文联主席、江西省作家协会主席。长期从事田野调查和民俗研究。著有《车头爹 车厢娘》等多部长篇小说及小说集、散文集,《灵魂的居所》《一杯饮尽千年》等专题性长篇文化散文,童话《泳族》《朱鹮下落不明》《树王选战正酣》,儿童小说《会成长的桥》等。
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理念逐渐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作家将生态意识、生态主题、生态观念注入儿童文学创作中。为使生态、自然变得可见,这些作品或以远离都市的乡土为背景,以怡人的田园牧歌来抵抗“唯发展主义”的现代主义逻辑,从而使孩子们得以打开另一种可能的世界;或描写现代人的贪欲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最终导致人类及其他生命体的生存面临巨大威胁,来引导孩子们树立正确的生态观;或将故事设置在一个生态、环境惨遭破坏的现代空间或未来场景中,以令人错愕的创伤性体验,引发孩子们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关注和思考。尽管这些书写主题、视角自19世纪起就屡见不鲜,但如此密集的生态书写不仅预示着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迫近,也显示了我们应对危机的决心和勇气。那么,生态儿童文学如何在此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呢?刘华在其新作《树王选战正酣》中进行了极富创造力的探索,无论在立意、架构上,还是内涵、美学方面,都呈现出了全新的面貌和气象。
首先,作品以生态整体主义的视角来构建故事,为生态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另类的范式和可能。人类中心主义一词于19世纪60年代被“发明”出来,用以描述和批判这样一种观念:人是宇宙的中心。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不少学者建议用生态中心主义来替代人类中心主义,但问题在于“中心”一词本身具有强烈的形而上学性,仍然意味着将人与自然二分。而在刘华的新作中,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关系被中国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有效地消解和缝合了,作家以“生态整体主义”替代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这两种相冲突的主张。在作品中,人不再是中心,故事围绕十棵古树竞选树王展开。这些古树各具特色,有的和蔼可亲,有的慷慨无私,有的热情聪颖,有的大智大勇,有的弘毅宽厚,有的坚韧不拔,等等。每棵古树都有一位形象代言人,但只有一位是小学生章木樟,其他九位都是动物。章木樟在智力和行动上并不具备绝对的优越性,他与其他动物作为古树代言人平等地参与叙事,竞选结果也并非机智的人类战胜了其他物种,尽管存在竞争关系,但他们和谐共处,这显然是作家审美理想或者说是作家生态观念的寓言化表达。
同时,作品的结构极具反讽色彩,小说虽以树王竞选开篇,但最终以“选而不竞”结束。表面上看,古树和动物通过语言编织的文本诱使大众为其投票,似乎是在隐喻性地揭示现实世界的权力、欲望和竞争等现象,或者说将复杂的社会问题转化为简洁而富有象征意义的故事。但实际上,所谓竞选不过是提供了一个讲述的平台与机会,从而让这些代言人围绕被代言的古树进行宣讲,并最终在整体上使得小说中那些可爱的生命体以及小读者们重新认知了生态。换句话说,故事尽管以竞选开启,但竞选的结果最终解构了竞选,因为十棵古树都有自己的历史与故事,都有其夺目的光彩,最终十棵古树共同分享“树王”这个能指,使得竞争或竞选这一现代主义逻辑得以被多元的价值尺度所重塑,最终实现了生态世界整体上的和谐与完满。这一看似皆大欢喜的结局实际上为孩子们提供了一种内涵极为丰富的启示:成功或者成就自我并非只有一个模板、一种路径,而是具有多样性,关键在于我们要听从内心的呼唤,把握好正确的方向,不怕艰辛,勇于开拓,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其次,作品具有强烈的后生态美学特色和深刻的人文哲思,将生态儿童文学书写推向了新高度。作家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中和”与“圆融”纳入创作,从而超越了人与自然、现代与传统、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对立。作品不再将城乡二元对立作为生态书写的支点,也不再将质疑“唯科学主义”、质询现代文明、质问现代主义逻辑作为生态书写的前提,而是向前迈了一步,立足当下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深入思考我们的生态保护之路如何有别于西方,并且试图为全球现代主义道路提供一种别样的可能或参照。比如,故事的发生地云梯山显然是一座古树博物馆,各种古树如秦樟、汉槠、隋茶、唐枫、唐榕、唐楠、唐银杏、唐红豆、宋槐、古罗汉在此矗立,但云梯山并非一片遗世独立的“飞地”,它不仅见证了历史,也和这里的山民、这里的鸟兽虫鱼在新时代的征程里绘就了崭新的画卷。作品为我们展现的既不是《老人与海》《白鲸》中那种人与自然激烈角力的图景,也没有像《沙漠独居者》《死刑台》这些作品一样将“人类中心主义”和“工具理性主义”的西方现代主义逻辑作为批判对象,而是试图展现一幅更为和谐、共生的生态愿景。经由作家所建构的诗意盎然的瑰奇空间,孩子们得以想象一个更为合理的生态世界。
显然,作家并不否认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曾给生态带来的伤害,但也并未有意将昔日的美好挽歌化,而是以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使孩子们相信只要珍惜我们的家园,未来会更美好,以古树代言人形象出现的那些濒危动物如金铁豺、黄喉貂、白颈长尾雉等,作为生态家园的一分子终将以“朋友之姿”再度生机盎然地登临生态舞台。只要我们保护得当,只要我们能平等地对待这些地球的精灵,视它们的生命同样珍贵,那么只要有合适的生存条件,万物自然生生不息。这部作品的价值也正在于揭示了当“保护生态,就是保护未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然成为共识,我们该如何让孩子们深切地感受到这些与人类长久共生的物种们的生存需要。更令人动容的是,作家不仅让这些花草树木、飞鸟走兽开口,让“他们”不再是它们,甚至让他们成为了“我们”。
最后,作品还具有极为内在的文化价值,为孩子们提供了一种重新打量世界并重新审视自我的维度。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每个生命体都有表达的权利和机会,并且有人愿意关注和聆听。作品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深邃而富有诗意的绿色世界,经由作家笔下的文字,我们仿佛穿越了时空的屏障,重遇了一系列在现代社会中日渐疏离的自然景致。在作家的笔下,那些原本应该与我们紧密相连、如今却成了我们遥远记忆中的碎片的植物与动物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我们共同构筑了一个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奇妙世界。这个世界中洋溢着和谐安宁的氛围,每一个生命都有自我表达的权利和机会,而且有人愿意聆听。这全然有别于我们当下的文化,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似乎大家都在“嘶吼”,但鲜有人聆听,也就难以形成具有凝聚力的共同体。云梯山不仅是一座生态山,也是一座文化山,每一个物种都承载着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底蕴,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诉说着过去的风雨沧桑和岁月变迁,并且听者众多。这当然要归功于作家雄健的笔力、丰沛的情感和出众的才学,经由作家的引领,孩子们不仅得到了知识上的满足,同时也获得了情感上的慰藉和文化上的认同。
另一方面是从叙事风格上看,作家的讲述是从容而缓慢的。成人世界的“快”对于孩子而言是灾难性的,是对丰富的生命体验的压榨,可怕的是这一逻辑已然延伸至孩子的世界中,使得孩子们感知、体验、思考世界的能力不断降低。《树王选战正酣》为我们提供了一次重新审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契机,让我们的感官浸润于如此鲜活的讲述中,使我们的意识重新具有了活力与纵深。与其说我们是在分享故事,不如说是在感受语言。这种语言并非我们日常劳作状态下信息化的语言,而是诗化的语言,在这样的语言构筑出来的世界中,生命体能够享有最充分的自由,这显然是文学的内在价值之一。书中的故事并不复杂,十场竞选演讲加投票构成了故事的主部,有趣之处在于简单的故事被饱满的讲述所填充,而作家的讲述一再地被“人物”的讲述所置换,由此讲述变成了讲述“讲述”。可以说,讲述“讲述”本身是破解集体性的自恋的文化症候的一剂良药,只有主体放弃自我讲述的滔滔不绝,转而关注他者,我们才能够打破自恋镜像,从而完成自我的蜕变与成长。在此意义上,作品引导孩子们从一己的小小天地走出来,迎向他人,迎向这个世界。
如果说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我们应该为孩子们提供什么样的三观,那么生态儿童文学则更为具体地指向如何对待一草一木,如何对待我们周遭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树王选战正酣》视为一种极富诗意而又理想化的生态乌托邦表达。作品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了人与自然的别样可能。人与其他生命体共同构成了复杂而微妙的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并非简单地相互依存,而是包含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尊重。刘华通过细腻的笔触,赋予了各种生命体丰富的个性和情感,它们不再仅仅是自然界的元素,而是成为了拥有自己故事和历史的生命体。这种对生态世界的全新解读,不仅为儿童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我们的现实世界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