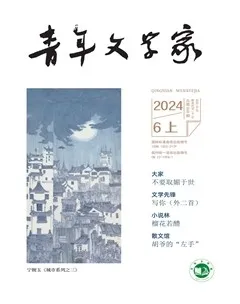归人不归
周语
我带着我的妹妹玛丽和海蒂在阿班特湖旁的这棵濒临枯死的老榕树下寻找今天的午餐。
自从父亲跟着远征的船只一起东征以后,城里的疫病和饥荒越来越严重了,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东西吃了。
此刻,我看着树上零零散散的几个蘑菇,惊喜地说:“甜心们,我们今天的午餐有着落了。”
海蒂两只眼睛亮亮的,伸出两只短短的胳膊,踮起脚去够树上的蘑菇。
玛丽一抬手,袖子往下缩了几厘米,紧紧勒住她的手臂。
羊毛做的上衣随着她的身子往上拉,露出了腰间一小截白肉,白得像软绵绵的羊羔,要是放进壁炉里烤上十分钟说不定还会流出金黄的油脂,油脂顺着白肉的纹路往下流,滴进火焰里。如果火烧得旺起来,不一会儿就能传出浓浓的、带着膻味的香。
我盯着那截肉,咽了咽口水。
玛丽的脖子轻轻扭向我,勒出一条细细的黑线,这线像是从她身侧湖面上的阴影里钻出来似的,直直映入我的眼。
我倒退一步,有些惶恐。
我想,我是饿疯了。
玛丽冲我露出一个微笑,两只眼睛弯弯的,湖水里浅浅的亮光照在她光洁、白皙的皮肤上,照在她沾着许多草屑的棕色长裙上。
我感觉到自己颧骨上的肉被扯得鼓了起来,僵硬地回了玛丽一个笑。
我低下头,两只干瘪的手指拨弄着海蒂扔下来的蘑菇和草梗。
小海蒂仔仔细细地摸着树干,发现再摘不到什么东西,蹲下身随意地捡起草叶来。
远处有船经过,她拍拍自己破烂的裙子,兴致勃勃地跑去湖边看着。
我抬头看着这棵老榕树,这棵老榕树大得出奇,我们三姐妹的身体加起来都没有它粗,比父亲登船远征前那个冬天看起来似乎又高了五六厘米,半圆的叶面从白皑皑的一片变回枯黄干瘪的样子,连叶尖上都不剩一小块白雪,树枝上零零散散地挂着几簇圆叶,树的下半段早已被虫掏空了大半,有个小羊羔那么大的洞。
我的祖父带着我的父亲在这棵树下玩耍过,我的父亲又带着我们来这里玩耍过。如今,我的祖父已经不在了,我的父亲说花开的时候会回来,也许我们等不到了。
看着船只远去后,海蒂跑回树边,把裙子往上扯了扯,左脚往树杈上一踩,两只白嫩嫩的手指死死抠着树皮,就要往上爬。
这棵老榕树轻轻晃动了一下,本就稀少的几簇叶子又掉下来几片。
“海蒂,下来吧。”
“不要。”
“这里没有蘑菇,没有鸟,也没有其他吃的了,我们该回家了。花还没开,明天再来等吧。”
“不,露西。你总是说没有,没有,你总是骗人,我才不会听你这个谎话精的话。”
我默默撑着膝盖站起来,看着湖畔金色的光辉,这光亮和父亲盔甲上的颜色可真像啊。
可是,父亲不会再回来了,他的荣光、爱与恨都埋在小亚细亚焦黑的土壤里,回来的只有写着他名字的薄薄一片纸。
玛丽手里捏着五六个灰扑扑的蘑菇,扔进我身前的木篮子里。
“露西,父亲真的没事吗?”玛丽蹲下身慢吞吞地整理着篮子里的采集物,她的嗓音压得低低的,整张脸上没有任何血色。
“没事的,没事的。他说花开就回来了。”
“可是……”
“没有可是。”
玛丽站起身,用柔软的手臂环住我的肩。
小海蒂坐在低低的树杈上,双手撑着粗糙的树枝,注视着平静的湖面。
我们都知道,这棵濒临枯死的树,再也不会开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