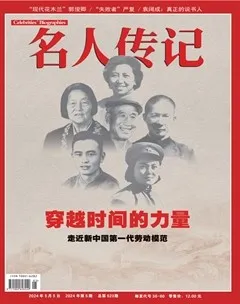“失败者”严复



1895年,甲午战败,清政府被迫割地赔款,四万万同胞痛心疾首。严复的悲愤更加刺心切骨。战场上牺牲的北洋海军将士,有他年少时福建船政学堂的同学,也有他在北洋水师学堂培养的学生。
此战后,严复大声疾呼,短时间内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一系列文章,抨击腐朽的清廷。他认为,中国向西方学习数十年后仍不堪一击,是因为没有从根本上学习当时西方的先进文化与精神。为此,严复凭借其特殊的西学背景,翻译了大量西方学术著作,成为中国“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然而,作为教育家,严复可谓一个“失败者”。他执掌过北大、复旦(1905年,严复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一北一南两大名校,却在这两所学校摇摇欲坠之时悄然脱逸;他教过的学生数以千计,可他真正得意的学生偏偏是他的编外女学生吕碧城;他一辈子为中国新学科的创立殚精竭虑,然而没有一个学科的鼻祖名号,他是当之无愧的;他不断高呼学术救国,他本人却不是什么大学问家,也没有写出哪怕一部里程碑式的学术专著。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严复(1854—1921),初名传初,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严复出生于儒医世家,幼入私塾,闽之宿儒黄少岩为其开蒙。1866年冬天,马尾船政局开局招生。严复以《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一文博得船政大臣沈葆桢激赏,被录为第一名。严复在福建船政学堂学习五年,1871年以最优等毕业,开始上舰实习。五年实习期间,严复随船游历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以及日本和东南亚等地,眼界大开。1877年3月,作为中国第一批海军留学生,严复赴英留学。1879年7月,严复以优异成绩在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完成学业,9月出任福建船政学堂教习。1880年8月,李鸿章延请其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洋文正教习,九年后任总教习。
北京大学首任校长,掌门仅八个月
1912年2月,严复出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5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严复出任校长。彼时,他已经五十八岁了。严复的感受,不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帝都”花。相反,在给夫人朱明丽的家书里,他把差事写得相当“油盐柴米化”:“本日又派大学堂总监督,薪水月三百两。此缺本系三品实缺京堂官,今不知何物矣。得差之后,便有人来荐管理员、教员等,可知凡事同前一样。”
“大学堂总监督”是三品京堂官,头衔响当当。可是大学堂的大问题,很快让严复忧从中来。首先,便是大学堂的经济危机——学堂缺钱,开学无望。与此同时,严复一家老小“十口浮寄京师”,家里入不敷出。双重压力之下,严复刚刚上任,即萌生退意,多次提及辞职。
当然,严复所面临的问题,远远不止经济困境。学生不安分,也让他头痛不已,“有学生彭姓兄弟号佛公、侠公,两人在《国风日报》数次造谣,与我反对,教员等极为不平,然只得不与计较”。而事实上,学生背后有更大的势力,正酝酿发难。在致函甥女何纫兰的信中,严复谈及:“不幸教育部多东学党人,与我本相反对,部薪折半,而大学堂全支,已是气愤不过,近又见舅得总统府之顾问官,以为月入必丰,于是更加媢嫉,百般设法动摇,欲令部中将大学校长更易。”
所谓“东学党人”,即留学日本诸人。无论学问还是人品,严复都相当鄙视他们,认为这些人没有学到西学真谛,甚至直接将他们贬为“东学小子”。但“东学党人”为数众多,拉帮结伙,渐成势力,甚至身居教育部要职。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辞职之后,接任的教育总长范源濂就是“东学党人”,而教育部系统的半壁江山几乎都是由他“钦定”的。
实际上,严复的对头,绝非有勇无谋之人。他们动用媒体,不断造势。《国风日报》《北京新报》《民立报》均对严复极尽造谣之能事,这让严复难以招架。其中,《民立报》的报道最具漫画性和戏剧性:
临时大学校长大鸦片鬼严复,昨日自天津返京,夹带大烟枪一具,大烟膏数十两,秘密藏之匣中,并大书特书曰“大学校长所有”六字。不意行抵前门,竟为站长查出,闻立即将烟具、烟膏和严复一并送到步军统领衙门去了。
这则短讯的标题是《大学校大校长大鸦片鬼之丑剧》。“大学校”“大校长”“大鸦片鬼”,三个“大”字,一行排开,令人瞠目,其杀伤力可想而知。
对此,严复的态度倒是相当坦然,他觉得这类谣言不值一驳。然而,无风不起浪。严复“被押被罚”虽非事实,他的烟霞癖却是事实。家书之中,他常常谈及戒烟带烟之事。1912年2月8日,他写信给夫人朱明丽,即嘱其带烟:“闻君潜来京在即,来时可托带鸦片二两来京,五元一两便可吃矣。”
经济困境、学生作梗、学部发难、舆论造谣,严复焦头烂额。然而,掌门北大,短短数月,他也干了几件颇有影响的事。首先,他向外国银行借款七万元,让学校躲过一劫。其次,他着手整顿学校,撰写《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将经、文两科合并成国学科,以迎合教育潮流。对此,蔡元培强调,“普通教育废止读经,大学校废经科,而以经科分入文科之哲学、史学、文学三门,是破除自大旧习之一端”。最后,也是严复最重要的贡献,在1912年7月教育部以经费困难要求停办北大的风波中,他没有袖手旁观,而是力挽狂澜,写下《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提出的四大理由,头头是道,振聋发聩。最终,停办之议被否。
即便如此,在掌门八个月后,严复还是悄然离开了北大。自1912年10月开始,三月之内,大总统像走马灯似的陆续任命北大校长和代理校长,被任命者有章士钊、马相伯、何燏时等。关于严复的去留,却无明文规定。
经历两场学生风波,模式如出一辙
在严复的北大去留问题上,学生泾渭分明,分为两派:拥严派和反严派。1912年10月10日,《大公报》发表声明《大学校学生公呈挽留严校长》,力挺严复。《民主报》则针锋相对,刊登《告白》:近有无耻之徒,假大学校全体学生名义,挽留已革校长严复,理、工、法、商四科并未与闻此事,用特声明。北京大学理、工、法、商四科同人公启。
两派学生,意气用事,甚至发生激烈对抗。
学生闹事,严复深得其益。但他拜见了教育总长范源濂,“声明学生种种暴动与我无涉”,颇有明哲保身的味道。他甚至用了“暴动”这个词,来定性这场拥戴自己的风波。由此可见,他的立场站在官家一边。与此同时,严复不忘指出问题的症结所在:这场风波乃是学部制造的问题,应该由学部解决。至于他本人,则为了教育,顾全大局,希望任劳不致招怨。对官家大表忠心,十分明显。然而,严复的两面性,并未让他在官场上左右逢源、进退有节,相反,他的保守态度,给他制造了强劲的对手,使他仕途受挫,风波不断。
其实,早在北大学潮之前五年,严复就已经历过一起学生风波——安庆高等学堂风潮。两次学潮的模式,如出一辙。
安庆高等学堂是安徽省第一所近代大学,学校虽创办数年,但因管理不善,成效不佳。1906年,安徽教育界领袖盛情邀约严复前往。4月8日,严复从上海乘船抵达安庆,担任安庆高等学堂监督一职,“至(校)之日,诸生欢迎若得大将,而教员中如姚仲实、胡敬庵诸君尤相推挹”。同年年底,严复再抵安庆,在学堂演讲《宪法大义》,反响轰动。所印讲稿五百多张,一抢而空,以至严复感叹道:“今日海内视吾演说真同仙语,群视吾如天上人,吾德薄何以堪此,恐日后必露马脚耳。”
谁知一语成谶。此后半年,学潮即起。闹事当日,学生早有预谋,一人拊掌为号,掀翻桌子,应者闻风而动。随后,学生们奔向斋务长周献琛处,肆意漫骂,驱逐斋务长,并一同驱逐严复招纳的闽籍教职员工五六人……
作为学堂掌门人,严复总结学潮原因,共计四点:官绅同流合污,以学堂为利薮;学生中劣者恐遭淘汰,以致大打出手;干将周献琛刚愎自用,开罪多人;安徽教育界人士制造舆论,煽风惑众。
严复没有细细反省自己的症结,问题似乎全出在别人的身上。事实上,他有两大问题:一是,他拿着顶薪,却没有尽到全职。查看安庆高等学堂职员和教员调查表可知,学堂职员、教员共计二十四人,严复的薪水一骑绝尘,遥遥领先,居然高达五百两;而教员十五人的薪水,总共才一千零六十两,平均每人七十两,体操老师才区区三十两。除了偶尔演讲外,严复以健康问题为由几乎从不教课。最关键者,他身为学堂监督,几乎“监而不督”,常常当甩手掌柜,遥控管理。他的大本营在上海,去安庆的次数屈指可数,即使偶尔待上几日,也大抱其怨:“安庆地方极陋,房屋如鸡栖,几椅粗糙,久坐令人股痹,故到此之后,羌无好怀。”更重要的是,严复对待学生缺乏宽厚之心。接手学堂第一年年末,严复主持学堂预科期末甄别考试时“大开杀戒”,不合格者高达三十八人。全城震悚,谓之手辣。严复认为,“经此一番淘汰,学生知功课之重,且一切唯在求己,均无所用人情势力,此堂是后可望必成矣”。对学生严加管教,无可厚非。然而,学堂风潮并不全是学生的问题,严复却同样“大开杀戒”,要求一定要“办到”“二十余人”,而不是像学台那样“敷衍”,只勒令退学五人而已。从严复处理学潮的态度上看,一个教育家,却不懂去爱一个个具体的学生。
此后,严复辞去了安庆高等学堂监督之职。
长于思考,催生众多新兴学科
严复不善治校,但长于思考。他对学科布局的建言,令人三思。他说:“考五洲之历史,凡国种之灭绝,抑为他种所羁縻者,不出三事:必其种之寡弱,而不能强立者也;必其种之暗昧,不明物理者也;终之必其种之恶劣,而四维不张者也。”严复认为,教育的三大板块为德育、智育、体育。其中,智育重于体育,而德育重于智育。
严复将体育之用矮化,最具体的显例是,在他执掌安庆高等学堂期间,两位毕业于安徽武备学堂的体操教员的薪水在所有教员中最低,每人三十两;而英文教员薪水最高者可得一百二十两,最低者也拿六十两。
至于为什么德育重于智育,严复的解释毫不含糊:“须知东西历史,凡国之亡,必其人心先坏;前若罗马,后若印度、波兰,彰彰可考。未有国民好义,君不暴虐,吏不贪污,而其国以亡,而为他族所奴隶者。故世界天演,虽极离奇,而不孝、不慈、负君、卖友一切无义男子之所为,终为复载所不容,神人所共疾,此则百世不惑者也。……惟此之关系国家最大。故曰德育尤重智育也。”不难看出,严复有着严重的道德崇拜倾向。但问题在于,严复所鞭挞的品德,如“不孝、不慈、负君、卖友”,更多地属于个人私德,有的甚至属于封建伦理;而对基于现代社会的公德,特别是现代文明赖以存在的基石,如自由、平等、正义、民主、法制,他则常常三缄其口,甚至讳莫如深。
尽管没有理顺教育几大门类之关系,但说严复是现代学科催生之王,并不夸张。早在1911年,严复便撰写《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一文,呼吁重视物理学。文中谈道:“可知物理科学一事,不独于吾国为变化士民心习所不可无,抑且为富强本计所必需。”推崇化学,严复同样不遗余力:“虽谓泰西今日之富强,化学实尸之,未为失也。盖自农桑医药,至于一切之制造,皆非化学不为功。”对于女学(女子教育),严复不但为之呐喊,而且投身其中,对学生吕碧城、甥女何纫兰等进步女性多有提携,可谓我国女学之先驱。甚至灵学,严复也兴趣盎然,大力研究。
与此同时,严复出大力引进的学科还有名学(逻辑学)、群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生物学等。通过翻译,他让这些西方学科,在中国安家落户。
催生中国新兴学科,严复之功,无人能及。
学术救国是其难以撼动的教育信念
严复之所以在内忧外患的中国催生一个又一个新兴学科,是因为他有一个难以撼动的教育信念:救国之道,唯有学术。
1914年,时任约法会议议员的严复向参政院提出《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议案,此文是严复的思想纲领之一。他为国把脉,指出国亡种灭有三大通患:一是“道德扫地,人心窳涣”;二是“贫者难富,弱者不振”;三是“民智闭塞,学术空疏”。其中,第三患最为致命。所以,中国教育的出路在于学术。
为了昌明学术,严复提倡实行奖励制度:“学成必予以名位,不如是不足以劝。……农工商之学人,多于入仕之学人,则国治;农工商之学人,少于入仕之学人,则国不治。”而晚清政府也确实实行了这样的奖励制度:留洋学生中有所成就者,如詹天佑等,均受到清廷的相应奖励,不少人名位相加。严复本人也“洋转正”,被授予他梦寐以求而久试不第的进士——1885年到1893年间,严复共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均落第;1910年1月,严复被赏文科进士出身。面对迟来的科举功名,严复作诗曰:“自笑衰容异壮夫,岁寒日暮且踟蹰。平生献玉常遭刖,此日闻韶本不图。岂有文章资黼黻,耻从前后说王卢。一流将尽犹容汝,青眼高歌见两徒。”喜悦酸辛溢于诗外。
然而,激励固然必要,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学术救国如何落实,即如何让中国学者有一颗追求新知、追求创造、追求真理的心。一度,科举八股被视为学术救国的最大拦路虎。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各地有了高等教育。然而,高等学堂形式具备了,但教师、学生,上上下下,并不追求高等教育的真精神,“理化算学诸科,往往用数月速成之练习,势必虚与委蛇,愒日玩岁”。这是严复所深恶的“中国今日学界不可医之病痛”。
学术救国,严复虽无铁腕,但有良方。1915年,他致函熊纯如(得意门生熊元锷从弟,严复视之为知己,通信不断),指点江山:
欧战告终之后,不但列国之局,将大变更,乃至哲学、政法、理财、国际、宗教、教育,皆将大受影响。学者于道,苟非深窥其源,则所学皆腹背羽矣。中国前途,诚未可知,顾其大患在士习凡猥,而上无循名责实之政。齐之强以管仲,秦之起以商公,其他若申不害、赵奢、李悝、吴起,降而诸葛武侯、王景略,唐之姚崇,明之张太岳,凡为强效,大抵皆任法者也。
严复洞悉世界之变,指出学者应探本溯源,抓住要害。问题是,一战之后,世界最大之变,变在科技。中国前途,亦在科技。严复所言虽无大误,然法制文明,在人治传统之下,难以生根,而国之大患,根植于此。严复曾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撰文阐述《论英国宪政两权未尝分立》,演讲《宪法大义》。这些都说明,对于法制问题,他有深究。但严复反对革命派,辛亥革命之后,一度拒绝剪掉辫子。他认为“根据文明进化论的规律,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应尽量使这种结构比过去更灵活,使之能适应环境,发展进步”。可谓方法正确,方向错误。
事实上,严复是一位最成功的“失败者”。
学校管理方面,严复任职四所学校,都身居要津,拥有发言权,而且留下一批历史文献,特别是《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和《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让他在教育史上青史留名。
学生培养不是严复的拿手好戏,但他也造就了一批栋梁之材,如民国总统黎元洪、翻译家伍光建、教育家张伯苓等。
学科建设,严复情有独钟。可以说,他是“学科基建狂魔”,生物学、逻辑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甚至有伪科学之嫌的灵学,他都打下梅花桩,晚年也乐此不疲。
学问之道是严复的终生兴趣。无论是公务劳神、危难分心,还是疾病缠身,严复从来没有放弃过一颗追求学问的炽热之心。
学校、学生、学科、学问,四学一体,严复游于其中,优于其中,忧于其中。
(原稿出自赵白生著、天津教育出版社2024年出版的《严复:难为世界人》一书。本文发表时,编者多有增删,并加章节标题,以符合本刊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