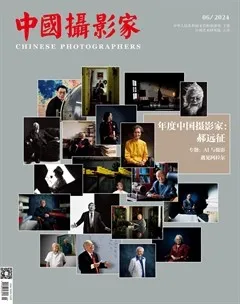游戏、实验和对话

杨梦娇(以下简称“杨”):你作品中出现的情境常常横跳或介于虚构的叙事和来自现实的经验之间,我们该如何理解你作品中的现实与“超真实”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尹航(以下简称“尹”):在我小的时候,北京房地产刚刚迈入狂热的发展期,售楼处比比皆是,而在每栋售楼处里最显眼的位置都会设立展示期房面貌的沙盘。我尤其着迷于观看沙盘模型中的室内空间,尽管它们并没有被赋予任何细节,却为我提供了想象的空间。我下意识地把自己未来的人生建构于模型空间的内部,想象诸多生命中的重要时刻在其中发生,甚至将这种想象蔓延到沙盘没有展示也不可能展示到的地方。而通过制作实体模型来观见并不真实存在事物的时代已经过去,它被后来的3D制图乃至现在借助AI生产的图像替代。这种现象的确印证了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预言,现实和超真实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纯粹的拟像甚至会扭曲现实。但我想强调的恰恰是现实与超真实彼此临近的暧昧边界。作品中的情境仍然来源于我们真实的生活,只不过在极端的情感氛围下,或者通过打破人们看待日常的习惯性视角,在介于虚构和现实之间的场景中,我们的想象力和感知变化会自然而然地把我们带领到由超现实包裹的真实世界中。
杨:结合你对摄影在当下处境的看法,谈谈你选择相纸作为模型材料的原因?你如何思考摄影中的物质性以及新物质性对摄影的影响?

尹:我曾在大学时期担任过打印室的管理员。微喷打印既昂贵又耗时,还不可避免地产生许多校色实验后被遗弃的边角料。我每次清理这些边角料的时候都会注意到相纸作为被动的介质其自身携带的鲜活历史和记忆。就像政治学家简·贝内特 (Jane Bennett)在《活力物质》(Vibrant Matter) 一书中谈论的,她认为那些被视为惰性的物质实际上充满惊人的活力,而其潜在的被感知的空间则蕴含着它的生命。我并非通过运用相纸来突出非人类世界的自主力量,而是借助相纸独特的承载图像世界的能力,尝试将其从客体工具转变为叙事主体,从而有效地将摄影与图像表达的不同形式统一在总体的视觉装置中。
杨:越来越同质化的世界正在将一切抹平,像素似乎可以表达一切质地。能否谈谈你在用传统的工作室摄影的方式来呈现这些实物场景的原因?以及你如何看待当代技术对图像生产和图像观看造成的影响?
尹:被当代技术加持的世界确实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生产出源源不断的仿真图像。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技术只是基于大数据的平均值所构建的算法结果。例如由AI生成的图像可以轻易塑造出很多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景观,但AI并不具备对图像背后情感和意义的领悟。摄影艺术家杰夫·沃尔(Jeff Wall)曾经将摄影师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通过直觉判断去捕捉即将发生事物的猎人,另一类则是勤劳培育影像的农夫。在我得知这个概念之前,工作室就一直是我种植和收获图像的场域。相比敏捷的猎人所着迷的捕获现成时刻的瞬间,我坚决地认为农夫所处的立场更有力地揭示了当代图像的诱惑性和不被信任的本质。在明确与不明确的边缘,农夫与构成图像元素之间的游戏、实验和对话或许才是激活图像生命的出路。
杨:在你的作品中,搭建模型的场所常常被比喻成舞台,而模型内部的真空结构极其脆弱、粗糙和无实际功用的本质几乎被掩藏起来。这种掩藏的必要性与舞台的幕后之间是否有关?更进一步地,它与人们生活的暗处之间是否也存在具体的关联?
尹:模型结构真空、脆弱、粗糙和无实用的本质是我一直以来对即将逝去之物的印象。而在我们眼前上演的一切,无论是真实发生的,还是来源于虚构,不都是转瞬即逝的舞台切片吗?事实上,也只有少数人会关心这些进入我们视线的、在我们脑海中产生的景象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它们始终处在阴影之下。这让我想到曾经有人用“积多成少”评价我的作品,具体指的是每一件作品背后工作量巨大,最后却以一张轻薄的照片展示。对这种看上去不对等的展示方式的疑问反而是我期望的效果,它指引观者对画面中物体的形成产生好奇,或者提出若干种可能性的假设。
杨:根据你从网络上选取高清图像,再将其打印在相纸表面,然后形成模型的过程,图像的细节不可避免地遭遇减损,但最后却又以大幅尺寸的方式输出,展现在观众面前,使得图像的损害和手工制作的痕迹被轻易看见。对此,你是如何考量图像压缩和放大尺度与视觉传递之间的关系?
尹:放大是我创作中十分常见的手段。我从网络上选择图像,将其编辑放大到近乎失真的状态。它们最后呈现出的粗粝噪点仿佛不同色系的白噪音定帧。整个过程在我看来是极端且暴力的,好比我把沙子的图像放大到看上去像是若干个气泡,把海浪图像放大到如同一根白线时,放大不仅意味着简化和信息的丢失,也是对事物原本形象的抹除、扭曲甚至篡改。而手工制作痕迹的暴露则更进一步地加深了手对图像干预的痕迹。它让观看不再顺畅,而是充满怀疑和阻碍。
杨:你作品中的许多画面都在表达人遗留下的痕迹,却为何避免人的出现?这与你在作品中普遍设置的由物组合的底色存在怎样的关联?
尹:我并没有避免人的出现。我的工作方法和传统摄影有很大的区别。传统摄影是对现实直接的框取,为了追求画面的平衡而不得不考虑取景内容的加减。我的摄影则从零开始,一切都来源于加法式的累积。如果初期没有设置人的存在,也就自然不会牵扯到对人的避免。对我来说,人的表情和肢体以及他们所处的境遇都过于具体,它们较之物体更容易将观者引向泛滥的共情,从而削弱他们对画面的直接联想。为了强化观者和画面浸入式的关系,我倾向于创造类似电影中交代故事环境的空镜头,因为单纯的物不仅意味着简化的场景,也是一个处于欢迎状态的更自由的留白空间。
杨:呈现节日过后的虚空和殆尽似乎是你揭示当代社会中隐秘欲望的策略,你如何处理来自公域与私域的视角?将其搅拌在你作品的画面中,从而形成一片混沌的情感空间?
尹:你所说的“混沌的情感空间”是对我作品中情感部分非常精确的描述。相比过去人们对共同生活的依赖,如今先进的技术已然为不同个体创造了投其所好的丰盛宇宙,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愈发被强化,人的存在也因此变得孤立。而节日就像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所说的,是“打破日常状态,把人联合起来的庆祝”。我将节日的氛围视为个体实现交往和物体脱离其功能性的鼎盛时刻,而节日过后的衰败景象就是这片混沌的情感所在的地方。通过展现这种狂欢落幕后的场景,物品被忽略、用尽、丢弃的状态则流露出当代社会人们精神状况的真实处境,它从曾经的过于饱满而自然走向枯萎,并被永恒地定格在朽败的无限延伸之中。
杨:你的创作最终落实为拍摄而成的图像,而非模型装置,甚至你会主动弃置那些模型。为什么坚持以摄影作为你的创作结果?
尹:现在,我们大都通过屏幕体验图像,从而忽略了图像的重量。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看图像的内容,却没有办法阻止图像的传播。每个人都是图像的宿主和传染源。在这样的世界里,图像是以轻快的方式传播的,而这种轻快的传播如同触碰到某种气味后联想到某个情景。模型装置在我作品中扮演的角色即是气味形成的源头,而我关注的则是气味本身不可见的重量感,以及这种重量感在传播过程中将可能被怎样的方式所感知。
杨:你的作品融入了许多对日常生活和情感经历的表达,这种个人情感如何与艺术创作相互关联?
尹:在我看来,日常生活是一片真正自由的、不受控制和不被预知的田野,它总是伴随很多偶然的奇遇。在很大程度上,我个人的情感只是引诱我关注并得以最终见证这些偶然的触发剂。当偶然被截取出来,如拼图一般组合形成新的叙事时,这些生活中既普通又奇妙的时刻便从某种被我们忽略的事物变成了主动追随和笼罩我们的能量。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艺术创作而言,这种活跃于边框之外的能量恰恰也是赋予边框内的景象某种免于阐释便能与人交流的独特语言。
杨:你的作品中充满了各种符号和隐喻,你经常使用的符号是什么?它们有怎样特殊的意义和象征?
尹:我的作品经常涉及运动,即便是静止的情景,也是为了引发对上一个运动瞬间的联想。相比电影里可见的运动和时间,传统摄影里的运动和时间常常因为一个备受禁锢的“决定性时刻”而被隐藏起来。但我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追踪和揭露摄影内部的运作机制为前提的。在我看来,发生在模型场景中的运动是试图无限趋近某种状态的过程,而与其同步的镜头的运动都是游移的,它规避了精确的立场,使得画面不被封闭的结论所束缚,时刻处于流动之中。因此,定格也成为运动的一部分,而非运动的结束,它让运动的起点和终点之间的距离变成了提供遐想的、不止一种可能性的路径。
作者简介:
尹航,1988 年出生于北京,2015 年本科毕业于旧金山艺术大学(AAU),2017 年研究生毕业于旧金山艺术学院(SFAI)当代摄影专业, 现工作、生活于北京。曾举办“消失”(深圳,蛇画廊,2023 )、“滑行在滩涂之上”(北京,新氧艺 O2Art 艺术空间,2022)等个展。
责任编辑/樊航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