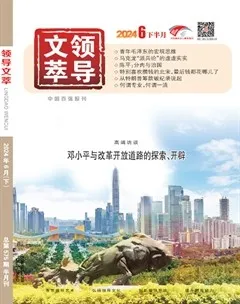剪辫子是件漫长的事
谌旭彬

梅兰芳是在1912年6月剪掉辫子的。此时距离清帝下诏退位已过去4个月;距离民国政府发布剪发令已过去3个月。梅兰芳的行动显然称不上积极,但相对身边其他人,却已可算前卫。比如,为梅管理服装和处理杂物的“跟包”,无论梅怎么劝,就是死活不愿意剪掉辫子。
梅兰芳身边人的情况并非个案。清帝退位了,革命军政府发起了带有强制色彩的剪辫运动,但知识分子、乡绅与百姓不肯剪辫子的案例其实很普遍,甚至不乏聚众暴力抗争的现象。
1912年前后,多数民众不愿意剪辫子或许尚有担忧清廷复辟的考量。但下面这些事实,就很难用担忧清廷复辟来解释了。
在安徽,民国成立两年了,绩溪周边乡村的留辫者仍极多。据《申报》 1928年9月16日公布的一项统计,民国已成立16年之久,北京仍尚有4689条“男辫子”未剪。
以上事实,也很难被归因为“生活习惯”。真正导致民众不愿意剪辫子的原因,是遗忘与美化。
对清朝初年的中原民众而言,脑后的辫子意味着被征服的屈辱史,意味着“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但当硝烟散尽,政权鼎革已成定局,这段屈辱史遂被当局用严密的文网层层遮蔽了起来。自顺治朝始,至乾隆朝终,共兴文字狱170余次,尤以乾隆朝为最,多达130余次。这些文字狱的核心目的之一,就是消灭清初历史。
如彭家屏乃康熙六十年进士,仅因藏书中有记载南明史实者,父子便俱被处死。藏书尚且如此,讲授、传播明清易代的历史真相,自然更无可能。而在明清易代的史实中,“剃发留辫”又是最为敏感者。连“发”字在清代的使用都一直处于战战兢兢的状态。如常用词“一发千钧”,因容易被人联想曲解为“以千钧之重来形容一发”,进而引申为对剃发政策的不满,清人便极力回避使用该词。王汎森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一书中说,清人花80余年所修纂的《明史》,“从头到尾未曾用过‘一发千钧或‘千钧一发”;《清实录》里同样找不出“千钧一发”,仅出现过一次“一发千钧”。
一个“发”字尚且如此,剃发留辫的历史会被遮蔽到何种程度自不难想象——乾隆时代的禁书运动中,连“女真”“建州卫”这类名词,皆因为有可能引起对清朝早期历史的联想,全列在抠、删的范围内。书籍中没有建州卫、没有女真、没有扬州十日、没有嘉定三屠……普通人当然也无法了解辫子之由来。于是,在晚清无知识的普通人眼里,剃发留辫仿佛已是数千年的固有习俗。
乾隆时代,曾静以“理气之分”来抨击清廷,认为汉人生于中土,禀气较纯,故生而为人;夷狄生于边陲,禀气不纯,故生而为禽兽。到了清末,这套毫无道理可言的“反动理论”,竟已成了知识分子用来维护清廷、对抗近代文明的趁手武器——郭嵩焘出使欧洲写日记赞赏英国“君民兼主国政”的制度,引来同乡大儒王闿运的激烈批判,王只承认大清之人是人,他搬出了曾静当年的理论,说“彼夷狄人皆物也”,那英国人都是禽兽之物,不过通了一点人气罢了。
在这样畸形的社会里苟且太久,苟且会慢慢变成生活的一部分,苟且的原始意味会慢慢消失,苟且会被美化,会变成理所当然和不容置疑。曾静的“理气之分”如此,辫子问题也是如此。曾经的压迫已经遗忘,曾经的屈辱已被美化。于是,辛亥革命后,地方士绅为保住自己的辫子不惜与新政权武力相向的冲突层出不穷——1912年7月,清帝已退位半年之久,山东都督周自齐派了宣传员前往昌邑县劝导民众剪辫。宣传员在县衙门口举行集会,公开剪掉了当地两名乡绅的辫子。次日,被剪了辫子的乡绅聚集民众公然打杀了27名无辫之人。
有形的辫子已是如此难剪,无形的辫子当然更是根深蒂固。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他公开发表了一份总统宣誓词。这份完全足以代表其个人意志的宣誓词,便露出了他脑中那根剪不掉的无形之辫:
……西儒恒言,立宪国重法律,共和国重道德。顾道德为体,而法律为用。今将使吾民一跃而进为共和国民,不得不借法律以辅道德之用。余历访法、美各国学问家,而得共和定义曰:共和政体者,采大众意思,制定完全法律,而大众严守之;若法律外之自由,则共耻之!此种守法习惯,必积久养成,如起居之有时,饮食之有节,而后为法治国。吾国民性最驯,唯薄于守法之习惯。余望国民共守本国法律,习之既久,则道德日高,而不自知矣!
通过不知来由的所谓西儒名言,袁抛出的论断“立宪国重法律,共和国重道德”,实在是错得离谱。这是一段非常荒唐的论述,绝不是一个被赋予了引领国家从秦制时代向民权时代转型这般重任之人该有的认知。
(摘自《大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