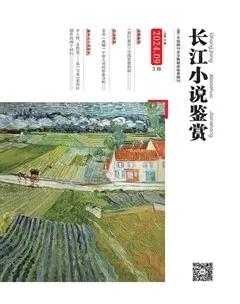阿Q的现代转生: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阿Q正传》仿作
李龙琪
[摘 要]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兴起了一股《阿Q正传》仿写潮流。仿作者们一方面为阿Q设置了学生、富豪等摩登身份,让他们从未庄来到都市,但其思想与行为却与此前的未庄阿Q一脉相承;另一方面,注入了浓厚的时代特征,刻画了战时社会环境中各式各样的阿Q变种。对《阿Q正传》的仿写得以在彼时蔚然成风,阿Q典型本身具有的高度的普遍性是不容忽视的前提。同时,战时社会塑造民族主义的身份认同,需要借鉴阿Q这一批判性的文化资源。
【关键词】 《阿Q正传》 仿作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鲁迅
[中图分类号] I10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2097-2881(2024)09-0039-04
早在1928年,钱杏邨就宣判了“阿Q时代”的结束。但是,在接下来的二十余年中,《阿Q正传》的仿作不断涌现,以创作的形式质疑了钱杏邨的判断。在这些仿作中,阿Q转生为小Q、亚Q、阿O等种种形象。比起在辛亥年间就被枪毙了的阿Q,他们所处的时代已经日新月异。但阿Q精神没有随辛亥革命远去,而是融入了他们的血液和基因。这些新式阿Q同样值得关注。但是,目前学界关于《阿Q正传》仿作的相关研究尚不充分,仅对个别仿作进行了细读,并未从宏观的角度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阿Q正传》仿作进行整体观照,也未交代为何《阿Q正传》的仿作会在这一时期层出不穷。本文则试图在整体梳理三四十年代《阿Q正传》仿作的基本创作风貌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具体语境,探查这些仿作对鲁迅原作的承传与变异,进而思索此时《阿Q正传》仿写热潮形成的动因。
一、从未庄阿Q到摩登阿Q:《阿Q正传》仿作中的人物类型
鲁迅原作中的阿Q尚是一个农民或流氓无产者,而仿作中的阿Q大多进了城,成为“城里人”。他们摆脱了农民阿Q的蒙昧状态,拥抱了现代城市文明。仿作中常见的摩登阿Q有两种:学生阿Q和富豪阿Q。
对学生阿Q的书写在《阿Q正传》的仿作中占相当大的比例,这些仿作多来自在校大、中学生发表于校园刊物上的文章。他们在仿写《阿Q正传》时,一般会自然而然地以校园生活为底本,以身边的同学为模特。他们的仿写情节较为简单,模仿痕迹也比较明显,基本是将阿Q的精神和事迹移到学生身上。有些学生阿Q继承了阿Q式的“瞧不起”,如马三郎笔下的女阿Q,穿着校服大摇大摆地去学校,仿佛自己是学生就高人一等,但到了学校,却对老师同学极尽巴结;王士年塑造的学生阿Q成绩好,就瞧不起成绩不好的同学,自视为城里人,便瞧不起乡村的同学。有的还继承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蔡观笔下阿Q的儿子小阿Q喜欢打架,打不过就喊别人“阿爸”,自称是一种明哲保身的手段……这些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学生阿Q学问远在连名字都不会写的老阿Q之上,但却透出了老阿Q的精神底色。由此可见,阿Q精神并不会因代际更迭和文化水平提高而消失,受过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身上依然存在阿Q的阴影。
在原著中,“不准革命”的阿Q死在了革命的第二天,穷困潦倒地终结了一生。有些《阿Q正传》续写者则试图为阿Q创造翻身的机会。在仿作中,阿Q真正过上了“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的上等人生活,成为上流人士。阿Q的发家史受到普遍关注。但在这些作品中,阿Q的“阔起来”不是靠他的“真能做”,而是靠各种不正当手段。在尤晨的《阿O正传》中,阿Q的私生子阿O儿时当乞丐,后来,一架飞机在镇上坠落,阿O趁机捡走飞机上的现金,成了亿万富翁。阿O的投机致富使他真正地凌驾于小镇居民之上,连昔日与他打架的阿猴(类似于与阿Q龙虎斗的小D)也成了他的手下。但是,某天,阿O在与妇女搭讪时被暗杀。结尾的“阿O死了,但阿猴在微笑着”[1],暗示阿O之死是阿猴的设计。从阿O投机成为富翁,到阿猴暗杀并取代阿O,在此,革命的潜能没有带来正面的变革,反而催生了不择手段、巧取豪夺的闹剧。
阔起来的上等人阿Q与未庄的穷苦阿Q的思维方式并无不同。在一些仿作中,曾饱受欺辱的奴才阿Q终于爬到了主子的位置上,但他却反过来加倍欺压在自己之下的奴才。在声笙《新阿Q传》中,新阿Q曾是流浪汉,后来到了上海,靠与地痞恶霸勾结树立起了权威。一次,他帮某公馆的太太摆平了桃色纠纷,太太送他巨额酬报,他便用这些钱办起了百货商店。他把伙计当成牛马,若伙计稍不合他心意,他便动辄打骂。他甚至将一个伙计折磨致死。高远东曾将鲁迅思想的内核概括为“相互主体性”。上述对富豪阿Q的书写正表明了,“单向度的人之为人、主体之为主体并不能消灭主奴关系”,只有把“立人”的命题延伸到社会性的相互关系领域,“主体才能成为‘相互主体,社会才能成为人人为人的社会,真正消灭了主奴关系的现代主体化的新文明才可能出现。”[4]
二、剧变的时代与不变的阿Q:战时社会中的“阿Q相”
三四十年代的《阿Q正传》仿作者们力图在对鲁迅原作的借鉴中注入新的时代思考和现实关怀。因此,这些仿作不只限于阿Q身份的拓展,揭示无论男女老幼、贫富贵贱,都或多或少沾染了阿Q精神的遗毒,也不只停留在对原作亦步亦趋的模仿层面,而是一种“在新的文化、政治和语言背景下对前文本的再创作,是作品穿越时空,从一种接受语境到另一种接受语境的变迁”[5]。
从14年抗战到3年解放战争,战争构成了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历史背景,救亡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考察此时仿作者对阿Q故事的重述离不开战时语境的参照。实际上,此时的很多《阿Q正传》仿作中都有战争的影子,有的甚至直接传达了仿作者的战时思考与批判。
首先,在民族危亡之际,抗日救亡是上至国家政府下到每个国民不容推卸的责任,以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拒绝反抗显然有悖民族大义。在国家政治的层面上,抗战初期,舆论普遍对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强烈不满。有人借助对阿Q故事的重述,以形象性的小说形式表达辛辣的讽刺。在高庆丰《阿Q与唐吉诃德的会谈》中,阿Q竟声称敌人进攻中国是为了将他们的万千头颅奉送中国。而敌人占领南京,并且还要继续西进,是因为送礼要送到家。他还矢口否认中国将面临亡国的危险,称中国的失败是败中取胜和胜利的退却。阿Q上述的荒诞言辞显然脱胎于当局的“不抵抗”言论,当局不抵抗的阿Q主义者的面目在这篇作品中跃然纸上。
在个体层面,为一己私利拒绝承担抗战义务,沉浸在个人的小天地中而不去接触残酷的社会现实的人也被视作阿Q。对学生来说,一味钻象牙塔、进研究室已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行为。林茂《小Q的故事》就讲述了只顾读书、不关心抗战的小Q精神胜利法失效的过程。小Q从不参与社会活动,认为读书之外的事都是国家的事,与学生无关。然而,“九一八”之后,他的梦想被当局的不抵抗政策断送了。他决心不再安分守己,积极参加抗日的社会活动。但是,他还是看不惯同学们与反动的学校当局的对立,认为要采取阿Q的精神胜利法,做有涵养的学生,理解校领导的苦衷,即使学校开除学生也是因为学生自己的问题。然而,后来学校竟以参加社会活动、玩忽学业为名,将成绩优异的小Q开除了。“孙子才敢开除我”[6]这类话从此失去了效力。作者讲述小Q的故事,意在提醒青年,在民族危亡之际,阿Q式的精神胜利不可取,要怀揣社会责任感,与中外反动势力做实际的斗争。
其次,揭露阻碍抗战的现实黑暗势力是战时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这一主题在彼时对《阿Q正传》的再创作中亦不鲜见。有的作者以尖锐的笔触揭露了战时阿Q出卖国家、发国难财的卑劣行径。阿Q“前世吃了假洋鬼子的亏,这一世他就想勾结真洋鬼子来捣乱”[6]。他一面逢迎外国权势者,帮他们摆好“人肉的筵宴”[8],一面仗势欺人虐待同胞,从中牟取巨额利益。《阿O起家传略》详细地描绘了“外形酷像阿Q”的阿O投靠侵略者大发不义之财的起家史。阿O本是王庄地痞,村庄被敌人占领后,他被任命为伪自治会会长。他精明能干,善于逢迎,加之善于运用各种肥己手段,他便很快发达起来。后来阿O“功成身退”,带着血腥钱投入上海商界,靠主子的扶助赚得盆满钵满。抗战胜利后,阿O带着钱财出逃,不知所踪。小说结尾的“但是阿O……——没有下文?”[9]却提醒人们警惕这种时代“弄潮儿”的再度出现。
最后,有些民众对战争的目的缺乏正确的认识,正如在阿Q看来,革命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两个现代阿Q的故事》中的两位现代阿Q对战争的理解与之并无二致。瘌痢阿毛是天津的一个裁缝,他听闻我军即将解放天津,便开始幻想娶银行行长的三姨太为妻。小刘在济南的银行当茶房,听说我军即将接管济南,他于是变得趾高气扬,不再完成上司分配的任务,还把银行的很多东西都搬到家里去了。可见,对于两位现代阿Q而言,解放战争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目的与他们无关,他们只关心“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10]。也可看出,广大民众如果缺少“深沉的勇气”“明白的理性”[11],对革命和战争抱有阿Q式的理解,以正义、民主、自由为追求的革命便难以实现其目的。因此,在战争中,启迪民智,消灭群众脑中的“思想敌人”同样不容忽视。
曾有人指出,“许多批评家说,阿Q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然而我们试看看周围,这种人却多得可以。过去潜伏着的这种品性,在这个战争里都充分暴露出来了。”可以说,对于战时“阿Q相”的发现与揭露,有力地证明了“鲁迅所描写的时代已经过去,是完全错误”[12]。也正如鲁迅所言,“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13]
三、艺术与时代的合力:《阿Q正传》仿写热的成因
尽管鲁迅认为“永远是炒阿Q的冷饭,也颇无聊”[14],但这丝毫不能浇灭人们仿写《阿Q正传》的热情。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对《阿Q正传》的仿写会在三四十年代蔚然成风?曾有学者指出,文本的传播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文本自身的魅力,二是社会的需求。前者由文本的固有属性决定,后者则是“文本在与流变着的时代背景中多种可变性条件遇合之后衍生出来的动力性因素”[15]。探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阿Q正传》仿写热潮,也可以从这两个方面进行思考。
对文本自身而言,《阿Q正传》能够迅速地被经典化,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坛中赢得崇高赞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小说塑造了一个“说不尽”的阿Q形象。阿Q形象自诞生起就被指认为“中国人品性的结晶”[16]“中国的一切谱的结晶”[17],成为当之无愧的国民性典型。同时,正如罗曼·罗兰曾认为法国大革命时也有过阿Q,阿Q的典型形象更是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性。由此,阿Q典型的高度普遍性使《阿Q正传》成为一种“可以无限演绎和变形”“能够不断被再写和再述”的“起源文本”[18],进而构成了《阿Q正传》被不断改写的前提。正是由于无论何时何地、何种身份的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分有阿Q的基因,所以仿作者们的尝试便顺理成章。
但是,《阿Q正传》的仿写自三十年代开始才形成潮流,小说发表的最初十年中的相关仿写作品却甚少。仅从阿Q形象典型性的角度无法解释为何在三四十年代《阿Q正传》仿写热的原因。故此,彼时时代语境的催化作用应被纳入考察范围。
如前所述,战争构成了三四十年代最大的时代背景。“九一八”以来,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使抗日救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日渐汹涌澎湃,塑造民族主义的身份认同,为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塑形成战时社会的迫切需要。作为“民族脊梁”的鲁迅精神被视作重构战时民族精神的重要资源。战时社会对鲁迅的推崇亦带动了人们对鲁迅作品的重视。如果说鲁迅的精神和人格给予民族精神正面的建设作用,对国民性负面典型阿Q的形塑则为人们对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和反思提供了批判性的文化资源,在战争语境中“以反思性的爱国主义方式投射于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正如时人所说:“我们现今的国家社会,不能再容有阿Q这样的人物”“为了抗战,为了胜利,我们需要时时刻刻枪毙阿Q”。基于这种时代需要,《阿Q正传》获得了广泛关注。也就不难理解,《阿Q正传》的仿作为何在此时大量涌现。这些仿作者为阿Q改换了身份和时代背景,但却保留了其精神内核,意在以文学创作的方式向人们展示:阿Q并没有死,战时社会中还存在着形形色色的“阿Q”。只有努力揭露并消灭国民性中的阿Q精神,才能求得抗战的胜利。而解放战争期间的《阿Q正传》仿写的时代背景处于抗战的延长线上,为了争取建设崭新的民族国家,国民必须具有良好的精神面貌,为此,同样也要摒除阿Q式的国民劣根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阿Q正传》仿作基本延续了鲁迅原作“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的创作主旨。在仿作者笔下,无论长幼、贤愚、贫富,都能在他们身上发现熟悉的“阿Q相”。在跨越了身份和阶层的同时,阿Q精神还穿越了时代。仿作者们敏锐地捕捉到了变动时代下的不变,成功刻画了战时社会环境下滋生的各种阿Q变种。彼时《阿Q正传》仿写热潮的出现,一方面,印证了阿Q形象的持久魅力,对宣判阿Q已死的言论提出了有力质疑;另一方面,顺应了战争中强大的民族主义时代思潮,为重塑民族精神、凝聚民族情感提供了助力。这些仿作的艺术水准虽难与原作比肩,但其借鲁迅思想与现实对话,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复现”鲁迅笔下人物的尝试却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说,《阿Q正传》的仿作者们正是以创作的形式接续、发扬了鲁迅的思想传统。
参考文献
[1] 尤晨.阿O正传[J].现代周刊(槟榔屿),1948(109).
[2] 鲁迅.“题未定”草(一至三)//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 齐雯.阿Q别传(续)[J].国风(上海1939),1939(3).
[4] 高远东.鲁迅“相互主体性”意识的当代意义[J].探索与争鸣,2016(7).
[5] 陈红薇.改写[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1.
[6] 林茂.小Q的故事[J].青年知识,1940(12).
[7] 丁力.阿Q转世[J].论语,1947(150).
[8] 鲁迅.灯下漫笔//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9] 阿O起家傅略[J].人人周刊,1945(5).
[10] 鲁迅.五十九“圣武”//鲁迅. 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1] 鲁迅.杂忆//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2] 周黎文,洪予.长篇漫画:阿Q之再生[J].青年月刊(苏州),1942.
[13] 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4] 鲁迅.360108致沈雁冰//鲁迅.鲁迅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5] 田义贵.经典文本的变迁与历时传播——以《红岩》为例[J].社会科学战线,2006(3).
[16] 雁冰,谭国棠.通信[J].小说月报,1922(2).
[17] 仲密.《阿Q正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1913-1983:第1卷.[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18] Julie Sanders.Adaptation and Appropriation (The New Critical Idiom)[M].Routledge, 2006.
(特约编辑 范 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