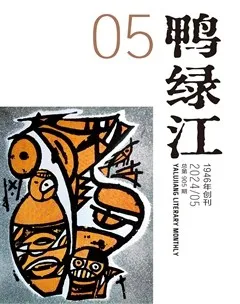春暖
1
这才几天,银星小卖部门外,盆中的荷花由盛而枯。枯败的叶子苍白无力,茎秆却挺着,一副站着赴死的样子。勤快的瑶坤将枯枝败叶剪去,留两枝枯茎:一枝枯茎上脸盆大的残叶在时令的安排下无奈地低垂,压得枯茎也有些歪斜;另一枝枯茎顶一个莲蓬,莲蓬倒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笔直向上,莲子或是掉了,或是被人抠去,莲蓬头像筛子眼儿一样。商店主人米平回来刚好遇见,愣住,剪去干什么?那个死样,难看,瑶坤说得干脆,擦着盆沿。留那么两根枯枝?带架。瑶坤收拾起剪下的残枝败叶,送到门外马路边的垃圾箱,回来间不住拍去手上残屑。走到荷花盆前,纤手一指,看看,多美!她黄白肤色,鹅黄发质,薄眼皮,眼睛浅陷,眼角一挑,把手一挥,颇有些得意,仿佛完成一幅杰作。
近年,插花是她的爱好,路边拔回一棵草,也能摆弄出景致。可是,这荷花盆直径90厘米,挺着一棵二尺高的枯茎,低着一个大脑袋,顶一棵三尺高的满是筛眼儿的莲蓬,何美之有?满盆枯叶,各有形象,集体抱个团,取个暖,还不孤独,多好?你留两棵枯枝孤零零迎风冒雪,很残酷!嘻,就是那般物,一年生一年死,孤独才美。喝茶还是咖啡?瑶坤洗好手,坐在茶台前烧水。
瑶坤小米平20岁,是她的店员。五年前,瑶坤犹犹豫豫在她店外,姐,用人吗?怯怯的。你什么情况?我……米平转身,进屋听听。瑶坤说丈夫去世,孩子念书,得活,说着,递上身份证。原来怎么活的?想换个地方活。无缘无故走到我门前,定有缘由。走过十几个门了,过来碰碰。收起你的身份证,相信一次人吧。你得保证商店物账相符、账款相符。卫生加做饭外加供饭。工资多少?看我们收入吧。瑶坤鸡啄米一样点头,被收留便是千恩万谢。
银星小卖部是米平30年前下岗后开的小店,60平方米,有公用电话、烟酒糖茶等。瑶坤到店后,就像沾了雨露,一天天滋润,不再怯怯的。她待人热情,礼貌周到,物品摆放齐整,柜台晶亮得能当镜子用。就是做的饭菜味道不咋样,她抽空去小饭店唠嗑儿取经,知道需要色香味。这天傍晚,炒鸡蛋时西红柿的葱、香菜搭配的红黄绿煞是好看,表面光鲜,却还是无滋无味。别花里胡哨了,米平爆锅,削一个白菜根,和半碗面粉,喷香可口的疙瘩汤做成,俩人饱饱胀胀。有米姐的疙瘩汤,我幸福上天了,瑶坤手舞足蹈地说。刷碗吧,天生的低等货,米平白她。你高等?争到什么了?还犟开嘴了。理儿?是不是这么个理儿?有疙瘩汤还不满足?瑶坤刷了两个人的碗,开账柜拿包下班回家。每天背个包,到店就上锁,不知道的,还以为背多少财产。米平到柜台里面坐下。瑶坤又就势坐对面。你不知道我包里背什么呀?餐巾纸、口红之类。有重要的。无非身份证、户口本、银行卡。还有?还有。什么?人生。米平略一愣,不动声色审视瑶坤。
瑶坤淡定,低头摆弄包。现在的人生是你见到的,前世啥样,谁知道?伤害了谁?得到现世?丈夫没了。米平定睛看瑶坤,你姐夫也不在了。他在世,我丈夫却走到世界尽头,我得用一生去寻,直到我离世那天,也不知道是否还能遇见。这一世,我竭尽全力修为,不求来世了。瑶坤一句话,点醒梦中人。米平开始思考起自己的人生,现实的,前世的,至于来世的,她不敢想象。
银星小卖部随着时代发展,项目有增有减。公用电话等小业务逐渐撤掉,最近新增了有机食品线下店等。网购通行后,什么东西都卖不动,有的东西或送人或自用。这些年来,银星小卖部也成为大家闲坐的地方。来闲坐的人爱文史的多,因为米平是中文系毕业,这些人在一起乐此不疲,讲地方的古,唠古老的地儿。年代的事儿听了很多。这个地区日本人侵略以后,自发的大刀会组织奋勇抗敌;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加入担架队的,整个一个全民皆兵;日本人枪杀中国人的黄泥坑还在;大刀会与日伪作战,墙上的枪眼儿还在;至于历次运动的场景,也历历在目……米平有很多联想,看不得荷叶那种低头的样子,看不得莲蓬满目筛眼儿,枪打的样子。
米平,近60岁,宽额,白肤黑发,有时特别是自己看书时,或听人讲古时,泪水没有闸门,爱自动流淌。她出生在一个古镇,爷爷是中医,家中几代人做小买卖。在不允许个人做买卖时,生意被合作化了;在允许做的时候,米家又是小镇第一家起营业执照的。她很小的时候随家下乡,十一年以后又回到小镇。家族中这样那样的问题经历过,也经历过同时代许多人都经历过的下岗、创业、改制及生与活。
她进小店后又转出门,看那俩枯枝,不忍心其孤零零,站在花盆边,算是陪它们,将瑶坤没有收拾净的枯枝捡起来,插进荷花盆。小瑶坤,下手那么狠,还能都剪了去?你是在欣赏枯败?快进来喝点啥?瑶坤再一次到门口喊米平。欣赏?米平蹲在盆旁扭头看屋里瑶坤,心里哼一声,但同时又想,一枝、两枝枯败与集体枯败,有什么区别?都枯败了,还有什么力量?还能取什么暖?自欺欺人罢了。
冬季,荷花盆中的水干尽,近乎结冰,银星小卖部的人会推来平板车,一人把车,多人帮忙,一二一二地将荷花盆挪到车上,推到房里一角,待春天冰雪消融时再推出来,在干裂的盆中灌满水,荷花渐渐冒芽、展叶、盛开、枯败,循环往复。这两盆荷花已养二十年,其间也换过土,重新清理过根系。
2
当年她喜欢荷花,脸盆大的叶子,绿油油,叶绿花艳,绿得真实,艳得奔放。卖花人说,这是绝好的一等荷花——大明湖荷花,放心养,泼实,放心看,一看千古。她满心欢喜,雇三轮车拉到商店,费力搬下来。米平看着它一个个枝叶绽出,从污泥中抽出洁净。它也静默地看着她,期盼着她来浇水与施肥。她们相互对着不懂的话。营养肥料中,有管枝繁叶茂的,有管根深蒂固的,当然,还有管花朵艳丽的。用洗净且锃亮闪光的贝壳布置在花盆的泥土上面,花盆也擦得锃亮,坐在荷花跟前,静待一切美好,像发家致富?像家和万事兴?像举案齐眉、白头到老?
有很长一段时间,米平特别苦闷,失魂落魄,六神无主。这是女人的特别时期,说是叫更年期。她不知道这是从30岁更到40岁,还是40岁更到50岁,抑或从50岁更到60岁……更是更了,心情却一直没有好。睡不好觉,吃八片安眠药也无济于事,黑天白天颠倒,恐惧,记忆力下降,忽而汗流浃背,忽而浑身打战,忽冷忽热,忽东忽西。很想大喊大叫,很想打人毁物。
她曾经多次失魂落魄地奔向父母坟前,苍天大地地悲歌一场,满腔浊气号出腔,长舒一口气,仿佛才又回过神来,回归人的模样。
或许一切都是嫁出来的毛病。婆婆家从农村搬来县城,他们租房结婚。后来他们说出,先租房后结婚,是娶儿媳妇,是媳妇到婆婆家,先结婚后接公公婆婆,是公公婆婆到儿媳妇家。年迈的公婆,有多么年迈呢?公公大她56岁,婆婆大她44岁,丈夫大她1岁。公公婆婆老来得子,供儿子念书确实不容易,她把他们看成爷爷奶奶。家里用15瓦电灯,灯泡尖顶,似一个核桃,散出绿油油的光,幽幽的,致使她不敢瞄一眼灯光,不敢在屋里行走,每次起夜,她都觉自己是一个幽魂,甚至怕自己吓着家人。每次做菜,公公会在跟前盯着,味素别放多了。每次饭快做好了,公公会艰难地右手放地上,右膝跪地上,左腿支棱,左手搭在左膝上,趔趄着身体,望锅底,看看煤是否烧靠。她生怕公公失重,就劲儿摔倒。为公公婆婆买一斤蛋糕,问多少钱?说是七毛四一斤,立即变脸,说西边小店七毛二一斤,赶紧退回去。乡下大姑姐到家里来,说邻居借塑料水管浇菜地,婆婆说:管头没刻上记号?别叫人截去。
他们是20世纪80年代末结婚,1992年,这个县城升格为县级市,在庆典那一天,婆婆将自己的金镏子拿出来,郑重其事送给她。那时,她的儿子已经3岁。在婆婆,可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她,仿佛至今才被认可。至今若干年过去,那个金镏子,她一直没有戴。时隔三年,那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啊。下岗后她做生意,营业执照竟是丈夫那边的亲属做法人。这种对别人的防范之想她没有,所以在屡屡遭到别人防范时,经年累月,五脏六腑以及思想受堵,话语少,不愿与人沟通。以至于内心灌满,卡到喉咙时,借机或是有个诱因,所有的不痛快会喷薄而出,可是,每次的喷薄都让她肝肠寸断,折腾得生不如死。
出嫁到另一个家族,真是一件困难的事,从一个家庭到另一个家庭,思想、行为、习惯都有差异,到一个陌生的境地,只认识恋爱中的男朋友,却将自己的身份置换给他们,由一个姑娘变成大奶、大婶、大嫂,去一个个应对兄弟、侄子、孙子,应对一家人的脾气、习性,得小心,得思考。不是自己纯粹实在就可以,不是自己把心掏出来就可以,得看那个时刻是否与他们同频,不然,掏出的心会无影无踪。与老人相处,挣工资交给婆婆;做小买卖时,80岁的婆婆在商店收款。这些都可以,她愿意把老人当爷爷奶奶对待。一个出生在海边小镇的米平,老觉得自己胸怀似海,老觉得自己能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做小买卖,叫下岗再就业。小店有一部公共电话,天天拿着BB机回电话的人多的是。只是很多回话的人,不是回给家里人,而是回给了外人:几点舞厅见,几点发廊见,几点饭店见,几点澡堂见……曾经的秩序乱了,在她看了别人的无序后,自己家也跟着无序。自己的男人呼也不回,不知男人所终了。她终于和丈夫也不同频了,这个家,没有家的滋味了。
不知男人所终,她找遍县城发廊、舞厅……她自己都不愿意进去的地方。挨门挨户进去,难以启齿!说家里丢了东西?羞愧感越来越盛。米平男人是念过书的人,其年迈父母抻断腰筋以砸锅卖铁之势供他读完中专,毕业后分配到县城林业部门工作。男人和她玩游击战,她转遍县城,从来没有找到他,或是他的眼线多,或是所有场所都是他的同案团伙?不知道。
她呆呆地坐在商店门口,常常点起烟,坐在门口吸,坐到太阳落,坐到月亮升,受风雨洗礼,任疾雷劈来,经年累月,她是小店的一座雕像。婆婆在小店里里外外一把手,俺儿可不是那样人,俺儿是读书人,就你瞎琢磨,俺儿要是,我头发丝儿吊死。婆婆恨恨地怼她。后来,当所有事实证明她儿的不是时,婆婆拍着桌子,命令一般道,家丑不可外扬。
一次,夜深人静,她往护城河去。路上的车疾驰与她擦肩,她无动于衷,丝毫不去躲避。路旁的高楼千家万户,闪耀着万家灯火,与她毫无关系。马路是东西向,护城河跨马路南北向,米平离开马路,顺护城河大坝慢慢往南面行走。这条河叫庄码河,曾经是庄姓人家的码头,当年渔帆点点,百舸争流,如今连庄姓的人都见不到,只留空名。靠近拦河橡胶坝时,她找地方坐下来。拦河坝再往前二百米,就是大海了。拦河橡胶坝是近年修的,用以蓄水,使这条河有个河的模样,因为上游水库蓄水,供大城市用水,这条河基本常年干涸,只有雨季有水。这条河是通海的两混水,经常没有水,难免臭烘烘的。地方领导有办法,修建拦水坝蓄水,河两岸修上景观,装上亮化,既免臭又观景,是县城人们饭余茶后的好去处。
深夜的河两岸,亮化工程隐隐约约,橡胶坝两岸没有高楼大厦,没有人家,映入水中的光亮飘飘忽忽。北面跨河马路上汽车穿梭,南面跨海大桥汽车穿梭,距离较远,听不见声音,虫鸣也没有,风声也没有,连空气都是丝滑的。渐渐地,在静谧中,她内心有些清凉的感觉,这么干净的夜晚仿佛治愈了她。一呼一吸间,她的心就紧凑,心神凝聚,心好像瞬间回归了该在的地方,魂魄在眼前飘摇,也一点一点附体,不再游离。天上,满天星光,星星的眼睛一眨一眨,像是在逗她。她多想有一双手拦她入怀,有一副肩膀供她依靠,有一个男人将她夸赞。都说,每个人都是顶星来的,那么,自己是哪颗星呢?
远处有光,不同于路上的车灯。一束光,晃一下绕走,晃一下再绕走,那光坚硬笔直,不散。她屏住呼吸,静静地坐在哪里,一动不动,观察那束不散的光。
那光渐渐靠近,在米平的不远不近处停下,因为是黑夜,她估摸不出距离。米平在草木掩映中蛰伏着,她自觉抬动下腿脚,不使腿脚麻木,扭扭腰,届时跑的时候别闪了腰。她摸索到身边一根尺把长的木棍儿,算是器械,放在身边,眼睛却时刻不离那束光的方向,看这“光”到底想干什么。同时手按住衣兜里的手机,又怕弄出光亮暴露自己,按着手机后背,可以随时掏出来拨打110。那年她40岁。
那光又往前靠近,直射她能有三四秒,移走,又前进,又移走。光射向她,米平本能地低头以防暴露。射向她的光又慢慢上移,在她头上悬着能有五六分钟,又住五六分钟,光在原位轻轻晃动,随后声音传过来:家去吧!家去吧!米平侧耳静听,听那光处发出的声音。我是护坝的,别害怕。这声音苍老。家去吧!孩子,家去吧!家去吧!光就对着她了。孩子,家去吧,家去吧,家里人不找吗?米平这才觉得是护坝人在说她。她埋下头双手护膝。孩子,起来,起来,家去,快家去!苍老的声音,节奏很慢,像爷爷的声音,像奶奶的声音,像母亲的声音,像父亲的声音,怕吓着她似的,苍老、慢且低沉,但是却坚定。她难以抬起头,怕别人认出她,又因为她已经泪流满面,那泪水一出,将一个刚才还刚性挺足的人瞬间抽去了筋骨,她泣不成声,她泪流满面。
是啊,她是父母的孩子。可是,父母已经离世,再也不能抚慰她,叫她一声孩子了。从没有父母那一天起,她已经脱了孩子皮,再也不是孩子了。家里人不找吗?家?家里人?家里人找?她找的就是家里人啊!家在哪里?她苦苦寻的就是家啊!
双眼藏了无尽的泪水,双眼是泪的出口,泪洒胸前,流向大地,深入庄码河。毛孔,是汗的出口,汗水也是泪水吧?血管流淌的血也是泪水吗?
腿都酸了。孩子,家去吧。苍老的声音又传过来。
她擦干眼泪,低头站起来,向光的方向拱拱手,她始终不敢抬头,怕护坝人认出她,就像做错了事儿,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她摸索转身,脚一步步踏稳台阶,上坝,沿坝向北移动。
那天晚上,她瓢泼的眼泪足以顶过她以往的哭号,因为在那么干净的夜晚,她不想撕破长空。那光跟着她走,她快,光快;她慢,光慢。老人怕吓着她,不靠近,只跟着她,但也绝不离开。硬是把她一步步逼出护城河外,逼上道路,逼回家。当她到家楼梯口处,再一次回头拱手,又一次泪流满面。
她谢谢老人,老人让她一步步回家。20年过去,那位善良的老人,她至今不知名谁,不识模样,但那束光却一直在心间亮着。
一个深秋,多年不见的男人出现了,着风衣架墨镜,刺棱头发,风衣忽闪。先到小店,如入无人之境,摘下墨镜翻抽屉,后到家里,翻箱倒柜,要钱。没有翻到钱,直接拽过米平,按沙发上,拳头挥过来,双手掐住米平脖子,钱呢?他面目狰狞,那双手仿佛镣铐,米平越挣扎越紧。米平昏死过去,魔掌松开。当米平苏醒过来后,一个姿势,躺到月亮升,躺到太阳落。丈夫,一个读书人,着了什么魔?
护城坝呀,跨河的护城坝!米平在坝上,南南北北走来走去。那天,天地昏黄,米平在昏黄的阳光下晃晃荡荡。她兜里有一张银行卡,里面只有三万元,是她几年省吃俭用攒下的。给了丈夫,自己分毫不存了,今后生活怎么办?不给,可能人钱俱毁;给了,可能会钱下留人。在坝上走了一天,米平决定还是给,留自己一条活路。交了卡,就等于缴枪投降。米平投了降,丈夫扬长而去。半年后的一天,来一群人砸门,必须交出房子,丈夫欠他们账,房子是抵押物。米平找到丈夫单位,回复早已辞职下海,此人与单位无关。报警,欠条写得分明。打官司告状,不等案子受理,米平已被人打得头破血流,并且被拘留起来,罪名是参与黑社会打斗。48天过后,米平放出来,但前提是签字还款,房屋产权移交。米平也有要求,必须签字离婚。
在万物竞绿的季节,米平将自己投进护城河,清除48天的屈辱,几十年来的憋屈。傍晚,月光下,一位光艳女人出水,长发飘飘,彻换衣物,洗心革面。
米平没有了房子,只在租来的小店坚持自己的营生。婆婆也搬到小店居住。婆婆愈发话少,一脸严肃。
米平常到护城河边走走坐坐,以舒浊气。后来,米平把荷花分盆,拿到护城河边种植。再到护城河边,便精心观看荷花。荷花长着长着,海潮上涨时,它向上游歪去,河水猛下时,它向下游倒去。不是湖塘荷花,掩起根部污泥,张扬着优雅。
一天,婆婆来到护城河,来到米平身边。米平平整一下草坪,掏出手绢铺好,让婆婆坐下。那手绢,是和丈夫认识时,元旦之际,丈夫给她的,红花绿叶,油笔篆书:米平元旦快乐!丈夫不在的日子,米平一直揣在兜里。米平坐下。婆婆眯起眼,指着荷花,这河有海水上来,我看的污泥浊水多了,不是有污泥的地方都适合荷花,饶了它吧。关于你的男人、我的儿子,有一句话叫,自屎不臭,自尿不臊。婆婆沉思着看米平,好久说,悟吧,拉我起来,咱们回家。
那之后,护城河干涸一段时间,阳光晒得河床龇牙咧嘴,污泥浊水死寂,臭味蒸发。又在那之后,护城河上游的滚子河像脱缰的野马,携带庄稼、牲口、房屋、树木,还有人,冲毁了橡胶坝,改道护城河,咆哮入海。海像佛,不容易,容纳万物。
一天傍晚,米平进货回来,婆婆躺在床上,人事不省。米平喊妈妈。婆婆费力地睁开眼。米平看见旁边两个空空的安眠药瓶,哭出声来。婆婆无力地说,我吃错药了,我们都吃错药了,对不起。婆婆走了,带着清醒,带着痛苦。米平多希望,在婆婆去的路上,阳光普照,没有羁绊。
3
早上,米平看到荷花盆结满冰,那两枝枯枝更加枯萎,还在冰中站立。近中午,阳光正好,敲开冰,喊几个人,掀荷花盆倒掉水,移到屋内。在捡起冰片时,枯枝粘在冰上面,被人一同撇远,枯枝根系早已腐朽,在冰的挟持下,还狐假虎威地站着。如果冬天一直不移挪室内,不知道那枯枝还能装模作样挺立多久。米平矛盾重重,不知道心痛它的孤独,还是蔑视它的腐烂。
荷花盆底沿靠近小卖部墙的地方,在条石夹缝中,生长着一株植物。阔叶,像瓜叶,又不是,看茎,又像是木本。八片阔叶,高茎四寸,生机勃勃,它在夹缝中生存,在背地里生存。面对冬季来临,面对保护它的荷花盆要移走,米平对它真是无能为力。仅一个夜晚过去,那个“生机勃勃”便已僵硬,它在寒冷中死亡,叶片生绿,木本四寸茎秆依然挺立。但愿春天到来时,还它以生命。可是,它在夹缝中,能生存多久?
这才几天,到了农历十月初一寒衣节。瑶坤说,她要去祭奠丈夫。米姐,你也去祭奠下婆婆吧。
米平先来到父母坟前,带来20束鲜花。这块墓地有19位先人墓,加上山神庙,每样贡品都是20份。当然,祖宗的其他子孙也来祭拜。各献各的礼。
近年,祖宗的子孙寻祖,米平才知道她是闯关东第五代人。第一代祖宗闯关东落脚英那河畔,给人家看山,死后便葬在山上,这座山叫平顶山。闯关东的哥儿仨,现在已经繁衍千余人。祖宗的子孙将宗谱上一世祖及闯关东哥儿仨与二代、三代祖宗墓地重新修整,有子孙家中墓地不合适的,也迁到此处,与祖宗一起。
米平家从小镇下乡,她的爷爷奶奶家也从小镇下乡,但是居于两地。爷爷去世时,是60年代末,伯父还没有“摘帽”,伯父悄悄把爷爷葬在自家自留地里。等米平母亲去世时,她们家已经来到县城,要去爷爷奶奶墓地安葬,爷爷奶奶墓地附近已经建成养鸡场,并且所在地也不允许外来人下葬,不管是否父辈、子辈。于是,米平的母亲另找安葬地点,当她父亲去世时,与母亲葬在一起。原来米氏家族近百人居住在一起,合力做生意,开诊所。时光把很多事情重新排列组合,把米氏家族生分开,死也分开。好在,随着时光进程,又让米氏家族寻到一世祖,米平把爷爷奶奶及父母墓地都迁来与祖宗一起。这才几天,才五代。
从山神庙、从一世祖开始,米平一一摆上鲜花,一一上香、压纸、洒酒。她坐在墓前,任冷风刮过。先祖从山东海阳县漂洋过海,几代人过去,在先祖面前,一排排墓碑竖立着。
她一遍遍跑到父母坟前号啕时,父母的坟就孤零零在一片山坳中。父母是否也没有找到父母,也没有找到根?现在一片墓地中,父母们找到了父母,他们安详了吗?先祖安详了吗?闯关东一世祖,更是孤零零地在当年闯关东落脚的平顶山,看子孙四散求生。先祖们是不是更有理由汹涌号啕,号啕他们跨海的艰辛、生存的艰难?如今,先祖们怀抱部分子孙,是团圆了,心满意足了,还是会再带着他的子孙寻找回家的路?
今年冬季来得突然,平顶山满目绿意,树木没有来得及进入秋天,转身直接入冬。人也在突然到来的季节中不知所措,夏天衣服没有收藏,秋季衣服没有上身,直接加棉袄,加厚棉袄,以御寒冷。
大风中,山林哗然,绿意荡漾。天气还会转暖,等太阳出来时,那些摇摇晃晃被冰雪覆压的树枝也会得到舒展。
米平没有去婆婆的墓地,不顺道,她想明天去。米平进小卖店前,习惯跺去脚上的尘土。今天去山上,她格外拍拍身,拍后背时,显得无比吃力。她笑自己也老了,这才几天。
瑶坤回来早,推开门,迎接米平进屋。看看,过来看看,她拽米平到荷花盆前,荷花盆一片新绿。蹲下看,原来不知何时,盆内生出一层红花酢浆草,倒心形的叶子,长满了一大盆“心”。她小时候下乡时跟村里小伙伴吃过,微酸,进嘴酸味儿直抵舌根,她们叫酸立久或是酸立囧。
她想让它们见阳光,便和瑶坤合力移动花盆,把它移到门口光线能照射到的地方。
阳光下那盆荷花,染了一层金色。
作者简介>>>>
周美华,庄河青堆子人,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庄河市作家协会主席。大连庄河市晴籁书院《庄河记忆》负责人。
[责任编辑 陈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