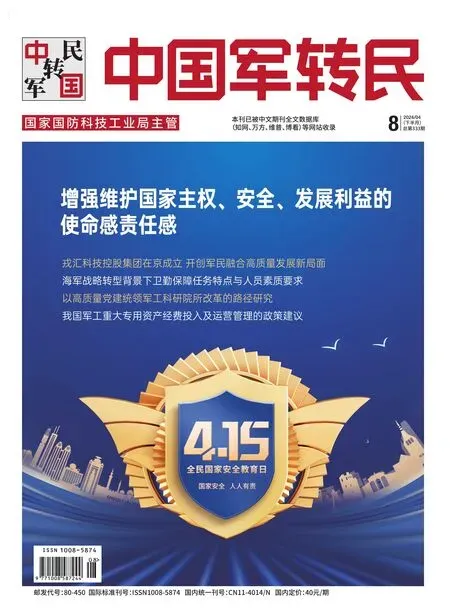建构主义视域下的巴以冲突动因研究
李宁
一、问题的提出
2023 年10 月7 日,哈马斯和以色列爆发了新一轮冲突。10月7日早上6点30分,哈马斯向以色列境内发射大量火箭弹,同时,大批哈马斯武装人员通过滑翔伞等方式进入以色列境内,同以色列军民发生激烈冲突。10 月8 日,以色列宣布国家进入战争状态。据相关报道,截止至2024 年1 月,本轮巴以冲突约造成23000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本轮巴以冲是自1948 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以来烈度最高、伤亡程度最大的一次冲突。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透过2023 年10 月的巴以冲突,反思巴以冲突的动因是什么。本文研究的并非某一次巴以冲突的动因,而是具有抽象概括意义的巴以冲突行为取向的动因。而本文根据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设:巴以双方长期存在互动,在互动中彼此产生消极的认知,双方产生了共同的观念,即巴以双方互为宿敌。而这个共有观念又决定了双方的行为,让双方爆发冲突。
研究这个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从现实意义的角度看,巴以冲突是威胁中东局势稳定的重大议题,然而中国在中东地区有重要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经济上看,中东地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枢纽,阿拉伯国家也是中国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而从安全上看,中东是伊斯兰教的核心地带,而中国西北地区有大量的穆斯林聚居,中东局势对于中国西北部的安全形势有重要影响[1]。那么,正确认识并妥善处理巴以问题服务的是中国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
而从学术意义的角度看,本文或有助于改进巴以冲突既有研究的问题。巴以冲突既有研究的主要问题在于变量过多、难以分类和忽略整体。而通过建构主义解释巴以冲突,可以把所有的自变量统合为一个“不良互动”,而曾经作为自变量的历史、宗教、领土、地缘等因素只需作为案例,证明巴以的不良互动和负面认知即可,而不必去纠结这些因素之间是否有重叠部分,那么,解释框架将会相对简约。
二、既有研究回顾
学界对于巴以冲突的既有研究主要从历史、实际利益、宗教、地缘政治、情报等几个角度解释巴以冲突的动因。
第一,从历史的角度。这种观点回顾了1948 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同巴勒斯坦进行的几次中东战争,并回顾了1987 年哈马斯组织成立,1993 年奥斯陆和谈协议,1995 年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以及2008 年-2021 年巴以双方多次交火等事件,最终得出了巴以冲突主要是因为巴以双方长期对立,积怨颇深的结论[2]。
第二,从双方实际利益冲突的角度。这种观点指出,巴以双方在领土、水资源等问题上存在尖锐冲突。以色列建国以后,经过五次中东战争,巴勒斯坦人所掌握的领土越来越少,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3]。此外,双方对于约旦河的开发和地下水的开采也存在争议[4]。
第三,从民族宗教纷争的角度。这种观点认为,巴以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宗教纷争,圣城耶路撒冷同时是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地,各方关于圣城的归属问题斗争已久[5]。
第四,从大国地缘政治的角度。这种观点认为,大国干预是巴以冲突的主要原因。大国干预主要体现在英美两国支持以色列独立建国,也体现在美国在911 恐怖袭击和伊拉克战争后对以色列的偏袒庇护。
第五,从情报的角度解释巴以冲突。这种观点认为,本轮巴以冲突是因为以色列情报部门失职,对哈马斯关注不够,进而给了哈马斯主动进攻的机会[6]。
学界对巴以冲突的既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变量设置过多而不够简约。从历史、民族、宗教、领土、地缘政治等方面分开解释巴以冲突的动因固然囊括了所有的解释变量,但是既有研究没能解释究竟哪个变量是巴以冲突的主要动因。第二,变量之间存在重叠部分。巴以问题背后是错综复杂又彼此纠缠的政治、经济、文化动因。例如,大国地缘政治也可以算作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关于圣城耶路撒冷的宗教纷争既可以归纳到历史层面,也可以算作领土争端。因此,这些动因是难以分类归纳的。第三,从情报失灵的角度解释巴以冲突,存在的问题是对细节重视过度而忽略整体。换而言之,这种观点没能做到透过现象看本质,仅仅把2023 年10 月巴以冲突的动因解释得较为透彻,对于几十年以来长期存在的巴以冲突动因却分析较少,所以这种观点并未给出具有一定普适价值的理论体系。
三、建构主义的理论分析框架
建构主义兴起于20 世纪80 年代。该理论的思想渊源可以从社会学、语言哲学、国际关系理论等多个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找到[7]。
首先,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有涂尔干、韦伯、吉登斯、米德等人。这些社会学家所研究的几个研究问题为建构主义提供理论基础。涂尔干和韦伯对于“社会世界是否与自然世界存在差异”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前者持一元论的观点,后者持二元论的观点。吉登斯的研究议题则为“社会结构与施动者的关系”。吉登斯认为,社会结构与施动者存在二元性,两者同时存在且相互建构。而米德主要研究的是社会互动,米德认为,有意识、有意图、有意义的符号互动造就了自我的身份和利益。
此外,语言哲学也为建构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索绪尔对罗素等人所提出的“语言结构等同于现实结构”和“图像论”提出了质疑。索绪尔开始研究语言的意义。此外,奥斯丁和维特根斯坦等人则研究语言的实践。他们认为,语言的意义和语言的参与者、语言的规则密切相关,语言本身也是一种互动行为。那么,语言的意义并不是先验的,而是通过主体间理解达成的。
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也为建构主义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例如,英国学派强调国家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单位,会受到国际法、国际规范和制度等非物质因素的制约。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强调通过领域扩展实现合作,其实就是在强调互动的作用,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理论也强调了非物质和非结构因素对国际关系的重要性。多伊奇的沟通交往理论则强调通过互动实现认同,进而塑造安全共同体。
那么,通过在社会学、语言哲学、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汲取营养,建构主义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基底。本体论方面,建构主义强调物质和理念。认识论方面,建构主义强调说明和理解。而在方法论方面,建构主义强调解释和实证并用。总之,建构主义是一个大的理论范式,是反思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桥梁。而建构主义内部又分成很多不同的派别,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有派别的共同特点。
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有以下几点。
第一,什么是社会事实。社会事实虽然离不开物质本身,但是也离不开对物质的诠释和理解。而对事实的理解源自实践互动。换而言之,社会事实和自然事实并不一样,自然事实完全一成不变,而社会事实是可以随行为体的互动而变化的。例如,无政府是国家造就的而非一成不变的,可能存在霍布斯体系、洛克体系和康德体系多种模式[8]。总之,建构主义认为,物质和观念是紧密联系的而非二元对立区分的。
第二,施动者和结构的关系。理性主义认为施动者和结构存在因果关系,建构主义却认为施动者和结构是互构的关系。“互构”不同于因果,因果中的“因”和“果”存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而互构的双方没有时间先后,两者同时进行。此外,建构主义所指的结构,不是权力结构,而是一种共同的观念结构。那么,国家是国际政治的行为体,可以视为施动者,而国家对自身身份的界定则是观念结构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国家通过互动产生对彼此的认知和对自身身份的界定,而认知和身份又影响国家之间的互动模式。总之,身份和互动是同时进行的。
第三,观念的作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观念,是指一种共有的文化,国家对自身身份的界定以及对其他国家的定位认知都属于共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对自身身份的确定的结果是国家对利益的界定,而对利益的界定决定了国家最终的行为。
总之,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在于,施动者之间互动通过交往产生了对彼此的认知,而彼此的认知在互动中不断加强,最终形成共有的观念结构。观念结构决定了施动者对利益的界定,进而决定行为。那么,本文的研究假设在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长期互动,但这种互动是负面消极的。在互动中,双方对彼此产生了负面的认知和对彼此身份的认定,即巴以双方互为敌人。那么,双方对彼此的利益界定就是打击消灭对方,所以双方会爆发武装冲突。.
四、案例验证
(一)巴以在水资源问题上的负面互动与认知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是极度缺乏水资源的国家。据统计,巴勒斯坦地区的人均用水量远远低于周边的黎巴嫩、叙利亚等国家。巴勒斯坦地区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地中海气候,夏季炎热干旱,冬季凉爽湿润,这种恶劣的自然气候决定了巴勒斯坦的一大特征就是缺水[9]。而以色列同样也是水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据统计,以色列境内大部分土地为半干旱或干旱,可耕地和地表径流极为稀少。而且,过度开采使得以色列境内的地下水含盐度高难以利用。所以,以色列目前可利用的淡水资源非常少,目前以境内可供使用的水资源仅为约旦河和一些含盐度较高的地下水。而按人口来算,以色列人均水资源量仅为全球的33 分之一,尚不到400 立方米[10]。巴以双方均为水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水资源的稀缺也成为巴以双方在水资源问题上恶性互动的一大先决条件。
那么,巴以双方在水资源方面的消极互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强行掠夺巴基斯坦的水资源和土地。例如,在1948 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就强占了联合国分治决议中规划的巴勒斯坦土地,并且将约旦河西岸60%的水抽离。第二,在用水方面采取双重标准对待境内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例如,1967 年,以色列当局曾颁布92 号军事命令,该命令将水资源列为以色列的战略物资。命令中,巴勒斯坦的用水量被严格限制,从1967 年到1978 年,巴勒斯坦人仅被允许打5 口浅井,而犹太人则打了35~40 口300~500 米的深井[11]。而在水价方面,犹太人可以以相对较低的价格购买到生活用水和农业用水;而巴勒斯坦人每年支付的水费却是以色列的15 倍[12]。可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水资源方面的互动是一种恶性的互动。
而巴以双方在水资源对彼此的认知也有如下表现:双方通过负面互动,确定了自身“水资源争夺者”的身份。以色列总统佩雷斯曾经表示:“有了水你可以操纵政治,有了土地你可以发动战争。”而巴勒斯坦水利委员会主席沙里夫也曾表示:“我们已经处于非常糟糕的境地,除非美国尽一切可能说服以色列,如果没有水,绝对不可能有和平,巴以和平协议的寿命绝对不会超过两年或三年”[10]。可见,巴以双方在水资源问题上的负面互动中产生了对彼此的负面认知,这种负面认知逐渐形成了共有观念:巴以双方在水资源问题上互为敌对,必须争夺水资源。那么,巴以冲突这一行为也就不难解释了。
(二)巴以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负面互动与认知
耶路撒冷位于约旦河西岸,是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圣地。耶路撒冷曾经被古以色列的大卫王设为都城,但是后来长期处于穆斯林的控制之下。19 世纪后期,犹太复国运动开始兴起,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开始有组织的迁居巴勒斯坦。但是,狭小的耶路撒冷老城容纳不下数量巨大的犹太人,因此,很多犹太人就在耶路撒冷西面建房定居,这个定居点被称作西耶路撒冷或耶路撒冷新城。而耶路撒冷老城被称作东耶路撒冷[12]。基督教和犹太教均将耶路撒冷视为圣地,犹太教认为,耶和华开天辟地的第一道光就是从耶路撒冷射向全世界的,上帝所创造的第一个人亚当所用的土就是耶路撒冷的土;而伊斯兰教认为,穆罕默德曾在耶路撒冷接受了天启,他曾示意,到耶路撒冷朝圣一次相当于在其他清真寺祈祷500 次[13]。
在耶路撒冷问题上,巴以双方的互动都是伴随流血冲突的消极互动。在1967 年的六五战争期间,以色列用武力夺取了整个耶路撒冷并将其作为首都。1967 年以后,以色列为了加强对耶路撒冷的控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以色列从外观上改变了耶路撒冷的原貌,破坏耶路撒冷作为世界三大宗教共同圣地的地位[12]。例如,以色列在占领东耶路撒冷以后,为了恢复犹太区,将200 多户阿拉伯人赶走;此外,为了便于犹太人祈祷,以色列将“哭墙”附近阿拉伯人的房屋全部拆除,这些举措使得大量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另外,在以色列政府的鼓励和纵容下,一些极端的犹太教徒曾经偷运炸药,意图炸毁圣殿山上的阿克萨清真寺。1990 年,大批犹太教狂热分子利用“结茅节”聚集在哭墙下向穆斯林挑衅,以色列军警却开枪镇压穆斯林,酿成了22 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的“圣殿山惨案”。
在这种负面互动下,巴以双方对彼此的认知必然也是消极的。例如,1988 年,特拉维夫大学曾经在以色列国内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当问到是否要将东耶路撒冷交给阿拉伯人时,98%的以色列人的回答都是否定的;此外,耶路撒冷的前市长科勒克也表示,统一的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的首都是不容谈判的[12]。而巴勒斯坦方面在巴解组织的《独立宣言》中也表示,巴勒斯坦国的首都“阿拉伯耶路撒冷”,阿拉伯民族不允许在耶路撒冷圣城问题上发生任何争论。
总之,在耶路撒冷问题上,巴以双方的互动是负面消极的,他们在认知层面也各自认为对方是耶路撒冷的权利是非法的。那么,巴以冲突也就必然爆发了。
(三)哈马斯和以色列的消极互动
哈马斯和以色列的消极互动可以作为巴以冲突的一个经典案例。中东战争使得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而在1964 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正式成立,哈马斯是巴解组织的一个分支,正式成立于1987 年。该组织强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反对世俗化,拒绝同以色列妥协,对于1993 年的阿以奥斯陆和平协议也坚决反对;该组织还主张通过暴力手段来恢复巴勒斯坦的领土[14]。此外,哈马斯曾于2006 年进入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参与立法,进而于2007 年控制了加沙地带。
哈马斯和以色列的负面互动可谓由来已久。自从哈马斯1987 年成立以来,一直同以色列频繁爆发流血冲突。1987 年哈马斯组织成立之后,就频繁向以色列发动袭击,作为报复,1989 年以色列逮捕了包括哈马斯创始人亚辛在内的多位哈马斯领导人物。2000 年,随着阿以和平协议的破裂,哈马斯组织多次以自杀式人肉炸弹的方式袭击以色列。2007 年,随着哈马斯对加沙地带取得控制,以色列立刻宣布哈马斯为敌对势力并采取了断水断电、禁运和关闭边境等一系列制裁行动[14]。因而哈以双方在2008 年12 月再度爆发武装冲突,此次冲突双方的伤亡人数在100 人左右,此外,冲突使大批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2014年,三名犹太青年在约旦河西岸失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声称哈马斯诱拐了这三名青年,以色列军队随即擅自进入约旦河西岸进行搜查,逮捕了上百名他们认为可疑的巴勒斯坦人,其中也包括多名哈马斯领导人,哈以双方随即再度爆发冲突。2018 年,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民众向以色列境内投放气球和风筝进行抗议,以色列随即出动军队,打死打伤多名巴勒斯坦民众,哈以双方再度爆发冲突。2021 年,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进行突袭,哈以双方因而爆发了为期11 天的激烈交火[15]。总之,哈马斯和以色列的互动基本上是以流血冲突的形式展开的。
而以色列与哈马斯双方对彼此的认知也是负面不良的。1988 年,哈马斯曾发布一份宪章,宪章中曾提到:“巴勒斯坦是穆斯林的祖国,因而哈马斯绝对不会向非穆斯林投降,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应进行圣战,将巴勒斯坦从以色列手中夺回来,这是巴勒斯坦穆斯林不可推卸的宗教责任。”2017 年,哈马斯领导人曾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发布一份新的纲领文件,这份文件强调,哈马斯拒绝承认1993 年《奥斯陆协定》的合法性,也拒绝认同国际社会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武力仍然是实现巴勒斯坦解放的唯一方式;对此,以色列方面也做出了回应,内塔尼亚胡表示,作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拒绝承认以色列国家的存在,此举是在愚弄世界,也不会得逞[16]。2017 年,哈马斯的领导人辛瓦尔曾经表示:“巴勒斯坦同以色列和解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如何将以色列彻底抹平”[14]。通过上述证据,可以看出哈马斯和以色列双方经过长期的负面互动,双方对彼此的认知也是十分负面消极的,“互为敌对”已经成为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共有观念,那么,哈以双方的严重冲突也是必然爆发的了。
五、结语
巴以冲突的背后动因涉及到政治、领土、历史、宗教文化等多方面原因,矛盾纠葛错综复杂,很多议题都同时包含着多重原因。因此,分门别类整理巴以冲突动因会使框架解释力不足。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借鉴建构主义的解释框架,将所有原因统合为巴以双方存在长期的负面互动,在长期负面互动中,双方建构了“巴以双方互为敌对”的共有观念,那么,这种共有观念会决定巴以冲突的行为。在案例选取方面,只需一些可以证明巴以双方负面互动和负面认知的案例即可。而在本文的基础上,有一些问题可做进一步研究。例如,以色列日前对拉法口岸展开军事行动,哈马斯一时难以招架,那么,巴以冲突的前景发展和影响是什么?此外,既然建构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和共同观念是可以变化的,那么巴以局势能否通过观念变革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