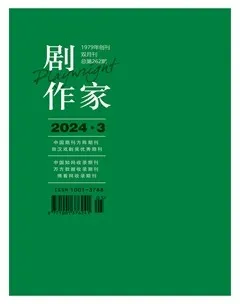明清拟男剧中女性之梦的梦情解读
李安琪
摘 要:《繁华梦》《梨花梦》《鸳鸯梦》三本剧作直观呈现出女性人物在现实中女扮男装、在梦中转女为男、由仙子谪仙为男的三种叙事模式[1]P123。本文将从主人公“出梦情感”这一角度进行文本细读,分析剧作之间出梦情感的差异性及两性梦境叙事的区别之处,剖析女性剧作家在梦境书写中的真实内心世界和精神理想。
关键词:明清;拟男剧;两性梦境;叙事模式
在明清女性戏剧作品中,女性作家的梦大多以自身的生活经历为蓝本。由于封建礼法的束缚,女性无法在现实中表达自我,只能借助戏剧作品的“梦幻”形式和“拟男”的性别错位叙事来抒写情志,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剧作家在封建专制时代对性别的反思。
一、拟男剧中“梦境叙事”之差异性
剧作家借助梦境表现主题的手法由来已久,女性作家无法挣脱性别和社会的枷锁,只能在出梦后继续将自己困于牢笼之中,选择回归悲剧现实。《梨花梦》《繁华梦》《鸳鸯梦》等几部拟男剧中主人公在梦醒时分的感慨,看似“播道”的背后,实则反映出明清女性剧作家在寻找自我出路和情感知己问题上的迷惘。
(一)出梦场景不同
为了更好地抒发情感、刻画人物形象,剧作家往往将梦境设置在特定的环境中,更有些剧作注重现实与梦境的对比,强调虚与实的意境转换,借现实的悲怆凸显梦境的美好。
《鸳鸯梦》的第一次入梦,场景设置在凤凰台莲花池旁,“前面高台陡峭……你看莲花池畔有鸳鸯一双,游戏于莲蕊之间”[2]P5几句唱白勾勒出梦境景象,其中凤凰台、并蒂莲花、鸳鸯构成梦境的重要意象。“凤凰台”作为梦中与现实两次出现的场景,具有从梦境延伸到现实的嫁接作用,蕙百芳出梦之后登临景色,遇见凤凰台,“恍与梦中相似”,同样的环境,引出了两位好友的上场。
《鸳鸯梦》的二次入梦是蕙百芳一人的独角戏,时间跨度从夜幕降临到天将破晓,长达一夜,环境上又以“今夜萧萧暮雨窗前逗,直恁的凄凄戚戚添孱愁”渲染其心境之悲苦[2]P15。在这孤独的秋雨之夜,蕙百芳独自睡去,梦中与琼公几句简短的对话后被猛地惊醒,铁马声嘶、家中孤灯冷落更令他心灰意冷。一系列抒情意象看似在营造环境,实则在场景的描绘中暗含蕙百芳的人生之感[3]P20。
《繁华梦》中的主人公王梦麟入梦和出梦都发生在家中书房。因读书无趣,王梦麟展开吴中美人图阅览。阅完美人,他俯身卧眠,善才童子将其变形为男子身份,采取了“在梦中转女为男”的叙事模式,开启了梦境中的人生历程。“省旧”一出,王梦麟独坐书房,“恍惚神魂散……揣心头似续还如断”,已有梦醒迹象,回顾一生,有了“猛想起这二十载的富贵荣华也,怕做了一枕邯郸午梦酣”的感悟,继而醉酒入眠,才有了后文的“出梦”。王梦麟从梦中惊起:“哎呀,好奇怪啊,这是什么所在?我方才身在书房,怎么得到此处?看此情境,竟是闺阁中的光景了。”虽同在书房,但王梦麟的身份已从极为富贵的官臣变回了初出闺阁的少女,梦境与现实的割裂让人一时无法承受。
《梨花梦》中的杜兰仙是在“问东风,心事知么”的困倦情思中入眠的。“原来有只小舟在此”,从梨花仙子口中透露出了第一次入梦的场景和现实中杜兰仙身处位置相似。现实中的杜兰仙一路风餐露宿,在“春色阑珊”之际扮为男装在湖上扁舟小坐,这里采用的是“现实中女扮男装”的叙事模式。恰好梦境中的地点也是一只小舟,但杜兰仙却在梦中小舟上遇见了知己梨花仙子。环境的相同让梦境更具真实感,也让杜兰仙得以展示才华。梨花仙子开口道:“今因梨花欲落,春色将阑。”此处的“梨花欲落”“春色将阑”表明此刻已是春残花落之际,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都处于怡情伤春的背景中。交谈甚欢之际,梦中小舟响起橹声,杜兰仙却“惊魂交错”在现实扁舟上醒来,仿佛梨花仙子刚刚离开,梦中场景和现实交叠在一起。
在“仙会”一出中,杜兰仙病妆出场,在她眼里,自己似“樊笼之病鹤”,于是杜兰仙“作倦态入帐卧介”,屡次尝试小憩入眠,最终再次以“入梦”的形式和梨花仙子、藕花仙子相会。两次相会虽都是在梦境中,但所处环境却大不相同。第二次梦境转移至琅嬛仙境,不仅营造出前文梨花仙子提到的“点化”环境,也更像是杜兰仙找寻到了在现实生活一再压抑下的精神寄托。可惜晓钟响起,杜兰仙在帷帐中被惊醒,万般无奈。
(二)出梦心境不同
《鸳鸯梦》在“仙子谪仙为男”的叙事模式中,让主人公蕙百芳两次入梦。从入梦前寻找心灵慰藉、梦中并蒂花开的隐喻到此处游历美景无人在侧的孤寂,蕙百芳对知己好友的期盼情绪层层叠加。第二次入梦恰逢八月中秋这个举家团圆的特殊节日,却下起了夜雨。蕙百芳二次入梦,“昨宵一梦甚蹊跷”,紧接着下文就交代了“蹊跷”二字的缘由:蕙百芳夜梦琼龙雕,琼龙雕长吁短叹,正当其开口细说时,蕙百芳便被惊醒,诧异已遣人询问琼公病情,听闻好转,为何有此一梦?“不知他凄凉病未消,还是我魂梦多颠倒”一句点出蕙百芳此刻魂不守舍,担忧好友病情的心急如焚。情绪还未消解,就收到了小厮传来的琼公半夜骤亡的噩耗,蕙百芳惊呼:“兀的不痛杀我也!”梦境的预兆显现出来,梦中情感和现实情感相互交叠,在此刻到达高潮“蓦地人惊到,顷刻魂也飘……摧残刎颈交”。两场梦境环环相扣,一虚一实,却都指向好友生离死别的悲惨结局。
《繁华梦》用将近二十出的篇目构建了王梦麟的梦境,到“省旧”开始出梦。王梦麟大梦醒来,“生急立起,叫介”“作呆状,四顾,忽惊介”“起身四望介”“看自身惊介”“作闷倒介”,一连串的肢体动作足以透露出其难舍梦中繁华,难信一切化为泡影,如痴如醉。王梦麟先是慢唱“梦迷离,神颠倒,猛惊回,魂魄飞摇”,对于美梦的破灭,王梦麟一时无法接受,“可惜我二十年的爱眷,竞逐浮云空矣”,其声泪俱下“只落得怨气冲霄”,句句唱词充满了对佳妻美妾的不舍与思念。王梦麟拍桌痛哭,情绪再次登上顶峰,“则被这案上诗书误了我也”掷砚笔、拍书的动作透露出王梦麟的一点哀怨,怨这一场梦是虚无荣耀,即使对人言说,也無人相信。到“出梦”的结尾,王生都无法接受现实,对理想的不能实现心有不甘,他羡慕汤显祖笔下的淳于棼、卢生能够迅速了解尘缘:“慕淳于境迢,羡卢生入道……做一个天荒地老的痴情稿。”王筠用了一出的笔墨来抒发王梦麟的失落感,他是到“仙化”中被麻姑点化后才有所醒悟。
《梨花梦》的主人公也是两次入梦,第一次入梦因“春色将阑,不忍负此幽芳”,杜兰仙与梨花仙子惺惺相惜,也为下文杜兰仙的忆梦成痴做了铺垫。这样的相谈甚欢在出梦后便更显凄凉,杜兰仙醒转叹道:“原来一梦。回想先时光景,好不凄楚人也。”赠花之后,杜兰仙对梨花仙子的相思更进一步,“只留下一点苦相思”。从“忆梦”到“悲秋”,都是杜兰仙在梦中和梨花仙子相遇相知后的情感宣泄,“茫茫人海,欲觅一知音如梦中人者,正不易也”,对知己之人的渴求让她日夜希望“重逢梦里”。
杜兰仙与梨花仙子的难舍难分推动情节发展走向高潮,对于杜兰仙而言,“就是富贵繁华,亦不过空花幻影”,她平生所愿就是再见梦中仙娥。第二次梦中,杜兰仙重回琅嬛仙境,一扫倦怠之气:“待我登绝顶,将平生意气摹想一番。”分离在即,杜兰仙被钟声惊醒,先是感叹“啊哟!原来一场好梦”,可不正是这一场好梦达成了她与平生知己再逢梦中的心愿?杜兰仙后又落寞下来“似我与两姊正在叙会,又被晓钟惊觉,倍觉凄凉”,但因一己情怀已经寄托于空幻的仙境世界,杜兰仙并没有过于沉溺在悲伤春秋中。
(三)出梦结局不同
《鸳鸯梦》第四出中的解梦之语让人恍然大悟:“只因尘梦未消,暂尔被谪人寰,使他离而合,合而离,显示一场春梦……人生聚散,荣枯得失,皆犹是梦,奇游真相乎?”蕙百芳经历了生离死别,参透了世事无常,经过吕洞宾的指点,只求升道解脱。叶小纨用“明日个众仙班齐列在瑶池上”的仙化结局为蕙百芳换得知己再会“今已后同登碧落,共渡悲航”。身为女子,即使是天上仙女,归宿也只能是重回仙班,历经的男子的一生不过是人世间的一场梦罢了。
《繁华梦》的“仙化”中,王梦麟带病登场,“急煎煎梦去无踪影,底事难追省”,此刻的王梦麟依然沉浸在出梦后的苦闷中无法自拔,日夜悲思,而他的一举一动依然是男子气概,全无女子神态。麻姑出现后,王梦麟仍悲悲啼啼:“可惜我半世功名,一生爱眷,就是这等罢了。”麻姑点破主旨:“恁看这世间真荣华富贵,亦不过野马浮云,谁保百年长在?况空虚幻境乎!”且告诉王梦麟梦中那班人物“皆因汝之一念”,王梦麟才有所顿悟“没来由为生为死,可不羞死人也”。而当他想要拜师时,麻姑却说:“这却早哩。尔今痴念难消,尘心未净。待你见性明心之后,吾当引汝超凡也。”卢生能够被点化入道,而王梦麟却只能回归现实生活,独自“见心明性”,思索人生的意义。“女和男一样须回省”是更沉重的悲叹,人生无常,世事瞬变。
《梨花梦》里的杜兰仙出梦后很快大彻大悟,进行了冷静的思索:“浮生幻影原如电……分不出女和男同一现。”以人生无常来安慰自己情愿难偿。杜兰仙之所以如此迅速地参透出梦之道,更多的是因为和梦中的梨花仙子再次相见的执念促使杜兰仙第二次入梦,在梦中和两位姐妹重逢,于她而言,执念已经得到满足,在梦中实现了愿望,她不需要升天仙化的虚幻结局来自我排遣,更能勇敢地面对现实。
简而言之,梦境的塑造承载着剧作家和笔下角色对现实生活的逃避和对理想世界的追寻,梦醒后的结局也与作者追求自身心灵的超脱相呼应。
二、两性梦境之叙事异同
男女两性的戏剧作品中所创造的梦境背后,大多预示着明清时期男女两性剧作家不同的内心渴求和精神困境。《邯郸记》和《繁华梦》作为男女两性作家创造的“人生之梦”,揭示了汤显祖和王筠所代表的男女两性各自的现实欲望和困境[4]P180。
《邯郸记》第二十九出,卢生要求夫人“和俺解了朝衣朝冠,收在容堂之上,永远与子孙观看”。此处卢生自主脱下官服,想让妻子放置在牌位前供后代供瞻,可见其对权力的留恋及痴迷不悟。《繁华梦》出梦之前,王梦麟是在睡梦中被妻妾脱下官服的,其梦醒之后与卢生的反应一样,都是寻找妻子、官服,这两个意象亦代表着王梦麟梦中最重要的东西:家庭美满、仕途风光。但二者相比,王梦麟更为不舍的还是圆满幸福的家庭和陪伴左右的妻妾,因此王梦麟并没有如卢生那般不舍仕途和荣华富贵。卢生出梦前并没有预兆,他临到死期仍痴而不悟;王梦麟出梦前已有预感“揣心头似绞还如断”“猛想起这二十载的荣华富贵,怕做了一枕邯郸午梦酣”。王梦麟身为女子,所见所闻有限,她对于建功立业并没有太多渴望,只是认为通过科举考试满足家族愿景,获得美满幸福的家庭,无论是科举还是官位都是为家庭生活服务的。因此王梦麟在出梦之前感叹:“本是个着裙钗……又何必拜相荣封侯。”王梦麟虽然自命不凡,但更多的是期盼有个和谐美满的家庭,她对于功名利禄相对于卢生而言并没有那么难以割舍。出梦之后,王梦麟的那句“可惜我二十年的爱眷”也足以见得王梦麟更为不舍的是夫妻和谐和家庭幸福。
《邯郸记》中卢生是由崔氏引其入仕,又让崔氏“去生须,拍生背”,令其梦醒,首尾相接;《繁华梦》里,王梦麟在书房观看美人图入梦,又由妻妾脱下官服后在书房出梦,解决了妻妾去处问题,亦首尾相接。但是《邯郸记》中的“崔氏”一角更像是一种符号,代表着传统社会秩序下相夫教子的女性。从崔氏是由卢生的坐骑“驴”幻化而来就足以看出汤显祖对她的人物设定就只是以扶持卢生作为自身价值的实现。而《繁华梦》通过梦境中王梦麟“转男—出游—高中—建功立业”的二十年生活历程实现了与现实自身地位身份的对调,创作者在梦境的情节发展中把人物命运交代给了观众,可以说,王梦麟的美梦代表了千万个同时代女性的理想愿望,从她的抒写中可以看到女性细腻的内心情感世界。《繁华梦》没有对王梦麟的仕途浮沉过多着笔,却将聘娶胡黄二妾及婚后一妻二妾的生活细节描写详尽。王筠笔下的女性人物都是活泼生动的,有得知丈夫婚前私定妾室,假意为难、耍性子的正妻谢氏,也有勇敢追求美好爱情,对婚姻有明确要求的妾室黄姬……[5]P30王筠通过梦所提出的议题是女性理想的家庭结构和生活环境。
《邯郸记》第二十九出中【二郎神】套曲一起,“难酬想,眼跟前不尽的繁华相”[6]P648,曲情变化,前后分明,吕仙点醒黄粱梦,卢生醒悟,愿随吕仙而去,然而却一直到下一出卢生被眾仙点醒,他才彻底了断尘念、有所忏悔。他的出世之心是真挚的,也是汤显祖辞官归隐、不问世事的精神折射。《繁华梦》中王梦麟被麻姑点醒,仍痴念未消,更多的是无法完成现实愿望的弃世之心,继续在现实生活中见性明心,“超凡”只是美好愿景,也是不得已收束全剧的常规之法。
汤显祖的“黄粱一梦”更多的是对封建黑暗官场的控诉,讽刺封建礼法后超脱精神的外化。而《繁华梦》的“女性之梦”则更生动地聚焦于在女性个人世界的焦虑和压抑。卢生的梦醒是汤显祖对官场幻想的破灭,梦醒时刻面对现实的痛楚,只有通过求证仙道来应对精神困境。而面对繁华梦醒后的失落,王梦麟领悟到即使身为男子,享受功名利禄也无济于事,一切都如同浮云,虚无缥缈。
三、余论
由是观之,梦境是明清女性作家寄情抒怀的一种载体,角色难以实现的愿望在梦境中得以实现。《鸳鸯梦》中,主人公蕙百芳的悲叹、伤情,正是叶小纨悼念姐妹情深的情感外化,现实中的求而不得,才有了剧中于亦真亦幻的仙道世界寻找姊妹踪影以求得心理慰藉的结尾。《梨花梦》中的杜兰仙对梨花仙子的相思来源于现实生活中對少时女伴的怀念,传达了封建才女对心灵知己的渴慕之情。而《繁华梦》,王筠创作的目的不仅在于发泄她对男性掌握家族权力的渴望,更在于通过对现实人物的重构,创造出其理想化的女性世界,在王梦麟梦醒之后,以其悟道作为结尾,也是因为在王筠眼中,也许只有悟道才能摆脱如梦幻泡影般的人生,王梦麟的出梦情感也是三部剧作中最为跌宕起伏的。
汤显祖在《复甘义麓》中曾言:“因情成梦,因梦成戏。”[7]P563出梦之后的结局,作者往往安排主人公参悟人生,仙化入道,这样超现实的处理手法也衬托出作者本身对自我出路的迷茫和寻求慰藉的逃避心理。通过梦境的营造,有助于更全面细致地了解明清拟男剧作者和笔下人物之间的情感联系,让我们得以在那个以男性为话语中心的时代,领略女性对自我生存境遇的体验与感悟。
参考文献
[1]徐钊:《明清女性“拟男”剧的酒梦书写》,《东方艺术》,2022年第5期
[2]华玮:《明清妇女戏曲集》,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3年
[3]陈雪琪:《叶小纨及其杂剧〈鸳鸯梦〉的艺术特色和女性意识研究》,吉林艺术学院,2019年
[4]毛劼:《从〈邯郸记〉与〈繁华梦〉看两性之异梦〉,《艺术科技》,2014年第4期
[5]崔淑晓:《从〈繁华梦〉到〈全福记〉——浅析王筠的情感理想》,《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6](明)汤显祖著,李晓评注:《紫钗记评注》,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
[7](明)汤显祖:《汤显祖集》,原中华书局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 姜艺艺 王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