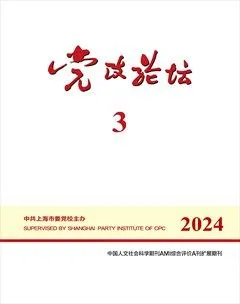破解“李约瑟之问”:新型举国体制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唐青州?孙文文
[摘 要]新型举国体制是新时代中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创新密码”,是中国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一大法宝。新型举国体制不仅是回应李约瑟难题,破解中国近代科学“断代”之谜的关键,也是破解科技创新政府与市场难题的关键,更是新时代破解科技创新急与缓的问题的关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发展阶段,持续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是在国际竞争中掌握创新发展主动权、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要求,充分发挥这一体制优势,才能从容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效保障国家长治久安。
[关键词]新型举国体制;李约瑟之问;科技自立自强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科技力量日渐成为大国角逐的重要筹码,在中美贸易争端的刺激下,2017年以来,中国科技遭到美国封锁和打压,随之而来还有科技创新与国际竞争力的日益密切,科技自立自强日渐成为事关国家安全的关键因素。新形势下,如何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驱动作用,抢占未来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先机,应对西方的科技封锁和打压,实施核心技术攻关,解决“卡脖子”问题,完成从科技大国向世界科技强国的转变,成为中国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举国体制的重要意义也再次凸显出来。
一、李約瑟之问背后的制度体制因素
作为拥有五千多年发展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在技术层面取得的成就曾举世称颂,而在欧洲文艺复兴之际,中国技术进步的步伐逐渐放缓,随着早期工业革命的发展,西方世界科技进步一日千里,逐渐将中国甩在身后。西方学者琼斯曾说:“中国在14世纪离工业化只有一根头发丝的距离。” ①相较于古代在技术上的独领风骚,中国近代科技的落后和缺失就显得尤为吊诡,甚至成为世界技术发展史上不可思议的谜题。因此,当20世纪30年代,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专家李约瑟先生提出著名的“李约瑟之问”,随即引发了中外学者的广泛探讨。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讲道:“中国人……在3-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 ②简言之,就是近代中国缘何无缘科学和工业革命的问题,中国近代科技为什么落后的问题。而今天,中国的科技水平已然稳居发展中国家前列,部分重点和关键领域甚至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进入并跑、领跑,科技实力从量的积累逐步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再一次与近代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整个世界来讲,现代中国科技的崛起又是一个匪夷所思的谜题,甚至可以说是新时代科技发展之问。
16世纪以来中国科技的由盛转衰与21世纪的重新崛起,弄清其中的偶然与必然,是解答李约瑟难题的关键所在。李约瑟之问的解答,必须要回应产生不了西方科学的近代中国,何以在现代取得一系列科技创新和突破这一问题。古往今来,学者们从制度、文化、经济等不同的层面去寻找李约瑟之问的答案,相继提出文化决定论、制度决定论与经济决定论等不同的回答。毋庸置疑,近代中国科技的衰落有其深刻的文化、经济、制度根源,既离不开根深蒂固的儒学本位的文化原因,也离不开在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体制”因素,多重因素的交织造成古代中国逐渐形成一种满足于既有技术成果、只讲技术实用而不究深层根源的定式,最终造成中国没能发展出一套体用兼备的系统科学体系。对比中国在近代的衰落与现代的崛起,不难发现,制度原因是影响中国现代科技发展的核心要素。如果说近代中国在科技层面的缺失有深刻的制度根源,那么新中国70年来的科技进步,举国体制之下的“中国式”创新则对李约瑟难题给出了回应。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经济、技术基础薄弱,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几乎从零起步,在“举国体制”引领下,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凸显出来,“五年计划”等中长期规划的实施下,由政府主导和布局的科技体系初步建立,数十年间,两弹一星、石油会战、人工合成胰岛素等一系列重大突破和成就相继实现,“一穷二白”的状况迅速改变,新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才得以站稳脚跟。改革开放后,中国科技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也是得益于政府对举国体制的不断完善。新形势下,以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为最高目标,以现代化重大创新工程为国家战略制高点,以提升我国综合竞争力、保障实现国家安全为导向的新型举国体制应运而生。在这一时期,中国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北斗导航等战略领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人工智能、5G、量子通信等新兴技术领域占据发展先机,无不彰显出中国制度的独特优势。
从近代中国科技落寞的遗憾,到现代中国科技成就的荣耀,再到明日中国世界科技强国的梦想,中国创新强国梦想的“制胜法宝”就是新型举国体制。新中国70多年奋斗史,也是70多年科技攻关史、创新史,新时代中国以新型举国体制下的科技成就,解答了世界疑惑,以科技创新回应了李约瑟之问。对李约瑟之问的追问和反思,不仅对于理性认识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兴盛与衰落大有裨益,同时对于理解当代中国所取得科技成就,继续推进和完善举国创新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二、新型举国体制破解科技创新政府与市场难题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也是推进科技创新的关键和难点。从推动技术发展的动力来看,市场与政府是两大基本来源,创新型国家的创建离不开政府和市场的双轮驱动。单纯的科技因素无法实现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不仅需要依靠市场经济和竞争机制的推动,也需要政府在科技发展和应用等方面的政策体系的支持、组织和开发。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企业的边界在哪里?如何实现政府与市场二者之间的有机统一和良性互动?如何把“联合研发”和“充分竞争”这对看起来矛盾的行为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些问题都是贯穿在科技创新全过程中的难题,也是新时代新形势下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难题。
在科技创新的发展和应用上,通过国家力量推动产业与技术创新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成为当前全面深化体制改革、推进科技创新的当务之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发挥政府作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只有明确政府发挥作用的边界,在科技创新活动中做到不“缺位”、不“越位”,才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才能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作为探索和解决科技创新政府与市场难题的一大举措,新型举国体制破解了科技创新过程中政府与市场难题。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初期资源配置由政府大包大揽的传统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制的一大特色,是建立在市场起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基础上,国家利用科技产业政策和其他手段引导市场,运用市场方式、经济手段解决国家科技创新工程立项、决策、预算投入、利益分配等问题。新型举国体制最显著优势,就在于能够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新型举国体制避免了两个极端,一是传统的由“政府强力主导、忽视市场作用”的极端,一是“完全依赖市场、不要政府介入”的极端。政府与市场绝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因此,在资源配置上,单纯的政府或市场方式都有着致命的缺陷,而新型举国体制则打破了这一矛盾和冲突,实现了二者的有机互动和补充。
与传统举国体制相比,新型举国体制最大的突破就在于,实现了由行政配置资源为主向市场配置资源为主的转变,在探索创新实践中政府与市场的准确定位中,解决了传统举国体制下的投入高、效率低、效益低的弊端。因此,在新型举国体制之下,在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创新活动中,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与政府统筹协调并不矛盾,而是在相辅相成的互动中,既能够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决定作用,又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二者相互配合,共同铸就协同创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强大合力,为重大科研突破和科技成就的取得保驾护航。同时,在继承传统举国体制的合理要素的基础上,新型举国体制的内涵和形态因时而变,契合了创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也在不斷地转变组织方式和运行机制,不同于以往直接运用行政手段调配资源、推动科技进步,而是尊重和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运用市场机制和相应激励手段,适应当前科技快速发展的新需要。
总之,新型举国体制不仅是对传统举国体制的创新,也是解决科技创新政府与市场难题的有效途径和成功尝试;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也是中国科技创新的一大法宝。只有坚持新型举国体制,才能够解决科技创新中的政府和市场难题,才能够实现科技与经济发展的紧密结合与无缝对接,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科技发展规律、政府与市场的各自优势得以进一步发挥的现代科技体制,使蓬勃的创新能量和创新能力充分释放,使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
三、新型举国体制破解科技创新急与缓的问题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被列为二〇三五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再次将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性提到了历史新高度。站在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已经吹响,然而面对一系列的重大科技成就,我们仍要思考,当前我国科技创新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即我国在诸多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受制于人的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和改变,核心技术能力短板问题成为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
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突破与创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更为迫切。“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因此,毋庸置疑,解决核心技术领域“卡脖子”问题,就成为中国中长期规划的“重中之重”。近年来,中兴事件、华为事件的相继出现,另外,我国在集成电路、操作系统、发动机、精密仪器等领域的短板也日渐显现,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日益凸显,成为掣肘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成为国家和科技工作者们的心头之痛。
事实上,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难题也成为危及国家安全的重大隐患。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西方发达国家在科技层面的戒备心理急剧抬升,国际科技合作的外部环境亦逐渐紧张多变。加之,在科技外交逐渐成为各国提升整体竞争力、主推经济增长的手段,科技创新领域的竞争态势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科技输出也日渐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方式,这都对科技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谁掌握了核心技术,谁就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也只有掌握了核心技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受制于人的情形,保障国家安全。
从科技创新的角度讲,“卡脖子”的核心问题不单单是某个科学难题、某个技术瓶颈、某项创新产品,而是中国科技创新体系和产业发展的整体运行机制和能力中的系统性薄弱环节。因此,“卡脖子”问题的解决需要依托创新机制的合力。这就需要新型举国体制的统筹和协调作用,需要政府发挥强化战略导向和目标引导作用,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集合精锐力量,作出战略性安排。换言之,只有继续坚持和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才能立足全球视野谋划创新,才能更好地统筹科技创新急与缓的问题,攻关核心技术“卡脖子”之急,兼顾科技创新整体协调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和保障,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实现从领跑到并跑,从并跑到开拓的转变。
四、结语
2023年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应对国际科技竞争、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我们加强基础研究,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技事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之路,印证了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经济发展的跨越,无法替代创新能力的积累,中国科技创新和攻关之路任重而道远。科技创新的“举国体制”,要结合新形势,不断探索适合我国转型期科技创新的制度安排,寻求更高效的科技创新组织方式。只有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定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才能够从容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突破技术封锁,有效保障国家科技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国家安全。
注释:
①参见Jones E. L. The European Miracle: Environments 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60.
②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唐青州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讲师;孙文文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王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