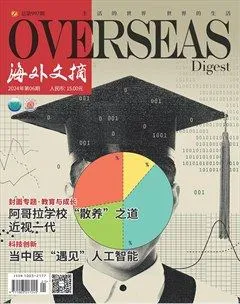近视一代
一只不理解的熊

| 全球趋势 |
从事验光工作十年后,玛丽娜·苏注意到,来到她诊所的孩子们有些不同寻常。越来越多的孩子需要戴眼镜,而且年龄越来越小。其中不少孩子的父母视力都很好,他们对孩子视力下降感到困惑。老实说,玛丽娜·苏也不知道原因。
她所受的教育告诉她,近视是一种遗传病。几十年来,美国的教科书一直是这样写的:父母有一方近视,孩子需要戴眼镜的几率会增加一倍;如果父母双方都近视,孩子戴眼镜的几率就会增至四倍。多年来,她诊断过的很多近视孩子的父母确实都是近视眼。她告诉我,这些父母往往会叹气:哦,不,他们可别也近视啊!但是,情况正在恶化。这一代孩子的视力突然变得比他们父母更差。玛丽娜·苏看到了越来越多没有遗传因素却近视的孩子,她曾问自己:“如果近视只是遗传的,那为什么这些孩子也会近视?”
玛丽娜·苏注意到的这个现象其实世界各地都有。在东亚和东南亚,这种转变最为明显:短短半个多世纪里,该地区青少年和年轻人的近视比例从大约25%跃升至80%以上。
美国上一次进行全国范围近视调查是在本世纪初,12至54岁群体中有42%近视,而这一数据在上世纪70年代只有25%。虽然没有近几年的大规模调查数据,但我询问过美国各地的眼科医生是否看到了更多近视的孩子,得到的答案是:“当然”“的确”“毫无疑问”。
在欧洲也是如此。与父辈和祖辈相比,现在的年轻人更有可能需要佩戴眼镜。非洲和南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近视率最低。据估计,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2050年,全世界将有一半人口近视。
这一趋势所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近视儿童数量激增。近视患者在中年时更容易出现青光眼和视网膜脱落等严重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可能导致永久性失明。一开始风险很小,但度数越高,风险就呈指数级增加。近视的年龄越小,以后的情况就越不容乐观。2019年,美国眼科学会召集了一个特别工作组,将近视视为一个紧迫的全球卫生问题。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眼科学教授、美国眼科学会政府事务医学主任迈克尔·雷普卡说:“我们正在试图阻止几十年后的失明大流行。”
| 復杂成因 |
我们视力显著下降的原因似乎显而易见:环顾四周,你会看到无数孩子沉迷于手机、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众所周知,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会消耗远视储备。400年前,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内斯·开普勒认为自己视力不佳的部分原因是长时间学习。过去,英国医生发现牛津大学学生的近视率比部队新兵更高,学风严谨的城镇学校的学生近视率比农村学校更高。19世纪晚期的一本眼科手册甚至建议避免一切用眼工作来治疗近视——“如果可能的话,去海上航行”。
20世纪初,专家们一致认为,近视是由“近距离工作”引起的,包括阅读和写作以及如今的看电视和刷手机。旧金山湾区的验光师利昂德拉·容说:“很久以前,人类是狩猎者和采集者。”我们依靠敏锐的远视力追踪猎物、寻找成熟的水果。但现代生活基本是近距离的室内活动。“我们通过外卖软件觅食。”
这个解释符合直觉,但很难证实。“每有一项研究证明近距离用眼对近视的影响,就有另一项研究推翻这个结论。”加州圣布鲁诺市的验光师托马斯·阿勒说。看书和看屏幕的时长似乎无法完全解释近视的发生和加重。
一些理论急于填补这片真空:或许研究中的数据是错的——受试者没有准确记录自己近距离用眼的时长;或许近距离用眼期间是否短暂休息比用眼总时长更重要;或许毁掉视力的不是近距离工作本身,而是它剥夺了孩子们户外活动的时间。主张户外活动重要性的科学家又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促进眼睛发育的是明亮的阳光,另一派认为是广阔的空间。
现代生活中有些东西正在破坏我们的远视力,但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会让你陷入各种科学解释的迷宫,我就遇到了这种情况。我曾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视光学教授克里斯汀·威尔德索特询问各类近视理论在生物学上的合理性。在两个小时的谈话中,她多次停下来指出接下来的内容很有争议。但她也表示,这些理论本质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近距离工作很久的人本来也不会花太多时间在户外。无论哪种理论是正确的,关于保护孩子视力的实际结论都是:少看屏幕,多参加户外活动。

现在,科学家们已经不再相信近视纯粹由遗传决定。这一观点在上世纪60年代大行其道,并在学术界流行了几十年,因为当时的研究表明,同卵双胞胎在近视方面比异卵双胞胎更相似——前者具有相同的遗传背景,后者则不然。基因的确在近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棘手的问题在于,同卵双胞胎不仅拥有相同的基因,还受到许多相同的环境刺激。
眼镜、隐形眼镜和激光手术都能帮助近视者看得更清楚,但这些方法无法从根本上纠正近视的解剖学问题。健康的眼睛像一个球体,而近视的眼睛像一颗橄榄。要减缓近视加剧,就必须阻止眼睛变长。我们已经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那就是“近视控制”,或者叫“近视管理”。
| 控制措施 |
过去20年里,亚洲的眼科医生发现特殊镜片和眼药水可以减缓儿童近视加剧。近视研究专家玛丽亚·刘告诉我,她第一次对近视产生兴趣是在十几岁的时候,当时她在天才儿童学校看着同学们一个个戴上了眼镜。学校竞争激烈,她记得自己从早上六点半到晚上十点几乎都在室内学习。大学毕业时,和其他几乎所有同学一样,她也戴上了眼镜。
几年后,她开始作为眼科住院医师实习,遇到了许多佩戴角膜塑形镜(OK镜)的年轻患者。这种夜间佩戴的隐形眼镜会改变角膜的形状,使光线在白天更准确地聚焦于视网膜,从而实现暂时性的视力改善。玛丽亚·刘注意到,戴角膜塑形镜的人似乎比戴眼镜的人视力更好。长期使用角膜塑形镜能否在某种程度上防止眼球老化,进而阻止近视加剧?事实证明,亚洲的其他科学家和医生也注意到了同样的趋势。2004年,一项有关角膜塑形镜的随机对照研究证实了玛丽亚·刘的预感。
那时,她在伯克利攻读视觉科学博士课程,研究近视问题。她的同学们都在研究基因治疗和视网膜移植等听起来很高端的课题,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研究“这么无聊的东西”。最后,她来到威尔德索特教授的实验室工作,研究小鸡的近视问题。
大多数人类婴儿天生远视。我们的眼轴一开始有些短,在童年时长到合适的长度,然后停止生长。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这一过程已非常精确。眼睛进化后期望看到的是自然光线和远距离视觉,如果环境信号错误——不管是由于近距离工作过多、户外活动时间不足、两者兼有还是其他因素——眼轴就会不断变长。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玛丽亚·刘说:“你无法让变长的眼轴缩短。”不过,你可以通过抵消错误的信号来阻止眼轴变长,这就是近视控制的目的。
获得博士学位后,玛丽亚·刘成为了伯克利大学的一名助理教授,她开始设想建立美国第一家近视控制诊所,在研究和实践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学校行政官员对此持怀疑态度。眼科中心的临床主任认为,此类诊所不会给视光学专业的学生带来好处,也不会吸引到足够多的患者,获得经济回报。但在2013年,玛丽亚·刘还是凭一己之力创办了伯克利近视控制诊所。她在周日借用检查室接诊,不收取额外报酬,也没有放弃任何教学或临床任务。几个月内,她的日程表就排满了。现在,这家诊所每周开诊四天,有1000名患者前来就诊——其中一些人驱车数小时穿过湾区的车流来到这里。
| 亚裔焦虑 |
2022年春天的一个周六早上,我到达诊所时,校园里其他地方还很安静,但诊所内已经挤满了在这里接受培训的视光学专业学生和住院医师。身材娇小、留着整齐波浪卷发的玛丽亚·刘在诊所里穿梭,效率惊人。前一刻,她还在检查患者眼睛;下一刻,她已经在安抚一位家长;后一刻,她又告诉工作人员打印机出了故障。
诊所提供三种治疗方法:角膜塑形镜、多焦软镜和阿托品滴眼液。前两种疗法可以改变眼球的光学特性,产生让眼轴停止变长的信号;而阿托品是一种药物,低剂量的使用似乎能通过化学方式改变眼球的生长通道。这些疗法可将近视发展速度平均减缓50%左右。2021年,美国验光协会的循证委员会向其成员发布了一份关于如何使用近视控制方法的报告。不过直到最近,这些疗法仍未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近视控制。在美国,这些疗法只能算作“超适应症用药”,换言之,医生可以在特定情况下自行决定是否采用。因此,使用这些疗法的前提是找到合适的医生。
玛丽亚·刘的诊所在亚裔人口众多的湾区取得了初步成功,这并非巧合。我在美国多个城市采访过的眼科医生都说,前来要求控制孩子近视的家长通常是亚裔。我在诊所遇到的家长中,亚裔确实占了很大比例。很多人是从其他移民或亚洲朋友那里听说近视控制的。
玛丽亚·刘还有一部手机,用于管理三个聊天群,群里是北美地区孩子接受近视控制的家长。问题不分昼夜地涌来。“我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看这个聊天群:谁丢了镜片?谁的眼睛红了?谁还有其他问题?”她说,“然后临睡前再看一遍。”她和一位患者家长一起建立了第一个群。在达到群成员人数上限后,他们创建了第二个和第三个群。现在,三个群里共有1500名家长。
| 治疗前景 |
湾区的收入中位数较高,这也是该地成为近视控制沃土的另一个原因:治疗费用昂贵。我在诊所遇到的许多家长都是工程师或医生。在伯克利,一副角膜塑形镜的价格超过450美元,初次验配费用1600美元,这还不包括每年多次复诊的费用。软性隐形眼镜一年的费用从几百美元到1000多美元不等。阿托品滴眼液一年的用量也要数百美元。孩子的近视控制通常要到十几岁或二十出头才结束。这些治疗不在医保范围内。
跨国眼保健公司如今将近视控制视为一个炙手可热的潜在市场。它们正在争取获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新型镜片和阿托品改进配方的批准,后者可以获得专利,而不是作为更便宜的非专利药出售。商业动机显而易见:如果到2050年全球一半人口近视,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客户群。“我们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商机。”“视镜”光学公司前首席医疗官乔·拉蓬说。这家加州小公司的近视控制技术已被眼科保健巨头库博光学和依视路联合收购。
2019年11月,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美国第一种专门用于减缓近视发展的治疗方法——库博光学生产的一种名为“美视”的软性亲水接触镜。另外,还有更多的疗法正在美国进行试验,其中包括几种改变眼球光学特性的眼镜。有的已经在欧洲和加拿大上市。伊利诺伊州迪尔菲尔德的验光师巴里·艾登说,这些眼镜一旦在美国获批,“将打开近视治疗的闸门”。他解釋道,越早开始减缓儿童近视的发展,效果就越好。
玛丽亚·刘告诉我,她希望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在未来能促使视力保险至少部分覆盖近视控制,让更多家长负担得起这种治疗。与此同时,库博光学加大了“美视”的营销力度。在我居住的布鲁克林公园坡社区,一家验光店最近挂出了“美视”的大幅广告,上面有两个面带微笑的孩子。旧金山市中心的一位验光师告诉我,看过“美视”广告的家长现在都会到她的诊所点名咨询。对近视控制来说,口碑时代正在结束,大众广告时代已然开启。
在验光配镜行业,近视控制常常与正畸相提并论——希望为孩子提供最好条件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父母不惜为此花费数千美元。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比较也很贴切。正畸也是一种针对现代病的现代解决方案。人类学家惊奇地发现,穴居人的牙齿整齐得令人难以置信。当我们的祖先从咀嚼生肉和蔬菜转为食用煮熟、加工过的谷物后,考古记录中才出现了歪牙。现在,我们的颌骨因用得太少而变弱,牙齿也更加拥挤和歪斜。而正畸是我们对不适应现代生活的身体进行改造的方式。
我们可能还不清楚整天盯着屏幕和长时间待在室内对我们有什么影响,也不知道哪个因素对我们的伤害更大,但我们明确知道的是,近视显然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与生物构造相悖的结果。我采访过的验光师都说,他们努力推动人们养成更好的用眼习惯,比如限制看屏幕的时间和进行户外活动,但也只能到此为止了。如今,让青少年远离手机可能与让婴儿吃生肉一样不切实际。
正因如此,我们陷入了当下的困境:每天往眼睛里放置化学物质和塑料片,希望欺骗眼球回到自然状态。
编辑:要媛